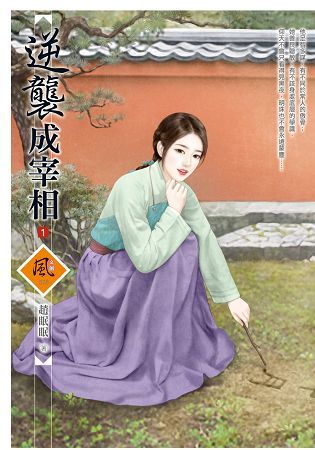第一章 初遇
顏粼睿坐在庭院迴廊前的石階上,看著湛藍的天空發呆。
此時正是金秋時節,陽光明媚,天高雲淡,一隊大雁在空中排成人字形向南飛去,漸行漸遠。院子裡種滿了菊花和木芙蓉,在花圃裡競相開放,一片奼紫嫣紅。迴廊邊上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樹,清風拂過,星星點點的金色桂花落在她的身上。
她閉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氣,感覺肺腑間都充滿了桂花的甜香……
「大玲子,妳又躲懶!庭院裡的石板路上這麼多落葉,妳掃了嗎?」
一聲暴喝將摟著掃帚、沈浸在甜蜜香氛中的顏粼睿拉回現實。
對,沒錯,大玲子就是顏粼睿落到這個時空後的名字。
自從懂事以來,顏粼睿一直抱怨爺爺給自己取的名字太中性,浪費了「顏」這個別緻的姓氏,可當她四個月前落到這個叫做大周朝的異世,成了御史府庶出五小姐柳惜棠院子裡的一個掃地丫鬟趙大玲後,曾經的不滿和不甘全都化為烏有。
趙大玲啊,多麼接地氣!抖落下來的土都夠種一筐蔥了,雖跟現代顏粼睿最喜歡的遊戲人物趙靈兒僅有一字之差,然而就是這點差別,成了土得掉渣的女漢子和飄逸靈動的萌妹子之間的分水嶺,將趙大玲和趙靈兒分到涇渭分明的兩個區域。
顏粼睿曾經反抗過,即便有了趙大玲這個不可更改的名字,眾人能不能在稱呼她的時候叫阿玲或是玲兒,聽起來也較清新一些。可惜,京城做為一個道地的北方城市,習慣在孩子,尤其是窮人家的孩子名字後面加一個「子」,比如說趙大玲的弟弟趙大柱就是大柱子,趙大玲就是大玲子。至於「阿」什麼,那是南方人的習慣;而在名字後面加個「兒」則是富貴人家女兒的嬌稱,顯然趙大玲身為廚娘的女兒,又是一個掃地丫鬟,並無此殊榮。
其實之前這個身體在還是五小姐院子裡的二等丫鬟的時候,是有一個說得過去的名字叫「雲湘」。五小姐院子裡的丫鬟本來都叫什麼香的,比如正在呵斥大玲子的蕊香、五小姐跟前的大丫鬟蓮香,後來五小姐覺得「香」字太俗氣,不襯她大家閨秀的氣質,又不敢大肆更改丫鬟的名字,怕夫人說她矯情,便將「香」換為「湘」,讀音一樣,卻不會引人注意而招來非議,彷彿還上升了好幾個層級。
雲湘在一次陪五小姐遊園的時候,正巧碰上嫡出的二小姐柳惜慈,這位惜慈小姐可一點兒也不慈善,兩人因為誰擋了誰的路、誰踩了誰裙子的小事發生了口角,二小姐仗著嫡姊的身分打了五小姐這個庶妹一巴掌,偏偏雲湘腦子不好使,衝過去替自己的主子出頭。
其實雲湘作為一個庶女的丫鬟也不可能太出格,不過是雙手叉腰、衝著二小姐嚷嚷了句「二小姐,妳不能欺辱我們小姐」,據說還推了二小姐一下,讓心高氣傲、不可一世的二小姐摔了個屁股墩兒,跌到了路旁花圃的泥地裡。
是不是雲湘推的不好說,顏粼睿個人覺得,雲湘應該沒這個膽量,混亂中是二小姐自己摔倒的也說不準,但是二小姐這個屁股墩兒是結結實實地記在雲湘頭上了。御史夫人汪氏心疼自己的親閨女,就讓管事嬤嬤剝了雲湘的外衣,當著眾人的面抽了二十鞭子。
雲湘只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女,在眾人面前被剝衣鞭打,自覺受了奇恥大辱,一時想不開跳了蓮花池,被救起時已經沒氣了。就在她那個做廚娘的娘哭得捶胸頓足的時候,顏粼睿穿到了雲湘的身上,睜開了眼睛。
夫人也怕鬧出人命,影響御史府的清譽,便留下了雲湘,沒有攆出府去。顏粼睿因為之前雲湘挨了鞭子又跳了水,背上的傷口發炎,昏昏沈沈的一直病著,在屋裡躺了三個多月才養好了身上的傷,又回到了五小姐的枕月閣。只是二等丫鬟降為了掃地的下等婢女,連雲湘這個名字也被剝奪了。
而原因很可笑,御史府二小姐柳惜慈素以京城才女自居,沒事吟個詩、作個賦傷春悲秋的很是風雅,時不時還會發起賞花會或詩社,邀請京城中的閨秀來開個「文藝沙龍」。她住的院子叫倚雲居,便給自己起了個「閒雲散客」的號,每每作詩便以「閒雲散客」署名。雖是閨閣中的詩詞,不宜外洩,但不知是她無意還是刻意,她引以為傲的那幾首詩詞流傳出去,因用詞花俏纏綿,便有那紈袴公子哥抄錄在扇面上吟誦,一來二去,被好事者稱為「閒雲公子」,倒也有了幾分名氣。
二小姐嘴上雖然說著「討厭死了,我那幾首歪詩怎地漏了出去,沒的讓人笑話!」其實心裡是頗為自得的,再加上家中庶妹的刻意奉承和其他巴結御史府的官吏之女的討好,更是讓二小姐覺得自己才高八斗、傲視文壇,只可惜生為女兒身,不然建功立業或金榜題名都是信手拈來的小事。
而二小姐自稱為閒雲散客,自然看雲湘這個名字不順眼。
「一個下等的掃地丫頭也配叫什麼雲湘?她本來的名字不是挺適合她的嗎?」
於是雲湘又恢復成「大玲子」,而自始至終,五小姐沒有為大玲子講過一句話。
顏粼睿對這件事很不以為然,之前的趙大玲可是為了替五小姐出頭才落個被打自殺的下場,可她也不怪五小姐,一來她本也不是大玲子,不過是異世的一縷幽魂,一場意外將她送到了這裡;二來,她也看得出五小姐在府裡沒什麼地位,她的親娘李氏不過是御史夫人當年的貼身婢女,為人忠心老實,夫人為了能更加掌控御史大人,才將她放在屋裡的。李氏因為不夠美貌,並不受寵,四年後生了五小姐後才抬為姨娘。現在夫人吃飯的時候,李姨娘還要在一旁站著伺候,這樣的出身,讓五小姐如何敢違背嫡出的二小姐?
唉,不提了,說多了都是淚。如今顏粼睿已經認了趙大玲這個名字和這個身分。從最初的迷惘困頓、悲傷失落到如今的不得不接受穿越這個現實,她用了整整四個月的時間。不管她有多不甘,卻也不得不承認,她回不去現代了,在現代的一切彷彿是一個遙遠的夢,如果她想活下去,就必須先老老實實地做趙大玲。
從今以後,在這個異世裡,沒有顏粼睿,只有趙大玲。
已經認命的趙大玲一邊想著,一邊站起身走到庭院裡的青石路上,機械化地揮動著手裡的掃帚,東嘩啦一下,西嘩啦一下,將金黃色的落葉掃到兩邊的花圃裡。
「大玲子,跟妳說過多少次了,樹葉要收起來扔到院外去,不要為了省事就掃進花圃,妳豬腦子?記吃不記打!」
還是那個聲音在訓斥她。趙大玲循著聲音看去,穿著茜紅色比甲的蕊湘杏眼圓睜,一手叉著腰,一手伸出食指遙指著她的腦門。那架勢,隔空都恨不得在她腦門上戳一個窟窿出來。
趙大玲停住,無可奈何道:「蕊湘姐姐,不是妳昨天說落葉要掃進花圃裡當作肥料嗎?」
蕊湘一頓,須臾更加氣急敗壞。「昨日花圃裡沒有落葉,自然要掃進去一些作為肥料,今日花圃裡的落葉已經夠多了,妳再把落葉堆進去,都把小姐最鍾愛的綠水秋波擋住了。妳做事不帶腦子嗎?!」
說著她走過來,翹起的蘭花指終於戳到趙大玲的腦門上。趙大玲偏頭躲過,看了看花圃裡淺淺的一層落葉和傲然開放的那株淡綠色的菊花,無聲地嘆了口氣。自己新來乍到,一切未明,只能斂眉低眼道:「是,蕊湘姐姐,我這就把落葉掃出去。」
蕊湘哼了一聲。「掃完地後再給園子裡的花澆點水,妳看看這些花都被曬蔫了!下午小姐還要到院子裡賞菊呢,別壞了小姐的興致!」
趙大玲低頭稱是,蕊湘這才滿意地扭著水蛇腰走開,一打簾子進了屋。
在趙大玲還是雲湘的時候,與蕊湘都是屋裡的二等丫鬟,平日裡關係不算好,女孩子之間少不了明爭暗鬥、斤斤計較的事。於是趙大玲成為下等的掃地丫頭後,蕊湘自覺出了一口惡氣,時時頤指氣使地指揮趙大玲做這做那,這也說明了大玲子之前肯定不是個聰明又圓滑的孩子,情商堪憂,當面頂撞二小姐,與周圍人關係也不算好,以至於她落難後,沒有人願意幫她說句話。
掃完地,收了落葉堆到院外,趙大玲將掃帚和簸箕放回到院子角落裡的雜物房。太陽已到了頭頂,雖是秋日,但午時的太陽依舊灼熱,烈日下不宜給花澆水,只能等下午了。趙大玲惦記著外院廚房那邊,她的娘是外院廚房的廚娘,這會兒應該正忙得腳不沾地。
趙大玲來到正房門口,本著在哪座山頭唱哪首山歌的處世哲學,隔著門簾問:「五小姐還有什麼吩咐嗎?」
簾子一挑,自屋中走出一個身穿湖藍色比甲的丫鬟,油光水滑的鬢髮上只戴了一朵草花,容長臉蛋,白白淨淨,正是五小姐跟前的大丫鬟蓮湘。
雖然趙大玲傷好後,到枕月閣當差不過幾天,但也知道五小姐原本有兩個一等丫鬟、兩個二等丫鬟。一等丫鬟是蓮湘和蘭湘,兩個月前蘭湘滿十八歲嫁人了;二等丫鬟就是蕊湘和趙大玲。
枕月閣裡還有兩個老媽子,一個是王嬤嬤,是小姐的奶娘,仗著奶過小姐在院子裡好吃好喝地養著,什麼都不幹。另一個是邢嬤嬤,五十多歲,一身病痛,基本上也是在屋裡養著。
五小姐院子裡的人本就差著編制,不能跟嫡出二小姐那一院子僕役比,同是庶出,三小姐和四小姐的院子裡也比她伺候的人多,如今又少了一個一等丫鬟,趙大玲也被降了級,就越發顯得人少。不過御史老爺一貫標榜自己是朝中的清流砥柱,一身灑遝,兩袖清風,夫人在老爺的感召下也奉行勤儉持家,這空缺的丫鬟就一直沒有補上。
其實一院子的人裡頭,趙大玲最喜歡的還是蓮湘,雖然模樣不如蕊湘俏麗潑辣,但為人穩重,做事也算公正,有時蕊湘支使趙大玲幹這幹那的,她也會站出來替趙大玲擋幾次。
蓮湘笑道:「也沒什麼事了,妳回去幫妳娘料理午飯吧。」
趙大玲依言退下,出了枕月閣,穿過內府的花園,再出了東南角的角門回到了外院的廚房。趙大玲的娘就是外院廚房的廚娘,專做下人僕役的飯,人稱趙嫂或是友貴家的,因為趙大玲早逝的爹叫趙友貴。
柳府有近百名僕從,內院的一等、二等丫鬟大多吃主子剩下的就足夠了,所以說一等、二等的丫鬟也相當於半個主子,比一般小門小戶的小姐都強。剩下的還有大約六、七十個末等丫頭和粗使僕役可就沒這個待遇,只能吃友貴家的做的大鍋飯。
趙大玲回到外院廚房的時候,她娘穿著粗布衣裳、圍著一個看不出顏色的圍裙正在灶上揮汗如雨。廚房裡有兩個大灶和一個小灶,小灶上燒著熱水,大灶一邊架著籠屜蒸饅頭,一邊是一個大鐵鍋,友貴家的剛炒好的白菜已經出鍋了。
友貴家的一邊將熬白菜盛到一個一個盤子裡,一邊粗聲道:「死丫頭片子,又跑哪兒瘋去了,飯都得了才回來!還不濟大萍子頂用!」
本來在趙大玲還是枕月閣的二等丫鬟時,外廚房這裡有一個十二歲的小丫頭大萍子做幫手的,可自趙大玲被降為末等丫鬟,不用再住在枕月閣貼身伺候五小姐後,外廚房的小丫頭也撤了。橫豎趙大玲要回來吃飯睡覺,正好給娘當幫手。
趙大玲趕緊答道:「並沒有貪玩,是枕月閣裡活計多,耽擱了時間。」
友貴家的憤憤道:「那一院子懶貨,就知道支使妳一個。也是妳不爭氣,好好的二等丫頭混成現在這樣,讓妳娘我在人前都抬不起頭來,採買的那幾個老貨天天拿妳的事當樂子說,」她在百忙中回身用油膩的手指戳戳趙大玲的腦門。「妳說,老娘一世聰明,怎麼就生了妳這麼個沒心沒肺的討債鬼!」
趙大玲抿嘴不言。友貴家的大概也覺得說重了,煩躁地揮揮手。「別跟死人一樣站著不動,去柴房拿些柴來,還要再熬一鍋小米粥。」
趙大玲應了,打開屋門來到外面,屋外幾步遠的地方是個小小的柴房,雜亂地堆著木柴和幾袋茄子、紅薯。木柴大多是大塊的圓木,還沒劈成可以放進灶膛的細柴。她從柴房裡撿了幾根劈好的木柴,又快步回到廚房。
友貴家的已經將粥熬上了,瞥了眼問道:「柴還夠用嗎?」
「不多了。」趙大玲一邊將柴火填到灶膛裡,一邊答道:「等我晚上回來再劈一些柴吧。」
友貴家的從鼻孔裡哼了一聲。「就妳現在瘦得跟小雞似的,還能拎得動斧頭嗎?」她不耐煩地用大鐵勺攪動著鍋裡的粥,升騰的熱氣讓整個廚房都顯得溫暖,一股小米特有的香味飄散在空中。
「有那把子力氣用在劈柴上,還不如動動腦子多在你們五小姐身上下下功夫,妳不知比蕊湘那個小蹄子強上多少倍,即便是夫人跟前的琉璃、瓔珞也不見得比妳好多少,偏妳不知好歹,白丟了一吊錢的月例……」友貴家的又開始老生常談。「妳好好在五小姐跟前表現表現,說不定五小姐能念舊情,讓妳重新回到屋裡貼身伺候――」
「娘!」趙大玲趕緊打斷她。「我現在不是挺好嗎?每日能回來睡,還能幫您……」
「好個屁啊!」沒等趙大玲說完,就被友貴家的啐了回去。「老娘怎麼生了妳這麼個沒腦子的賠錢貨?從頭到腳沒有一絲伶俐勁兒!一個燒火掃地丫頭能有什麼前程?跟在小姐跟前那是多大的體面!妳在府裡得臉,連老娘和妳兄弟也能讓人高看一眼。等將來妳隨著小姐陪嫁到夫家,若是能被你們小姐姑爺看上,飛上枝頭做個姨娘,那就成了正經的主子了。等再生個兒子,就是小少爺,將來出息了考了狀元,那……」
友貴家的越說越興奮,已經開始展望飛黃騰達的人生,趙大玲在友貴家的將她封成一品誥命夫人前及時將話題打住。「娘,粥要滾了。」
友貴家的趕緊撤了柴火,掄起大勺將熱粥盛到一個個粗瓷盆裡,最後蓋棺定論道:「總之,幹什麼都比做掃地燒火丫頭強!」
趙大玲不置可否地揭開蒸籠,將冒著熱氣的饅頭撿到盤子裡。在枕月閣需要掃地、做各種雜務,還要不時被蕊湘使喚著做這做那,外廚房雖清苦勞累,但她覺得也比奴顏婢膝地跟在五小姐跟前強。端茶倒水自不必說,還要手洗五小姐的貼身衣服,伺候她沐浴甚至是如廁……簡單來說就是要全方位地伺候她吃喝拉撒,而且還要擺出一副甘之如飴的姿態,也許蓮湘、蕊湘她們確實有這個覺悟,打心眼裡認為能為她們小姐服務是無上的榮耀,但趙大玲肯定做不到。
陸續有外院、內院的僕役來領取中飯了,最早來的是二少爺院裡的小廝奎六兒,一個賊眉鼠眼、油嘴滑舌的小子,二十好幾了還沒娶到媳婦,進門就涎皮賴臉地往趙大玲跟前湊,閉著眼睛誇張地抽抽鼻子。「玲子妹妹,今天用的什麼頭油,這麼香!」
趙大玲低著頭扭腰躲開,奎六兒正要湊過來,就被端著瓷盆過來的友貴家的一下子拱開。「小兔崽子,又跑來招欠,皮癢了是吧!」
奎六兒嬉皮笑臉地道:「我的親嬸子,這幾天我跟著二少爺當差,忙得脫不開身,這不是想您和我玲子妹妹了嗎?」說著隔著友貴家的壯碩身軀,一雙老鼠眼直往趙大玲臉上和身上瞟。「兩天不見,玲子妹妹出落得越發水靈了。」
「出去當差?是給二少爺餵馬吧!」友貴家的毫不留情地揭穿奎六兒。
奎六兒一臉訕訕。「我伺候得二少爺的馬膘肥體壯,二少爺還賞我一壺好酒咧!」
「少廢話,趕緊端著午飯滾蛋!」友貴家的將一盆粥和一盤饅頭推到奎六兒面前。
奎六兒悻悻地將午飯放進食盒裡,仍不死心地盯著趙大玲,露出獻媚的笑容。「那玲子妹妹,我先走了,晚上再來看妳。」趁友貴家的不備時,又從旁邊盤子裡抓起一個饅頭咬在嘴裡,一溜煙跑了。
「兔崽子!」友貴家的拿著大馬勺追了出去,奎六兒早就跑遠了,友貴家的只能對著奎六兒飛奔而去的背影惡狠狠地詛咒。「撐死你個小兔崽子!」
回到廚房,友貴家的仍罵個不停。「挨千刀的貨,就愛占小便宜,多吃多占,噎死他得了……」
趙大玲勸道:「算了,一個饅頭而已。」
友貴家的拍著灶台。「不光是饅頭,奎六兒那兔崽子壓根兒沒安好心,賊眉鼠眼的,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敢把主意打到妳身上,我呸!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那副德性。他再敢來招惹妳,看我不打得他屁滾尿流,連他那獨眼兒的爹都認不出他來!」
友貴家的絮絮叨叨地罵著,趙大玲只好安慰她。「咱不理他不就得了,下次他再過來,我躲開就是了。」
友貴家的轉轉眼珠。「不行,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我得斷了那兔崽子的門路。」 友貴家的苦想了一會兒,須臾一拍大腿。「有了,昨天聽金根家的說,今日府裡要進一批僕役,都是官府那邊新入奴籍的官奴,說是有十來個人呢,回頭我找金根家的說說,死活得給我這外廚房配個能劈柴打水幹粗活的小廝,讓他給外院的少爺們送飯,就省了那些醃臢貨跑來礙眼。」
金根家的以前是夫人的陪嫁丫頭,後來夫人將她指給府裡管家馬金根做媳婦,現如今在府裡統管廚房採辦,平日裡很看不起友貴家的,見到趙大玲娘仨兒更是眼睛長在頭頂上,迎面過來只能看見她的鼻孔。
不過為了杜絕奎六兒之流以拿飯的名義來大廚房騷擾閨女,友貴家的決定放下臉面去要一個小廝幫忙幹雜活,順便往外院各處送送飯。
友貴家的連說辭都找好了:各處都忙得腳不沾地的,還得巴巴地騰出一個人來取飯,不如有個人能將飯菜熱騰騰地送過去。
趙大玲用現代的話總結,就是友貴家的要將服務關口往前移,為大家提供便利,從而提升外廚房的整體服務水準。
趙大玲覺得這是個好主意,畢竟劈柴挑水這樣的體力活,她和友貴家的幹得很吃力,有個小廝幫忙也是好的。
友貴家的出去找趙大玲那皮猴一樣在外面玩的弟弟大柱子,趙大玲則簡單地吃了口饅頭、喝了一碗粥,接著回枕月閣當差。
下午的第一件事便是澆花,這是上午蕊湘就安排下來的活計,趙大玲從雜物房裡拿出木桶和一個葫蘆瓢。本來柳御史的府裡有專門的園丁,統管府裡的花草樹木,但是趙大玲所處的這個枕月閣位於府中東南角,離老爺夫人的正屋頗遠,住的又是不受寵的庶出五小姐,因此園丁壓根兒很少光顧,日常花圃的打理也就落在了趙大玲的身上。
枕月閣格局簡單,一個不大的院子,兩邊沒有廂房,只有抄手遊廊從院門連著正屋。正屋三間,中間的作為廳堂,右邊的是五小姐的臥房,左邊的那間是五小姐繡花看書的屋子,貼身的丫鬟和婆子則住在後院的耳房裡。
院子雖然小,花草卻種了不少,除了院子邊上一棵高大的桂花樹外,還有一棵一人合抱的槐樹。正屋外有兩株木芙蓉,此刻豔粉色的花朵簇擁著,擠滿枝椏,開得正熱鬧。院子中是一條石子鋪成的小路,兩邊的花圃裡種滿了菊花,白色的胭脂點玉、紅色的朱砂紅霜、黃色的香山雛鳳、紫色的龍吐珠、淡綠的綠水秋波……將並不精緻的院子點綴得生機盎然。
院外幾十步遠就有一口水井,雖然一桶水還不至於沈得拎不動,但來回幾趟打水澆花,還是讓趙大玲出了一身的汗。終於澆完最後一片花圃,趙大玲抬手抹去額上細密的汗珠,才得以喘口氣。
勞碌的一個下午,趙大玲累得腰都直不起來,雖然她不覺得自己是個多嬌氣的人,但是上輩子可從來沒幹過這麼多體力活。回到外廚房時天都擦黑了,友貴家的已經做好晚飯,各院的僕役也都差不多將飯取走了。友貴家的在盛鍋裡剩的娘仨兒自己吃的菜,鍋鏟敲著鐵鍋鍋沿,叮噹作響。
趙大玲洗了手去幫忙,四處看了一下,屋裡並沒有新派來的小廝。她去碗櫥那裡取吃飯的碗和筷子,卻被地上的東西絆了一下,差點兒摔倒。
「喲,誰把一袋子紅薯放屋裡了?」趙大玲拿了碗筷,繞過那個袋子回到灶台前,一邊用開水燙了碗筷,一邊問友貴家的。「娘,不是說今天會撥過來一個小廝嗎?人呢?不會是馬管家變卦又不給了吧?」
友貴家的用手裡的炒勺指指地上的那袋子紅薯,憤然道:「我就說金根家的平日裡眼睛長在腦袋頂,怎麼我一說她就同意了呢,原來憋著壞呢,弄來這麼個等死的。」
趙大玲大吃一驚,那袋子紅薯原來是個人?
她走過去就著灶膛裡的火光仔細打量,果真是一個人形。那人面向裡頭,蜷縮在地上,滿身血污,身上的衣服都碎成麻袋片了,被乾涸的血跡浸染著辨不出顏色,怪不得她一開始以為是一袋子紅薯呢。
她蹲下來,小心翼翼的用手推了推他的肩膀,他一動不動,一點兒反應都沒有。
不會是已經死了吧?趙大玲將手指放到他鼻下,感覺到有微弱的氣息吹拂著她的指尖,像是蝴蝶的翅膀在搧動,看來還活著。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逆襲成宰相(1)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88 |
古代羅曼史 |
$ 197 |
中文書 |
$ 197 |
文學作品 |
$ 213 |
小說/文學 |
$ 225 |
古代小說 |
$ 225 |
華文羅曼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逆襲成宰相(1)
趙大玲前世是個嫁不出去的理工女,穿越後成了大戶人家的灑掃丫鬟,每日過得平淡無奇,直到一個全身是傷的男人出現在面前,他雖淪落為小廝,但一身的氣度風華在在說明了他有秘密……
他足智多謀,有不同於常人的傲骨;
她善良聰敏,有不該身處底層的學識,
仰天不會只看得見黑夜,明珠也不會永遠蒙塵……
趙大玲前世是個能幹的理工女,穿越後卻成了御史府的灑掃丫鬟,
父親老早就過世,母親在外院廚房當廚娘,
弟弟尚小不經事,自家沒靠山也沒銀兩,
前世的滿身才幹無用武之地,還要對其他丫鬟的戲弄忍氣吞聲,
雖日子過得無趣得緊,可為了生存,明哲保身才是正理!
直到一個全身是傷的俊美小廝出現在面前――
他滿腹珠璣,揀菜像在寫毛筆,還寫得一副好對聯,
其他小廝愛在嘴上占她便宜,他卻說男女授受不親,
當他們家被欺負而孤立無援時,是他找來幫手助她一臂之力,
他隱姓埋名,雖為官奴,可一身的氣度風華在在說明了他有秘密……
作者簡介:
趙眠眠,自由作家。任性而為,隨心而作,喜歡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用文字講一個故事,體驗著故事中的人物或欣喜、或悲傷的心境,領悟著他們的悲歡離合、愛恨情仇,跟隨他們一起笑、一起哭。寫作本身就是一件快樂的事,只盼在滿足自己的同時,也能夠打動看文的你。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初遇
顏粼睿坐在庭院迴廊前的石階上,看著湛藍的天空發呆。
此時正是金秋時節,陽光明媚,天高雲淡,一隊大雁在空中排成人字形向南飛去,漸行漸遠。院子裡種滿了菊花和木芙蓉,在花圃裡競相開放,一片奼紫嫣紅。迴廊邊上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樹,清風拂過,星星點點的金色桂花落在她的身上。
她閉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氣,感覺肺腑間都充滿了桂花的甜香……
「大玲子,妳又躲懶!庭院裡的石板路上這麼多落葉,妳掃了嗎?」
一聲暴喝將摟著掃帚、沈浸在甜蜜香氛中的顏粼睿拉回現實。
對,沒錯,大玲子就是顏粼睿落到這個時空後的名字。...
顏粼睿坐在庭院迴廊前的石階上,看著湛藍的天空發呆。
此時正是金秋時節,陽光明媚,天高雲淡,一隊大雁在空中排成人字形向南飛去,漸行漸遠。院子裡種滿了菊花和木芙蓉,在花圃裡競相開放,一片奼紫嫣紅。迴廊邊上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樹,清風拂過,星星點點的金色桂花落在她的身上。
她閉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氣,感覺肺腑間都充滿了桂花的甜香……
「大玲子,妳又躲懶!庭院裡的石板路上這麼多落葉,妳掃了嗎?」
一聲暴喝將摟著掃帚、沈浸在甜蜜香氛中的顏粼睿拉回現實。
對,沒錯,大玲子就是顏粼睿落到這個時空後的名字。...
»看全部
TOP
目錄
序
第一章 初遇
第二章 療傷
第三章 躺槍
第四章 玉碎
第五章 演技
第六章 維護
第七章 風波
第八章 對聯
第九章 暴露
第十章 致富
第十一章 過年
第十二章 欺辱
第十三章 勸慰
第十四章 坦言
第一章 初遇
第二章 療傷
第三章 躺槍
第四章 玉碎
第五章 演技
第六章 維護
第七章 風波
第八章 對聯
第九章 暴露
第十章 致富
第十一章 過年
第十二章 欺辱
第十三章 勸慰
第十四章 坦言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趙眠眠
- 出版社: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6-16 ISBN/ISSN:978986328733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12頁 開數:正25開【14.8*21公分】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