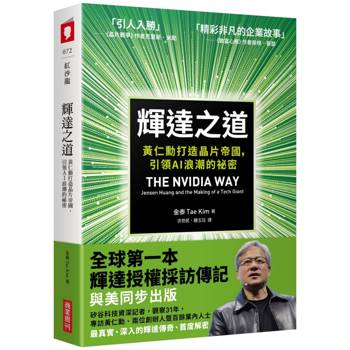不曾歷經過生死一瞬,
又豈知如此相擁的意義?
又豈知如此相擁的意義?
因為皇帝的一道恩典,讓納蘭崢得以在書院學習,
身邊同窗除了一群貴族子弟,還有那看似散漫、時則精明的太孫殿下。
兩人糾纏數年,當初的對頭冤家,如今多了小兒女的曖昧,
湛明珩太了解她,一顰一笑、眼波流轉間皆是默契,
雖不讓他輕易嚐甜頭,卻也凡事為他著想。
興許是初見時她明亮的眼與不甘示弱的嘴,抑或是這些年在書院共患難的光景,
教他的眼光就只追隨她,再難斷捨離。
而納蘭崢又何嘗不明白這兩小無猜的情誼?
他會在書院長廊下與她一起罰抄書,會因其他公子打她主意而吃醋;
也會在她落難時第一個找到她,放下身段跟她說對不起。
他總是這樣,時而霸氣,時而溫柔,教她一顆芳心為他陷落,
她以為兩人會一直相偕走下去,
殊不知一場西域使節來訪的宴會,竟絆住了他倆的腳步……
本書特色
故事千迴轉,情意扣心弦/池上早夏
常言道:「不是冤家不聚頭」,
此番招惹了那金尊玉貴的人,
她之後還有好日子過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