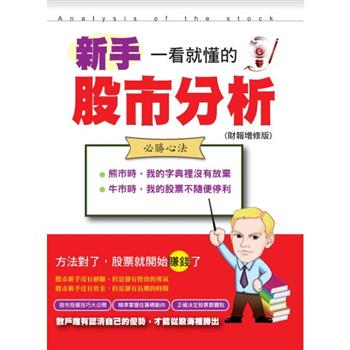第一章
距帝都一千多里的臨洲城,自古以來都是江南富庶之地,地肥糧多,商賈雲集。臨洲城往東,就是渡古縣,渡古縣靠近運河,通都運河從渡古縣城穿過,碼頭上一片繁忙,往來的船隻都要在此處停靠補給。商賈們出手大方,帶動了當地的酒肆行當,酒旗迎風招展,樓內肉菜飄香,進出的商客絡繹不絕。
運河的碼頭上,搬運貨物的苦力們忙個不停,這份營生也讓當地的壯丁們能拿到不少的工錢,放眼整個臨洲城,渡古是出了名的富縣。
渡古縣衙坐落在城東邊,莊嚴肅穆,衙府的後院裡,住著現在的縣令趙書才的家眷。
院子西屋的外間,趙縣令與夫人董氏坐在椅子上,面色不豫,下面的小凳上,一位素色衣裙的嬌美婦人哭得梨花帶雨。
趙縣令黑著臉,他本就膚色深,眼下尤其顯得難看,方臉闊耳,身形粗壯,委實不像是一縣父母官,倒像是鄉村的農夫。趙家從他往上數五代,都是在土裡刨食的莊稼人。
夫人董氏一臉濃妝,臉刷得雪白,唇抹得猩紅,本身長得也不過爾爾,極為普通,與一般的農婦無異。
小凳上的婦人則完全不同,脂粉未施的臉上,淚痕斑斑,妙目盈淚,淚珠如斷線的珍珠一般,順著白淨的面頰往下淌,讓人我見猶憐。
董氏與婦人的傷心不同,眼中全是幸災樂禍。「鞏姨娘,也是我這個主母心慈,讓妳自己養著三姑娘,可三姑娘讓妳養在身邊,倒是壞了性子,不知從哪兒學來的狐媚招數,一個未出閣的姑娘當眾與男子糾纏不休,我這個做嫡母的不過是說兩句,就尋死覓活。」
趙縣令瞪她,董氏搖了下手中的團扇,撇了下嘴。「三姑娘心氣高,別的公子看不上,倒是好眼光瞧上鴻哥兒,趁鴻哥兒下學之際前去癡纏。也不看看自己的身分,鴻哥兒可是少卿大人的嫡長子,哪裡是她一個庶女能高攀的?」
一席話說得趙縣令面色發沈,董氏換了口氣。「老爺,三姑娘被養得性子輕浮,別人只會說我這個嫡母的不是,妾身著實委屈。」
鞏姨娘淚痕猶在,乞憐地看著趙縣令。「老爺,三姑娘自小性子如何,別人不知,您還不知嗎?」
趙縣令憶起三女兒怯懦的樣子,不悅地瞪一下董氏。「就妳這婦人,嘴裡沒個好話。鴻哥兒和雉娘也算是表兄妹,在一起說個話,旁人也不會多想,偏到妳的嘴裡就成了和男人拉扯。」
被丈夫訓斥,董氏恨極,手中的帕子絞得死死的,狠狠剜了眼鞏姨娘,又看向前方內室。大夫進去一會兒了,裡面連個動靜都沒有,若三姑娘真有個三長兩短,看她怎麼收拾這小賤人!
不一會兒,一位年長的白鬚大夫提著醫箱出來,鞏姨娘急忙上前。「王大夫,三姑娘如何了?」
王大夫撫了下鬚,不看她一眼,對著上座的人。「回大人、夫人,小的已盡力施救,三姑娘……許是耽擱的時辰太長,怕是……」
「不、不會的……」鞏姨娘哭喊著,衝進內室。
內室中,面容慘白的少女躺在榻上,年歲約十七,正值妙齡,少女雙眼緊閉,長睫如羽扇,柳眉粉唇,膚色白得明淨,吹彈可破,巴掌大的小臉蛋惹人心憐。她了無聲息地躺在那裡,像被粗魯折斷的嬌嫩花兒,脖子處的紅痕觸目驚心。
鞏姨娘撲上去,哭得傷心。
趙縣令和董氏走進來,趙縣令的眼中有一絲惋惜。三女兒長相出眾,雪膚花貌,以後無論是聯姻或結交顯貴,都是好助力。
董氏見榻上的少女似乎已無生機,只覺內心暢快。三姑娘生得貌美,將自己的女兒都壓得抬不起頭,夫君也對她頗重視,言語間還想替她攀一門高親,這讓人如何能忍?
她對自己身邊的婆子喊道:「妳們還不快將姨娘拉開?人死燈滅,理應入土為安,切莫再擾了三姑娘的生魂。」
婆子們就要上前拉扯鞏姨娘,鞏姨娘哭得越發大聲,哀求地望著趙縣令。「老爺,三姑娘身子溫熱,妾不相信她已經……求老爺,讓妾再守一會兒,說不定等下三姑娘就會醒來。」
「鞏姨娘,將將斷氣之人身子都是溫熱的,收殮之人常趁著這溫熱之際,替死者更衣淨面。妳讓開,三姑娘的後事要緊。」
「不……」鞏姨娘死死地撲在榻上,將女兒護住。兩位婆子不敢使全力,鞏姨娘是大人的心頭肉,若說背著大人,她們不會客氣,可眼下大人還站在屋內看著,她們是不敢放肆的。
董氏略帶委屈地看著趙大人。「夫君,你看,妾身一片好心,倒是枉做壞人。」
她用帕子擦了下眼角,便有白色的粉末子掉下來。趙大人厭惡地轉過頭,看著哭得上氣不接下氣的愛妾,憐惜地出聲。「憐秀,夫人說得倒是沒錯,雉娘的後事要緊,妳讓開吧。」
「老爺……」鞏姨娘淚流滿面地搖頭,看得趙大人的心又軟了幾分。
董氏恨得不行,對兩個婆子使眼色,兩個婆子又上前去拉鞏姨娘。鞏姨娘死死地護著榻上的少女,不肯起身。突然間,似乎聽見一聲極輕的咳嗽聲,她驚喜地抬起頭,就見榻上的少女眉頭皺了一下,又咳嗽一聲。
她歡喜地叫著。「三姑娘,妳可醒了!」
趙大人和董氏看見這一幕,一個鬆口氣,帶著高興;一個猶不甘,滿眼怨毒。
榻上的少女長長的睫毛顫了幾下,睜開雙眼。她孱弱的面容像玉瓷一般,如墨雲一般的髮絲散在枕頭上,水眸看起來矇矓一片,帶著茫然;粉白嫩唇無血色,分外嬌弱,讓人想抱在懷中好好地呵護。
趙大人讓下人去將未走遠的王大夫追回來,老大夫氣喘吁吁地進來,就對上少女的目光,他一驚,連忙上前探脈。
半晌,王大夫道:「三姑娘應是剛才一口氣憋著沒上來,眼下許是被人一動,反倒是將那口氣頂出來,得了生機。」
他這一說,鞏姨娘喜極而泣。剛才那兩個婆子使勁地拉她,她緊緊地抱著三姑娘不撒手,反倒是救了三姑娘一命。
董氏臉色陰霾,狠狠地剜了兩個婆子一眼。
王大夫開了一個外傷的方子,讓人敷在少女的脖子上,再纏上布條,又重開一個調養的方子後,便起身告辭。
榻上的少女始終一言不發,鞏姨娘哭起來。「三姑娘……」
少女垂下眼眸,長睫顫動,似未清醒。
鞏姨娘不敢大聲,淚漣漣地捂著嘴哽咽。「三姑娘,妳為何要想不開尋短見?幸好老天保佑,烏朵這丫頭來得早,要不然……妳讓姨娘可怎麼活得下去啊?」
董氏閒閒地道:「鞏姨娘,雉娘才醒來,妳就跟哭喪似的,小心又驚動閻官,將雉娘未定的魂給勾走。」
少女睫毛掀起,似無意般地看了她一眼。
董氏只覺後背一涼,待細看,又見榻上的少女半垂著眼,一副半死不活的樣子,暗道自己眼花。
趙縣令不悅道:「雉娘才剛醒來,妳說什麼閻官,也不嫌晦氣。」
「老爺,我這也是心急。」董氏露出委屈的神色。
趙縣令哼了一聲,看向鞏姨娘。「憐秀,雉娘才剛醒來,又敷過藥,還沒什麼精神,最該好好休息。」
鞏姨娘不捨地站起來,神色哀傷地同他們一起走出房,房內只餘一位黑瘦的丫頭。
少女聽見關門聲,又睜開眼,指了指桌上的白瓷杯子,又指了下自己的喉間。黑瘦丫頭眼腫如桃,定是被淚水泡的,見她的動作,明白過來,自責道:「都是烏朵粗心,三小姐必是口乾。」
叫烏朵的丫頭斟滿一杯茶,將她扶起,腰上墊了個枕頭,杯子端到她嘴邊。她伸手接過,慢慢地小口喝著,嗆了幾下,一杯下肚,喉嚨處舒適不少。
少女將杯子遞給烏朵,不經意地看到自己的雙手,十指瑩白透亮,纖纖如玉,她一愣,垂下眼眸。
烏朵以為她是累了,忙又扶著她躺下。
雉娘,如今她叫雉娘。
少女盯著頭頂的幔帳,眨了下眼,緩緩地閉上。
睡夢中,似乎又回到暗無天日的前世,東躲西藏,惶惶不可終日,連睡覺都從未踏實過。猛然似是看見自己渾身是血地躺在馬路中間,四周車來車往,行人如織,有尖叫聲和喧鬧聲,身體裡湧出的血在地上暈成大朵的花,她睜著眼,看著天空的那朵白雲,慢慢地隨風飄蕩……
眼皮不停地下垂,她不甘心地閉上眼。雖然活得艱難,可她還沒有活夠。
翌日幽幽轉醒之際,就看見坐在榻邊上的鞏姨娘,繁複的交領古裝衣裙,顏色素淨,雖年歲看起來並不小,卻楚楚動人,別有一番風姿,一副想抱她又不敢抱的樣子,哭得哀戚戚的。
她思索著一個女兒該有的樣子,露出一個微笑。
外面走進一位婆子,手中端著雕花木盆。鞏姨娘拿帕子按了按眼角,扶她起來梳洗,說話間,雉娘知道這位婆子姓蘭,是鞏姨娘的心腹。
烏朵掀簾子進來,手裡端著一碗米粥,雉娘方才覺得腹內空空如也,就著兩碟小菜,硬忍著喉間的不適,將米粥喝完。
鞏姨娘見她喝完,眼眶更紅,問黑瘦的丫頭。「烏朵,妳今日去廚房要吃食,可有人為難妳?」
烏朵似乎遲疑一下。「姨娘,王婆子倒沒有為難什麼,只不過話說得難聽些,奴婢就當作沒有聽見。」
鞏姨娘聞言,眼眶又紅了,抽出帕子抹起淚來。
雉娘的手頓一下。她發現這位姨娘眼淚真多,簡直就是個水做的人。
雉娘將碗遞給烏朵,指了指自己的喉嚨,對鞏姨娘搖了下頭,鞏姨娘哭起來,聲音哽咽。「三姑娘如此懂事,姨娘明白的,身為妾室就該守妾室的本分,從未想過要和夫人爭什麼。妳自小乖巧,縱是二姑娘多次尋妳的不是,妳也只是忍著,這次若不是她們太過分,妳怎會……幸好菩薩保佑,妳大難不死,否則……」
說完,鞏姨娘的眼淚掉得更凶。
她眸光微冷。菩薩高高在上,哪能看見人間疾苦。
她靠在榻上,蘭婆子和烏朵收拾好,便退了出去,屋內只餘母女二人,鞏姨娘淚眼汪汪地看著她。「妳不過是與表少爺不小心碰了下手,二姑娘就嚷得人盡皆知,說妳不知羞地癡纏表少爺,上趕著貼上去。可姨娘知道,妳是個本分的孩子,平日裡避那表少爺都來不及,又怎會做出如此事情?此事妳爹自會明查,妳為何想不開,自尋短見……」
竟是這樣。不過是被男人碰了一下手,原主便被逼得尋死。
外間有腳步聲傳來,鞏姨娘停住不語,將淚擦乾。門簾掀開,進來的是董氏。
鞏姨娘站起來朝她行禮,董氏看也不看她,挑剔地看著榻上的雉娘,裝模作樣地嘆口氣。「昨日我思來想去,雖然雉娘不知事,可我身為嫡母,卻不能看著她再做傻事。姑娘家的名節何其重要,眼下,此事還不知道瞞不瞞得住,倒不如乘機將雉娘的親事定下。」
聞言,鞏姨娘大驚。
董氏立在榻邊上,居高臨下地俯視著。「雉娘雖年歲最小,可事急從權,出了這檔事,若知情,哪還有人家願意聘她為正妻?倒是我這個嫡母心善,想著母女一場,實不忍心……我那娘家姪子一表人才,身強體壯,雉娘嫁過去,看在我的面子上,我那嫂子也不會說什麼。」
鞏姨娘臉色瞬間煞白,抖著唇。「夫人,此事老爺可知?」
董氏似笑非笑地看著她。「一個庶女的親事,我當嫡母的作主便是,何必驚動老爺?此事就這麼定了,雉娘好好養傷,就等著嫁人吧。」
說完,董氏便揚長而去。
鞏姨娘白著臉,看著榻上的女兒,大哭起來。
雉娘實在是有些看不上只知道哭的鞏姨娘,她掙扎著坐起來,鞏姨娘淚眼矇矓地望著她。「怎麼辦?夫人居然如此狠心,那董家少爺十分凶暴,聽說髮妻就是被他生生打死,不行……我要去求老爺……」
鞏姨娘哭著,掩面跑了出去。
雉娘看著房頂的木梁,垂下眼眸,半晌,使勁地拍了下榻,弄出聲響。外間的烏朵進來。「三小姐,可有什麼吩咐?」
雉娘對她招了招手,又指了指衣櫥。烏朵會意,取來一套綠色的衣裙,替她換上,又將她扶到梳妝檯前,綰了一個髮髻,綁上髮帶。
菱花鏡子中映出少女的模樣,墨髮如雲,膚如凝脂,卻又弱質纖纖,綠色的衣裙也未能將其容色減半分,分明是一朵美麗的小白花。
喉嚨處還是火灼般的痛,她強忍著不適,讓烏朵扶著出去。一走出門,外面的陽光刺得她雙眼睜不開。
自然的氣息撲面而來,她深吸一口氣,再睜眼看著這陌生的院子,此時無心細看,轉向烏朵,艱難地吐出一個字。「父……」
烏朵反應過來。「縣令大人在前衙。」
雉娘點點頭,示意前去。
還未走近,就聽見鞏姨娘的哭聲。
三堂是縣令的辦事之處,此時不僅趙縣令在,文師爺也在,鞏姨娘就這樣闖進來,文師爺連忙迴避,正巧碰到趕來的雉娘。
文師爺與她遙遙見禮。雉娘不動聲色地打量著他,只見他不到四十的樣子,長相儒雅,身量中等,雙眼如炬,滿是睿智。
雉娘低下頭,烏朵彎腰行禮。「文師爺。」
這人是師爺,倒是有些出人意料。
文師爺避走,雉娘進去,就見鞏姨娘哭著,父親臉色黑沈,緊抿著唇,背著手,氣沖沖地往後院走去。
鞏姨娘哭著小跑著跟上,對雉娘使一下眼色,示意她不要再跟。雉娘微蹙下眉。便宜父親明顯不贊同董氏的行為,董氏為何還要向她們透露此事。
她看著鞏姨娘嬌怯的身影,恍然明瞭。董氏分明就是故意說給她們聽的,意在自己。她才從鬼門關前走一趟,以原身的性子,若得知馬上就要嫁給一個有暴力傾向的男子,怕是一氣之下會再尋死。
董氏想要自己死,這才是目的。
雉娘想通關竅,倒是不急。以她的姿色,趙縣令必不會讓她隨便嫁人。
自古以來,婚姻之事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萬沒有她一個未出閣的姑娘參與的道理。她慢慢地穿過園子,不動聲色地打量著這縣衙後宅。
此時正是花紅柳綠,青翠接紅豔之時,花圃裡不甚名貴的花兒開得豔麗,花朵滿枝,爭奇鬥妍。
院子不算大,青磚黑瓦,飛簷翹角,正中一座涼亭,八角紅柱,亭邊繁花簇簇。
她體力略有不支,靠在烏朵的身上,指一指涼亭。烏朵將她扶過去,坐在長凳上。院子實在算不上大,坐在涼亭中,都能隱約聽到東廂那邊傳來的聲音。
男人的怒吼聲和女人的哭聲,還有一道尖刻的辯駁聲。
雉娘神色未明,環顧這略不真實的一切,不經意掃到園子的另一角,那裡不知何時站著一位青年。青年約二十歲左右,身著白色長袍,雲巾束髮,長相英俊,透著一股書卷氣,望向雉娘的眼神癡迷中帶著深情,待看見她脖子上纏著的布條,眼神中有痛心,還有一絲憐憫。
青年慢慢地走過來,烏朵行禮。「見過表少爺。」
表少爺?與原主碰了一下手的表少爺。
表少爺目光痛惜。「雉表妹,妳……」
雉娘起身,扶著烏朵的手,就要往回走。這位表少爺還是遠著些的好,才不過是碰了下手,嫡母就能逼得原主去死,若是再有瓜葛,不知又要惹來什麼麻煩。
見她欲走,青年急道:「雉表妹,鴻漸願承擔責任,照顧表妹終生。」
雉娘細品著他的話。只是照顧,而不是娶,這位表少爺貪圖的不過是她的美色,打著讓她為妾的主意。她目光微冷,垂下眸子,對他的話恍若未聞。
青年追上來,堵住她的去路,面帶急切。「雉表妹……」
「鴻表哥。」
一位粉裳薄紗的少女急急地朝這邊走來,她約十六、七歲的樣子,細眼塌鼻,卻一臉極濃的妝容,百花分肖髻上插著一支鏤空累絲金釵,金釵下墜著一顆鑲金珍珠,隨著她走路的動作左右晃動,閃得人眼花。
「二小姐。」烏朵行禮。
少女理都不理她,目光含恨地看著雉娘,然後轉身盈盈地向青年見禮,頭上金釵上的珍珠擺盪出優美的弧線,將她原本一分的長相襯得多了二分的美麗。「燕娘見過鴻表哥。」
「二表妹多禮,鴻漸這廂有禮。」
男人略略地彎腰,雙手作了個揖,回一個禮。
雉娘用手指摳一下烏朵的掌心,烏朵忙對兩人告罪。「表少爺、二小姐,三小姐身子不適,奴婢先送三小姐回屋。」
段鴻漸見她臉色蒼白,又看向她包紮著的脖子,欲言又止。雉娘裝作沒看到的樣子,低下頭去,露出白瘦細嫩的頸子。
*欲知精采後續,敬請期待5/22上市的【文創風】636《閣老的糟糠妻》1。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閣老的糟糠妻(1)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65 |
華文羅曼史 |
二手書 |
$ 175 |
二手中文書 |
$ 197 |
中文書 |
$ 197 |
文學作品 |
$ 198 |
世界羅曼史 |
$ 225 |
古代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閣老的糟糠妻(1)
「多謝恩公出手相救,大恩大德無以為報,
小女子願來生做牛做馬,結草銜環,來報恩公再生之恩。」
「好,欠恩還報,我必上門索之。」
雉娘一睜眼就是死裡逃生,可才喘口氣,又發現自己身處困境……
父親是個小縣令,生母是柔弱的妾室,嫡母與嫡姊蠻橫凶狠,
竟逼得她的前身以死證明清白,沒想到她穿越而來又活了,
讓嫡母更是恨得牙癢,使盡下流手段要毀她名聲,指婚、私會外男樣樣來,
她與姨娘防不勝防,千鈞一髮之際,幸得一位神秘的公子出手相助;
她驚險逃過一劫,於是將他視為恩公,
除了以身相許,她決心公子要自己做什麼便做什麼!
只是天底下真有這麼善心的男人麼?她都沒做什麼事,他卻是處處出手,
連自家後宅的陰私事都幫她料理了,這位公子是否太神通廣大了些?
對自己又如此好意,她又能回報他什麼呢……
本書特色
她與姨娘活得困苦,在嫡母嫡姊手下討生活的日子,
若不是有了一位神秘公子的幫助,哪能逃過各種陷害手段?
她有心回報,可他跟自己索要的卻是……
作者簡介:
香拂月,晉江文學城簽約作者,八〇後的懶宅女。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宅在家裡,看書或者發呆。第二喜歡的事情就是看風景,一年四季,都是美景。
最大的愛好就是寫文,把自己喜歡的故事寫出來,供讀者們閒暇之餘輕鬆讀來,愉悅身心。堅持不寫悲劇,生活已是夠艱辛,誰也不願意忙碌了一天,還要為故事中的人物糟心。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距帝都一千多里的臨洲城,自古以來都是江南富庶之地,地肥糧多,商賈雲集。臨洲城往東,就是渡古縣,渡古縣靠近運河,通都運河從渡古縣城穿過,碼頭上一片繁忙,往來的船隻都要在此處停靠補給。商賈們出手大方,帶動了當地的酒肆行當,酒旗迎風招展,樓內肉菜飄香,進出的商客絡繹不絕。
運河的碼頭上,搬運貨物的苦力們忙個不停,這份營生也讓當地的壯丁們能拿到不少的工錢,放眼整個臨洲城,渡古是出了名的富縣。
渡古縣衙坐落在城東邊,莊嚴肅穆,衙府的後院裡,住著現在的縣令趙書才的家眷。
院子西屋的外間,趙縣令與夫人...
距帝都一千多里的臨洲城,自古以來都是江南富庶之地,地肥糧多,商賈雲集。臨洲城往東,就是渡古縣,渡古縣靠近運河,通都運河從渡古縣城穿過,碼頭上一片繁忙,往來的船隻都要在此處停靠補給。商賈們出手大方,帶動了當地的酒肆行當,酒旗迎風招展,樓內肉菜飄香,進出的商客絡繹不絕。
運河的碼頭上,搬運貨物的苦力們忙個不停,這份營生也讓當地的壯丁們能拿到不少的工錢,放眼整個臨洲城,渡古是出了名的富縣。
渡古縣衙坐落在城東邊,莊嚴肅穆,衙府的後院裡,住著現在的縣令趙書才的家眷。
院子西屋的外間,趙縣令與夫人...
»看全部
TOP
目錄
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香拂月
- 出版社: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5-25 ISBN/ISSN:978986328865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開數:正25開【14.8*21公分】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