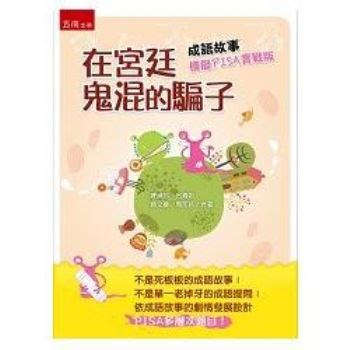「七叔……你可以幫我的忙嗎?」
「好,我答應妳。」
這幾個字,說得低而輕,卻頗有力道,是千金一諾的篤定。
文創風683《七叔,請多指教》2+封 蘇自岳◎著
蕭敬遠從沒想過,多年後再見到她,竟會是在這種情況下──
一場皇位之爭將京城鬧了個天翻地覆,官家女眷遠避郊外,
這傻丫頭為救娘親和弟弟,竟以自身當餌引開流寇,好在他早一步找到人。
總之他又救了她一次,只是這回狀況更加凶險,真真把他氣得無法言語!
可見她害怕得嚎啕大哭,他也不忍再罵,唉,究竟該拿她怎麼辦才好?
打從初相見,他就發現這葉家小丫頭與眾不同,眸若秋水、靈氣逼人,
有時語帶玄機像是知道些什麼;有時又天真呆萌得像個小女娃。
世間女子唯有她可以衝著他任性撒嬌耍賴,讓他如此牽腸掛肚,
就是意識到己身的情意逐漸無法掩藏,他才自請離京,
何況她是娘中意的姪媳人選,他身為叔伯輩不便搶親,又恐心上人對他無意……
可當聽見她說「別丟下我」時,他想通了──自己的媳婦自己護著!
他要將她娶進蕭家,當他定北侯之妻!
本書特色
葉青蘿開始習慣依賴七叔,而七叔意識到自己萌生不該有的情感,因輩分有所差距自請調駐外地。數年後在追捕反賊的行動中跟葉青蘿重逢,再度表明情意,但葉青蘿擔心嫁入蕭家會再遭遇不測而拒絕了……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七叔,請多指教 2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5 |
二手中文書 |
$ 165 |
華文羅曼史 |
$ 188 |
古代小說 |
$ 197 |
中文書 |
$ 197 |
文學作品 |
$ 225 |
古代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七叔,請多指教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