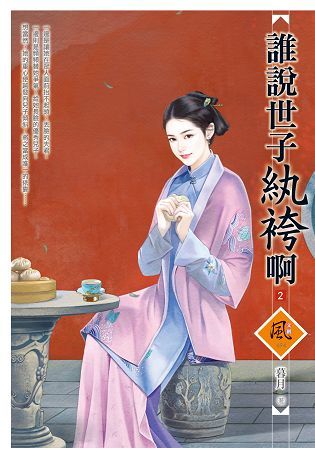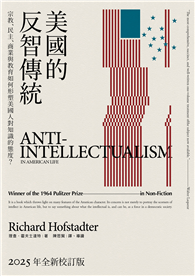第十一章
隔得數日,魏雋航忽又想起妻子嫁妝鋪子一事,遂召來心腹侍從一問,知道夫人已經著人將那錢掌櫃送進了衙門,他托著下巴想了想,又吩咐道:「想個法子,讓那錢掌櫃的嘴巴放乾淨些,我不希望從他口中說出什麼有礙伯府名聲之話來。」靖安伯府名聲不好,夫人必會不高興,夫人不高興了,他心裡也就不痛快。既如此,那便得從根子上斷絕了這個可能。
那人領命而去。
魏雋航拍拍衣袍,本想到正房裡尋夫人說說話,忽地想起今日夫人回了伯府,腳步一拐,便轉向了習武場。
這個時候,霖哥兒和蘊福應該都在習武場練習才是。
果不其然,離得遠遠的便看到魏承霖在場上舞劍的身影。視線往另一旁掃去,又見一個小小的身影正扎著馬步,正是初習武的蘊福。
他看得心情大好,招來丫頭取些茶水點心來,坐到一旁一邊品著茶、吃著點心,一邊觀賞著兒子的英姿。
「好,舞得好!不愧是我的兒子!」看著魏承霖收回劍勢,他再忍不住大聲喝彩。
英國公到來時,看到的便是這樣的一幕──不學無術的兒子蹺著腿、捏著點心往嘴裡送,不遠處孫子迎風練著他親自教導的劍法,便是那個名為蘊福的孩子也認認真真地扎著馬步。
滿場看來,就只有那個悠哉悠哉地品著茶點的身影讓他牙根癢癢。
他深深地呼吸幾下,很努力地壓下心裡頭那股火氣。這混帳除了會哄得他母親眉開眼笑外,其他半點本事也沒了,這吊兒郎當的模樣,哪有半分魏家子孫的樣子?真真是……不氣不氣,都這麼多年了,要氣也早該氣飽了!
「祖父!」還是魏承霖率先發現了他,連忙上前見禮。
蘊福也看到了,同樣想要過來行禮,卻不料他一雙小短腿站了太久,才剛一動,整個人「啪」的一下,一屁股便坐到了地上,半天爬不起來。
魏雋航被兒子這聲「祖父」唬了一跳,手忙腳亂地將那些茶點收好,也沒有發現蘊福的窘狀。
「父親。」
英國公瞪了他一眼,到底還是想著替他留幾分面子,不欲在孫子面前教訓他,只道:「你隨我來,我有事要問你。」
魏雋航應下,上前推著他那沈重的木輪椅,一直將他推回了書房。
「不知父親想問些什麼事?」細心地將英國公腿上的毯子蓋好,又替他倒了杯溫水放在他身邊的小圓桌上,魏雋航才小心翼翼地問。
英國公瞅了瞅他,端過溫水呷了幾口。
或許這小子還能再添一個優點,便是夠細心。也虧得他這麼多年了還記得自己自傷後便只喝溫水,不沾茶與酒。這般細心,還會哄他母親高興,若是位姑娘便好了,卻偏偏是個混帳小子!
可心裡那點惱意到底被兒子這個貼心的舉動給打消了。
「我怎的聽聞,你置外室之事,陛下早已知道?如此看來,難不成陛下竟還幫著你隱瞞?」英國公緩緩地問了此事。
魏雋航心中一個激靈,表面卻不顯,撓撓耳根,不好意思地道:「當日確是被偶然微服外出的皇帝表兄撞了個正著。」不由得又想到自己替那人揹的鍋,遂話鋒一轉,繼續道:「不過皇帝表兄說,妻不如妾,妾不如偷,置外室雖然不是什麼光彩事,但也算不得什麼大事,不過是天底下男人都會犯的一個小錯罷了。」
英國公一雙濃眉死死地擰著。「陛下果真說過這番話?」
「這是自然,他是皇帝,難不成我還敢誣衊他?」魏雋航一臉的無辜。
「陛下此言著實差矣!男子漢大丈夫,堂堂正正,坦坦蕩蕩,娶妻便娶妻,納妾便納妾,這般偷偷摸摸地在外頭置外室,實非大丈夫所為,又置家中妻房於何地?」英國公滿臉的不贊同,想了想還是有些不放心,於是吩咐道,「磨墨,我要上摺子好好與陛下說說這番道理!」
「哎,我馬上準備!」魏雋航心裡那個高興啊,一溜煙地跑到書案前磨起墨來。
他家老爺子可是位認準了理便一定要唸到你明明白白、生生受下才肯甘休的!
後來英國公連上三道摺子與元佑帝一番理論,讓元佑帝煩不勝煩,卻偏偏奈何他不得,當年他還是位不受寵的皇子時,就有些怕這位姑丈的唸叨,童年的陰影,哪會這般輕易消失?如今便是身為皇帝的他,也依然有些抵擋不住,因此對將禍水東引的魏雋航更是恨得牙癢癢的。
如此,魏雋航才感到稍微出了口氣。
沈昕顏並沒有讓梁氏有喘息的機會,在將錢掌櫃押送官府後,當日她便帶著秋棠回了靖安伯府。
她這般突然地回來,府上眾人都有些奇怪,但也沒有多說什麼,而梁氏更加想不到她此番回來的目的。
「可是有什麼事?」到底是一母同胞的兄妹,靖安伯察覺她的神色有異,低聲問。
沈昕顏並沒有回答他的話,而是衝著二房和三房的夫妻道:「我有些話想與大哥、大嫂說。」
那兩房的夫妻立即知趣地起身告辭。
梁氏見狀,不知為何心裡有些不安,勉強揚著笑道:「這是怎麼了?難不成是世子爺又在外頭有了人,妳想著讓娘家人替妳出面?」想來想去,估計也只有這個可能了。
前一陣子英國公世子置了外室之事便傳得沸沸揚揚,一直到後來由世子夫人親自出面著人將那外室抬了進府才消停。
沈昕顏沒有理她,接過秋棠遞來的重新抄過的帳冊,親自交到靖安伯手上。「大哥,這冊子記載的是大嫂這些年來從我鋪子裡取走的銀兩,有部分銀兩的去處我也做了詳細記錄。」
靖安伯臉色一變,不可置信地回頭望向妻子,見她臉色倏地慘白,心裡「咯噔」一下,知道妹妹所言非虛。他的妻子竟然真的夥同外人偷取妹妹嫁妝鋪子的銀兩?!
「妹妹胡說些什麼?雖然咱們是一家人,可這種話也不是能胡亂說的。」梁氏強撐著道,視線卻一直往靖安伯手上那帳冊瞄,發現那冊子相當新,心思頓時一定。「我竟不知何處開罪了妹妹,讓妹妹這般誣衊。若是這些年來,怎的這帳冊還如此新,倒像是剛剛才寫好的一般?」
「大嫂沒有說錯,大哥手上這本確是我讓人重新抄寫的,原來的那本我還好好地收著。大嫂也別急著否認,我今日敢直接將此事扯開,便是有了十分的證據。」
「毒婦!」那廂,靖安伯顫著手大概翻閱了一遍,越看便越是心驚、憤怒,終於沒忍住,猛地揚手,重重的一記耳光抽向梁氏,將她打得撲倒在地。「妳不但偷取昕顏鋪子裡的錢,居然還用來放印子錢?誰給妳這般大的膽!」這才是讓他最最憤怒的地方!偷取小姑的錢已是不可饒恕之罪,而她居然還膽大包天地放印子錢,這一放就是數年,數額之大,著實令人心驚。這萬一讓人發現,對靖安伯府來說,就是一場滔天的禍事!
沈昕顏冷漠地望著眼前這一幕,若非她親自讓人去查,只怕也不會知道她的嫂子居然這般大膽。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她放印子錢一事那錢掌櫃並不知曉,否則,若是他在公堂上那麼一嚷……靖安伯府也就到此為止了!
「我、我沒有!你不能只聽她一面之辭,這些所謂的證據全是假的、假的!」梁氏死不承認。她自認行事謹慎,此事的知情人數不出五根手指,這些人又全是她的心腹,是絕對不會背叛她的。故而,哪怕沈昕顏再怎麼言之鑿鑿,她照樣咬緊牙關不肯承認。沒有證據,那一切便只能是誣衊!
「妳還不肯承認?!真當我是那等蠢物,什麼都不知道是不?」靖安伯氣得臉色鐵青,已有些發福的身軀不停地顫抖著。
「大嫂身邊的那位梁嬤嬤好些日子不在府裡了,大嫂難道從不覺得奇怪嗎?」沈昕顏忽地問。
梁氏呆了呆,心中劇跳。梁嬤嬤?梁嬤嬤不是因為小孫子受了風寒,需要告幾日假回家去嗎?難不成、難不成……
「她全招了。」沈昕顏緩緩說出了梁氏心裡最害怕之事。
梁嬤嬤可是她的陪嫁嬤嬤,她的事從來就沒有瞞過梁嬤嬤,若是梁嬤嬤出賣自己,那她根本毫無分辯的餘地。梁氏終於徹底癱在了地上,知道大勢已去。
「妳這毒婦,妳這毒婦!我、我要休了妳,休了妳!」靖安伯氣紅了眼,一轉身便打算去寫休書。
沈昕顏眼明手快地拉住他。「大哥慢著!」
「妳不必多說,此等招禍的毒婦,靖安伯府絕不能容!」
「那大哥可曾想過慧兒那幾個孩子?」沈昕顏輕聲問。「有一個被休的母親,你讓孩子們今後如何見人?」
靖安伯的腳步終於停了下來。
梁氏見狀,心中一定。對啊,她還有孩子!便是看在孩子們的分上,他都不能將自己休了!只是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想到的生財之道,怕是從此便要斷個乾乾淨淨,她便忍不住一陣心疼。
沈昕顏並沒有理會她,只是靜靜地看著兄長。
靖安伯的臉色幾經變化,眸中好一番猶豫不決,最終,把心一橫,沈聲道:「既如此,便將她送到家廟,此生此世再不准她出現人前!」
「不行,不能將她送到家廟!」梁氏還沒有來得及說什麼,沈昕顏便已衝口而出。
「為何不能將她送到家廟?」靖安伯不解。
沈昕顏只覺得腦袋一陣鈍痛,上一輩子在家廟的那些痛苦記憶再度襲來。半晌,她才勉強平復思緒道:「好好的主母突然送到了家廟,這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訴世人,她犯了不可饒恕之錯嗎?這與直接將她休棄又有何分別?」
最主要的是,經歷過上一輩子,她對「家廟」二字便先生了排斥,更反感動不動便將人送到家廟去。梁氏的情況與上輩子的她不同,若是被送進去,梁氏所出的那些孩子這輩子也就不用抬頭做人了。
畢竟,上輩子她被送進去時,已經是「太夫人」,而且又不是掌中饋的主母,再怎麼也能把話圓得好聽些。
可梁氏不同,她還年輕,更是一府的主母,突然被送進家廟去,豈不是更招人閒話?
休棄不得,又不能送走,不得不說,確是有些棘手。
「既如此,便讓她病了,從今往後好好在屋裡養病,再不准離開半步!」
突如其來的怒喝聲驚醒了一臉為難地看著彼此的兄妹二人,二人回頭一望,竟見沈太夫人拄著枴杖走了進來,正怒目瞪視著地上的梁氏。
「禍家精!」沈太夫人啐了梁氏一口,只差沒有一枴杖打過去。
「母親!」沈昕顏連忙上前扶著她落坐。
「你們說的話我都聽到了,是我識人不明……」想到自己當日親自提拔的得力助手竟成了最大的蛀蟲,沈太夫人一臉痛心,更覺對不住女兒。
「這與母親有什麼相干?人心會變,再忠厚誠實之人也有變貪婪的時候。真要怪,也要怪女兒這些年不聞不問,以致助長了他們的貪念。」沈昕顏柔聲勸道。
靖安伯跪在沈太夫人跟前,一臉愧色。
沈太夫人長長地嘆了口氣,目光落到跪在身前的梁氏身上,眸色一冷。「活至這般年紀,我也算是見過不少人,可卻從不曾見過哪一個女子似妳這般無恥!妳也算是令我大開眼界了。」
梁氏一陣難堪,咬著唇瓣一句話也不敢說。
「母親,是兒子之錯,兒子對不住妹妹,也對不住府裡。兒子會想方設法將她放出去的錢都收回來,至於她貪的妹妹的錢,便拿她的嫁妝錢來還……」
「那是我的嫁妝,將來是要留給慧兒他們兄妹幾個的──」梁氏頓時便急了。
「妳動昕顏的錢,那也是她日後要留給盈兒兄妹二人的!」靖安伯毫不客氣地打斷她。
「你不能、不能這樣……都拿走了,日後慧兒他們怎麼辦?」梁氏扯著他的衣袖,語無倫次地道。想了想又有些不甘心,大聲道:「若不是你無能,我一個婦道人家何須想法子賺錢!」
靖安伯陡然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盯著她,半晌,才慘然道:「是,全是我的錯,是我無能,讓妳一個婦道人家不得不想法子偷取親妹子的嫁妝錢,更讓妳一個婦道人家不得不昧著良心賺些傷天害理之錢。」想了想,又是一陣心灰意冷。「如此無能的我,想來也無顏再留住妳了,咱們便和離吧!從此以後,妳走妳的陽關道,我行我的獨木橋,再不相干。」說完,重重地朝著沈太夫人叩了幾個響頭。「母親,孩兒不孝,孩兒無能,只怕要讓靖安伯府蒙羞了。」
沈太夫人眼眶微濕,只連道了幾個「好」,卻是一句話也說不出。
沈昕顏再也按捺不住,猛地跨出一步,重重地抽了梁氏一記耳光。「妳簡直、簡直是豈有此理!」
梁氏在說出那番「無能」的話時也後悔了,男人都是要面子的,被她當面這般罵無能,只怕這夫妻情分便算是斷了。和離雖然比休棄好聽些許,但又有何分別?離了靖安伯府,她還有什麼?
「伯爺,是我錯了,是我錯了,求求你再給我一次機會!我不要和離,不要和離……」眼看著靖安伯已經在書案上提筆,她方寸大亂,撲過去摟著他的腿苦苦哀求。
早被她傷透了心的靖安伯絲毫不理她,下筆穩健。
梁氏見狀更怕了,知道這回這個老實到近乎木訥的夫君只怕是來真的,當下起身奪過他的筆用力擲到地上,語無倫次地道:「你不能、不能這樣,不能這樣……」
靖安伯不理她,從筆架上重新抽取一枝毫筆,蘸了墨又要寫。
梁氏再度奪過扔在地上,生怕他再去取筆,乾脆便將筆架推倒,把墨硯打翻,好好的書案頓時就一片凌亂。
「不要不要!伯爺,我真的知道錯了!嫁妝、嫁妝都抵給妹妹!印子錢、印子錢我也收回來,從此之後洗心革面,再也不會碰了!妹妹,妹妹,我知道妳心腸一向就軟,大嫂求求妳幫我勸勸妳大哥吧!母親!母親,兒媳真的知錯了,求您看在幾個孩子的分上,便饒了我這回吧!求求您了……」
梁氏瘋了一般在沈昕顏及沈太夫人跟前又是哭求、又是下跪,絲毫不見往日的雍容體面。
沈昕顏咬著唇瓣,心裡對她恨得要死,卻再說不出什麼狠話來。
梁氏千錯萬錯,可待子女的一片慈心卻是真真切切的。
只是,休棄也好,和離也罷,卻不是她可以作主的。她的兄長性子一向寬厚,可一旦觸及了他的底線,就是八頭牛也拉不回來。
如今他鐵了心要和離,別說她,怕是連母親也未必勸得住。
梁氏作為他的枕邊人,想來也清楚他的性子,否則不會哭得這般絕望。
「爹爹,不要趕娘親走!慧兒求求您不要趕娘親走!」房門突然被人從外頭撞開,下一刻,一個小小的身影便如同炮彈一般衝了進來,一下子就撲到靖安伯處,摟著他的腿放聲大哭。
「都是怎麼侍候的?怎的讓姑娘闖了進來!」沈太夫人見孫女衝了進來,勃然大怒。
緊跟在沈慧然身後侍候的丫頭嚇得一個激靈。
「還不把姑娘帶下去!」沈太夫人見狀更怒了,喝斥道。
那丫頭連忙上前將沈慧然從靖安伯身上扒了下來,半哄半抱地便要將她弄出去,哪知小姑娘掙扎得太厲害,她老半天抱不起來,一個沒用力,沈慧然便掙脫她撲到了沈昕顏跟前。
「姑姑,求求您幫慧兒勸勸爹爹不要趕娘親走……」
看著姪女哭得上氣不接下氣,沈昕顏嘆息一聲,正想要說什麼,那廂的梁氏已經撲了過來,摟著女兒放聲大哭。
一時之間,偌大的屋裡便只響著這母女二人撕心裂肺的哭聲。
也不知過了多久,沈太夫人才長長地嘆了口氣,問木然站在一旁的兒子。「你確定還想要和離嗎?哪怕將來慧姊兒會因為有這麼一個和離的娘親而受人指點,峰哥兒兄弟日後也會抬不起頭做人?」
靖安伯的臉終於出現了裂痕。
沈昕顏知道,兄長最終還是心軟了。她也說不清是鬆了口氣,還是有些失望。但可以肯定的是,日後梁氏便要漸漸隱於府內,再不能掌一府事宜。
「是,孩兒還是確定要和離!」
斬釘截鐵的話響起時,沈昕顏陡然瞪大眼睛望向有些陌生的兄長。
靖安伯痛苦地合上雙眸。
若妻子僅是偷取了妹妹的嫁妝錢倒也好說,他便是砸鍋賣鐵也會想法子將這錢還上,可她偏偏還不知死活地去放印子錢,那些黑心錢是能賺的嗎?長達數年,積累的金額足以徹底毀掉靖安伯府!
伯府不是他一個人的,他不能因為自己這一房犯的錯而連累其他兄弟。
可一切歸根到底,還是他沒用,沒能給妻子富貴榮華,以致讓她一個婦道人家走上了歪路。
「妳放心,和離之後,這輩子我也不會再續娶,我會好生撫養峰哥兒兄妹幾個長大成人,絕不會讓人欺辱他們。至於妳的嫁妝……妳便帶走吧,有了這些錢物傍身,妳若是安安分分,下半輩子也能夠衣食無憂了。」
梁氏的哭聲早在他說出「確定和離」時就停了下來,努力睜大矇矓的淚眼想要看清眼前的男人。
「你怎能如此狠心?你怎能如此狠心!我們這麼多年的夫妻,你怎能如此狠心!」她不知道還可以說些什麼讓這個男人改變主意,只知道此時此刻,她真的後悔了。
「爹爹,不要、不要……」沈慧然年紀雖小,可也看得清爹爹鐵了心要趕娘親走,頓時又急又怕,嚎啕大哭起來。
「還不將姑娘抱下去!」靖安伯雙眸通紅,不敢去看女兒,厲聲朝著手足無措的侍女斥道。
那侍女再不敢耽擱,使出吃奶的力氣硬是將小姑娘給抱了下去。
女兒的哭聲被隔絕在門外,梁氏終於徹底絕望了。
*欲知精采後續,敬請期待11/27上市的【文創風】694《誰說世子紈袴啊》2。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誰說世子紈袴啊(2)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誰說世子紈袴啊(2)
一邊是讓她在眾人面前抬不起頭、丟臉的夫君,
一邊則是頻頻替她爭氣、給她長臉的優秀兒子,
想當然,她的重心便越發向兒子傾斜,將之當成唯一的依靠……
上輩子身為英國公太夫人,沈昕顏本該過著人人欣羨、敬重的生活,
然而因為與媳婦不合,她竟落了個在家廟瘋癲而亡的淒涼下場,
雖然心中有怨,但所謂人死如燈滅,死都死了,為何又讓她重生啊?
望著銅鏡中那張年輕了十幾歲的臉,她頓時有些懵了,
前一世的苦太過痛徹心扉,她根本不想再經歷一回呀!
無奈上天偏要讓她重來,既如此,那她決定這輩子好好為自己而活,
她學會了放手,不再將視線鎖在兒子身上,竭力阻止前世的悲劇重演,
甚至,她還與人合作起溫泉莊子的生意,日子過得有聲有色的,
女人啊,身上果然還是要有錢才有底氣,這話真真說得沒錯!
漸漸地,她發現許多從前錯過的美好,譬如……她那個「平庸」的夫君。
本書特色
暮月/兩情若是久長時 又豈在朝朝暮暮
他是京城中有名的紈袴世子,一輩子一事無成,
她嫁得不甘不願,自然也沒在他身上多花心思,
可是,就是這個男人,無論她犯了什麼錯,始終都維護著她,
臨死前她想的最多的不是她又愛又怨又恨的兒子,而是他……
作者簡介:
暮月,懶洋洋的書蟲子,愛啃書、愛宅,喜歡天馬行空、胡編亂造,不甜不寵不爽「三不」且不入流作者,碼字全是為愛發電,堅持認真對待筆下每一個角色,最享受完結每一部作品的那一刻。
TOP
章節試閱
第十一章
隔得數日,魏雋航忽又想起妻子嫁妝鋪子一事,遂召來心腹侍從一問,知道夫人已經著人將那錢掌櫃送進了衙門,他托著下巴想了想,又吩咐道:「想個法子,讓那錢掌櫃的嘴巴放乾淨些,我不希望從他口中說出什麼有礙伯府名聲之話來。」靖安伯府名聲不好,夫人必會不高興,夫人不高興了,他心裡也就不痛快。既如此,那便得從根子上斷絕了這個可能。
那人領命而去。
魏雋航拍拍衣袍,本想到正房裡尋夫人說說話,忽地想起今日夫人回了伯府,腳步一拐,便轉向了習武場。
這個時候,霖哥兒和蘊福應該都在習武場練習才是。
果不其然,離...
隔得數日,魏雋航忽又想起妻子嫁妝鋪子一事,遂召來心腹侍從一問,知道夫人已經著人將那錢掌櫃送進了衙門,他托著下巴想了想,又吩咐道:「想個法子,讓那錢掌櫃的嘴巴放乾淨些,我不希望從他口中說出什麼有礙伯府名聲之話來。」靖安伯府名聲不好,夫人必會不高興,夫人不高興了,他心裡也就不痛快。既如此,那便得從根子上斷絕了這個可能。
那人領命而去。
魏雋航拍拍衣袍,本想到正房裡尋夫人說說話,忽地想起今日夫人回了伯府,腳步一拐,便轉向了習武場。
這個時候,霖哥兒和蘊福應該都在習武場練習才是。
果不其然,離...
»看全部
TOP
目錄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暮月
- 出版社: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11-30 ISBN/ISSN:978986328935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開數:正25開【14.8*21公分】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