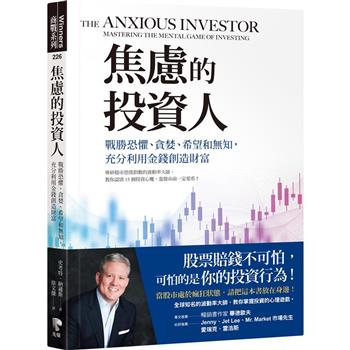VOCALOAD名曲改編
囚人與紙飛行機 三部曲系列故事完結篇
『囚人』、『紙飛行機』是?
「只要有妳在,無論何種謊言……」、「只要有你在,我就有活下去的意義……」。透過柵欄相戀的囚人和少女戀愛故事為主題的樂曲。猫ロ眠@囚人P於2008年投稿、描寫囚人視角的『囚人』,和2009年投稿、描寫少女視角的『紙飛行機』被稱為「鏡音三大悲劇」之一。故事性豐富的這兩首樂曲,在NICONICO等網站廣受歡迎。另外描寫同一世界前後的故事,以「囚人前後史曲系列」為題的動畫,第一節「英雄」和第二節「明日」也已經投稿上傳。
http://www.nicovideo.jp/watch/sm5117285
【主要登場人物】
希耶.卡露拉
史帝佩德醫院院長。以「人畜無賴(No Pain)」外號聞名的「帝國四大狂種」之一,擁有世界第一的醫術。
莉亞.凱洛
史帝佩德醫院六樓主任,也是《黃泉回歸之書》其中一頁、專治「不治之症」的醫生,同時為少女「露莉」的主治醫生。
梅嘉.法洛斯
收押在史帝佩德監獄的囚犯,擁有「天災兒」的能力。凡是有答案的問題,她都能解開,因此被視為危險人物關進監獄隔離。
凱姆拉爾.弗拉古
史帝佩德監獄副典獄長。非常溺愛妹妹(少女),以狂軍師「無表亦無?(No Side)」外號廣為全國所知。
米露卡.奇賽朵
史帝佩德監獄副典獄長。曾隸屬被譽為最強的「帝國戒騎士」,外號最狂戰士「命運停止(Parallel World)」,是監獄中武力最強的人。
哈魯.巴克
皇帝亞盧斯特意隱瞞的親生兒子,被派到史帝佩德醫院當實習醫生。目前正在莉亞.凱洛底下學習。其幼稚又自由奔放的個性讓莉亞傷透腦筋。
作者簡介:
猫ロ眠@囚人P
使用VOCALOID進行創作的作曲人,2008年以『逃獄』投稿NICONICO動畫,出道。之後也投稿了第二作『囚人』。2009年以另一個『囚人』為題投稿了『紙飛行機』,包含『囚人前後史曲系列』在內的相關樂曲廣受歡迎。另外也投稿了以『終末史曲系列』為題的第一章『新世紀』、第二章『理想鄉』以及第三章『一縷願望』。2012年以《囚人與紙飛行機 少年悖論》出道成為小說家,同時遊戲專案「災禍之夢」也在進行中。2012年7月成功以CLΦSH(96猫×囚人P)的名義,成功出道成為音樂家。2012年11月,執筆撰寫第2本小說《囚人與紙飛行機 少女難題》。2013年以CLΦSH之名進行新企劃,推出附CD的小說《FINALΦFICTION前奏曲》,以及包含廣播劇CD的書籍套組《FINALΦFICTION 喜歌劇》。
章節試閱
第1章 正命題
前言 莉亞「生而瘋狂的醫生①」
[一]
──我和他的相遇,是在我「平凡無奇日常生活的一頁」中突然降臨的。
那是我二十一歲那年,尚未到史帝佩德醫療研究所任職,還不是個稱職醫生時所發生的事。當天那件事,也成為我略為觸及醫生本質的契機。
若要講述我的人生,到底該從哪裡開始說起才好呢?思考過後,我想最好從和他相遇的那天開始。
和他相遇,這種說法或許有點偏離核心。
正確來說是偶遇才對。那天,我偶然碰上了「絕對惡」。
要講述我的人生卻不提及那天的事,就像討厭起司卻走進以起司料理餐廳一樣莽撞(這是我使出渾身解數想出的笑話)。
在那之前的人生,不過是個一介小姑娘的日常物語,連描述價值都沒有的無聊過場。對了,我想序幕是最貼切的形容詞吧。
既然偶然碰上他改變了……不,是他改變了我平凡無奇的日常生活,就算你們不奢求壯觀的場面,多少也期待看到戲劇性的情節吧。可惜的是,我無法回應你們的期待。畢竟那個機會,是毫無前兆突然降臨。
這種太過湊巧又不自然的偶遇,算是小說中的三流情節,連小孩子都高興不起來的彆腳發展吧。
但我經常在想,說到底現實就是這種東西。
世人常說「現實比小說還離奇」,我卻覺得要是小說比現實荒謬那還得了。小說終歸是讀物,只會發生能成為伏筆的事,主角也大多會得到幸福,更會提供讀者能接受的解釋。換言之,就是種有條理、公平且合理的娛樂。
現實卻不是如此。沒有回收便消失無蹤的伏筆多不勝數,努力過後可能完全得不到回報,也可能輕易獲得成功,更不會提供當事者半點解釋,是種沒條理、不公平也不合理的扭曲娛樂。
當然也不會有故事高潮。
沒人能保證這次偶遇會是往後的伏筆,也沒有證據能證明這次的偶遇中帶有伏筆。若問我是否因此得到幸福,我也無法回答。說到底,這次偶遇究竟該不該發生的問答本身就不存在。
世界就是矛盾和不可能命題的連鎖,絕對不具有能和大眾小說比肩的合理性。
不過,只有一件事我能確定。和他的偶遇、邂逅──就是改變我人生的瞬間。
那是在我「總是對人生絕望,喪失生存的目標甚至考慮尋死的時候」。
狹窄房間充滿宛如黏在肌膚上的濕氣,被令人窒息的寂靜所支配。冷冰冰的電子音微微震動空氣,彷彿無法忍受現場的寂靜。
房間中有五個人。
一個人躺在床上閉著雙眼一動也不動,另外四人則圍在她身邊站著。床上那人和她的兩位家屬,以及兩位非親非故的人,共計五人。
不、只剩下四個人了。
「上午2點19分,宣告患者死亡。」
明明是自己說出的話,那過於冷靜的音調卻令我差點苦笑出來。我拚了命才忍著沒笑出來。
「還、還沒……她還沒有死……」
年約三十五歲的男性家屬說著,用失焦雙眼來回看向我和床上的遺體。我早就習慣這種眼神,也早就看膩了。
「什、什麼宣告死亡……不要說廢話了,快點治好她啊……」
「這不是廢話,你的夫人已經過世了。」
「妳……妳不是醫生嗎?」
男人顫抖的手粗暴抓住我的前襟。我沒有抵抗,只是任由他把我扯過去。
看來這個男人,似乎誤以為醫生是神明之類的東西了。
「明明才正要開始啊……米奇要怎麼辦才好……他才五歲耶!?妳到底明不明白!?這孩子還需要母親啊……」
「對此我深表同情。」
「我才不想聽這種話!給我盡全力救她啊!拜託妳,好不好……算我求妳……」
「已經逝去的生命,是無法治療的。」
我只是冷淡地、機械般地回答他的問題。話中不帶任何感情,也用態度宣告沒有參雜感情的必要。
「我的任務已經結束了。」
男人瞪我的眼神猶如看到什麼髒東西般不屑,好像我是某種骯髒卑鄙,光碰到就渾身不愉快的生物。
「……可惡!」
胸口傳來一陣衝擊,令我跌坐在地。看來是男人狠狠推了我一把。在場的護士想過來攙扶,我卻用眼神示意她不要靠近。
男人趴到再也不會動的妻子遺體上一個勁地哭喊。那不在乎外人眼光的模樣,在在讓我明白他有多麼深愛妻子。
不過,這和他有多愛妻子毫無關係。
他的妻子──已經死了。
我屏氣吞聲怕打擾到男人,和護士靜靜離開房間。只有遺體和死者家屬的房間之中,沒有醫生存在的必要。
喀啦啦啦,我關上房門。
「啊哈哈……」
然後──
「……我又殺人了。」
──像是斷了線的木偶般跌坐在地。
「醫、醫生!?」
和我一起走出房間的護士嚇了一跳,伸手想要扶我起來,卻被我全力揮開。
不知是察覺到了什麼還是基於同情,又或者是顧慮到我的感受,她就這樣默默地離開現場。
不對,正確來說,她是為了我而離開。
「啊哈哈哈……哈哈……」
──我又什麼都沒做到。
說什麼病人宣告死亡,說什麼已經死了。
不要自欺欺人了。是妳殺的,是妳親手殺了那個女人,是妳──殺了那個男人深愛的女人。
「哈哈……嗚嗚……」
妳算什麼「天才少女」,算什麼不治之症的專家啊。明明沒救過眼前的任何一個人,只是對他們見死不救,到底有什麼臉自稱天才啊?噁心、噁心死了!
「嗚……嗚嗚嗚……」
患者的生命齒輪出了問題,但我卻從齒輪開始無法咬合到最後一刻,都沒能為他們做什麼。不管我再怎麼掙扎,仍舊無法阻止他們的生命自我手中滑落。
我無能為力,對他們見死不救。
「可惡……可惡可惡可惡可惡啊!」
敲打地板的鈍重聲音,在深夜中的醫院昏暗走廊迴盪著。
結果我根本沒有改變。
從那天開始就完全沒進步。
給予別人「我一定會治好」的希望,再將他們推落「人死不能復生」的絕望深淵。一路走來的我,只是不斷重複這項作業罷了。
先給他們希望再奪走,這種行徑實在太卑鄙太陰險,根本是邪門歪道。
是打著「我會救你」的旗幟,光明正大玩弄人命的詐欺師。
我到底在幹嘛呢?
明明是為了拯救人命,想盡可能守護他人的笑容才立志成為醫生。如今卻為了摧毀別人的笑容,過著辛勤工作的每一天。
先破壞,再奪走而後解開,最後殺死。
明明是將渺小理想與無聊理念強壓在別人身上,骯髒地活到今天,卻仍舊相信有能拯救的生命,相信患者總有一天會得救,相信有人會對自己微笑。
我就是抱著這種想法,才能撐過艱辛的學習和痛苦的修練,克服所有障礙,比誰都努力地救人。這種話由自己來說有點奇怪,但是,我真的很努力了。
下次一定、下次一定要守住這個人的笑容,所以再努力一次吧,莉亞。我就是這麼欺騙自己,走到現在這一步。
明明是這樣的。
「對不起……我好像……已經不行了……」
但我好像撐不下去了,眼眶湧出的淚水滑過臉頰。
現在這雙手中,除了骯髒又醜陋的自己之外什麼也沒有。
「我到底是為了什麼……才活到現在的?」
啊啊,我應該早點注意到才對。
我一直在研究,想知道到底什麼不好、到底什麼不行、到底哪裡有問題,現在我終於得出答案了。
只要看到那男人看著我的眼神──彷彿在看殺人犯的眼神,即可輕易明白。
一旦說出現在浮現在心底的答案,一切就會結束。
這種行為,如同從脆弱又危險的鋼絲上摔落,會將數十年來,好不容易才讓我成為我的某種東西破壞殆盡。
那句自我矛盾的話,會讓一切畫下句點,永遠無法復原。
可是──或許我就是想要結束一切。
我一定是想看到終結。
「我才是……一切的罪魁禍首。」
如今,一切都結束了。
但我也因此得知──結束即是一切的開始。
「妳說得沒錯。」
突然,頭上有道彷彿在腦中溫柔攪拌的聲音傳來。
「……咦!?」
我被那道不像人類的神祕聲音嚇到,不禁抬起被眼淚糊得亂七八糟的臉往上看。
隨即看見──一個奇妙的人類。
人類。從外表只能得知這點情報的存在,就站在我眼前。但我甚至連他的性別都無法判斷。他的聲音明顯是個男性,身上那件露出大片肌膚的白衣縫隙中,卻可以看到女性特有的胸型和曲線,就算綜合醫學的觀點來看──也無法得知他確切的性別。這名男聲女身的人類,有著令人不舒服的稚嫩長相,黯淡的綠髮底下有對紅綠異瞳,頭上還別著海蟑螂當髮飾,散發出既奇妙又怪異的氣質。
──我忍不住因為他的「不尋常」而縮起身子。
宛如硬把不同的拼圖碎片拼在一起,強行鑲嵌成人形的異樣存在。
仔細一看,才發現他身邊還有一個人。
剛才目光都被那個奇妙的人吸引而沒注意。他身邊還有個相較之下,散發出正常人類氣息的女性。她一頭紅髮梳理得整整齊齊,穿著形似秘書的服裝看起來相當嚴肅。她雖然有著軟綿綿的女性氣息,卻也有著不輸男性的銳利視線,莫名討人喜歡。
奇妙的人類,以及隨侍在他身邊形似秘書的女性。
他和秘書以俯視我的姿態站著。
「妳是『惡』,還是無可動搖的『劣惡』。」
他對我這麼說。
他那遠離現實的空虛聲音在我腦中迴響,令我有種錯覺,好像他只是對嘴,實際上聲音來自別的地方。他果然有著男性的聲音,而且還是深具說服力的澄澈美聲。
只是聽他說話,心跳就不由自主地加速。
「那、那個……」
「少用蟲鳴蓋過我的話,益蟲。不──妳已經是害蟲了。」
清晰明亮,彷彿在耳邊呢喃似的奇妙聲音打斷我的話。
我八成正被人破口大罵吧。換作平常的我,聽到他第一句話時就會動怒,狠狠揪住他的前襟。
可是現在卻不一樣。
對於心靈崩潰的我來說,聽到他的漫罵不但不感到憤怒,甚至還被他的部分話語打動。
如同不協和音,又如同泛音共鳴。
至於原因──我不知道。
「讓開,『劣惡』。那裡是我要走的路──也是妳無法掌握的未知。」
「什麼?哇啊……呀啊!」
話一說完,他就強行推開我,朝病房的門伸手;他想打開我剛離開不久、目前仍不允許任何人靠近的病房大門。
「等等,喂!不可以!」
「無聊。」
他毫不理會我的制止,喀啦啦地用力推開大門。一雙眼睛哭到紅腫不堪的丈夫隨即憤怒地看過來。
但是沒多久,他的眼神從憤怒轉變為驚愕。
因為走進病房那人的樣貌宛如異形。
「可以離開『那東西』身邊嗎?無關人士。」
他的一句話,令病房本來就很緊張的氣氛更加緊繃。
不只死者家屬,連我也被他難以置信的發言嚇得說不出半句話。
他剛才稱呼大體為「那東西」,稱呼死者家屬為──無關人士對吧?現場最適合被稱為無關人士的,明明是他才對。
丈夫當然沒有聽從他的話離開死者身邊,不,應該說他驚訝到無從反應。
「愛爾比。」
似乎是等得不耐煩了,那人冷冷看著動也不動的丈夫數秒,出聲叫喚站在他後方的女秘書。
「是。」
「我允許妳──驅除障礙。」
「遵命。」
名喚愛爾比的女性語氣平板地回答,以流暢的動作自口袋中取出手術用橡膠手套,並熟練地戴上。
那對銳利的雙眼輕輕一動。
「妳……妳要做什麼……」
驚魂未定的丈夫勉強擠出聲音發問。
但是愛爾比卻完全不於理會,徑直地走近他身邊──
「欸!?」
──掐著他的脖子,把人舉了起來。
「唔、唔咕……啊唔……」
「爸爸!」
看到這副光景,小孩忍不住大聲哭喊。
母親過世當下之所以沒哭,是因為他還沒理解發生了什麼事。倘若換作父親在自己面前被勒住脖子,他當然會受到驚嚇。
「爸爸!!」
「唔呃…………」
在孩子的喊叫中,被喚作爸爸的男人似乎斷了氣,雙手依循重力虛脫下垂。
「爸爸────!唔!」
愛爾比沒有把丈夫放下,就這麼直接朝小孩的頸部踢了一腳,令他失去意識──閉嘴不再說話。
「愛爾比,到此為止。」
「遵命。」
愛爾比聽到那人的吩咐,立刻鬆開雙手。
曾經身兼丈夫和父親二職的物體,就這麼伴隨鈍重聲響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
「怎麼……搞的……」
這時,我終於成功發出聲音。
要說是話語有點靠不住,若說是獨白又缺乏見解。不過是如同恐懼心引發的呢喃,猶如慘叫一般。
僅僅15秒的時間。
突發狀況和我無法理解的事卻接連發生。面對這過於偏離常軌的現實,我只能──狼狽看著一切。
「愛爾比,準備。」
「遵命。」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聽見我拚死發出的慘叫,只見他們開始進行某種準備。
「啊……啊啊……啊……」
怎麼搞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突然現身並闖進病房動用暴力。我根本搞不懂他們想做什麼、做了什麼,又正要做些什麼。我怎麼可能會知道呢。
那人走近方才男人趴在上頭哭泣的床鋪,毫不猶豫地掀開上頭的布。
有個再也不會張開眼睛的人類正躺在床上。
「這就叫死了?無聊。」
「您說得沒錯。」
「啊……啊啊……」
他們兩人完全無視我的存在,開始進行某種準備。
……等等。
……喂。
給我慢著!
「……你們兩個!!」
我叫了出來。
安靜得宛如有惡魔走過的病房中,只聽得到我慌亂的呼吸聲。
霎時,那人不帶有嫌麻煩的意思,也不含厭惡情緒的冰冷視線掃了過來。就像單純的反射動作。
他感覺不到任何感情的動作,讓我一時心生膽怯。
「女人,妳想幹嘛?」
居然還問我幹嘛?
那是我要說的話吧!
於是我擠出勇氣開口說:
「踐踏死者家屬,圍在屍體身邊……你們是蒼蠅不成!?」
「蒼蠅也不壞。」
他完全不在意我使出渾身解數的叱責,不只如此,我甚至從那張幾乎面無表情的稚嫩臉蛋上,感受到一絲喜悅。
「那、那個……這可是褻瀆死者的行為!你以為有人會允許你這麼做嗎!」
「下達許可的人──是我。」
「……咕。」
我又接著大叫了幾句,他還是沒有任何反應。反而是他帶著堅定信念的視線,撼動了我的心。
「雖然妳的發言偏離重點,但妳也抱持某種驕傲吧。不過,在場所有的東西,從頭到腳都是我的。連妳用遺體來形容的東西也不例外。」
「什……什麼……?」
「女人,我正冀望要擺弄『那東西』。」
說到「那東西」的同時,他朝遺體看了一眼。
「我就允許放棄擺弄的妳──在這裡觀賞到最後吧。」
他在說什麼?他在說什麼?他在說什麼啊?不行,真的差太多了。
我面前的這個人類,其價值觀及人性全都凌駕於我──不,是瘋狂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突然就冒出來……你們到底想幹嘛!這裡可是醫院喔!誰、誰會讓你們在這裡亂來……我現在就去叫憲兵……」
「女人,妳的氣勢不錯。我改變主意了,就允許妳──任意行動吧。」
「我真的會去叫憲兵喔……」
「愛爾比,繼續。」
「──不准動!」
看到他們無視我的制止,打算對遺體出手,我──對他們舉起手術刀。這並非經過深思熟慮的行動,而是處於亢奮狀態的大腦,在一瞬間對身體下達此命令。
可是沒過多久,我便親眼證實這個行為不具任何意義。
「……咦?」
一次。我不過眨了一次眼,手上的手術刀就消失不見──刺進天花板。
「咦?……咦?咦?」
我來回看向自己的手,以及天花板上的手術刀。
剛才發生了什麼事……?
「愛爾比,我不記得曾經允許妳採取行動。」
「真是非常抱歉,我願意接受任何懲罰。」
只見愛爾比半跪在那人面前,低頭這麼說。
意思是……她剛剛對我做了什麼嗎……?
什麼跟什麼,到底是在幹什麼啊!
「草履蟲,別把妳那愚劣至極的腦袋垂在我面前,真讓人不舒服。」
「真是非常抱歉。」
或許是我的錯覺,愛爾比好像很高興的樣子。那人冷冷瞥了愛爾比一眼,將視線掃向我。當下我感覺自己的心臟被緊緊揪住。
「女人,手術刀雖出自人手,卻是使人活命的道具,不是用來保護自己的東西。」
「唔……」
「──做好覺悟吧。」
「!?」
他的眼神突然變得銳利。
龐大的惡寒一口氣蹂躪整間病房。
「女人,妳剛才說過吧。」
「噫……」
──他朝我這裡踏出一步。
我的背後有什麼冰冷的東西竄過。
「患者的身體不好、死者家屬的運氣不好──」
「啊……啊……」
一步接著一步,我們之間的距離漸漸縮短。
我想逃離逐漸逼近的異形,企圖往後退卻無法動彈。
恐怖。
我好害怕好害怕,身體卻僵在原地,發軟的雙腳也無法移動半步。
「我才是一切的罪魁禍首。」
「不、不要過來……」
然後,他終於來到我面前。
「啊……唔……」
我因為過度恐懼而跌坐在地,再次被高個子異形俯視。
那雙冰冷異瞳俯視著我。
不要……住手啊,拜託你住手……
「女人,少自以為是了──」
說著他朝我伸出右手。
「噫……!」
那右手掠過我的臉──
「『惡』皆我之物。」
──溫柔地撫摸我的頭。
很溫柔、很溫柔地撫摸著。
「咦……?」
事情來得太過突然,我需要一點時間才能理解發生了什麼事。
他……這個異形般的人類,正在摸我的頭?我一時還以為他在我頭上塗了什麼奇怪的藥。
但實情並非如此,至少我很清楚這點。當那隻手碰到我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其中不帶任何敵意。
「不論身體狀況、健康狀況、治療法甚至疾病,這一切──全都不是『惡』,反而是善。別隨便把這些歸到『惡』的範疇裡來。」
他輕聲說完,便轉身再次朝遺體走去。
「自願沾染惡的覺悟本身──即是醫療。」
接著和遺體面對面。
「而我──即是醫療。」
他從幾乎沒有履行衣物機能的白衣口袋中,拿出橡膠手套迅速套上。
那副模樣,簡直──就像個醫生。
「啊啊……」
為什麼我沒有注意到呢?
仔細觀察不就會發現了嗎?
銘刻在那件白衣背後的紋章──
──是帝國最頂尖醫生的證明,外號「人畜無賴」,《黃泉回歸之書》持有者紋章。
拯救了最多人命者的稱號。
「『被形容為遺體的人類』,看來妳遇到的醫生不好。對沾染上惡感到猶豫不決的半吊子似乎遇上了瓶頸。妳就後悔,然後認清現實吧。在我路過這裡的當下──」
然後他──第一次笑了。
露出扭曲的笑容。
「──就代表妳的運氣很『善(好)』。」
後來,我親眼目睹世上最頂尖的醫療過程。
由「人畜無賴」執刀的手術,對我的衝擊實在太大了。
「女人,妳認為世上最像地獄的地方是哪裡?」
他雙手插在口袋中,靜靜凝視坐在地上的我。
──手術只花30分鐘就結束了。
他那不像人類的荒唐技法,以及看似毫無根據、超乎常理的技術狂舞令我震驚不已,只能掛著愚蠢的表情傻站在原地。
從結論說起──患者復活了。
我不僅受到莫大的衝擊,甚至懷疑天地反轉了。然而就某種意義上來說,的確是反轉了沒錯。
我本來以為死去的人類,居然復活了。
心電圖監視器發出聲音的那一刻,我因這難以置信的事實而淚流不止。
人若死而復生,等同於干涉不可逆轉的現象。
簡直就是奇蹟。
「……」
不對,這世上並沒有奇蹟,就像人類不會死而復生一樣。
沒錯,說到底,我只是被奇蹟一詞沖昏了頭,想要使用復活這種卑鄙的詞彙來模糊事實而已。不對,這才不是什麼奇蹟。是我捨棄的患者被他救回一命──僅此而已。
事實就是如此。
「……世上……最像地獄的地方?」
當手術結束,患者重新開始呼吸的同時,他彷彿對患者喪失興趣般,冷漠走出病房。正當他走過蹲在門口的我身旁時,突然停下腳步,問了我這個問題。
忽然聽到這莫名其妙的問題,我只能像鸚鵡般重複他說過的話。
「沒錯,就是『惡』集結的地。那麼是哪裡?戰爭?紛爭?革命?恐怖行動?不,若要稱人類屢次犯下大屠殺的地點為地獄,那還遠遠不夠格呢。」
他平淡地說著,好像沉醉於自己的話語之中,又像對世界發問。
而我只是聽著。
「最多人類死去的場所,才是世上最像地獄的地方,也就是──醫院。」
那對異瞳之中,閃著對於惡的完全沉醉與自戀之情。濕潤的瞳眸裡,倒映著我的樣貌。
「女人,有點自覺吧──妳委身於史上最惡劣的場所,將自己的心靈奉獻給史上最差勁的概念,這是無可動搖的事實。少對醫療和醫生抱有希望或妄想。拯救人命這種話全都是詭辯,只不過是偽善罷了。聽好,妳──是最差勁的。是無可救藥、陰險又惡劣的存在。」
我是陰險……又惡劣的存在。
為什麼他要對我說這種話呢?
「而我正是──『絕對惡』,是地獄的所有者,亦是醫療本身。」
撲通!我的心臟用力跳了一下。
為何我的心會跳得如此激烈?連這種時候都忍不住用醫學的角度思考,我對自己的不解風情感到不耐。
直接用言語表述的話,就是我現在非常感動。
包容我至今所有過錯還游刃有餘的那份理念、那份器量,還有──那個人,撼動了我的心。不,說我的心即將被他奪走也不為過。
「女人,妳說要拯救人命是吧?這種違反常理,比褻瀆人命更不人道的殘忍行為,不是惡人就無法做到。聽好──能拯救世界的,只有『惡』。」
「……」
能拯救世界的,是惡。
「那、那種事……」
「女人,給我聽好了。歸根究柢惡就是因子,經常互相推託,偶爾互相爭奪的稱號。正因為有某個存在成為惡的根據,『正義』才能潔淨地虛張聲勢。說到底,『正義』不過是將『惡』強加於某處的結果。」
並非正義存在,而是有名為惡的因子存在的理論。
也就是惡因子論。
「而身為醫療的我,會接受『正義』強加於某處的所有『惡』。」
就像打掃的時候,弄髒抹布就能讓地板變乾淨一樣。
這彷彿在聲明,把那條抹布和髒汙一起捨棄就是正義。
「實際來說,世界正被定義的『正義』所佔據,但不管哪個時代,能拯救世界的都只有『惡』──被稱為『惡的存在』,這是無可動搖的事實。」
喀擦喀擦,他頭髮上的蟲子配合這番話動來動去。
「自願沾染上惡的覺悟,才是醫療不可或缺的東西。不管是令人作嘔的倫理、令人厭煩的道德還是令人不快的人道,在我面前皆為平等空洞的聲響。」
「……」
「身體狀況『惡』化?『惡』運連連?機器的狀況『惡』劣?那不過是妳假扮正義所抱持的幻想。」
在旁人聽來,這番發言不過是謬論,但卻深深感動了當時的我。原因連我自己也不清楚。儘管那是一般人不會當真的理論,我還是像要依賴那不尋常的事物般,接納了他的理論。
況且,我實在不認為他說的話是錯的。
沒錯,他和我這種人不一樣,說的話合情合理。即便表達方式錯誤、想法扭曲,他也有無論如何都不會動搖的絕對信念。有著就結果而論,確實能拯救人命的絕對理想。
還有實際拯救了無數人的實績。
「高興吧,女人,妳被我看上了。既然妳靠自己抵達並敲響了真理的大門,我就招待妳進來吧。妳已經獲准成為《黃泉回歸之書》的一頁,並得到跟隨我的權利了。」
《黃泉回歸之書》──聽到這個名字,我的心便充滿無法言喻的興奮。對,這個名字是所有醫生的憧憬,君臨醫療頂點的集團名稱。雖以少數精銳組成,卻無人能掌握其全貌、時常走在現代醫療最前端的異形集會。被納入其中一頁代表什麼意思?獲准加入又是什麼意思?
事情嚴重了。
「可、可是……像我這種人……」
「女人,我應該說過要妳別自以為是。我說過,所有的『惡』在我面前,全是黯淡不清的道理,因為我才是惡的定義、惡的標準。」
這席話,在認定我是惡的前提下說出口,還像是擁抱般溫柔地接納了我。這令我品嚐到未曾有的悖德感、愉悅,以及──安心。
「女人,我這個『絕對惡』允許妳──做為我的手足,為我的理想犧牲奉獻。」
他說完便轉過身去。那飛揚的白衣彷彿在呼喚我跟上。
然後,我再次目睹他背後的紋章。
──帝國最頂尖醫師的證明,《黃泉回歸之書》持有者的紋章。
也是拯救了最多人命者的──榮譽與稱號。
啊啊,我一定是為了和這個人相遇,才會努力到今天。並非基於某種道理,也缺乏任何邏輯和倫理。此時的我,純粹是出於直覺、出於本能地如此覺得。他的身上,有讓我產生這般想法的東西。
他的存在即超乎常理,只有走在同一條路上的人才能理解他的領袖魅力──他擁有這種絕對的魅力。
沒有任何伏筆,也沒有任何預兆。我當下突如其來地發誓──
我這輩子──都要跟隨這個人。
第1章 正命題
前言 莉亞「生而瘋狂的醫生①」
[一]
──我和他的相遇,是在我「平凡無奇日常生活的一頁」中突然降臨的。
那是我二十一歲那年,尚未到史帝佩德醫療研究所任職,還不是個稱職醫生時所發生的事。當天那件事,也成為我略為觸及醫生本質的契機。
若要講述我的人生,到底該從哪裡開始說起才好呢?思考過後,我想最好從和他相遇的那天開始。
和他相遇,這種說法或許有點偏離核心。
正確來說是偶遇才對。那天,我偶然碰上了「絕對惡」。
要講述我的人生卻不提及那天的事,就像討厭起司卻走進以起司料理餐廳一樣莽撞(這是...
目錄
5 序章
15 第一章 正命題
101 第二章 反對正命題
163 第三章 二律背反「生與死」
5 序章
15 第一章 正命題
101 第二章 反對正命題
163 第三章 二律背反「生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