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書迷引頸期盼,英年早逝的天才科幻小說作家出道作
2015年10月劇場版隆重獻映
2015年10月劇場版隆重獻映
‧「2000年代SF BEST」第1名
‧「BEST SF 2007」第1名
‧第1屆PLAYBOY推理大獎
‧「SF Magazine創刊700號紀念2014ALL TIME BEST SF」長篇部門第5名
‧被譽為世界最頂尖的科幻作品,出版後掀起日本科幻文學界滔天巨浪
‧日本罕見的本格國際軍事謀略懸疑小說
‧宮部美幸、伊阪幸太郎給予極高評價的作家
‧百萬人氣恐怖片達人 LittleDiDi、中華科幻學會行銷長 千秋仁、推理作家 天地無限、百萬部落客 貝克喬、科幻小說家 洪凌、暢銷書籍《詭辯》作者 張渝歌、知名科幻作家 黃海、小說家 謝曉昀好評推薦。
911以後,面臨「對抗恐怖主義」的轉機。各個先進國家皆導入徹底的管理體制,肅清恐怖分子,落後國家則開始大量爆發內戰及大規模屠殺。而在各地莫名發生 的屠殺事件背後,有個謎樣的幕後黑手──約翰‧保羅,美國上尉克拉維斯‧薛帕德為了尋找他的蹤跡,因此趕赴悲慘的屠殺現場……。那個男人的目的為何?引發 大量屠殺的「虐殺器官」的真面目又是什麼?
【各界好評推薦】
殘酷的世界,黑暗的情節,華麗的詞藻,這是一部天才作家才寫得出的偉大作品。──百萬人氣恐怖片達人 LittleDiDi
黑暗科幻極致之作,文字衝擊腦內皮質猶如烙印般的深刻!──中華科幻學會行銷長 千秋仁
在第三世界製造動亂的屠殺之王、誓言維護世界和平的特戰菁英,聯手在近未來的亂世裡譜出史詩之作!超越常識的最終真相讓文明世界戰慄不已!──推理作家 天地無限
堪稱日本科幻史的「四大奇書」,美如詩的文字寄宿了最瘋狂的滅絕!──百萬部落客 貝克喬
它能不能持續穿越時代我不知道,但我確定伊藤計劃是個天才。──暢銷書籍《詭辯》作者 張渝歌
作者的文字魔力讓讀者有如觀賞一部限制級的特種部隊軍事暗殺行動電影;你不得不佩服這位日本作家對美國情報組織與歐洲、中亞民情的了解。
充滿詩意的文字,融入豐富的人文社會與近未來的科技道具和知識,討論了文學、哲學、電影、文化基因、痛覺遮蓋技術、人體ID、侵入鞘……主人公是一個具有豐饒思想的美國特工,小說的看點就在暗殺行動中提出了道德倫理、人文與未來科技的反思。──知名科幻作家 黃海
從"語言與其他進化論的演變一樣,是為了適應而演化的一種器官"以及"聲音與視覺不一樣,聲音可以直接繞過意義,觸及靈魂"──以此觀點所延伸成的《虐殺器官》。
這是部基底設定於戰爭,於動盪的渾沌中,穿插了最基本對人類的自由、良心、語言能力、價值觀、道德感的哲學與生存的反覆辯思;不僅是一部科幻或戰爭小說,更是在哲學與人性思維的構思上,以戰爭的殘酷包覆住原有的心性來激發出各式矛盾並存,並且兩者都接受的,讓人宛如置身在剃刀邊緣的驚悚與深刻。──小說家 謝曉昀
(按姓名筆畫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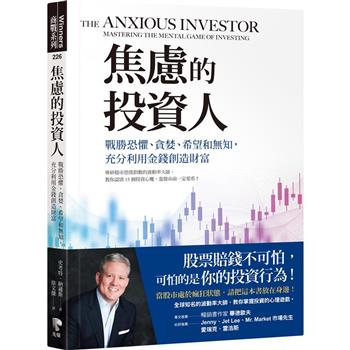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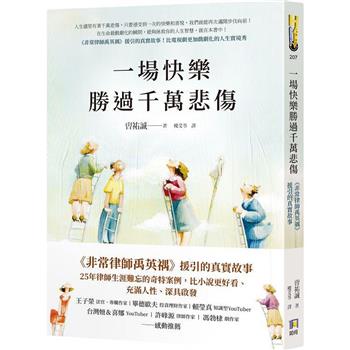








先說喜歡這部小說的點在於人性的寫實面與多重道德議題的思考面向,使其不僅止於描寫未來世界的高端技術,更著重於人在理性與感性之間的衝突。 雖然在一開始看到書名與動畫電影的預告時,就已有預感裡面的故事是脫離不了血腥暴力的情節,但在第一頁仍然被文字描述而映入眼簾的場景給驚訝到,沒想到作者會在一開始就直接用如此衝擊的畫面讓故事登場。在閱讀的整體過程中,既帶給我說不出的平靜,卻也同時有著難以言喻的沉重。原以為戰鬥的場面會佔故事篇幅的一半以上,但事實上,人物的對話內容,不論是與他人的談話還是主角內心的自白,才是彰顯整部小說在思維上具有相當深度的原因。儘管伊藤計劃已在2009年過世,但在接下來的國際發展中,似乎有部份確實是在應驗小說中的情節,例如ISIS的出現、北韓的核武試射、特定國家(近期像是委內瑞拉)的動盪不安、人民個資的安全疑慮等等。補充一點,雖然主角與故事內容主要都圍繞在美國與其他戰亂的國家,但在閱讀時,仍然覺得這是一位擁有美國人身軀的日本人在述說與觀察眼中的一切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