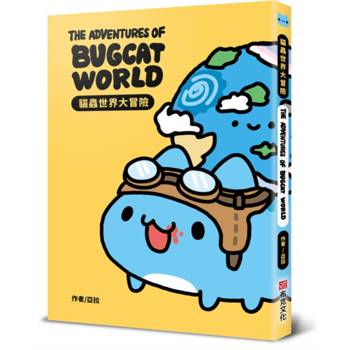天空的彼岸
那座山的後方到底有什麼?從我懂事的時候開始,就經常望著遠方的景色發呆,思考這件事。我出生的城鎮位在高山山谷間的盆地,我只能看到城鎮周圍像高牆般的山脈,和山脈上方的藍天。父母開了一家小麵包店,每天凌晨兩點起床做麵包,清晨六點到傍晚六點開店營業,完成隔天的準備工作,晚上九點上床睡覺,日復一日過著這樣的生活。麵包店的名字叫<薰衣草烘焙坊>,但我爸爸和媽媽從出生到現在都一直在這個城鎮生活,也從來不曾出門旅行,從來沒有看過北海道那片紫色的花好像地毯般的薰衣草田。向來不苟言笑的爸爸想要取一個好聽的店名,吸引城鎮上的太太來買麵包,於是就打開向鄰居「萬事通」借的植物事典,把聽起來不錯的外來語花名寫在廣告單的後面,讓媽媽從中挑選後決定的店名。但是,他們的意圖似乎發揮了作用,<薰衣草烘焙坊>很受左鄰右舍的歡迎,他們週末、假日都無法休息,每天都忙著做麵包,所以也沒空理會我這個獨生女,我總是怔怔地想像著山後方的世界打發時間。
也許山的後方也有一個像這裡一樣的城鎮,有一個和我同年紀、長相也一樣的女生,但她並不是麵包店的女兒,她爸爸是跑遠洋線的船員,每年只回家幾次,但每次都帶了從世界各地買的可愛人偶和漂亮的布送她,她媽媽很會做衣服,用爸爸買的漂亮布料為她縫製漂亮的洋裝。那個女生每天都穿著漂亮洋裝去學校上課,同學都羨慕不已,但其實她對穿這些衣服絲毫不感到高興,因為沒辦法和大家一起去河邊玩,或是去爬樹。她很希望盡情地玩耍,不必在意身上那些衣服,哪怕只有一天也好。某一天,她和媽媽一起去了鄰近城鎮的麵包店,遇見一個長得和自己一模一樣的女生──。
我曾經把這個幻想的故事告訴過一個同學。她叫小野道代,在小學六年級時,因為銀行員的父親工作的關係搬來這裡。以前就認識我的同學即使看到我在上課時,或是放學後呆呆地看著遠方,也早就司空見慣了,但道代覺得很奇妙。
「妳的腦袋裡都裝了什麼東西?」
她一臉好奇地問我,我雖然有點不好意思,但不希望她認為我弱智,所以就把前一刻在腦海中浮現的世界告訴了她。
「太有趣了!後來呢?」
聽到她拍著手這麼問,我也很傷腦筋,因為我的幻想都只是心血來潮,很少有完整的故事。我這麼告訴道代,道代說這樣太可惜了,建議我把幻想寫下來,寫成一個完整的故事。我覺得心血來潮想到的時候,針對想到的事思考才好玩,所以覺得她的提議有點麻煩,但還是敷衍地回答說:「是啊。」沒想到道代隔天送給我一本可愛花卉圖案的筆記本,我就不得不寫下來了。我總算完成了兩個長相相同的女生調換身分的故事,道代稱讚說,我寫得很好看,甚至還說我以後可以當作家。我一笑置之,覺得她太誇張了,因為這種鄉下麵包店的女兒怎麼可能成為作家?
「至少對我來說,妳已經是作家了。」
道代一臉嚴肅地斷言,建議我試著寫其他故事,而且她說想要看有發生命案的故事。雖然我知道世界上有推理小說,但從來沒看過。因為父母從來沒有幫我買過書,學校圖書室裡只有文學全集。我以前看的書中會有自殺或是殉情,卻從來不曾有過命案的情況。我對道代說,我不可能寫出自己從來沒看過的故事,道代借給我一本橫溝正史的《本陣殺人事件》,既然書名就有「殺人事件」,必定是可怕的故事。如果看了之後,晚上不敢去上廁所怎麼辦?我能夠看完這本大人書,不會中途放棄嗎?這些擔心顯然都是杞人憂天。父母早早就上床睡覺後,就是無聊的漫漫長夜,即使時鐘已經指向十二點多也毫無睡意,所以一個晚上就把那本書看完了。
一棟老房子的偏屋發生了命案。慘遭殺害的新郎和新娘的枕邊有一把傳家之寶的名琴,金色屏風上有奇妙的血跡。因為戶外積了厚厚的雪,所以命案現場是密室──。
簡直就像是在這個城鎮發生的故事。也許必須住在東京才能當作家,但故事發生的舞台可以在鄉下,而且,這樣反而會讓故事帶有獨特的氣氛。當我體會到這一點時,腦海中立刻浮現一棟老舊的房子,似乎聽到了住在那棟房子裡的三姊妹爽朗的笑聲。殺人的方式最好不要見血,所以要不要喝農藥?美女和農藥格格不如。那毒草呢?我去學校的圖書室調查了有毒的植物,創作了那個故事。筆記本上寫了十頁的內容,只是小孩子想出來的稚拙故事,甚至稱不上是短篇小說,但道代也發自內心地樂在其中。
「我直到最後都沒想到,原來不是在茶裡下毒,而是把毒塗在茶杯上。」
聽到她的感想,我忍不住自鳴得意,開始思考下次要用什麼方法殺人呢?故事要有讀者,才值得記錄成文字,在中學一年級結束時,道代搬走之後,我雖然仍然會幻想,但完全無意用文字的方式記錄那些幻想。之前寫故事的筆記本也送給了道代。道代說,希望筆記本可以借她把故事抄下來,以後隨時可以看,但我的故事都在腦海中,所以不再需要那本筆記本。道代送了我三本橫溝正史的書作為回禮。我覺得這份回禮太厚重了,想要只選一本,但道代說,比起在書店可以買到的書,這本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書更有價值,硬是把三本書都塞到我手上,並希望我繼續寫故事。
中學二年級時,我無法再埋頭故事的世界。因為麵包店負責收銀台工作的小松小姐結婚了,她必須每天在家送先生出門上班,所以我每天清晨六點到八點期間必須顧店。在去店裡之前,必須做好去學校的準備,所以每天凌晨五點就要起床,無法熬夜看完一本書。而且,我顧店的那兩個小時是最忙的時間,去上班、上學的人都會來店裡買麵包,我根本沒時間發呆。一次又一次重複把麵包裝進紙袋、在收銀機上算錢,收錢、找錢的作業,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其他同學都一臉神清氣爽地走在上學路上,我已經精疲力竭。上課時也無暇幻想,而是深深陷入夢境的世界。但是,我並不討厭顧店的工作,店裡的客人都是老主顧,所以可以觀察原來這個城鎮住了這些人,然後記住每個人喜歡的麵包,暗自為他們取了德國麵包爺爺、巧克力螺旋麵包太太之類的綽號,根據家庭主婦購買的麵包種類和數量,想像不同的家庭情況,有很多讓我樂在其中的要素。
火腿哥也是老主顧之一。他穿著附近很少看到的制服,每天清晨六點五十分走進店裡,買火腿三明治和火腿麵包,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暗中叫他「火腿哥」。他每天都買這兩種麵包,所以我幾乎不看他托盤上的麵包,就裝進紙袋,在收銀機上輸入價格。但是,在我剛上中學三年級的某一天,我像往常一樣,把紙袋和找零的錢交給火腿哥,當他離開很久之後,才想起在他來之前,火腿三明治就賣完了。因為附近一所中學的老師買了大量火腿三明治,說要請球隊的學生吃。火腿哥的盤子上的確有一個三明治,所以那應該是雞蛋三明治,比火腿三明治便宜三十圓,我找錯錢了。雖然原本打算等第二天早上時再還給他,但如果他發現多收了他的錢,氣得跑來店裡投訴,我就會被爸爸罵,還是趁今天把錢還給他,我決定去等他。
我向同學描述了火腿哥的制服特徵,同學告訴我說,那是鄰鎮京成高中的制服,我猜想他八成是搭長途巴士,所以從放學四點左右開始,就在離麵包店一百公尺外的巴士站等他。火腿哥從五點半抵達的長途巴士上走了下來。我跑上前去,把放在口袋裡的三十圓遞給他,他一臉訝異地看著我。因為我在收銀台時穿著白色工作服,頭上包著三角巾,所以他沒有認出我是麵包店的女生。在麵包店的時候,無論遇到任何客人,我都可以應付自如,但那時候我緊張得不知所措,結結巴巴地告訴他,我多錢了他的錢。
「只為了三十圓,妳就一直在這裡等我嗎?」
火腿哥似乎很驚訝,他也沒有發現我多收了他的錢。
「但我在看書,所以一下子就過去了。」
我拿出夾在腋下的書給他看。
「女生看推理小說,真難得啊,妳喜歡嗎?」
我點了點頭,他問我還有什麼事,我告訴他,只有以前的同學搬家前送我的三本書,火腿哥說,他有很多江戶川亂步的事,可以把他的書借給我看。因為他是麵包店的客人,而且是比我年長的男生,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向他借書。雖然猶豫了一下,但想要看更多推理小說的心情戰勝了一切。只要有時間,我就會一看再看道代送我的那三本書,但無法再度體會第一次閱讀時的震驚。我想要再度體會拍著大腿說:「原來是這麼回事!」,和「我就知道是這樣」,不禁莞爾的快感,於是向他鞠躬,拜託他借那些書給我看。火腿哥第一天清晨就帶了江戶川亂步的《孤島的鬼》給我,但因為收銀台前有很多人排隊,我無法好好向他道謝,所以每次還書給他時,我就在長途巴士站等他。因為火腿三明治和火腿麵包早就賣完了,所以我連同裝了卡士達麵包的紙袋一起交給他。他當場把麵包分成兩半,我們一起坐在長途巴士站的長椅上,一邊吃麵包,一邊聊書。隔天早上,火腿哥又帶了新的書來借我。
捨不得很快看完,想要細細體會故事意境的心情,和想要趕快看完,和火腿哥討論劇情的想法總是在內心天人交戰。有一次,我等在長途巴士站,結果五點半的那班長途巴士上不見火腿哥的身影。我早上才遇見他,隔天早上也會再看到他,但我就像錯失了相隔多年的重逢般失落。我坐在長椅上,茫然地望著遠方,想像著他不知道在幹什麼。時間在轉眼之間就過去了,六點半的那班長途巴士抵達,火腿哥走下車。我見到他時興奮不已,但他劈頭就斥責我,天已經黑了,一個人在這裡不是很危險嗎?我難過得哭了起來,他對我說,今天因為學生會有活動,所以才晚回家了,以後晚回家的日子會在早上告訴我。但如果在收銀台前對我說這些話,我的爸爸和媽媽就可能會知道我和他見面的事。於是,他提議會用暗號通知我。如果搭平時那班長途巴士回來,就買和平時一樣的麵包;如果會晚回家,就買別的麵包。
「忙得必須要晚回家的日子,不吃自己喜歡的麵包沒關係嗎?」
那是我最關心的事,我甚至想要為了他偷偷預留火腿三明治和火腿麵包。
「我媽也經常去買,妳家的每一種麵包都很好吃。」
我從來沒有像這一刻那麼為自己身為麵包店的女兒感到驕傲。我之前就曾經在店裡幫忙切乳酪,或是在土司麵包上塗奶油,我打算認真向爸爸學做麵包。
暑假快結束的某一天,我和火腿哥坐在長途巴士站的長椅上時,竟然也怔怔地看著遠方。雖然和火腿哥單獨在一起時很緊張,但有時候也會有完全相反的平靜心情,就像河底的石頭會隨著水流不時露出水面。不知道是因為他像雛人偶中模擬天皇、皇后的內裹樣一樣皮膚白淨,還是聲音平穩,說話彬彬有禮,即使我們從來沒有牽過手,即使我們之間保持了相當的距離,如果有熟人經過,也會以為只是兩個在等長途巴士的陌生人隨便聊幾句,但火腿哥身上散發出的平靜空氣包圍了我。
「妳有時候會像這樣凝望遠方,是可以看到什麼嗎?」
「山後方的世界。雖然我很想去,但沒辦法去,所以只能想像。」
「那妳可以去看看啊,要不要我帶妳去?」
火腿哥說,他就讀的高中就在山後方的那個城鎮,搭長途巴士不到一個小時就到了。我多年的夢想就這麼輕而易舉地實現了。星期天,我騙爸媽說要和同學一起去學校讀書,和火腿哥約在長途巴士站,一起搭上了長途巴士。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搭長途巴士。小學和中學的畢業旅行都曾經有機會去城鎮以外的地方看看,但我兩次都在前一天發高燒,只好含淚請假,所以我一直以為我受到了詛咒,無法離開這個城鎮,也因此覺得只能在幻想的世界離開這裡,沒想到長途巴士在城鎮的兩個巴士站停車載客後,就駛向郊區的山路。長途巴士在蜿蜒狹窄的山路行駛,我原本下定決心,要好好欣賞沿途的風景,但我沿途拼命忍著想要嘔吐的感覺,雙眼只能緊緊盯著握在腿上的雙手。我果然受到了詛咒,惡靈糾纏著我,不讓我離開這個城鎮。我的臉上冒著冷汗,膝蓋不停地顫抖,但可能在深山山區沒有設站,巴士始終沒有停靠。正當我覺得胃裡的東西湧到喉嚨,想要大聲叫喊:「讓我下車」時,火腿哥的手臂伸到我面前,為我打開了窗戶。涼爽的空氣吹進車內,我終於稍微舒服了一些。
「妳可以睡一下,到站時我會叫妳。」
我得知火腿哥察覺我想要嘔吐,覺得很丟臉,但還是乖乖閉上了眼睛。當我靠在椅背上,覺得腦袋變輕了,意識和詛咒都立刻消失了。
我們在電車車站前的巴士站下了車,火腿哥去車站商店買了汽水給我,說暈車時喝這個會比較舒服,我們一起坐在商店旁的長椅上喝汽水。我第一次知道有暈車這種症狀。這時,列車駛進車站。這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列車。雖然我狼狽不堪地從山後方的城鎮來到這裡,但我發現這裡只是比我住的城鎮稍微大一點而已,並不是大城市,城鎮周圍還是被山脈包圍。我問火腿哥,越過那座山,是更熱鬧的城鎮嗎?他告訴我,那個城鎮和我們住的城鎮差不多,眼前這個城鎮是這一帶最大,如果想去大城市,就必須從這裡搭很長時間的列車。
「我想我應該一輩子都會住在那個城鎮,即使離開那裡,最多也只是來到這個城鎮而已。」
「這裡幾乎可以買到所有的東西,如果妳想要買什麼,可以告訴我。」
我再度想到火腿哥每天都要往返這麼長的距離,我問他需要花這麼長時間通學的學校是怎樣的地方,他立刻帶我去參觀了京成高中。現代化的穩重紅磚校舍,似乎已經象徵了這裡是優秀學生聚集的地方。假日也有社團來校活動,校舍內傳來吹奏樂演奏的聲音,棒球隊在校舍後方的操場上練習。
「火腿哥,你在優秀的學生聚集的學校當學生會幹部,代表你很優秀。」
「剛好相反,因為我不太優秀,所以其他同學都把雜務推給我。妳剛才說火腿哥,是我的名字嗎?」
慘了。那只是我暗中叫他的名字,但因為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所以不叫他火腿哥,也不知道要怎麼稱呼他。他都直接叫我「妹妹」,我總不能叫他「哥哥」。
「……對不起。」
「沒關係,我很喜歡火腿哥這個名字。是不是把公一郎的公拆成兩個片假名時,剛好和火腿的發音相同?」
火腿哥笑著說道。我這才知道原來他的名字叫公一郎,但不好意思告訴是來自他常買的火腿三明治和火腿麵包,只能默默點著頭。火腿哥也帶我去參觀的校舍,教室內窗明几淨,走廊的牆上掛著學生的油畫作品。我對他說,很羨慕他每天可以在這種地方上學,他說我也可以報考這所學校。
「妳很喜歡看書,這裡剛好有文藝社。」
我也第一次知道還有文藝社這樣的社團。我問他,文藝社的活動內容是什麼,他告訴我說,社團活動時,成員會朗讀書籍,然後討論感想,也會自己寫詩和小說。我很驚訝在這種鄉下地方,除了我以外,還有其他人寫小說,而且還成為社團活動,更希望自己也能夠加入。
「但是,我不可能啦。我可能沒辦法每天都要搭巴士上學,而且我也沒那麼聰明,今天你能帶我來參觀,就已經太幸福了。」
火腿哥並沒有繼續推薦我報考京成高中,在學生會辦公室前,遇見了他的同班同學,那個同學調侃地問:「這個女生是誰啊?」火腿哥面不改色地說:「帶親戚的孩子來學校參觀一下,因為她現在讀中學三年級。」我忍不住有點失望。聽到那個同學對火腿哥說,你現在哪有閒工夫帶別人參觀學校?我才知道火腿哥是高三學生,也才發現在巴士站聽我說閱讀感想,以及在假日出遠門,都造成了他的困擾。
離開學校後,火腿哥帶我去了書店。剛好看到橫溝正史又推出了新作品,還看到有一大片都是江戶川亂步的作品,簡直是一個讓人陶醉的空間。書店裡有多少書,我就有多驚訝,但因為我瞞著父母出門,所以身上只帶了平時省吃儉用存下的零用錢,只買了橫溝正史的新作品,和一位叫松木流星的作家所寫的《霧夜殺人事件》。雖然是第一次看這位作家的作品,但書名有「殺人事件」幾個字,就令人充滿期待。火腿哥買了兩本江戶川亂步的書,但我忍不住為他擔心,他不是要準備考大學嗎?有空看小說嗎?
走出書店後,他又帶我去了文具店。我讀的那所中學對面也有一家文具店,但只是一坪多大的空間內陳列了基本的文具而已,這家文具店的空間足足有那裡的十倍大,而且商品也很豐富,有漂亮的鋼筆,還有皮革封面的筆記本,很多都是我從來沒有看過的精美文具。我買了信紙和信封,有的有可愛插圖,還有四周畫了爬蔓薔薇的進口信紙,每一款都很吸引我。和剛才在書店時一樣,我也東挑西選了很久,在徵求火腿哥的意見後,才終於決定。我必須在傍晚之前回家,所以就離開文具店去巴士站。火腿哥問我要寫信給誰,我告訴他,要寫給已經搬離這裡的同學,並把小野道代的事告訴了他,但省略了寫小說的事。那時候我和道代持續通信聯繫,差不多每個月寫一封。
「道代目前人在東京,你以後也要考東京的大學嗎?」
「我打算報考幾所學校,但我最想去讀北海道大學。」
北海道比東京更遠,我只知道是北方很寒冷的地方。
「對了,妳家和北海道有什麼淵源嗎?」
我很納悶,他為什麼問這個問題,但很快就想到是因為店名<薰衣草烘焙坊>的關係。
「非但沒有任何淵源,我爸媽和我甚至沒去過北海道。當初只是喜歡薰衣草這幾個字的語感,所以就用來當作店名。火腿哥,你為什麼想去讀北海道大學?」
火腿哥告訴我說,那個學校有一位他很想追隨的老師。因為我們是藉由書結緣,我以為他讀文科,沒想到他更擅長理科的科目。我聽了之後,更覺得不能再向他借書了。我打算告訴他,今天已經買了新的書,他已經也借給我看很多書,以後不用再借給我了,卻遲遲無法開口。他每天都會來店裡買麵包,所以並不是完全無法見到他,但還是會感到寂寞。我擔心自己會哭,決定下了巴士後,臨別時對他說這些話,然後直接跑回家。但在上車之前,我覺得應該在暈車之前先睡著,所以一上車就閉上了眼睛,當我再度睜開眼時,發現火腿哥背著我站在<薰衣草烘焙坊>門口。聽到我爸大聲喝斥:「妳在幹嘛?」時,我立刻嚇醒了,從火腿哥背上跳了下來。原來剛才巴士到站時,火腿哥搖不醒我,只好把我背回來了。
「妳欺騙父母,到底去哪裡了?」
在爸爸的質問下,我坦承請火腿哥帶我去參觀了京成高中,還說因為知道那所學校有文藝社,所以產生了興趣。我不想讓爸爸知道我只是想去看看山的另一邊是什麼樣子,而是有明確的目的,沒想到反而起了反效果。
「妳是麵包店的女兒,參加什麼文藝社。以妳的腦袋,讀這裡的高中就足夠了。況且,如果是這樣的話,一開始就應該老老實實說清楚再出門,還說要和女同學一起讀書,是不是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爸爸說完,狠狠瞪著火腿哥,但即使遇到這種狀況,火腿哥也不慌不忙地鞠躬道歉說:「對不起,未經你們大人許可就帶令嬡出門,但我想和令嬡交往,我是認真的。雖然目前我要考大學,令嬡也要考高中,並不是理想的時機,但我一旦考上大學,就要離開這裡,不過,我在大學畢業後,仍然打算回來這裡找工作,所以請你們那時候再回答是否同意我和令嬡交往。」
爸爸和出來勸解的媽媽,還有我這個當事人都目瞪口呆,說不出話。火腿哥向我們鞠了一躬後,轉身回家了。
「他是哪一家的孩子?」
「是萬事通的兒子,聽說是個高材生。」
「高材生為什麼會看上我們家的女兒?」
「對啊,這孩子整天只會發呆。」
爸爸和媽媽看著火腿哥的背影說道,我在腦海中重溫著他剛才說的話,思考著令嬡是誰這種莫名其妙的問題。幾天後,火腿哥的父母也登門拜訪,火腿哥和我就變成了父母公認的關係,但我忍不住想,這樣真的好嗎?我的確喜歡火腿哥,但未來的事可以這樣輕易決定嗎?是不是完全沒有顧及我的意見?雖然在當時的情況下似乎無可奈何,但火腿哥在對我父母說那些話之前,如果曾經給我一些暗示,我或許就不會有現在這種感覺,所以我整天怔怔地看著山後方的後方,看著天空的遠方,似乎想要為自己的心尋找一個安身之處。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故事的結局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4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故事的結局 作者:湊佳苗 / 譯者:王蘊潔 出版社:台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1-27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故事的結局
如果是你,會讓故事有怎樣的結局呢?
手捧「未完的故事」時,新的人生齒輪開始轉動。
這次的湊佳苗有別以往,無毒又暖心!
「天空的彼岸」
「往過去,往未來」
「百花山丘」
「漫漫崎嶇路」
「超越時間」
「湖上的煙火」
「街燈」
「旅途的盡頭」
在8篇短篇小說中,內心充滿迷惘的主角,
分別前往小樽、富良野、美瑛、旭川、摩周湖、洞爺湖、札幌等北海道各城市。
懷孕三個月發現自己罹患癌症的智子;想要放棄成為職業攝影師夢想的拓真;雖然得到了心目中理想公司的內容,卻沒有自信的綾子;反對女兒前往美國的木水;在證券公司工作的工作狂愛茜……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時,他們獨自前往北海道旅行。他們在旅行途中拿到了一疊書稿,那是「天空的彼岸」這個沒有結局的小說,而真正的結局,會是──。
作者簡介:
湊 佳苗
1973年出生於廣島縣,畢業於武庫川女子大學家政學部。
2005年入圍BS-i新人腳本獎佳作。獲得2007年、第35屆創作ラジオドラマ大獎,同年以「聖職者」獲得第29屆小說推理新人獎。
2008年,出版長篇小說《告白》,也以此作獲得週刊文春「最佳推理小說Best 10」的第一名及第6屆本屋大賞,並於2010年6月改編為電影,由松隆子、岡田將生等人主演。2010年的作品《望鄉 海之星》,獲得第65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短篇獎。
著有《告白》、《少女》、《夜行觀覽車》、《為了N》、《往復書簡》、《境遇》、《藍寶石》、《贖罪》、《花之鎖》、《母性》、《白雪公主殺人事件》等書。
TOP
章節試閱
天空的彼岸
那座山的後方到底有什麼?從我懂事的時候開始,就經常望著遠方的景色發呆,思考這件事。我出生的城鎮位在高山山谷間的盆地,我只能看到城鎮周圍像高牆般的山脈,和山脈上方的藍天。父母開了一家小麵包店,每天凌晨兩點起床做麵包,清晨六點到傍晚六點開店營業,完成隔天的準備工作,晚上九點上床睡覺,日復一日過著這樣的生活。麵包店的名字叫<薰衣草烘焙坊>,但我爸爸和媽媽從出生到現在都一直在這個城鎮生活,也從來不曾出門旅行,從來沒有看過北海道那片紫色的花好像地毯般的薰衣草田。向來不苟言笑的爸爸想要取一個好聽...
那座山的後方到底有什麼?從我懂事的時候開始,就經常望著遠方的景色發呆,思考這件事。我出生的城鎮位在高山山谷間的盆地,我只能看到城鎮周圍像高牆般的山脈,和山脈上方的藍天。父母開了一家小麵包店,每天凌晨兩點起床做麵包,清晨六點到傍晚六點開店營業,完成隔天的準備工作,晚上九點上床睡覺,日復一日過著這樣的生活。麵包店的名字叫<薰衣草烘焙坊>,但我爸爸和媽媽從出生到現在都一直在這個城鎮生活,也從來不曾出門旅行,從來沒有看過北海道那片紫色的花好像地毯般的薰衣草田。向來不苟言笑的爸爸想要取一個好聽...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湊佳苗 譯者: 王蘊潔
- 出版社: 台灣東販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1-27 ISBN/ISSN:978986331950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8頁
- 商品尺寸:長:210mm \ 寬:147mm
- 類別: 中文書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
|

 2018/12/31
2018/12/31 2016/10/23
2016/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