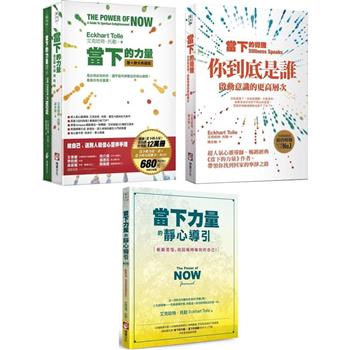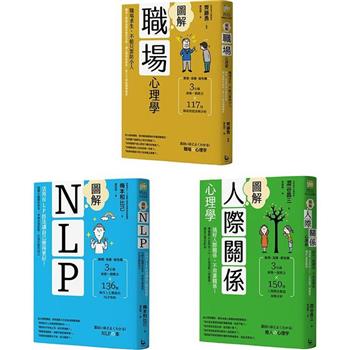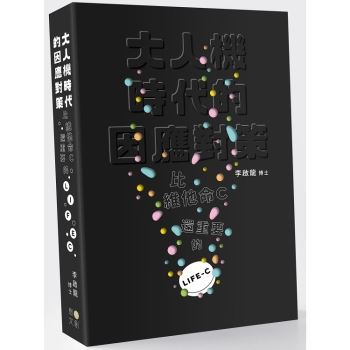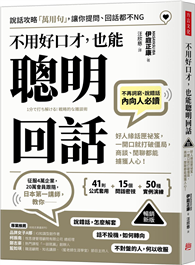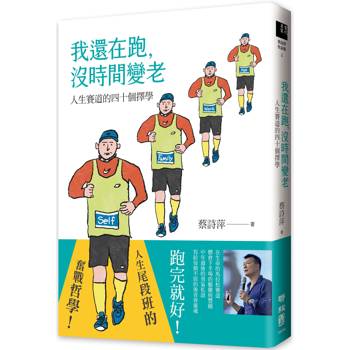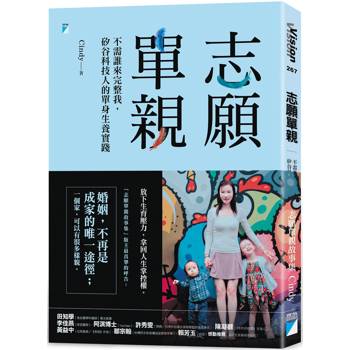導讀者簡介:
林保淳
臺灣新竹人,臺大中文博士,現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喜劍好俠,對古典說部及通俗文學、民俗傳說有濃厚的興趣,近幾年專心致力於武俠小說的研究,有《解構金庸》、《古典小說中的類型人物》、《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與葉洪生合著)等書問世,頗獲好評。
神話‧仙話‧妖話‧鬼話──中國人的想像世界
林保淳(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很久很久以前……
這是我們聽熟了、看慣了的說故事的常見開場白。說故事的時候,把這個「很久很久」的時間拉得愈長、愈遠,故事內容就可以愈不受現實世界的拘限,說故事的人就大可憑藉著自己豐富的想像力,盡情發揮,構築出一齣一齣的故事。
但無論多久遠的故事,總都有一個源頭,誰是第一個講故事的人呢?這個故事的內容是真的還是假的?戰國時代的大詩人屈原,寫了一篇浪漫瑰奇的〈天問〉,把後世聽故事的人的疑惑,一股腦的都拋了出來: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是誰最先說出來的呢?)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連天地都還沒有形成,他是如何考究出來的?)
故事,經常是不經意間產生的,剛開始一個人偶然間說了某一段「可能發生」的事件,就成了故事;然後,兩個人、三個人……無數的人都這麼說,於是,在輾轉流傳下,往往就成了神話或傳說,變成了某個民族根深蒂固的傳統。
神話,是一種想像出來的故事。雖說是「神」,但卻是以「人」為基準點想像出來的。小時候,大概很多人都會問媽媽一個問題:「我是怎麼來的?」我記得我媽媽的回答是「石頭裡迸出來的」。這個答案儘管顯得荒謬,但非常具有神話的性質,或者可以當作我們認識神話的一個起點。
當然我們清楚的知道,我們都是爸媽結合下生出來的,透過科學常識,我們甚至還可以知道其中牽涉到的生物學、遺傳學的種種知識,不可能像孫悟空一樣是從石頭裡迸出來的。但是,爸媽又是怎麼來的?爸媽的爸媽、爸媽的爸媽的爸媽……呢?追溯上去,在很久很久以前,第一個「人」是怎麼來的?中國古代神話中創造出女媧和盤古,據說女媧會「摶土造人」,盤古能「開天闢地」,我們(人)和世界就是這樣產生的。但是,就如同屈原的質疑一樣,「女媧有體,孰制匠之」?那女媧和盤古又是誰創造出來的?所有的神話,都是從一個疑問句開始的,我們是怎麼來的?天與地是怎麼形成的?宇宙萬物和我們是什麼關係?四季為什麼會輪轉?天為何會刮風下雨?人為什麼會出生和死亡?為什麼?為什麼……一連串圍繞著我們生活周遭,與我們生命息息相關的問題,都必須要有個答案,而神話,這個「關於天地的初創、神靈的奇蹟,以及說明風俗習慣、儀禮和信仰的起源與意義的故事」(《教育部國語詞典》),就是一種解答。
正如我們不可能是從石頭裡迸出來的一樣,神話故事的解答經常是不可靠的,也往往是不合理的,故事時間愈久遠,往往內容也愈荒誕,屈原問「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月亮究竟有什麼能耐,能夠消失而又重圓?又有什麼好處,讓玉兔願意住在上面?)傳述月亮能夠死而復生,上面還有玉兔的說故事的人,從現代的角度看來,真的是毫無科學常識的,人類都已登陸月球的科學昌明時代,有誰還會相信?但神話就是有這個本事,能在口耳相傳下,讓你不由得不「以假當真」,正如同當媽媽跟我們說了這個解答後,我們雖不能確信,至少會感到心安,就是這個心安,便足以讓我們暫時拋開心中的疑惑,繼續迎接我們即將來到的生活。
不過,媽媽為何說我們是「石頭裡迸出來的」,而不說是海裡撈起來的、路上撿到的或是什麼植物生長出來、動物轉變而來的等等,也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當然,我們可以想見媽媽一定熟知《西遊記》裡孫悟空誕生的故事,在潛意識裡不知不覺就讓她作了這樣的回答。在這裡,就牽涉到每一個人傳述故事時的特殊文化背景了。因此,中國人於清夜中仰望月亮時,多半不會想起阿姆斯壯如何踏出他的「人類一大步」,也不會像熟知西洋掌故的余光中一樣,覺得「星空,多麼希臘」,我們也許會像辛棄疾一樣,想起月中的嫦娥、蟾蜍、玉兔和瓊樓玉宇的月宮:
飛鏡無根誰繫?(高掛天空的月亮是誰拿線將她繫住的?)
嫦娥不嫁誰留?(嫦娥在月亮上幾千年,誰留著不讓她出嫁?)
謂經海底問無由,恍惚使人愁。(有人說月亮是從海底升起的,這真的沒有道理,且讓人不禁替她發愁)
怕萬里長鯨,從橫觸破,玉殿瓊樓。(因為海裡有萬里長的大鯨魚,難免擔心它縱橫往來,撞壞了月亮上的美麗的宮殿樓宇)
蝦蟆故堪浴水,問云何、玉兔解沈浮?(而且,蝦蟆固然會游泳不怕水,但請問玉兔懂得游水的技巧嗎?)
若道都齊無恙,云何漸漸如鉤?(假如說兩個都不會有所損傷,那為何圓月又會漸漸變成一鉤彎月?)
辛棄疾雖然對月亮的神話傳說有不少趣味盎然的質疑,但更多的是浪漫的想像,而這些想像則是從我們對豐富的文化了解中轉化而生出來的,神話,不僅是人類對一切事物的「可能如何」的解釋,也是一切文學藝術創造力的根源。這就是神話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很多人認為,中國在傳統儒家「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影響下,原本豐富的先民神話逐漸在「理性」的壓縮下而褪色、消退了,因此流傳下來的神話多半只有殘篇斷語,粗具輪廓,而缺乏像希臘神話般系統、完整而瑰奇炫麗傳說。這話是有道理的。中國許多可能非常具有魅力與想像的神話,例如相傳我們的祖先黃帝是有「四面」的,但在儒家理性思考的解說下,卻變成了「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再如傳說中出入伴隨著風雨,且只有一隻腳的「夔」,孔子卻把「夔一足」(夔只有一隻腳)解說成「夔一,足」(只要有夔一個就夠了),就把怪獸轉變成黃帝的樂官了。的確,儒家的思維往往壓縮了神話的想像力,而中國文化向來以儒家為主導,因此過去可能曾經有過的浪漫而美麗的神話傳說,就如此逐漸湮沒消失了。
不過,想像是人類心靈無可壓抑的本能,條理嚴密的理性儘管可能壓制住想像的發揮,但中國傳統文化並不只儒家一脈,來自道家(道教)、民間信仰以及後來傳入中國的佛教思想,在儒家思想主流外,卻能擺脫重重的限制,以洸洋自恣的想像,為我們重新開啟了許多宛如先秦古神話般奇妙炫麗的仙話、鬼話與妖話。
仙話的起源與道教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主要是為解答人類有關「生死」問題的困惑。人生在世,總難免一死,但多數的人都非常畏怖死亡,因為一旦人體消亡,人在世間所有值得留戀的人事物,都將隨之幻滅。假如人能不死,那有多好?傳說中仙人是不會隨著時間而消亡的,大海之外,甚至還有館閣玲瓏,種滿琪花瑤草的海外仙山,人間也有一種「不死藥」……仙人世界、仙人故事,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逐步建構完成,我們所熟知八仙、七仙女、西王母,乃至《封神演義》、《西遊記》裡的怪異炫麗的故事,就是這樣形成的。
鬼話(鬼故事),是因應於人死之後的問題而產生的。人死之後被稱為「鬼」,他們沒有固定形體,只有魂魄;和人一樣,鬼也有善有惡,有好有壞。他們居住在哪?鬼的世界和人類世界有何不同?鬼和人可以有什麼樣的聯繫?……一連串有關鬼與人的故事,從漢代開始就在我們的文化中廣泛流傳,六朝小說、唐人小說、宋元筆記中有數不清、說不盡的「鬼話」,而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可以說是集其大成的了。
妖話,是講妖怪的故事。世間所有「反常」(這是相對而言的)的人事物,就稱為「妖」或「怪」,正因其與「常」相對,因此就與一般我們生活周遭習慣了的事與物發生關聯。世間為何會有反常的妖與怪出現?他們的出現代表了什麼意義?妖怪的反常與人世的正常有什麼關係?反常的妖怪是否也可以找到「常」的規律?……這些都是引人入勝、趣味盎然的疑問,而正因其反常,所以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可以全解說明白,也因此就有了非常大空間可以容納我們的想像力作無限的馳騁,從魏晉南北以來,我們也流傳下許許多多妖異而炫目的傳說故事。
無論是神話、仙話、鬼話或妖話,事實上我們的祖先都為我們創造並遺留下非常豐富而珍貴的遺產,可惜的是,多數接受西式教育的人只知道星空是非常希臘的,不知道其實天空一樣可以非常中國,只要你願意打開書本,尤其是這本《中國神話》,就可以窺探出中國人的想像世界是有多神奇微妙了。
然後,你也不妨發揮一下現代人的想像力,在古人瑰奇的想像世界中再創造,也許,《西遊記》可以改寫成中國的《哈利波特》,《鏡花緣》也可以成為中國的《魔戒》……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中國神話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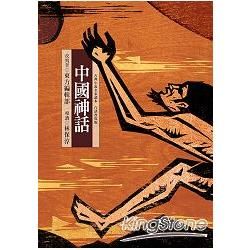 |
中國神話 作者:東方編輯部/改寫 出版社:台灣東方 出版日期:2014-11-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24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神話
話說《中國神話》
中國神話是從古代流傳下來的故事,從天地開闢、神靈誕生、人類的出現,到各個朝代的形成、重要君臣的出生……等,無所不含。經過無數年代的口傳,再慢慢以文字定型,同一個傳說往往因轉述者戲劇性的誇大,或特意加強布達的重點,而出現不同的版本。這本書裡羅列的八十七則故事,有些用現代人的認知看來,會以為荒誕無稽;有些又似乎已隨著代代相傳的價值觀,理所當然的深植人心,成了傳統。也正由於傳說的多變性與難追溯性,反而更能顯出一個民族的想像力和創意。
原著
蒐羅於:《山海經》、《拾遺記》、《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述異記》、《搜神記》、《玄怪錄》、《太平廣記》、《江湖紀聞》、《子不語》、《聊齋誌異》……等儒、釋、道典籍。
「神話」、「仙話」、「妖話」和「鬼話」都是從傳說開始的。可能不經意間某人說了某一段「可能發生」的事件,它被其他人聽進去了,然後,兩個人、三個人……無數的人都跟著轉述,於是,在輾轉流傳下,就成了我們現在聽到、看到的樣子。閱讀這些故事,不僅讓人驚嘆它們在虛實間穿插得如此巧妙,也讓人讚嘆經過長時間演化成的故事,竟是這般有趣。
作者簡介:
推薦序
導讀者簡介:
林保淳
臺灣新竹人,臺大中文博士,現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喜劍好俠,對古典說部及通俗文學、民俗傳說有濃厚的興趣,近幾年專心致力於武俠小說的研究,有《解構金庸》、《古典小說中的類型人物》、《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與葉洪生合著)等書問世,頗獲好評。
神話‧仙話‧妖話‧鬼話──中國人的想像世界
林保淳(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很久很久以前……
這是我們聽熟了、看慣了的說故事的常見開場白。說故事的時候,把這個「很久很久」的時間拉得愈長、愈遠,故事...
林保淳
臺灣新竹人,臺大中文博士,現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喜劍好俠,對古典說部及通俗文學、民俗傳說有濃厚的興趣,近幾年專心致力於武俠小說的研究,有《解構金庸》、《古典小說中的類型人物》、《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與葉洪生合著)等書問世,頗獲好評。
神話‧仙話‧妖話‧鬼話──中國人的想像世界
林保淳(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很久很久以前……
這是我們聽熟了、看慣了的說故事的常見開場白。說故事的時候,把這個「很久很久」的時間拉得愈長、愈遠,故事...
»看全部
目錄
混沌傳說
盤古開天闢地
女媧彩石補天
太陽的傳說
太陽之母
燭陰
神射手后羿
夸父追日
月亮的傳說
吳剛伐桂
嫦娥奔月
玉兔搗藥
太陽追月
星星的傳說
牛郎織女會
七夕乞巧
支機石
雨的傳說
赤松子化雨
西海異人
一行和尚祈雨
風的傳說
石尤風留夫
鄭公風
崔玄微奇遇
下關風
雪的傳說
祈雪救百獸
霜雪降五穀豐
召雪歌
雲的傳說
望夫雲
朝雲暮雨
驅雲使者
雷電傳說
電光石火
雷祖誕生
雷公的替身
孝媳電母
彩虹的傳說
神奇金瓶
彩虹化身
彩虹吐金
彩虹隱身
龍的傳說
龍生九子
黃帝乘龍升天
鯀...
盤古開天闢地
女媧彩石補天
太陽的傳說
太陽之母
燭陰
神射手后羿
夸父追日
月亮的傳說
吳剛伐桂
嫦娥奔月
玉兔搗藥
太陽追月
星星的傳說
牛郎織女會
七夕乞巧
支機石
雨的傳說
赤松子化雨
西海異人
一行和尚祈雨
風的傳說
石尤風留夫
鄭公風
崔玄微奇遇
下關風
雪的傳說
祈雪救百獸
霜雪降五穀豐
召雪歌
雲的傳說
望夫雲
朝雲暮雨
驅雲使者
雷電傳說
電光石火
雷祖誕生
雷公的替身
孝媳電母
彩虹的傳說
神奇金瓶
彩虹化身
彩虹吐金
彩虹隱身
龍的傳說
龍生九子
黃帝乘龍升天
鯀...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改寫:東方編輯部、導讀:林保淳
- 出版社: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11-01 ISBN/ISSN:9789863380573
- 語言:繁體中文 適讀年齡:10歲以上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4頁 開數:14.8 x 21 cm
- 類別: 中文書> 少兒親子> 少兒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