沾滿鮮血的魚叉深深刺入幽暗腐敗的魔船
東方經典套書「福爾摩斯系列」改版上市,自10月起即以新封面帶給讀者新的視覺呈現,在世代交替的過程中,希望喚起更多人兒時的回憶,同時讓更多人有機會再次接觸到這套經典著作。
在推理小說的領域,福爾摩斯是一個十分成功的人物,不僅跨越世紀,更躍然紙上,深刻地刻畫在每個人的記憶裡,藉著此次改版,期喚醒大家心中的「福爾摩斯。」
十一年前一名銀行經理捲款潛逃,十一年後他所攜帶的股票重現市面,銀行經理的兒子輾轉打聽到這些股票是由一名船長手中流通出來的,才想找他問個究竟,沒想卻傳來船長遇害的消息。福爾摩斯知道這件事後,為什麼能憑著一紙徵求魚插手的啟事,就能將凶手繩之以法呢?
書中主角簡介
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
生於1854年。鄉紳後代,長他七歲的哥哥麥考夫是內閣祕密調查局局長。夏洛克在牛津大學專攻化學,不擅交際,愛思考。精通劍術、拳術。被同學的狗咬傷後,兩人反而成了莫逆,一次拜訪同學家,推測出同學父親的一樁陳年往事,也因此引發他踏上偵探一途的興趣。23歲在大英博物館附近的蒙塔格街創立私家偵探社,一邊研究科學,一邊接辦同學介紹的案子。27歲與退役軍醫華生結識,並合租貝克街221號B室(221B Baker Street),兩人協力辦案。
每日必讀大量報紙。最大的興趣是音樂,拉得一手好小提琴,最不離手的嗜好是抽菸斗。射擊神準,善於運用心理學和邏輯學分析推理。偵查過六十件膾炙人口的案件。58歲隱退。
約翰‧H‧華生Dr. John Hamish Watson
於1852年,26歲獲得倫敦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結業後隨軍赴阿富汗任軍醫,28歲負傷回倫敦。結識福爾摩斯後,兩人合租貝克街221號B室。36歲與梅麗結婚,搬出貝克街,自己成立診所。42歲,梅麗過世,結束診所,再回貝克街。其間皆不間斷的跟隨福爾摩斯辦案,並詳細記錄偵案過程,再發表於報章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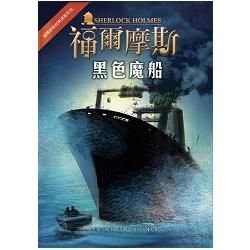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