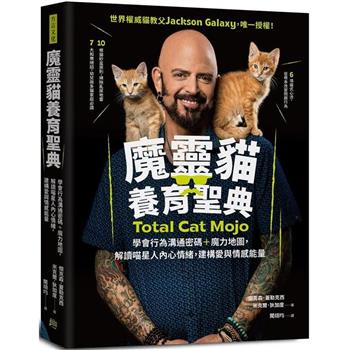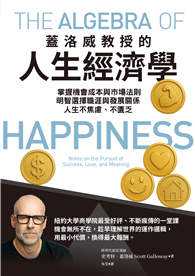自序
雪天裡的蝴蝶
收到這本集子裡的作品,都有較強的故事性,完全可能改編成四部引人入勝的電影。這會讓「先鋒」讀者嗤之以鼻,但也許會贏得部分比較傳統的讀者的喜歡。
〈白棉花〉的創作,是因為張藝謀。那時,他好像剛拍完蘇童的〈妻妾成群〉,苦於找不到能改編成電影的小說,所以他就讓手下人把我找了去,約我寫一篇描寫農村生活的、場面宏大的小說。我反覆想了,除了戰爭或歷史,要說場面大,在和平年代裡,那就只有幾十年前的人工開挖河流的情景。我參加過這樣的工程,深知其中的艱苦,寫成小說是沒有問題的,但要想在銀幕上表現,幾乎不可能,你的錢再多,要調動幾十萬老百姓,也不是件容易事。
我突然想起七○年代初期,在縣棉花加工廠工作時的情景。那時,半個縣的棉花集中到加工廠裡,棉花垛得像小山一樣;送棉的隊伍排出十幾里長,場面的確很壯觀。新棉一上市,數百個有點門路的農村姑娘便集中到廠裡來了。雖然在這裡工作的時間只有幾個月,但對她們的影響卻是巨大的。一季棉花加工完畢,她們都或多或少的有了改變。她們在加工棉花的時候,棉花也把她們加工了。那時候在農村千頭攢動的農村集市上,我一眼便能認出在棉花加工廠當過臨時工的姑娘。她們喜歡戴一個自己做的、用漂白粉漂得雪白的特大口罩,而且總是把一根帶襻兒掛在耳朵上,讓嘴巴忽隱忽現。因為戴了大口罩,所以她們的眼睛都顯得特別大、特別黑。她們的第二個特徵是喜歡戴藍套袖。這些原本是工作的需要,離開加工廠後卻成了她們高人半頭的標識。在她們內心裡,自然也是以此為榮、以此為美的。我跟張藝謀談了這個構思,他認為有點意思。但等我寫出來後,他可能找到了更好的小說,於是這事就拉倒。過了幾年,有位叫周曉文的導演找到我,提出要拍〈白棉花〉,還跟我簽了合同,但終究沒拍成。又過了幾年,香港一個姓杜的製片人想拍〈白棉花〉,跟我頗為認真地談過數次,但最終也是不了了之。
〈父親在民伕連裡〉,應該是《紅高粱家族》的續篇之一。在《紅高粱家族》裡,父親還是個頑童,在本篇裡,他已是一個身體健壯、久經磨難、具有了豐富人生經驗的青年。在他的身上,繼承了爺爺輩的英雄豪氣,但增添了更多的流氓氣。原來我想在這篇之後,再寫幾個系列中篇,編成《紅高粱家族》的第二部,但因為少年有痔,痛疼難忍,等把痔治好,已經沒有了續寫的興趣。也許有一天還會把早就有了構思的父親的故事寫完?此篇一發,即被我的一個對影視特有興趣的老鄉看好,他說等他賺夠了錢,一定要把它拍成一部大片子,可他好像總也賺不到錢。最近聽說他辦起一個轟轟烈烈的大藥廠,「殺人劫道,不如在家賣藥」,父親走上銀幕的日子大概不遠了吧!
〈紅耳朵〉裡的主人公是有原型的。但這原型並不是一個人。我認為這篇小說中的主人公王十千,是一個真正的高士,他的思想遠遠地超出了同時代的人。他對待金錢和財富的態度,再過一個世紀,恐怕也是和者蓋寡。此篇可以參照著我的短篇小說〈神嫖〉來讀,那篇裡的主人公王季範先生,是王十千的孿生兄弟。這對難兄難弟的事蹟,合併在一起,應能塑出一個富有象徵意味的典型形象,是不是不朽,我不敢說。也許在不久的將來,等我心血來潮的時候,我會自己動手,把它弄成一部電影。
〈戰友重逢〉是一篇被四家刊物退了稿的作品,退稿的原因一句話也說不清楚。這部中篇是我少有的寫軍隊題材的作品,我自認為比同類題材的作品寫得都要深刻,而這也就是屢遭退稿的主要原因吧?在本篇中,我著力探討了英雄的問題,機緣和湊巧,可能使一個怕死鬼變成英雄;而真正具有英雄氣質的人,卻可能像狗一樣窩窩囊囊地死去。
自從《豐乳肥臀》遭到不允許辯解的批判後,我已經兩年沒有寫小說。我甚至連編一本集子的興趣都沒有。去年夏天麥田出版公司的總編輯陳雨航先生和在美國教中國文學的王德威教授來北京讓我編一本集子,我當時答應了,但回家後即興趣全無,並且很快就把這事忘得乾乾淨淨。不久前王德威教授又來函催問,這才想起來。麥田出版公司和王教授如此抬舉我,使我受寵若驚,但還是拖到今日才開始編,懶惰頹唐得實在可以。但願從此之後,能重新煥發熱情,再寫一點讓朋友們看了高興、讓英雄們看了不高興的文章。問題的可悲在於,我真正的朋友,就像雪天的蝴蝶一樣少;而那些恨我的英雄卻像夏天的蒼蠅一樣多。但可喜處也在這裡,能在雪天裡生存的蝴蝶,必是不尋常的異種;而能吸引了成群蒼蠅的,必有特殊的氣味,不是狗屎,便是海鮮。
我是寧願做了狗屎去肥田,也不願被做成脂粉去塗抹英雄們的面孔的。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