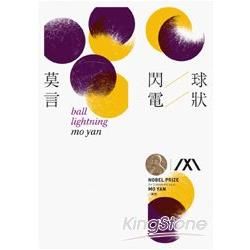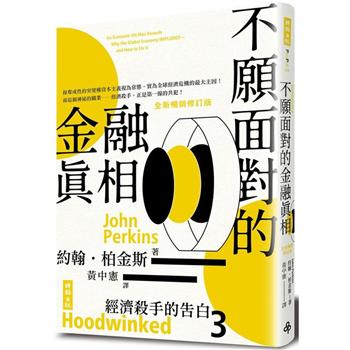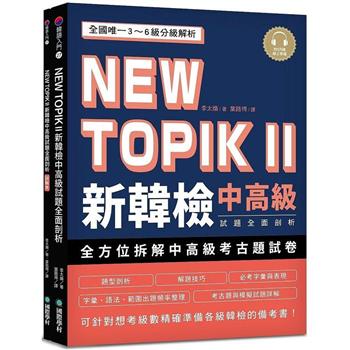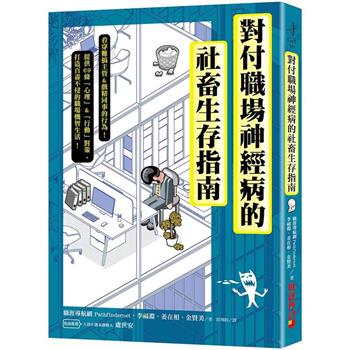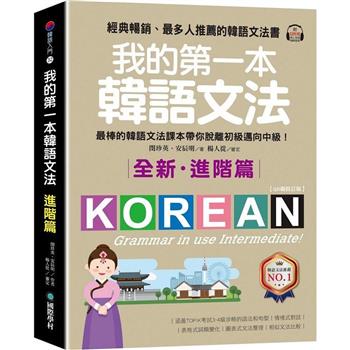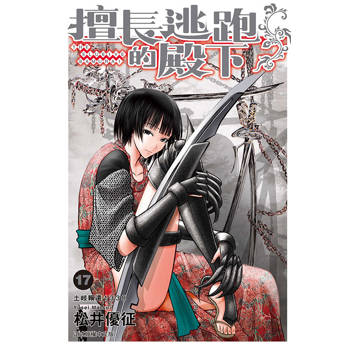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代序/作者的話
收到本集中的作品,創作時間最早的,當屬〈球狀閃電〉。那還是一九八四年冬天,我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書的時候。〈球狀閃電〉是我的「成名作」〈透明的紅蘿蔔〉之後的第一部作品,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兩部作品是姊妹篇。在〈透明的紅蘿蔔〉中,主人公還是一個少年,到了〈球狀閃電〉裡,這個少年已經長大成人、娶妻生子。本篇首發表於一九八五年《收穫》第五期。
〈築路〉創作於一九八五年暑假,發表在一九八六年的《中國作家》第三期上。時任該刊主編的馮牧先生託責編向我轉達了他的看法,他認為〈築路〉比〈紅高梁〉好。馮先生的話未必是真理,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一部作品,能入了他的法眼、也不是件容易事。一個做人作文都十分嚴謹的老資格評論家誇獎一部作品,必然有他的道理,可惜我當時沒有讓責編去問他,為什麼說〈築路〉比〈紅高梁〉好。事情過去了十幾年,已經很少有人知道我曾經寫過〈築路〉,而〈紅高梁〉依然是貼在我的「名氣」外衣上的一個耀眼的標籤。由此可見,一部作品就像一個人,有它自己的命運。
發表於《收穫》二○○○年一期的〈司令的女人〉,這部作品中大量地使用了類似於民間快板一樣的語言,褒貶不一。但這部作品對於我真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其實是我的長篇小說《檀香刑》的前奏。
〈掃帚星〉此篇作於二○○三年。咱家當時對闖關東的事兒頗感興趣,研究了很多植物學著作,掌握了一些動物的知識和林業生產知識,還專門去過長白山。咱家原計畫冬天去趟東北,沿松花江、烏蘇里江、黑龍江考察,再去看看大興安嶺;夏天再去一次,沿黑龍江進入俄境,入阿莫爾河,一直航行至入海口,那裡,幾百年前,是中國人的土地。可惜因事,計畫未能實現,這部構思中的長篇也就此流產。
〈變〉這篇文章的由來,緣起於二○○五年一月,女兒笑笑陪我去義大利烏迪內領取NONINO國際文學獎。其間,結識了印度加爾各答一家出版社的編輯NaveenKishore。女兒與他用英文交談,我坐在旁邊看他。這是一個面部輪廓極為鮮明、沉默寡言的黑皮中年男子。穿一身黑色制服,披一件黑色風衣,提一架看上去十分沉重的黑色照相機。風衣的領袖、皮鞋的幫沿、相機的邊角,都磨得發了白。我請他吃了一盤麵條,他給我拍了一張照片。當時互留了電子信箱和通訊位址,但分手之後,也就基本上把他忘記了。二○○六年年初,突然收到他的郵件,說希望我能給他們出版社寫一篇描述三十年來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的文章,我感到這個題目太過寬泛,自己難以勝任,便婉辭了。但架不住他一再來信勸說,最後竟允許我「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想寫什麼就寫什麼」,這樣,就沒有理由拒絕了。拿起筆來才知道,我不可能「想怎麼寫就怎麼寫」,也不可能「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拿起筆來才知道,他給我的題目,還牢牢地約束著我。他還發來了當年為我拍的那張照片,附在郵件上,黑白的,有些酷。我這樣的臉他竟然能拍出酷的感覺,可見是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