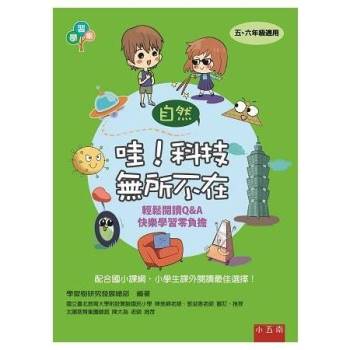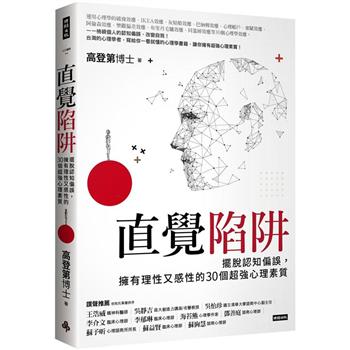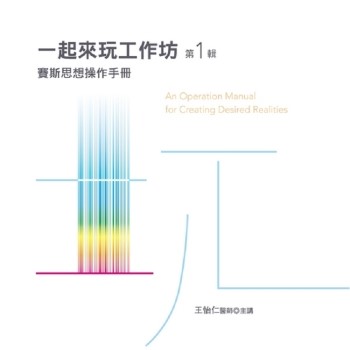「真的是這邊嗎?沒看錯地圖吧?」
「沒有,你繼續往上開去就行了。」
「怎麼你的朋友挑房子要挑這麼偏遠的地方?」
「他說喜歡這座山的名字,反正他就是個品味極怪的傢伙。」
駕駛座上傳來有一搭沒一搭的對話,讓我不費心神也能咀嚼出內容,更讓我在意的,是這輛車子給我的冷意。
星期三,是我復活節假期的第一天。
我答應恭鶴蒼的要求,把三天假期留給了他。
「真的沒問題嗎?」感受車裡的莫名寒意,我小聲喃道。
會錯意的恭鶴蒼扭頭扔了我一句:「別擔心,都說了有我在。」
說到這個我也憂心起來,但看到對方信心滿滿,我只好信服他的實力。
想起上星期晚上回家後的事,就算沒有被當場嚇死,我也要抱著自己哭。
我說的就是從向太太處回家的那一夜。
當安寧憂把車子開到姑姑家樓下,我才想起一件嚴重可怕的事。
「所以說,你到底在我家裡幹了什麼?」忐忑不安地問向恭鶴蒼,對方露出一個更讓我擔憂的使壞笑容,給我一句忠告:「別說我不提醒你,不要被家人發現,悄悄回到房間去,在裡面看到什麼也不要叫。」
恭大道長啊你不要嚇我好嗎?
小孩子嘻嘻嘻的心情極佳,就像巧心設下了滿懷惡意的陷阱,然後等著別人進入他的傑作時,欣賞對方落入後露出的醜態。
不是我說,恭鶴蒼在這方面真的和小孩子一樣!
戰戰兢兢地下了車,再小心翼翼地回到姑姑家,看到玄關上姑姑的室內鞋不在時心頭更是澆了一盤冷水──姑姑這晚沒加班!
現在是晚上十點,姑姑和歲都沒有熬夜看電視的習慣,所以客廳早就一片漆黑。我摸黑回到自己的房間前,邊留意白氏母子的舉動,邊深呼吸幾下,想起恭鶴蒼帶有陰謀的笑,不禁再次畏懼地抖起來,好不容易穩下不安定下心後,我開門而入。
房燈亮著,桌前坐著一人影,背影怪熟悉的,我驚喊一聲「歲?」發現認錯人後立刻捂上嘴巴。
對方聽到我的聲音後回頭,站起來行了個禮,對我報以一笑。
「恭迎杜畏大人回來,但容小神無禮提醒,您還是關上門為好。」
嘴巴還在捂著,我愕然看看對方再愕然看看房門,在驚疑未定下輕聲地關上門。
一看到他,我就明白恭鶴蒼一整天的奸笑原因何在。
眼前站著的男生和我長得一模一樣,不論身形至五官、髮型至輪廓,就連我手掌上的痣也是鉅細無遺地相像,比起照鏡子,我更認為這個人是從鏡子裡走出來的另一個我。
「該不會你就是……」
「對,小神正是蒼大人的召喚神,容鏡。」名叫容鏡,卻套著杜畏外殼的人,再行了個禮,畢恭畢敬地回答。
我該先吐糟哪裡?兩個杜畏碰頭了其中一個行禮了?那個杜畏叫自己為神了?那個杜畏尊稱活體火山為「大人」了?恭鶴蒼我要現在打電話給你,問你什麼是「召喚神」嗎?
大腦混亂起來,見我愣愣發呆不說話,容鏡依然恭敬地問:「杜畏大人是否身體抱恙?請到床上稍作休息,您的校內作業我已經為您處理完畢,請您安心歇息便好。」
竟然附帶完成功課的功能啊,是說神仙會做我們的功課嗎?
把我拉到床上,容鏡打開衣櫃拿出我的睡衣,動作流暢得不像第一次進入我的房間一樣,我彷彿看到了我不在家時,容鏡如何代替了我的位置,和歲、和姑姑相處。
心裡滋味奇怪。
正想向容鏡搭話時門外響起輕敲,「哥,你剛剛叫我?」
糟了,剛剛沒預想到房間裡會有另一個我,看到背影以為是歲便不小心叫了出來。
我支吾應了聲,生怕歲會開門進來,慌張地望向容鏡。
對方明白我的難處,立刻點頭行禮,小聲說:「那小神就此退下。」
話剛說完,他便砰的一聲炸出白煙消失,看著自己瞬間在煙霧下不見,奇怪的滋味更是複雜。
「你沒事吧?」在白煙剛好消散之際,歲扭開門進來,看著一臉呆然的我問。
除了沒事外我還可以回答什麼?看著我不停搖頭,歲皺起臉指著地板問:「那是什麼?」
剛剛容鏡一直站著的位置上漏下一張雪白的紙符。
「這是容鏡的真身?」我遞出紙符,恭鶴蒼在倒後鏡瞄了一眼後否定,「怎麼可能,那只是召喚符式。好歹他也是神,才不會委身在人界的紙裡。」
你也會說好歹,為什麼還使喚神仙?
恭鶴蒼神氣地白我一眼:「就連神力也能隨便用,使役一兩個神仙又有何奇?」
好吧,我都忘了凡識的開山祖宗,可是把十二個神仙壓榨在不平等條約之下的。
「所以召喚神到底是什麼?」那天容鏡走得太快,加上被阿洛抓去登山時發生的一連串怪事,若不是恭鶴蒼為我故技重施,都不知要再等多久我才會想起。
想到這,不由得為正在姑姑家以我的容貌,替我瞞天過海的容鏡感到又憂又愁。
可是坐在副駕駛座上的小孩子,根本不會正視我的問題,讓我開始深究在初次見面時,他要求我做的事能不能如願達成──還問什麼問題?你都不回答我好嗎?
「這座山要繞上去還真麻煩哩!」顧著為安寧憂指路的恭鶴蒼,一手拿著地圖一手拿著黑影先生寫給他的地址,淡然地說:「虧你們還有興致來登山。」
不,在阿洛眼中登山是次要,主要的是來尋鬼屋。
「不過登山也能遇到那種事,杜畏你的命和靈界還真有緣呢。」恭鶴蒼嘻笑一聲,懶得理我的大聲呼叫。
能投胎再生的話,我才不要這種緣份啊……
說到那天,下山後阿洛像沒事人一樣地回復平日作風,拖著我們吃完甜品後,便在車站各散東西,彷彿已經把山上遇到的事忘記了,只剩下一頭霧水的其他人一直耿耿於懷,而清楚不過的我,更是恨不得想抓住阿洛問個詳細。
所以在當晚我立刻打了個電話給恭鶴蒼,聽完我的話後,小孩子只是沉思了片刻,說了聲「交給我」後,便連續幾天沒回醫館,看樣子是不知道溜去哪調查了。
「話說,那隻女鬼的事還沒查到嗎?」三番四次地出現在我面前,要我不在意也不行,更不用說上次在香港墳場和在半山公路也躲過術士的耳目,囂張地在我這個菜鳥面前亮相,這讓自詡靈感並無退弱的恭鶴蒼,自尊受挫地氣憤不已。
說到痛處,小孩子皺起臉來說:「終歸看到的只有你,連鬼氣也感受不到,我無處著手。」
也就是說毫無進展,這明明就是有可能關係到自身退化的線索。
消不了氣的恭鶴蒼問了一聲:「它沒對你幹什麼吧?」
「沒有,就只是要我看另一隻鬼。」想起那隻身體刷白而眼眶黝黑的斷頸幼鬼,我不禁打顫,越回想越覺得那面相令人心寒和怨憐,還帶著一絲莫名熟悉。
「也沒有對你幹什麼吧?」
「也沒有,就只是指了地圖一下。」我拿出因濕水而乾成硬紙的地圖指了一下,「他指的大概是這裡。」
恭鶴蒼甚無興趣地瞥了一眼,想移走的目光突然明亮起來,接過我的紙認真和自己手上的地圖對比一下,問道:「杜畏,你登的那座山叫什麼?」
對討厭和無興趣的事物便會不屑一顧的恭鶴蒼,竟然會問我與他無關的事,我既好奇又意外地回答:「吊燈籠。」
正在駕車的安寧憂咦了一聲說:「這裡?」
唔?「這裡」的意思是?
連忙望出車窗,剛好見到道上立著的指示牌上寫著熟悉的字眼。
吊燈籠。
好,我現在就試試把腦海裡最糟最壞的預想全湊合起來。
◆ ◆ ◆
車子停在荒涼的小徑前。
看著崎嶇狹窄的石頭路,這是汽車能駛入的最大限度,安寧憂滿意自己能把我們送到這裡來,卻煩惱著如何在不平坦的小路上安全倒車。
我按照恭鶴蒼的吩咐,從車後座拿出用三個尼龍繩紮起來的紅色大繩球,和他準備給我的背包。
拍拍半扁的背包,打開一看裡頭全是咒符和一串長長的佛珠,我奇怪為什麼會有佛教的東西後皺眉一問:「只有這些裝備沒問題嗎?」
「夠了,反正知道黑影先生屋子的大概位置,很快就會到。」把道袍塞入布袋,準備就緒的恭鶴蒼拍拍手說:「我們上山吧,杜畏你拿著繩球邊走邊放線,不要讓繩子斷了。」
這是做路標嗎?讓我們回程時用的?
「不對,是讓我上山帶你們下來用的。」安寧憂微笑回答,看了我倆一眼,掂量著自己說:「不知道我能不能同時抱兩個人下山呢?」
奇怪,我和恭鶴蒼能行能跳,為什麼要靠安寧憂抱下山?
「走吧杜畏,別再聊了。」扔了這麼一句的恭鶴蒼徑自踏上小徑,走了兩步轉頭說向白髮醫師,「我找到屋子後打電話給你。」
「唔,如果收不到你們的電話那一小時後我來找你們。」
「好,那之後就拜託憂了。」
說完了讓我半懂半不懂的話,被恭鶴蒼催促一聲,我開始了第二次登山之旅。
◆ ◆ ◆
果真是星期天走過的山,看著地圖以及不遠處的自然景觀,我默默念起來。為了證實我的想法,我決定問問屋主的朋友。
「你說過黑竹籤……黑影先生喜歡四處旅行是吧?他多久回來香港一次?」
「想喊人家別名就大方一點,別彆扭著。」嘴角忍不住上揚的恭鶴蒼答我:「聽說上一次回來已經十三年前的事了。」
果然如此。我大力拍額,響聲惹來領路人的回頭。
「有問題嗎?」
「好像有點問題。」不曉得黑竹籤知不知道他的屋子有個奇怪的別稱?上星期天還引來某個熱血又衝動的傢伙領軍尋訪呢。
不過,還有別的問題。
手上的地圖顯示了整個船灣郊野公園,連附近的村落屋邨也一並列印在紙張上,一直心裡有異的我找了片刻再喊了聲果然。
「向家大宅所在的村子就在山下不遠呢。」
「是嗎?又如何?」
「黑影先生的屋子十三年出現一次,而向太太的兒子也是在十三年前遇險的。」
「是嗎?又如何?」
「就……你不覺得很巧合嗎?」
前頭的小孩子聞言停下腳步,轉身,冷冷地說:「我說過的話你忘了嗎?」
是我神乎奇技還是對方身上的開關很多,能一下子戳到恭鶴蒼的制冷點?我心頭一顫,吱聲回答:「沒有。」
不斷發出乾冰冷霧的恭鶴蒼盯了我良久,緩緩地說:「這次的委託是什麼你要好好牢記,別再想有的沒有的事,有時無端插手某件事,下場會很慘的。」
看似忠告更似回想的話,讓我納悶又好奇,但脾氣能瞬間丕變的恭鶴蒼還是不惹為妙好了。
我只好把腦裡的假設暫放一邊,專心手頭的繩球好好放繩。
走著走著,熟悉感又奔上腦袋,這條山路我有印象,不就是星期天才走過的嗎?
扭過剛剛經過的岔路,我踏上了上次下山時所走的路,只要走向岔路的另一邊就是阿正帶我們下山的方向。往上繼續走,曾歇息逗留過的小平地證實了我的想法。
慢著,如果再沿路而上,不就有可能回到那個見鬼的山溪?
走到另一條岔路口時,恭鶴蒼先是頓一下停腳步,看向一望無際的山景,目光聚焦在某處對我輕聲問:「你說見鬼的地方就是那裡?」
朝他看目光看去,上次走得匆忙沒有發現,這時才知道原來我們落荒而逃,卻沒跑得多遠,休息的地方離山溪只有十多分鐘路程,而在逃跑時忽略了的岔路上,可以隱約看到那條清水潺潺的山溪。
「要去看看?」
「不,沒必要,雖有陰寒鬼氣外洩,但只是普通的飄浮靈,去了也不會有什麼發現。」靈感可真一絕的恭鶴蒼哼了一聲,心情不爽地撇頭走上山。
知道他著急那女鬼的事,因為到現場,卻依然找不到她的這件事情而生起悶氣,我應了一聲,默默地跟在他身後踏上岔路。
再走了二十分鐘,我們攀過山路、脫離小徑、拔開林葉後,出現在眼前的是一處山谷。雖幽暗寂靜但卻鳥語花香,空氣清爽得讓我心情舒暢,真是個休息野餐的好地方。
「到了,杜畏,繩放完了嗎?」扔下布袋,恭鶴蒼自然沒有把這美麗的景色放在眼內,抽出褐紅的道袍披上身。
「還沒有。」我舉起手上消耗了大半的尼龍繩球,張望了幾眼,突然地心頭一跳,立刻退回幾步,踏上一塊大石後用雙手比出了相框的手勢。
「把剩下的繩隨便綁上一棵樹,然後……你怎麼了?」在布袋上貼了一張符紙,轉過身原本也想給我上貼一張的恭鶴蒼,現在卻抬頭看著我發愣,「你這是什麼登山遊客的心態。」
不不不,我立刻放下手,像吃了碗加了不同調味料的麵般臉都拉了下來。
「我只是想說,果然是這裡啊。」
再一次聲明,阿洛的直覺真不可小看!這不,消失的鬼屋被她指對位置了!看著和靈異照片裡一樣的景色,我乾笑起來,幸好她提早下山,要不然我們那天可有得受了。
「怎麼露出一副靈魂被榨乾的蠢臉?」恭鶴蒼瞪大圓眼,奇怪地看著我,再次指示我綁好繩球後,往我背上……不,往我背包後貼上紙符,再掏出手機準備打給安寧憂。
拿出手機發現沒有訊號,恭鶴蒼乾脆得連重撥都免了,看到我細細打量著背包上的紙符後,便解說起來:「現形符咒,以防進屋後袋子被隔絕在屋外用的,別弄掉。」
「隔絕?什麼意思?不對。」我環視了山谷好幾圈,踩在毫無人煙的地方上問向他:「黑竹籤的屋子呢?我們都看不到又怎樣進去?」
「屋子一直就在。」恭鶴蒼責怪我一聲,然後往身後一指,突如其來的景象把我嚇得跌坐地上。
原本空無一物的山谷綠地上,竟出現了一間歐式大宅,因長年歲月的磨洗而顯出殘舊之姿,但更為這家充滿異國風情的古老大宅,增添了濃郁的典雅氣息。
看著牆身快被爬藤植物攀到二樓的大屋,我震驚得說不出話來。
屋子太大了吧,大得不是我會忽視的程度好嗎?
好笑地看著我啞口無言、指手劃腳,恭鶴蒼笑過之後,便邁向大屋邊走邊說:「別忘了這屋子的主人是誰。」
又是那種我想看,才能看得到的原因嗎?如果一心想來找屋子的話,絕對會看得到對吧?想到阿洛,我又顫抖一下的在心裡說了聲慶幸。
「他是個怪人,別再被這些小事嚇到了。」
想起靈異照片上的手掌,我恢復心情,跟上去認同地補一句:「而且還長得很高。就實話,如果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我還想叫他長腿叔叔。」
剛進醫館時除了他一身黑,我更忘不了他細長的腿,都勾起我對某套著名卡通的童年回憶了。
前頭傳來的爆笑聲,在下一秒立刻變成被捂上的忍笑,看著那小身板的肩頭強烈地顫動,我就知道他絕對想起了那首耳熟能詳的旋律。
恭鶴蒼你的笑點也太容易戳到了吧!有著先前好幾次的經驗,我心裡都要大叫我真的很意外啊!
念了一句「就說不少人也這樣認為啊黑影你就不信」的話,恭鶴蒼領著我來到大屋門口,掏出一把黑影先生借他的老式銅黃製鑰匙。
下一步應該是插入鑰匙推門進內,可恭鶴蒼卻在染上微黃的白木大門前停下來,轉過身來嚴肅認真地看向我。
「身上有錶嗎?」
冷不防一句把跟著肅靜起來的我弄至反應不過來,指著口袋說:「手機可以嗎?」
「更好。」要我開啟手機的某個功能,恭鶴蒼凝重無比地下達指令。
「這關乎著我們的性命,到了一定要告訴我,知道不?」
把這次委託想得輕鬆的我不由得緊張地點頭。
◆ ◆ ◆
打開門後出現在眼前的,是外國片裡常看到的豪華大廳,地上舖著看似價值不菲的紅地毯。當我還看得目瞪口呆時,恭鶴蒼拍拍我,伸出手說:「牽著我。」
你說什麼?
從紅地毯上回過神來,我又對著小孩子白皙的小手看個出神。
「就叫你牽著我,你聽不到嗎?記著,進去後立刻按下手提電話。」皺眉拉過我的手,恭鶴蒼二話不說地拖著我步入大屋。還在回神之際,踏入大屋的我便立刻感到強烈的怪異感!
大門處像是立著一面看不見的薄膜,觸碰時阻力極大,若不是牽著我的小孩子施重力道,暗示我要穿過膜牆,我可能會因為這面透明的牆壁,而陷入膠著。
我略微用力一蹬,好不容易才能穿過大門,在兩腳完全踏上紅地毯之時,身體裡,似乎有什麼東西被扯走,隔開在薄膜外。不適的異樣感,驅使我回頭尋找,可大門已砰的大力關上。
剛剛的奇怪感覺是怎麼回事?
回頭正要問恭鶴蒼,一陣強烈的靈力在眼前炸開。
「遵行汝之靈約,聽從吾之契言,守墨,命汝啟現吾前。」小孩子捏著召喚符的同時結出手印,靈力集中在白紙上順著墨字的線條凜然衝出,在面前匯聚成一個人形。靈力還沒穩定下來,一個穿著黑袍,以黑緞布蒙著眼睛,皮膚像宣紙一樣雪白光滑的長髮男人,已飄在半空向恭鶴蒼行禮。
「守墨遵從蒼主人之命令顯現神體,不知主人有何吩咐?」
又一個一見面就行禮的傢伙出現了!
「用最快的時間,把這屋子裡的入侵者搜出來。」揮袖劃出的布響聲是行動的訊號,恭鶴蒼簡明直接地下達命令,如從水墨畫裡跑出來的男人,再次低頭行禮,「一切謹遵蒼主人之吩咐。」
話音剛落,蒙眼神砰的散化開,再咻的飄離大廳。
「守墨,主要負責追蹤、搜索、結界,我另一個召喚神。」像扭開汽水蓋般輕鬆平常的恭鶴蒼沒事人地說:「為了盡早完成委託,找守墨來就最好的了。」
我說你太快進入狀態了吧!哪有人在門剛關上,便一聲不吭地放手下出來?
看著墨般的霧散向樓上,恭鶴蒼揮手一擺,準備往一樓搜查。
到這時我才能仔細打量這間屋子,走進能容納數十人共舞的大廳,圓形的大堂邊有兩條鑲著花紋的扶手樓梯,樓梯在平台上會合,其交合點上立著一座大概兩米高的古老大鐘,滴答滴答地搖晃鐘擺。
擺放大鐘的平台兩旁再有樓梯延伸,和二樓的看台連接。大廳左右兩側各有一條寬敞的走廊,看樣子是通往大宅內的。
這時一聲明顯的齒輪接合聲,大鐘接著響起了平穩安詳的鐘聲,在這大屋裡沉沉響著。
噹——噹——噹——噹——
把一切視若無睹的恭鶴蒼扭身向左邊的走廊,邊大步走著邊問我:「電話按了嗎?」
我連忙點頭說:「雖然差點忘了,但我還是有按下來。」在吐出另一句話前立刻亮出手機,我才能避免小孩子放過來的殺人視線。
哼了一聲,恭鶴蒼迅步行走的同時,扔我一個叮囑:「就算屋子是黑影先生的也不要大意──不想死就不要離開我。」
即使在窗外有溫和陽光的沐浴下,我還是對這間無人的寂靜大屋感到迷茫與不安,這提醒我,就算是世上最笨的人,也不會願意單獨行動。
「對了,你有來過黑竹籤的屋子?」總覺得這平靜的空間裡危機四伏,我壓抑著腦內的不祥想法問。
一臉平淡的恭鶴蒼說出嚇人的話:「可以的話,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踏入他的屋子。」
有這麼可怕嗎?
「就是不知道他的屋子裡有什麼,所以我才會召喚神一起找。」
原來是未知的可怕啊……
「說到底,什麼是召喚神啊……」終於抓到空隙,我看向如夢初醒,並且終於發現沒有跟我解說的恭鶴蒼。
「當作是日本的式神就好了,不過要記得,召喚神通常只有凡識的人才會使喚,而且要召喚的條件也比較麻煩。」
「式神嗎……那你有多少個召喚神?」
「四個。能改變外貌的容鏡、負責防守的守墨,還有兩隻打架很狠的傢伙。」
說到這裡,我不得不生出一個強烈的疑問:「既然有能攻能守的召喚神在,為什麼上次不叫他們出來?」有他們在至少會輕鬆一點,犯不著被揍到滿天飛吧?
預料到我會問這個,恭鶴蒼還是嘆一聲,沒好氣地說:「就說了喚出召喚神要有條件,像守墨他一定要在我身軀絲毫無損的情況下才肯出現。」
這條件有點兒怪呢,像嫌棄你的血一樣。
「這是他的要求,我也沒辦法。」小孩子聳聳肩,在擺著長桌的空蕩大飯廳裡看了幾眼後,便領著我在走廊上,快步走向大屋的更深處。
黑竹籤的屋子面積比在外面看到時還要大,從正門經過飯廳,再走過長廊上一整排的房間已經很花時間,更不用說要把房間逐一打開檢查。
雖然恭鶴蒼和我已努力地快速搜查,那個暴躁的活體火山,甚至連踹帶踢地踹門,但我們還是留在大屋左邊的位置,更不用說還有二樓。
風風火火地踹個沒完,耐性全無的恭鶴蒼回頭問我:「過了多久?」
「快十分鐘。」一直握著手機的我立刻回答,看到他焦急的嘖一聲,老早已埋下的不安感,更擴展至我心頭。
恭鶴蒼不是預定要花三天來完成委託嗎?為什麼從進屋起,便匆促不已地行動,就像和時間比拼一樣。
「蒼主人,守墨已找到大屋的入侵者。」
頭上突然傳出聲音,把稍不留意的我嚇了一跳,看到黑白分明的蒙眼神浮在半空向恭鶴蒼行了個禮。
為此喜出望外的小孩子大聲叫好,「快帶我去。」
遵命一聲後再行記禮,守墨轉身飄向轉角位,引領我們步上樓梯奔向二樓。
還在爬樓梯的小孩子高興得不像恭鶴蒼本人,說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看來不用兩天就能完成任務了。」
恭鶴蒼你是不是有什麼重要的事忘了告訴我啊!
◆ ◆ ◆
衝上二樓後直接拐進走廊,蒙眼神帶著我們跑到右側的房間,然後在一扇門前停下。
此時樓下傳來安穩的熟悉聲音,噹噹噹噹地又響了四遍,讓匆忙中的我不得不在意起來——鐘聲又響了?
「這裡?」追上去的恭鶴蒼卻像聽不到鐘聲一樣,象徵性地問一句,腳卻已經踹開門。
誰來教他基本的入門禮儀,你就不會敲門說聲我進來了嗎?
門十分脆弱地被小孩子一腳踢開,砰地在寂靜走廊裡發出巨響,在回音還未完全沉寂之前,房裡傳出一聲驚愕的狂怒咆哮。
「是你!」
吼叫像炮彈的轟炸聲,一個龐大的人影衝了出來,直直撞向被吼聲嚇到的小孩子,一併撞到牆上發出第二聲巨響。
完了!沒了!這樣一撞一壓,恭鶴蒼不變成肉餅,不就對不起壓在他身上那個滿身肌肉的男人!
大力一撞好像還沒能發洩肌肉男的滿腔驚怒,他抓緊身下的小孩,仿彿要用盡吃奶的力般,捏緊青筋暴現的拳頭,舉過頭頂作勢往死裡揍。
不好了!我大叫一聲,在肌肉男分神之際,我猛力撞開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當肌肉男被我撞飛,在半空一直飄著的守墨飛近主人立馬起了個結界。
負責防守的角色,為什麼要等被揍之後才發技能啊?
「在攻擊中開放結界,恕守墨做不到。」蒙眼神還是用著一副,恭敬得像系統預設般的態度說。
這是什麼玩網遊時,會蹦出來的技能限制提示!
蒙眼神沒再理會我,而是帶上隱隱關切的視線,看向靠在牆上的小孩子,「蒼主人您沒受傷吧?有的話請告知一聲,讓守墨回去。」
這是什麼使役!他真的是你的主人嗎?
被壓在牆上的小人兒咳了一聲,把一直護著頭縮起身的姿勢放下,艱辛地吐話:「沒事,就痛得發暈,你可以檢查一下。」
聞言還真檢查起來的守墨飄左又飄右,最後下了判定:「蒼主人果真無恙,那守墨依然留下。」
這不是主從,是上司下屬吧?而且是任性下屬仗著「我走了就沒人幫你工作」的態度,欺負無可奈何只能屈服的上司,這是種以下犯上的關係啊!
「阿雄哥!」
在我呆看這場奇怪的職場模擬劇時,打開的房間裡走出一個青年,看到地上抱著手臂吃痛的肌肉男後愣了一下,轉頭瞪視我,「臭小子,你竟然揍了阿雄哥!」
先生請你看懂情況,剛剛是你的阿雄哥想揍死恭鶴蒼!
怒火中燒的青年卷起衣袖,猛衝過來就想給我一拳,我嚇得立刻抱頭大叫。
「阿聰,停手!」厲聲一響,衝到眼前的拳頭停下,準被揍人的、準備被揍的,所有人的視線都望向房門的第三個人。
一位氣勢冷厲的短髮女人。
「可是這臭小子……」
「閉嘴,你們就不會看清楚再打嗎?」女人打斷青年的話,把他唬得不敢作聲。
走到恭鶴蒼面前,女人打量了幾秒,邊好奇他身上的褐色道袍,邊露出溫柔的笑,化開了臉上的冷酷。
「對不起呢小朋友,是那位大叔叔認錯人了才會揍了你,還痛嗎?沒事吧?」
不知道是平白無故挨了重擊,還是對方喊自己為小朋友,氣呼呼的恭鶴蒼生硬壓下怒火,悶聲哼句:「沒事。」
盡管不像沒事,但女人也沒再多理睬,只說聲「那樣就好」後,便叫青年扶起肌肉男。
在我和恭鶴蒼之間看了兩眼,她最後對上我說:「你們也是迷路到這屋子裡來的嗎?正好,我們三個遇到麻煩了,要你們幫忙,進來再說吧。」
完全沒有商量的餘地,女人掉頭就走入房間,只剩下我和恭鶴蒼兩眼互看。
還有頭頂那隻飄來飄去的蒙眼神恭順地說:「守墨好像還沒檢查蒼主人的背部呢,勞煩您站起來轉一圈好嗎?」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杜孽紀事(二)古宅裡的不速之客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132 |
輕小說 |
$ 174 |
奇幻 / 科幻小說 |
$ 194 |
驚悚/懸疑小說 |
$ 198 |
小說 |
$ 220 |
驚悚/懸疑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杜孽紀事(二)古宅裡的不速之客
★ 最驚悚卻也超爆笑——看杜同學今日會用怎樣的樂觀態度,面對悲觀的未來!
★ 兩款隨書附贈書籤——「小白兔」帥氣現身、「白毛醫生」溫柔登場!
★ 這次附錄四格將透露作者的真正意圖!原來,全都是因為……
要經歷一場生死關頭很簡單,只要做到以下三步驟。
一、接下老朋友黑影先生的驅逐委託。
二、調查老主顧向太太的兒子超渡事件。
三、捨命答應損友的登山尋找鬼屋大冒險。
順利完成以上三步驟的杜同學,正在努力逃命中。
困在那棟每十三年才現身一次的古宅裡,唯一的護身符——恭鶴蒼也和自己失散了。
無奈只好獨自一人亂闖,可杜同學這一闖,竟闖進了深深的謎團中。
杜家的家族使命?未曾聽過的危險身份?招來禍害的能力?
杜同學他想,這應該不是什麼紅顏禍水女主角要臥底殺敵兼復興老家的故事吧……
我清醒過來再哇聲大叫,連跑帶跳的跑下樓梯,衝到大門前的高柱後,才能夠轉身喘氣。
那一團團不祥的黑讓我胃痛,平台上的外國人把玩著黑火,看著氣喘吁吁卻又故作鎮定的
我,又一個一看就知道不是我能對付的傢伙,想起剛剛大廳裡彌漫滿天鬼氣,難不成我會像呆
頭鵝一樣,聽他的指示走上去,是因為被他魅惑了?
「拜託,你都說自己呆了,我還用得著魅惑嗎?」男人誇張地擺手,還露出一臉無奈。
作者簡介:
神紙
一頭能按鍵盤的熊。
老是認為自己名字裡有「熊」字。
每天睡上十小時再碼字十小時是熊生目標。
嗷嗷。
Blog
鬼燈暗照:shenzhik.pixnet.net/blog
相關著作
《杜孽紀事(一)路祭與問答》
章節試閱
「真的是這邊嗎?沒看錯地圖吧?」
「沒有,你繼續往上開去就行了。」
「怎麼你的朋友挑房子要挑這麼偏遠的地方?」
「他說喜歡這座山的名字,反正他就是個品味極怪的傢伙。」
駕駛座上傳來有一搭沒一搭的對話,讓我不費心神也能咀嚼出內容,更讓我在意的,是這輛車子給我的冷意。
星期三,是我復活節假期的第一天。
我答應恭鶴蒼的要求,把三天假期留給了他。
「真的沒問題嗎?」感受車裡的莫名寒意,我小聲喃道。
會錯意的恭鶴蒼扭頭扔了我一句:「別擔心,都說了有我在。」
說到這個我也憂心起來,但看到對方信心滿滿,我只好...
「沒有,你繼續往上開去就行了。」
「怎麼你的朋友挑房子要挑這麼偏遠的地方?」
「他說喜歡這座山的名字,反正他就是個品味極怪的傢伙。」
駕駛座上傳來有一搭沒一搭的對話,讓我不費心神也能咀嚼出內容,更讓我在意的,是這輛車子給我的冷意。
星期三,是我復活節假期的第一天。
我答應恭鶴蒼的要求,把三天假期留給了他。
「真的沒問題嗎?」感受車裡的莫名寒意,我小聲喃道。
會錯意的恭鶴蒼扭頭扔了我一句:「別擔心,都說了有我在。」
說到這個我也憂心起來,但看到對方信心滿滿,我只好...
»看全部
目錄
序 章
第一章「對不起是我錯了!」
第二章「我討厭和你對話!」
第三章「請給我們一個恰當的稱呼!」
第四章「女性真是個奇怪的存在!」
第五章「再看一次還是會怕!」
第六章「別老是忘記告訴我!」
第七章「你們就不能告訴我嗎!」
第八章「你真的不是人!」
第九章「還不是結束的時候!」
末 章
後 記
附 錄
第一章「對不起是我錯了!」
第二章「我討厭和你對話!」
第三章「請給我們一個恰當的稱呼!」
第四章「女性真是個奇怪的存在!」
第五章「再看一次還是會怕!」
第六章「別老是忘記告訴我!」
第七章「你們就不能告訴我嗎!」
第八章「你真的不是人!」
第九章「還不是結束的時候!」
末 章
後 記
附 錄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神紙
- 出版社: 麥田 出版日期:2014-01-10 ISBN/ISSN:978986344045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40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驚悚/懸疑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