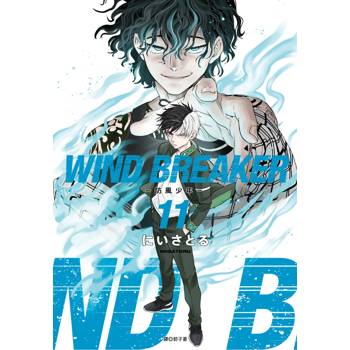本書以中國的美學原則為基礎,藉此取徑幫助我們對沈從文小說的美學面向有更一貫的認識。同時,作者也研究了沈從文人生後半段較不為人所知的作品。在討論其作家生涯之後,試圖探索他後期投入物質文化研究、反身性的作品,是否能夠讓我們洞察他邁入中晚年──從一九四九年兩度自殺到一九八八年逝世這段時間──自我認知的變化。
沈從文的作品中清楚顯示他一直嘗試了解人存在的本質。從一開始對鄉下人的欣賞,認為他們是連年天災與戰亂威脅下還自由自在活著的人,到否認「自由意志」的概念是一種控制的形式,沈從文一直屈服在未知的自然力量底下,也因此,「憂愁」成為他小說之中常見的主題。他辛苦走過個人啟蒙的第一階段,也就是知識化(intellectualisation)的過程,他在一九五○、六○與七○年代之間,處身於湖北與四川毫無邊際的自然山水中,但同時也完全理解自己所掌握的自由狀態,其實一直都是一種知識上的理想。在《另一種自由的追求》中,作者試圖跨越作品本身的歷史脈絡,挑戰把沈從文之作品視為一個整體的詮釋,進而尋找這位自喻「無從馴服的斑馬」的五四作家在知識與文學發展上的真實軌跡。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另一種自由的追求:沈從文美學研究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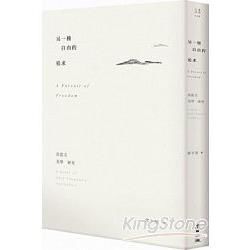 |
另一種自由的追求:沈從文美學研究 作者:邱于芸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14-02-13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88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86 |
小說/文學 |
二手書 |
$ 110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文字研究 / 文學綜論 |
$ 237 |
文學 |
$ 237 |
文學人物傳紀 |
$ 264 |
中文書 |
$ 300 |
藝術總論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內容簡介
目錄
推薦序 因愛而生的追尋
代序 沈從文與我
導論
第一章 作為「鄉下人」的沈從文
第二章 後期的自我書寫:鄉下人的堅持
第三章 沈從文的小說──論技巧
第四章 論中國物質文化:心與物遊
結語
注釋
書目
序
代序
沈從文與我
約莫二十多年前的一個秋夜裡,時值十八歲的我,匆促地決定遠行,正為一個沒有歸期的旅程準備著行囊,行李箱裡滿滿是為了一切未知而準備的衣物。
此刻的我,對於過去,我一無所戀;面對現在,也毫無辦法,只有未來如一雙大眼睛緊緊盯著我。皮箱裡,只能塞進一件剛買的羽絨衣,聖經紙印的英漢字典,還有幾包感冒藥、正露丸,幾盒中國結、臺灣茶,當成伴手禮。最後,似乎還少了點什麼,才想起該帶幾本聊以解悶的中文書,除了一本天下雜誌出的《發現臺灣》,我只挑了三本不大不小的散文書:《老伴》、《來客》與《鳳子》,作者—沈從文。
記得高二時,一位來自業界的國文老師在一堂讓我印象深刻的作文課裡,告誡著正直慘綠青年的我們:「如果你們能像沈從文一樣,被稱作大師的話,你們盡可以寫:『……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為「茶峒」的小山城時,有一小溪,溪邊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只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隻黃狗。』但如果還不是大師,最好乖乖的按照我說的方法寫你的文章。」我總覺得這不是對沈從文的誇獎,他那「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隻黃狗。」特別慢下來,顯得大聲。但我卻始終不記得他所謂的正規的開場是什麼,更不知道那段話就是《邊城》的第一段,但卻切切實實地把沈從文這名字給牢牢記住了。
這三本書其實來自我母親。因為人生的總總不巧,我與她在我小時候沒能同住在一個屋簷下,見面的機會極少,時間也不能長。一年也許不到一次兩次,正值青少年時期的我,每次見面,裡裡外外,一轉眼又是另一個孩子。她總是急躁地想把對我的言行舉止的觀察一一清點完畢,大多都是她不滿意的髮型、穿著等等。雖然常因意見不合而鬧得兩人不說話,而我卻每每利用在她家的時間,企圖探索一個平時不能接觸到的世界。當時的她正在廣告公司工作,茶几上總有許多雜誌跟最新出版的讀物,有如逛書店般,一落落滿滿散發著新書味道的書報,永遠令我玩味……《人間》、《當代》、《聯合文學》、《赫賽》、《佛洛姆》。儘管沈從文始終成了一個解不開的迷。玩心甚強的我,卻也把這事遠遠拋在腦後。然而最引起我興趣的,還是亮晶晶的服裝雜誌。
她總說「想看就拿去吧!」那一次,她大大稱讚了沈從文。但是滿載而歸回到住處後,翻閱著這些名著,對缺乏抽象思考的我來說簡直像極了無字天書,讓我從此有種陷入困境的感覺。在遠行前的前一夜,我在書架上又發現了這幾本沈從文,在這充滿告別氣氛的夜裡,卻成了一扇讓我隱約感覺到在英國可以跟臺灣這個母親連結的窗。
由於當時優雅博學的劍橋市對我這個沒文化的黃毛丫頭實在太無聊,店家早早打烊,也沒有像加州中國小店會賣賣臺灣過期書報。也就真如當初的打算,每每在念英文念到困頓、人生乏味的時候,翻開當初隨手裝箱的這幾本書,雖看不甚懂,但這難度讓我有種不得不敬畏它的神性,讓我不至於隨即陷入尋求人生捷徑的陳腔濫調,反而願意老老實實留在劍橋懺悔,重新做人。幽幽遠遠的湘西,有我理解母親的符碼,對生命高度有一種莫名的嚮往。對於人生,就這麼樣一點點地,慢慢地明白了點道理。
異鄉一待好幾年,直到大學入學前的暑假,我在香港無意逛到大大十一卷的《沈從文文集》,我似乎帶有那麼一點自主與義務性地買了兩套,一套送母親,一套搬來英國。這個舉動,開啟了我關注沈從文的起點。他所寫的故事也成為這兩位從未同住的母女話題中的最大公約數。每每讀到一篇新故事,或發現了他的生平事蹟,我都像個去討獎、等表揚的孩子,滔滔不絕地全盤托出。兩人從此易地而處,原來的陌生變成了熟悉。
母親長期獨處臺灣東海岸一個叫做鹽寮的地方,在倚山面海的小水泥屋裡,望著潮起潮落,每天為了與自然為鄰不曾間斷地勞動著,掃了又落,落了又掃的樹葉,為菜園除草驅蟲,上山巡視水源,每天劈柴燒水趕猴子。而遠在劍橋的我則與臺灣日夜顛倒地,望著綠意盎然的康河,聽著自己騎車踩出的鉸鍊喀啦聲穿透學院間中古時期的小巷弄,也是一天天挨著過,面對自己,也面對著排山倒海的課業壓力。
我養成了週六晚上睡覺前打電話給她的習慣,就像海浪日夜拍打著岸邊鵝卵石發出來的聲響,我和她的心智,就在這潮起潮落間磨成了細滑的輪廓,安靜了。
記得一個半夜,電話的另一端是她興致高昂,分享她偶然間發覺的感動。描述著她每天就寢前,總讀著沈從文的文章,從他的一字一句中,她了解到他細膩的情感,即使從未謀面,今生也絕無機會,但他已像是一位認識很久的朋友。我總在半夢半醒之間,聽到母親喜悅的情緒,這次,忽然有種不捨。感受到她的孤單,我倆依順著沈從文一生的沉浮,漸漸活出了自己的調性,漸漸知道人總要誠實地回到面對自己的現實。還有一次,也在劍橋夜深人靜時,我能夠親身感受到她所描述眼前東方乍現魚肚白的日出,終於知道什麼是「詩的境界」的那種驚喜與感動。
我也藉著與她幾年來漫長反覆沉澱討論中,感受到文字的力量,開始了我用下半個十年對文學的熱愛與追求。生命感知的歷程千軍萬馬地湧入在意識的前端,形成語言,化為了文字,透過作者的「安排」,我們感知到「存在」。存在於文字中,人又回到了生活,走遠了,文章在後面。好事者讀了,在其中起了作用,如遇知音,如暖流穿過。望著天上的繁星,與一位無從謀面的靈魂交談著。
沈從文的經歷與反思一直成為我自我檢定的標準,也一直期許著要成為一位自主如他的人,同時也能如此溫柔面對芸芸眾生。但是,卻是一直等到我念研究所時才決定要把他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
在那當下,留在英國度過餘生似乎已成為定局,當初離家時的打算,業已成真。帶著孩子,我必須找一個能夠藉以為生的工作技能,想來想去,除了教中文外,似乎沒有別的專長。於是寫了一個沈從文美學的研究計畫,我在信裡約略說了我與沈從文的關係,並老實地說,如果我需要花上好幾年學懂一件事,沈從文的一生會是一個值得做的選擇。我未來的指導教授蘇文瑜博士(Dr. SusanDaruvala),很快地就寄來了入學通知。
蘇文瑜是周作人專家,周作人在五四文壇裡,算是跟沈從文有過交集的。就這樣,我拜託劍橋大學圖書館,為我代訂一套剛剛出爐的《沈從文全集》(全三十三冊)。一個月以後我日以繼夜,展開了改變我一生的讀書計畫。
近一百年前,一個鄉下小兵,在一家新文學刊物做校對時,用極微薄的薪水訂了從北京寄來的「申報」,接受了五四的思潮,隻身到北京,想學點功夫,做一個有出息的讀書人。因為命運總總安排,諸事不順的情形下,他學寫文章,賺取稿費以餬口,幾年後,竟然也闖出了些名堂,成為五四文學的先鋒、鄉土文學的代表。
這個人就是沈從文。沅水和辰河流域的風土、世世代代的愛恨與哀愁,被他運用的文字,或畫或雕刻地,從紙面上跳了出來。他以流著屈原血液的熱情與悲憫自居,寫下《邊城》這樣的哀歌。那些水手縴夫的豪情與吊腳樓夜裡的每一晚都如訣別的最後纏綿,使鳳凰城如今有成千上萬名遊客朝聖。
二○○五年,我跋山涉水,也加入了千萬人的行列,拜訪了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中心,認識了許多花了一生研究沈從文的專家。我入住於一個有無線上網的吊腳樓裡,窗外是沱江裡一艘艘遊船,伴隨著的是用霓虹燈管裝飾的水中舞台,以及苗族少女用麥克風高歌遊客所點的臺灣歌謠──鄧麗君的〈小城故事〉。
穿梭於鳳凰城的小巷小弄,我的注意力不時落在店家內外玩耍的孩子上,或群聚或單獨拿著竹籤朝天比劃,或成群討論著如天大的行動,我見到了沈從文兒時的模樣。
和她的心智,就在這潮起潮落間磨成了細滑的輪廓,安靜了。
記得一個半夜,電話的另一端是她興致高昂,分享她偶然間發覺的感動。描述著她每天就寢前,總讀著沈從文的文章,從他的一字一句中,她了解到他細膩的情感,即使從未謀面,今生也絕無機會,但他已像是一位認識很久的朋友。我總在半夢半醒之間,聽到母親喜悅的情緒,這次,忽然有種不捨。感受到她的孤單,我倆依順著沈從文一生的沉浮,漸漸活出了自己的調性,漸漸知道人總要誠實地回到面對自己的現實。還有一次,也在劍橋夜深人靜時,我能夠親身感受到她所描述眼前東方乍現魚肚白的日出,終於知道什麼是「詩的境界」的那種驚喜與感動。
我也藉著與她幾年來漫長反覆沉澱討論中,感受到文字的力量,開始了我用下半個十年對文學的熱愛與追求。生命感知的歷程千軍萬馬地湧入在意識的前端,形成語言,化為了文字,透過作者的「安排」,我們感知到「存在」。存在於文字中,人又回到了生活,走遠了,文章在後面。好事者讀了,在其中起了作用,如遇知音,如暖流穿過。望著天上的繁星,與一位無從謀面的靈魂交談著。
沈從文的經歷與反思一直成為我自我檢定的標準,也一直期許著要成為一位自主如他的人,同時也能如此溫柔面對芸芸眾生。但是,卻是一直等到我念研究所時才決定要把他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
在那當下,留在英國度過餘生似乎已成為定局,當初離家時的打算,業已成真。帶著孩子,我必須找一個能夠藉以為生的工作技能,想來想去,除了教中文外,似乎沒有別的專長。於是寫了一個沈從文美學的研究計畫,我在信裡約略說了我與沈從文的關係,並老實地說,如果我需要花上好幾年學懂一件事,沈從文的一生會是一個值得做的選擇。我未來的指導教授蘇文瑜博士(Dr. Susan那堵隔絕蠻苗的城牆看來疲憊,上頭站的是無數靦腆面對相機的遊客,下方坐著一排兜售地方名產、頭頂花帕的苗婦。漢苗雜處的情景依然,取代打鐵店、線鋪子的是取名「從文」或「邊城」的旅店茶坊,外頭擺著一本本印刷精美的遊城導覽與沈氏的散文和小說。整條街的忙碌帶著一種鎮定與從容,耳邊迴響的是一段段一個遊子對故鄉的思念,化為文字,為他夢裡的湘西留下一個恰如其分的說明。
我在虹橋橋墩一家賣苗衣的攤位前停住了腳,循著斑駁的牆面掛滿的藍黑相間滾邊鮮豔的苗衣,看到一位遊客,盡著一位遊客的使命,專心地找一件紀念品。她朝著一位黝黑瘦小的男子問:「這件怎麼賣?」「一百二十塊錢!老東西,最後兩件了,收不到了!」他操著強烈的口音,語氣堅定,兩手匆忙地將牆上每件衣服拍平打直,眼睛不時的探索遊客的反應。「哪有的事?開玩笑!」這時帶路繞街的導遊從她身後跳出來打破了沉默。那位大哥毫不修飾,緊接著對遊客說:「妳喜歡這玩意兒?我帶妳去買!這錢夠妳買個五件、十件!」
我偷偷地望著那瘦小男子,遊客和導遊走遠了,那男子給了龍哥一個抱怨的眉頭,蹲下來,從口袋拿出菸來點,眼睛望著頭頂上,兩岸山邊以綠樹鑲成邊框的藍天。
沱江邊蹲著幾位少女拿著木棒敲打衣褲的聲音轉移了我的注意力,挨近江邊的棒子落在濕布上的低沉與不規律節奏,和踮著腳尖伸頭張望等著依次搭船遊江的外來客各自找到了平衡。小城裡的動靜雖因時空的不同改變了它的組合,吊腳樓裡,取代煙花女子和水手的打情罵俏聲是一邊端著海尼根一邊朝著酒保眉開眼笑的少女。沿街充滿的打鐵聲與叫賣豆腐腦的情調絲毫未因為賣的是泡沫紅茶而遞減,我依稀看到翠翠的爺爺進城打酒敏捷的腳步,和陪著翠翠逛大街的黃狗好奇雀躍的模樣。鳳凰街上人們頂著的豔陽同樣曾經在沈從文的文章裡滋養著翠翠,而書裡的陽光卻又走了出來照耀著我,對於人事,也就多了另一番體會。
回到劍橋,我依然日以繼夜地寫著博士論文,夜裡還是常常抱著電話跟母親討論著沈從文故事裡的奧祕,隨著他半世紀前的思辨,我強烈感覺到儘管載具千變萬化,作為一個永遠的知識分子,需要多少的篤定,才能不隨波逐流;要多少耐力,才能抵得住來自家庭、政治、社會各界的拉鋸。面對生而為人的苦難,我們又有多少勇氣能夠挺身而出。我不是一個作家,但我熟讀著他的每一句經典名句,用著他的寬容來與世界共處。「照我思索,可以理解我,照我思索,可以理解人。」我帶著這樣的神性,一點一滴建構我心中的世界,讓自己勇敢,除了付出,與世無爭。
感念這幾年來在劍橋的歲月,一路上,伴我成長的師長們,蘇文瑜與程思麗(Sally Church)。還有一群相互砥礪的夥伴與兩位可愛的孩子,東亞圖書館的馮南華女士、來自耶路撒冷的柯阿米拉教授、天資聰穎的藍詩玲(Julia Lovell)學姊、李約瑟研究中心的古克禮(Christopher Cullen)老闆,以及我所帶過的每一位學生。我在劍橋大學圖書館的茶室與花園裡與他們度過無盡的春夏秋冬。他們伴著我,永遠願意做我第一個聽眾、論文的第一位讀者。我也感謝體諒我的家人,對於從小頑固不羈的我,在這一路支持我走向一個有價無市的行業。這一切都是我的幸運,沒有大家,我不能夠在今天得以按照我對沈從文美學的認識,來建構我日後對文化、社會與個人修為的理論基礎。
最後感謝麥田出版社。在臺灣這個似乎已經沒什麼人記得沈從文的時代,面對湘西鳳凰快要淪為商業旅遊的犧牲品的時候,還願意藉由這本書來還原一個其實距離我們並不遠的年代,有一個拗直的鄉下人,用他的文學生命換取心中的自由,如此愛他的故鄉。而我也致力效法以「無從馴服的斑馬」自居的沈從文,用美與自由來愛我的故鄉。
邱于芸
二○一三年八月於臺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