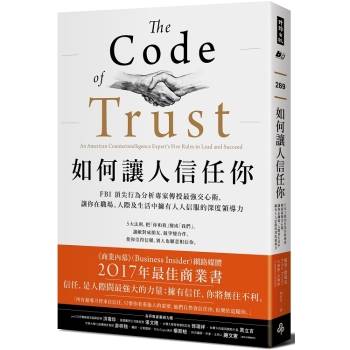反骨怪咖小說家──張萬康,繼「台灣文學獎金典獎」百萬長篇小說首獎《道濟群生錄》後,又一戲謔人生動人之作。
作家、編劇袁瓊瓊/專文推薦──「素人是可以亂入的;以亂入為表,內裡其實計算精準。看上去似是嬉笑怒罵,骨子裡卻懷抱巨大悲傷。」
「在我以為,俗民文學本無城鄉之分,至少我看我自己某種程度上就是在做俗民文學,說我的作品俗或不俗似都成立。說我的作品低等、低能、低級,我愈是當作恭維我優雅,我愈是感到我成功了。 」──張萬康
一個把「北原山貓」當作偶像的失業又離婚倒楣父親「我」,攜帶不斷以手機與女同學互傳曖昧簡訊的小學早熟兒子,搭乘火車北上,預備到台北一○一「找死」……
「我」的自殺之旅,充滿了隨遇而安的氛圍。「我」一下憂鬱,一下又充滿了詳和之感,偶爾甚至還感覺快樂。這個要去死的人,周身一點死亡氣息也沒有。
台北城裡沸騰的一○一夜店,龍蛇雜處著來自各方的族群;落魄的父親轉而混在其中,他能改變想自殺的命運嗎?最後該死的人又是誰?
小說以父子二人內心獨白的形式作為對話,無厘頭的劇情,呈顯世人們所處的當下,這個本來就攪和不清、混亂失序的世界,也抗議這個失衡的人生。
這樣一本或許應該界定為思考死亡(或思考生命)的書,卻被張萬康寫成了某種嘉年華,那些好鬥,雜交,嗑藥,醉生夢死,完全可以被界定為「社會所不齒」的群類,在張萬康的書寫下活蹦亂跳,生猛激突,似是比所謂的「正常人」,要活得更豐富更有生命感。
作者簡介:
張萬康
一九六七年生於台北蟾蜍山。
一九九○年文化大學美術系西畫組畢業。
二○○六年獲聯合報短篇小說首獎。
二○一一年出版長篇小說《道濟群生錄》、《摳我》。
二○一一年《道濟群生錄》獲台灣文學獎「金典獎」百萬長篇小說首獎。
二○一二年出版《ZONE¬──張萬康短篇小說選》。
相關著作
《ZONE--張萬康短篇小說集》
《摳我》
《道濟群生錄》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素人是可以亂入的--《笑的童話》序 / 袁瓊瓊
《笑的童話》是一個愛情故事。書中雖然不乏一些男人女人當眾宣淫的描寫,然而這愛情其實不是人與人之間的。書裡的愛情存在於男主角與世界之間。這位男主角無名無姓,只在某處出現過形跡可疑的「菲哥」二字,似是指男主角,又似是指某電視主持人,套用張萬康的句型就是:說是他也可以,說不是他也可以。
書中的這個「我」,整個的面目模糊。沒有他的長相,沒有他的職業,不知道他的知識水平,不知道他的年紀,不知道他哪裡人,本省或外省,只知道他「不是」山地人。對於「我」,我們比較知道的,不是他「是」什麼,而只是他「不是」什麼。
我們知道他「不是」有錢人,「不是」好丈夫,也「不是」好父親,甚至有可能「不是」個正常人。他經歷了什麼,作者沒有描寫,在故事開始的時候,「我」已經在生命的谷底,生意破產,老婆棄他而去,和念國小五年級的兒子相依為命,而似乎兒子照顧他比他照顧兒子的時候還多。
因為書中人物,從微不足道的腦性麻痺乘客,到「戲份」重大,對「我」的命運產生扭轉效果的海梨仔,張萬康都不吝描繪,讓人看到其形貌栩栩,所以我認為獨薄於這個「我」,是作者有意為之,或許模糊化可以造成一種普遍感,這個人物不只是他自己,還代表某個階層,某個群體。
而對這個「群體」的界定,並不是社會學那種。書裡的「我」,與其說是貧窮階層的代表,或者失敗或失意者的代表,我寧可認為他是那種熱愛生命熱愛世界,卻得不著相等回報的人。
在生命中的某一天,「我」決定自殺。他的自殺計劃是跳101大樓。帶著兒子,是因為想讓兒子目睹他跳樓的場面:
「孩子你會因我的死亡更強悍,更獨立。意外目睹我的一場死亡,或許有那麼幾年或更久你會感到恐懼,然而正因為這場遭遇你將不必也不再對任何事物懷以恐懼。」
「那是老爹盼望你強悍的手法。我把死亡作禮物送給你。你要懂爸爸,爸爸給的與其說是死亡,不如說是生命。只有死亡才能體現生命。」
這樣重大的命題,將死亡作為「生命禮物」來贈與。但是「我」的態度卻極為「憨顢」,甚至糊塗。
雖然「我」自己說自殺這件事他「醞釀已久」,但是他毫無計劃。忽然就決定要到學校接兒子。在去學校的路上,邊走邊做自創的平甩功「進階版」。學校正在上課,老師不讓他帶兒子走,他跟老師吵架,又隨口編了自己得癌症的理由。等老師終於放行,兒子的大書包成了問題,於是就索性出清內容物,打包寄走。
身上只得千把元,又還要帶兒子一同上台北,所以只好坐火車(他跟兒子說高鐵爛透了)。明明已經沒錢了,他還替隔壁座的大學女生買飲料和便當。結果到了101,剩下的錢不夠買門票,於是他讓兒子買兒童票上高樓去「觀賞」台北全景。自己那個要從高樓跳下來的計劃就此趕不上變化,宣告破滅。
「我」的自殺之旅,充滿了隨遇而安的氛圍,似乎「死不死」和「活不活」是可以相提並論的事。「我」一下憂鬱,一下又充滿了祥和之感,偶爾甚至還感覺快樂。
看張萬康的小說是個混亂的經驗,我得不斷的從自己現有的認知中退出,去嘗試理解「我」的生命情景。雖然一般看法,一個準備去死的人,還活得如此繽紛熱鬧,是非常奇怪的。通俗點講就是:這個要去死的人,周身一點「死亡的氣息」也沒有,甚至作者也不準備用陰暗的氣氛來干擾他。「我」看到什麼都讚嘆不已,好像透過死亡之眼發現新世界。看到女人他全想上,看到男人他全想挑釁。這樣一本,或許應該界定為思考死亡(或思考生命)的書,卻被張萬康寫成了某種嘉年華,那些好鬥,雜交,嗑藥,醉生夢死,完全可以被界定為「社會所不齒」的群類,在張萬康的書寫下活蹦亂跳,生猛激突,似是比所謂的「正常人」,要活得更豐富更有生命感。
張萬康從出道以來,外界一直有兩極化的評價。喜歡的極喜歡,厭惡的無法卒讀。我個人應該是兩種都有。在閱讀的時候,事實上同時在這兩種感受間進出。有些部份覺得「這傢伙亂寫」,有些部份卻覺得太厲害了。但是全書看完,卻不能不感覺內中有無以名之的,極粗糙,卻又廓然完全的什麼。
他的寫作渾似毫無章法,看不出脈絡結構。但是如此行雲流水,讓人不由得讓他帶來帶去,等到終於繞到了山停水窮之處,掩卷之餘,發現自己被張萬康帶著在遊樂場裡已經兜完了一整圈。故事在說什麼無所謂,重要的是你玩過了。
在書後附錄裡,張萬康解說他的寫作,用了「素人是可以亂入的」為自己開脫,事實上我以為這句話是張萬康「精神所在」,雖然現在已經是成名作家,不過張萬康一直保持素人精神,隨心所欲的亂入。這到底是某種天份,還是他自己刻意造作,進而成為他個人風格,這一點其實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以亂入為表,內裡其實計算精準。看上去似是嬉笑怒罵,骨子裡卻懷抱巨大悲傷。
在書的前半部,「我」帶著兒子坐在火車上。他感受著窗外雪山隧道的美景,又突然對隔座的大學女生產生了龐大的熱情。於是順理成章開始把妹。他跟女大學生擠到火車的小廁所裡,渴望發生點什麼,卻又臨時改變主意,讓對方全身而退。或許正因為準備結束生命,「我」反而看到生命之美無所不在。他對女大學生的那段幾近無厘頭的告白,若說是對著某個對象,不如說是對著這個世界。「我」對於這個世界的傾慕,深情,得不著回報,自覺受傷害,卻又依舊決定原諒。那整套的喃喃,雖然似是有個傾聽對象,其實更像是自我表白或某種控訴:
「只有我愛你,你一片空白。甚至你無法在一片空白中鍾愛我或需要我。你的角色只是聽,你無須回應。因為你太假了!
「我希望你好好聽,聽完還可能愛上我,但我沒差,我大不了犧牲自己讓你愛我。
「因為我是徹頭徹尾,包括在厠所的每一句我是用心對你說話的。的並且我不惜用自己的身體和你的身體對話,我的動作和你的動作對話。」
如同那位女大學生,世界對他的告白也並無回應。於是「我」說:
「不過我願意原諒你。」
赫拉巴爾為他的小說〈中魔的人們〉創了一個新詞:巴比代爾(PABITEL),赫拉巴爾自己解說「巴比代爾」是怎樣的一種人:
「這是一些身處極度灰暗之中而又能『透過鑽石眼孔』看到美的人。
他們善於從眼前生活中找到快樂,善於用幽默,哪怕是黑色幽默,
來極大的裝飾自己的每一天,甚至那些最悲慘的日子。
他們說出的話被那些理智的人看作是不合理的,
他們所做的事情是體面人不會去做的。
他們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彷彿語言選中了他,
要通過他的嘴巴來瞧見自己。」
我覺得赫拉巴爾這段話完整的形容了「我」在書裡所代表的族群。對於這類人的價值,我無法比赫拉巴爾說的更好了。
名人推薦:素人是可以亂入的--《笑的童話》序 / 袁瓊瓊
《笑的童話》是一個愛情故事。書中雖然不乏一些男人女人當眾宣淫的描寫,然而這愛情其實不是人與人之間的。書裡的愛情存在於男主角與世界之間。這位男主角無名無姓,只在某處出現過形跡可疑的「菲哥」二字,似是指男主角,又似是指某電視主持人,套用張萬康的句型就是:說是他也可以,說不是他也可以。
書中的這個「我」,整個的面目模糊。沒有他的長相,沒有他的職業,不知道他的知識水平,不知道他的年紀,不知道他哪裡人,本省或外省,只知道他「不是」山地人。對於...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旅途中
北原山貓
(唱)
原住民 原住民 長得不一樣
有的那麼黑 有的那麼白
有的那麼高 有的那麼矮
看來看過去 就是不一樣
原住民 原住民 長得不一樣
有的那麼瘦 有的那麼胖
有的那麼寬 有的那麼窄
看來看過去 就是不一樣
原住民 原住民 長得不一樣
有的那麼大 有的那麼小
有的那麼長 有的那麼短
看來看過去 就是不一樣
HO HAI YA NA
HOI YA NA HO HAI YA
米酒喝下去 什麼都不怕
子:
因為你個子還小,感覺不出走道很窄。爸爸還說,就算我們今天坐的是高鐵,走道也窄窄的。
不過我也沒想坐高鐵,我還是想坐飛機。爸說高鐵爛透了,自以為很快。我都沒坐過飛機。
爸一邊脫下書包,因為他幫我背,一邊叫坐在位子上的那個人起來,因為他佔了我們的座位。爸只呃……一聲,還沒講話,那個人就張開眼睛,迅速站起。他穿過我們面前時,爸對他說:「如果你真的很累,我們可以輪流坐。」那人沒看爸一眼,也沒搭腔,就挪到前面去了。他走出車廂,門「企」一聲打開,冷氣流竄進來,留給我們。爸把書包躺到我頭頂的鐵架。那個書包其實是空的。
坐靠車窗的那個姊姊在看我,那眼神好像說爸很多話。然後她把頭掉向窗外。我和爸被她拋開的速度比窗外景物被拋開的速度還快。我也不是很在乎她到底討不討厭爸,和我。
爸讓我坐在她旁邊,他要去後面坐,這樣可以從後面看著我吧我猜。如果他坐這裡就要轉頭,除非他很愛玩一二三木頭人。我延伸我的腳,玩了一次鐵踏板,升起和放下。我只玩一次,不然爸會說我沒規矩。
車廂內的座位客滿,有幾個人站著,爸是其中之一。嗯啊,原本他是有位子的,只是他買到的位子不是在我旁邊。讓我坐下後,他本來要過去我斜後方一段距離的一個位子,也是靠走道的位子,也是有一個人坐著,那個是爸買的座位。但他決定不過去了,用食指豎在鼻前,然後握拳,這是跟我比一個「不要出聲,沒關係」的手勢。我回頭看那邊,那個人有時站起,有時坐下,不是看有沒有佔到座位,而是看窗外,想知道這是哪一站的樣子。不過火車開始走的時候,我才發現他還有另一個原因讓他一直坐不穩。他身體搖搖晃晃,很難保持不動,脖子和臉歪歪的,不對,是身體半邊都歪歪的。爸小聲跟我說:「腦性麻痺。」他的脖子晃動的樣子好像隨時可以張開來變成傘蜥蜴。他的皮膚曬得很黑,頭髮也像曬成乾草。他穿的那件外套很鬆很大,方方的,看起來舊舊的,大概是從紅色褪成暗紅色,上面繡了白色的四個大字「NCAA」,有點像撿來的衣服。過一會兒他開始發出嘎嘎嘎嘎「火星語」的通話聲音,他的耳朵上面戴了一個藍芽耳機,正在跟某個首領進行接觸那樣,我只聽得懂幾個字:「……瓶蓋……黃道……活動中心……五個……」
我猜爸爸不想打擾他。我也覺得他有點可憐,我們學校發的運動夾克都比他的好看,爸就很愛我們的夾克。不過他都有藍芽耳機,超酷的,出任務,很有可能他是一個殺手,偽裝身體不靈活和口齒不清,而且是狙擊手,槍法神準。在月台時,爸問我冷嗎,我說不會。他研判說我穿的這件學校的棉夾克還蠻暖的,如果有做大號的他也想穿。我皺眉頭說大人穿很醜吧。他說藏青色配白線條很好看。我覺得搞不好是吧,但我還是告訴他很醜,他聽了哇哈哈笑。買票後,他說我們運氣普通好也普通差。我們買到的不是站票,這是普通好。我們的座位無法連在一起,必須分開坐,這是普通差。不過誰曉得他後來也沒得坐。當時他還說鐵路局很奇怪,站票的錢跟座票的錢一樣,如果能讓他買一張站票、一張座票,然後站票的錢可以半價,這樣我們就可以把這一半的錢用去台北吃好料。然後他說總之我是他的福星,還好不是兩張站票。不知道為什麼我聽了有點難過,我害了他,我這麼想。不過想到可以去台北,於是我又不難過了。我提醒爸爸:「你忘記講Molisaka。」爸回過神來,咧開他的大嘴:「Molisaka!」
〈摩莉莎卡〉,是北原山貓的一首歌。從我很小的時候喇,他就一直喜歡帶我唱他們的歌的喇,還要帶動作,跳舞那樣。他說過快樂不快樂都要喊Molisaka的喇。不快樂的時候,喊一聲就會快樂。快樂的時候喊了,快樂更多,像噴泉開花一樣開到破錶。他說喊「莎」的時候就可以把快樂整個套住,然後喊「卡」就可以很奸詐的把快樂收網那樣收回來。爸說北原山貓的合音比大小百合還讚,我也覺得!不過我沒聽過大小百合。
父:
早上做完李鳳山師父的平甩功,精神比較抖擻。走了一段路到學校,氣也走順了。我有心理準備會遇到點阻礙。
平甩功是站著甩手的簡易氣功運動。兩腿分開與肩同寬,手打直往前甩到肩膀的高度,連甩四下,第五下必須半蹲下來,也就是手臂划下來時腰部一鬆,蹲下。巧妙的是手往上帶起來的剎那,必須再蹲一次,起身時順便配合手把身子帶上來。也就是說你必須連續蹲兩次,但乍看又只有蹲一次,第二次像是鋼琴白鍵旁的黑鍵小半音,可以說是渾然太極之陰陽一分為二,二合為一。平甩功以十分鐘為一個基數。至少照三頓(餐)做一個基數,一天三個基數心曠神怡。想一口氣做個一、兩小時也不為過,雖然那種停不下來的姿勢或說狀態很好笑,但健康就是這麼盧進身體的。
開大門,走大路。在家做完一個基數,上路後,身體開了,我臨時決定邊走邊做平甩功。這是我的創意,對基本功的一種應用,學功夫最重要的就是應用。平甩功那一蹲蹲出了太極也是我個人的創見,我蠻想申請專利,呃……應該說是寫一篇論文投到報上的民意廣場,或健康版那種。不過還是算了吧,發明蚵仔麵線的人也沒申請專利,想一想還是古人大方豁達,孫越說「好東西和好朋友分享」,伍思凱則用發育中的歌喉唱〈分享〉,我沒有朋友,可是我還是想分享。人生來應該分享,不該獨享,這是我的看法。你說那老婆呢?真是老梗,但我笑了。
嗯,其實梗這個字應該寫成哏。有人告訴我這是相聲的術語。
邊走邊做平甩功真的很酷。問題是第五下要怎麼個蹲法。經試驗後發現,走路時腳步不是呈現一前一後嗎,我趁機踩一個弓箭步,這是頭一蹲,剎那間施點巧勁兒,流暢的又一蹲,身子就帶起來了。我一路邁大步街上走去,行人注意到我,等我越發流暢動作,我也忘記是否被注意。我覺得我成了一個上了發條的英國御林軍人偶,而且我對我自己進行閱兵。我一邊享受這般忘我,一邊化去我心裡的刺激和緊張情緒,因為我生命歷程的最後一場戰役才要展開。
其實,我多慮了,根本沒人注意我的動作。這世界,沒人會注意誰什麼了。交會的剎那也就岔開了,不會記住你多一秒。
難關在意料之中。班導不讓我把羽羽帶走。(發音「羽魚」,聽起來像只有「魚」。)這個男老師體格很壯,我覺得他應該去當體育老師。他比我高半個頭,Polo衫紮進牛仔褲,棉衫下隱約有厚實的胸肌。手臂超粗,還不必用到臂力,青筋觸到我就可以把我ㄉㄨㄞ死那樣。我說這不需要理由,他是我的兒子,這就是我要帶走他的理由。我低估了他,他不光是胸大無腦的體育健將,他說了一套我的行為將對小孩產生不良影響的理由。孩子對學習會失去尊重、容我坦率的說隨隨便便把小孩帶出學校又何必送來呢?很老套的連珠砲。我聽到尊重這兩個字,有點不悅,但還好我做過心理準備,並未發火。我淡淡的說:「你講得太嚴重,讓尊重失去空間。」其實我更想說的是,人只想尊重他的胃,而胃只想和食物彼此尊重,你害人家的胃液變酸。我告訴他:「因為羽羽習慣來上課,天亮了,我就讓他先來上課,我尊重天。在我……決定以前,我……必須尊重他。」他無可奈何,很客氣的冷笑一聲,於是我用手掌砍劈我的胸口那樣抵住自己:「是我的錯,我忘記阻止他。」
我們站在五年五班的走廊談判。漸漸我聽他講話時有聽沒到,望著教室內趁老師不在,從座位起來調皮打鬧的孩子。我用大拇指比著教室:「他們在你背後比較快樂。」他一看過去,小孩統統觸電一般回到座位。
「你看他的表情,他想跟我走。」我對老師這麼講,因為羽羽沒跟他們打鬧,一直朝我們注視,等待著答案。我察覺坐羽羽附近的一個小女孩也專注的望著我,從那表情我意識到她深愛羽羽,忽然我感到一陣幸福。肯定就是許鈺珊,電話裡我聽過她的聲音。
「抱歉我看不出來。」他的這句話幾乎激怒了我,尤其在這幸福的一瞬。
「我跟他比較熟,還是你跟他比較熟。」講完我盯著猛男不放。
他開始訴說他有著一份責任,聽到這兩個字使我必須壓制我自己的脾氣,我發現我的手開始發抖,搞不好之前比向教室的大拇指已經在抖。更可惡的是他接著說: 「孩子是你生的,但不是你的私人財產。」
#%^*&^##&^!~%))我語無倫次起來。我暗吃一驚,難道被識破什麼,當下兇起來:「我是要帶他去死嗎!」一口氣我繼續說:「說穿了死我一個人!我不拖孩子下水!」說完這句,我和猛男都怔住。我懊悔不小心說出帶走羽羽的目的。我趕緊做出一種強忍悲傷的模樣,扯了一個謊:「我必須和我兒子談談,我得了癌症。」
於是我成功劫走我兒子。那句話效果卓著,早知道一開始就這麼說。當他和老師錯身時,我在門口趕緊牽住他的手離開。我回身對老師講:「還有愛滋。」
沒人再能奪走他。好像從三年級以後我沒牽過他。否則怎麼訓練男孩成為男人。
子:
爸超愛北原山貓。他不止一次說過:「從你在你媽肚子裡的時候,就開始和我唱北原山貓跳舞了。」我心想難怪媽受不了你。
大人說這叫胎教。大人隔著肚皮會幫你點播一些歌來聽。爸說我是他創造出來的。他說不單單是聽習慣而已,而是北原山貓真的很好聽。他講這話的時候眼神也不能說多兇,……嗯!對,是正經。記得媽一旁說:「你幹嘛裝正經。」爸很正經的用眼睛看我的眼睛。我不得不同意他。
「不是裝正經,我只是裝神祕。」爸爸把食指立在鼻頭前這樣不動,五秒鐘過去,他突然燦笑。然後我笑出聲音。我很想告訴他,你不用裝正經我也會同意你,雖然我也不覺得多神祕。爸會讀心術,突然說:「現在還早,以後你會知道音樂的神祕,」他頓住,然後才講:「因為……」我搶著和他一起講出:「Molisaka!」
結果是我搶拍又搶白,他要講的不是這個。他愣了一下,兩手一攤:「Molisaka不是要這樣出來的。亂用就會不靈!你太愛喊它就是不懂它。」我沒搭腔,希望爸爸告訴我他原先想講的是什麼,但他接著講:「算了。」我想他真的會讀心術。
有次他醉酒。就是媽離開之後他常喝酒的那陣子,那次他對我說:「說真的我不認為你對北原山貓膩了。也可能你膩了,只是你還不知道。我愛不愛爸爸呢?」我聽不大懂,他是說他自己愛不愛他爸爸,還是模仿我、讀我的心說這句。說完,他發出恐怖的笑聲,接著喀喳一聲斷裂,坐倒在地上。他大笑不停:「椅子在這種時候總會斷掉,跟電影演的一樣。」我已喝醉了。我真的喝醉了。他就這樣唱。我很不願意他這樣唱,因為很難聽。記得他對我說過:「如果心情不痛快時,去唱北原山貓的歌就是污辱北原山貓,因為那只會讓你更不痛快。真心想快樂,你才能唱北原山貓的歌。」他身上散出不好的味道。我說:「不要唱。」他立刻用手刀切歌:「停!我沒忘記我說過的話!」他看起來很兇,我想我冒犯了他,不該提醒他。他是叫自己停也叫我停。「你懂嗎?你懂,我知道。羽羽啊,你是懂我的喇。」他好像很盼望,又好像對我有信心,我知道他在道歉。這時候他哭了。那次是我第一次聽他哭,這使我很難受,好像有人把他打流血,但我幫不上忙。「我一無所有了。我只剩下你。但我給你壓力。我對不起你羽羽。羽羽我不配的喇。」「我知道你很愛爸爸,但你發現不愛爸爸更舒服。」「我問你一個很沒必要問的問題,我和你媽,你比較喜歡誰?你自由講,我會保守祕密……」說著他又笑到前仆後仰:「我說的不是尿床,千萬不要誤會爸爸。我是說之前那個問題我想把它當成祕密。」他還繼續笑。我以為他忘了這問題,後來他笑到一個段落想起,追問。我很快就答:「我比較喜歡你。」但我真沒心情。他聽了對我用力豎起大拇指:「我要把它當成祕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還是要當祕密。因為有祕密的感覺才可以保留很久。」
然後手放下,往後揮落,他順便把手按在地面作支撐那樣,然後問:「那她如果回來帶你,你會不會跟她走?」我遲疑起來:「走多久?」他坐直起來:「為什麼?你媽很賤你知道嗎?」我說:「我知道。」他說:「理由?」我搖頭表示不知道。他突然用力打滾,背過身咆哮:「在軍中沒有理由!」回過臉來他帶著安慰的笑容說:「這裡不是軍中。」然後他說:「其實你只是好奇她在哪。正因為你不知道她在哪,所以你想跟著她。」我說:「沒錯。」他點點頭又搖起頭:「我不相信你比較愛她。」我突然想到許鈺珊對我說過:「喜歡和愛不一樣。」我想糾正爸,但算了。但我借用許鈺珊對我說過的一句話答覆他:「然而我是在乎你的。」爸聽了哇哇流淚,說我很孝順,並又開始講他對不起我。「我是有比較喜歡你,也不會想跟她走。」我蹲下來摟著他拍拍。我覺得我說的是真心話。爸哭得緩慢。「羽羽我沒事的。」這時我的眼淚滑出來。但我沒出聲音哭。然後爸說:「還好。」「唔?」我問。他說:「還好是夏天,不然我們這樣哭會感冒。」我說:「被你發現了。」
我不願像以前那樣嘗試扶他躺到床上,因為他很重。他嘴裡唱著山貓的〈布農族飲酒歌〉,他真的好快樂:
我已喝醉了。
我真的喝醉了。
請你原諒原諒我的
因為喝醉了
啊呀 MIS BU SUK SAI KIN
早上起床喝了一點點
中午晚上也喝一點點
不知不覺喝了多少
我要算一算
唉呀 喝了一大堆
啊呀 MIS BU SUK SAI KIN
而且他一唱歌就扭身體,更不好抓,我就讓他躺地板,把他姿勢喬一下,拿小毯子幫他蓋肚子。他說過肚臍是弱點。以前我嘗試把他拖到床上,搞得反效果鬧不完,而且我會哭起來,因為太重我真的沒辦法。爸媽以前常吵架的時候,記得我那時候已經小三,卻開始尿床一兩年,到媽消失了還繼續尿。直到升上小五才沒尿。那時候我實在很擔心,有次去表弟家住,因為一起睡我好怕我尿到他們身上。爸媽帶我看醫生,後來媽還買一種藥給我,什麼老阿伯膀胱丸的,還是沒辦法,半夜還是狂噴。大概就是從爸開始酗酒我才沒再尿床。我猜是他把我的水份吸收過去。以前我都包尿片,實在很怕同學看到。我看到蜜蜂就想起我包尿片。蜜蜂的屁股一大坨。萬一被同學發現,我猜我會被叫小蜜蜂。爸後來把藥丟掉,跟媽吼說我是心理因素,吼她不要在我面前吵架,媽說現在先大小聲的是你。但他們就算沒在我面前吵,我的情況還是沒改善,就像水龍頭故障。媽有次跟我說失火很需要你,我問她為什麼,爸衝過來罵她對小孩這麼刻薄,她哭說比刻薄沒人比你強,爸說我至少沒對孩子刻薄,我放火把家燒了算了。於是我大哭起來。從那次之後我就比較少哭,爸媽也沒再對我講嚇到我的話。雖然還是會尿。媽媽還是走了。
還好爸酒量很好,很少在吐。爸躺地上快睡著時,閉著眼睛咕嚕咕嚕:「如果兩個人之中有一個必須感冒,我希望那個人是我,但你不必陪我,不然會被我傳染。」爸一向很愛和我看戰爭片,有一部片班長受傷走不動,叫班兵先閃:「我以班長的身份命令你。GO!NOW!」起先他是叫班兵射殺他,班兵不願意,於是他命令他走,在他走之後,手中緊握一顆手榴彈準備和敵人同歸於盡,爸說這種片很蠢:「時間太多。」於是這時候我對爸說:「嘿咩,時間太多。」爸聽了沒搭腔,像一隻大烏賊放在地板上,漸漸睡著。我小小聲唱〈歡樂飲酒歌〉給他聽,這是慢版的飲酒歌,爸說過這首歌很有情調,會把人帶到遙遠的夢鄉。朋友們,大家一起來,喝了這杯老米酒,喝了它啊,不要隨便亂跑……
爸不是原住民,媽也不是。但爸就是愛北原山貓,他說他們不但是活寶,還是國寶。我們班都說北原山貓不紅,爸對我說偉人死後才紅,反之偉人死後就不紅的話那表示他不是偉人。他講到「紅」的時候把指頭對著我,講到「偉人」又指一次,很像交代一個重要的祕密給我那樣,也有點像發現我生字簿漏寫一行那樣。爸說他跟媽第一次約會,就是學北原山貓唱歌擄獲芳心的,因為媽喜歡笑。他說他還記得那首叫作〈快樂的台灣人〉,沒錯,也是合音很棒的一首歌。
「陶逽和周杰倫那不叫歌,那只叫唱片。」這是爸說的。我問爸唱片是什麼,搞了半天原來是CD。他說:「我習慣講唱片的喇。」
爸爸失業很久,發酒瘋也很久。我喊Molisaka顯然是沒用的。他摔完東西,會叫我:「不准收!」不准我去撿他K爛的東西。「節儉是種美德。留著,下次還可以摔。」他還怒吼,要我別再發出Molisaka,其實我不是故意的。有一次我勸不動他,也找不到我該說的話,好像被傳染喝醉一樣我無意中自言自語這麼一聲。他的反應傷透了我的心:「我是因為陪你玩,不知道要玩什麼才和你玩北原山貓的喇!其他的時候我不想再聽北原山貓!摩你媽雞巴莎卡洨啦!唱什麼山地歌啦,令老母攏跑去樹仔腳啊啦!」
但我原諒了他。第二天我上課時他還在睡。放學到家後,爸誇我很懂事。他沒談到他昨天的話是不是事實,我也沒想追問。就算他只是陪我玩才唱那些歌,那我更要感謝他。「那我以後還可以唱北原山貓和喊Molisaka嗎?」我故意這樣問他。他笑說:「我會跟你一起唱。」可見他記得他喝醉時說的話。
不過我想知道:「媽為什麼跑去樹仔腳?」這句他卻忘了。等他搞懂後,他說:「我亂講的。我也不知道她現在在哪,搞不好搬去山裡的別野去了吧。」我跟爸說:「應該唸別墅。」他笑說:「去你的,你很沒幽默感。」我被他惹笑。這時候他突然用力摟住我:「你放心!我會帶你去見識。我們找一天上台北。」其實我沒要求過這些,他這樣我突然覺得很監介。(尷尬)
想不到沒事先講,這天他來學校接我。我們走在走廊上,他牽我的那隻手離開,改搭在我肩上,神祕的對我說:「我有事告訴你。」我等著他說。他說:「學校還好吧。」我說:「嗯。」不知道他問這做什麼。「一切還好吧。」他又問。我說:「都好。」走出校門,他講:「我帶你去台北。」我說:「幹嘛?」他說:「玩。」
然後他就幫我背書包。平常我都自己背,問他為什麼這樣,他說:「我想背嘛!」好像撒嬌,真好笑。爸兩手空空的,單肩掛著我的書包:「好重,你書包放石頭喔。」我說:「哪有。」他說:「我猜你裡面藏了一頭大象,不過我背得動。」我說:「我也背得動。」他說:「但我更背得動。」我說:「你好愛爭。」他猛然瞪著我,很不悅那樣。他說:「我是在幫你!」我趕快講:「好啦好啦,我知道。」他送出一口氣,像是深呼吸後那樣呼出,手又搭到我這裡來:「是我太那個了。……你知道嗎?我對你有信心,你以後會比我強八百倍。」
好像有一件事在等他決定,他帶我在街上站了很久。
終於他開口:「我們用得上。」於是進到旁邊一家7-11,他填了單子,把書包裡的東西全部拿出來,花一元買了塑膠袋,把東西裝入袋內綁好,又掏出一把銅板,用宅急便寄出。他暫時叫我拎著空空的書包。他先填單子,填好後把書包接過來上肩和我出來。我看到他寫收件日期是明天。收件地址是我們學校。收件人他寫我們班導。爸說:「因為你的功課就是他的功課。」
第一章 旅途中
北原山貓
(唱)
原住民 原住民 長得不一樣
有的那麼黑 有的那麼白
有的那麼高 有的那麼矮
看來看過去 就是不一樣
原住民 原住民 長得不一樣
有的那麼瘦 有的那麼胖
有的那麼寬 有的那麼窄
看來看過去 就是不一樣
原住民 原住民 長得不一樣
有的那麼大 有的那麼小
有的那麼長 有的那麼短
看來看過去 就是不一樣
HO HAI YA NA
HOI YA NA HO HAI YA
米酒喝下去 什麼都不怕
子:
因為你個子還小,感覺不出走道很窄。爸爸還說,就算我們今天坐的是高鐵,走道也窄窄的。
不過我也...
目錄
推薦序:素人是可以亂入的──《笑的童話》序/袁瓊瓊
第○章 亂代序
他們或他
第一章 旅途中
北原山貓
旅途中
第二章 在台北
在台北-1
在台北-2
在台北-3
在台北-4
最後
跋-從田尾到花盆
附錄-給愛寫作、愛文學的蘭咖們
推薦序:素人是可以亂入的──《笑的童話》序/袁瓊瓊
第○章 亂代序
他們或他
第一章 旅途中
北原山貓
旅途中
第二章 在台北
在台北-1
在台北-2
在台北-3
在台北-4
最後
跋-從田尾到花盆
附錄-給愛寫作、愛文學的蘭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