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名稱:快樂的死
在一樁精心設計的謀殺案之後,梅爾索獲得了人人羨慕的財富,過著財富與時間都有充分餘裕的生活。然而,梅爾索仍然不幸福。
不滿足的他,企圖尋找人生下一個快樂的來源。在一生中,一個人如何感覺自我的滿足、生命的喜悅?因為穩定的情感關係、激情的性愛,抑或個人不受拘束的自由?
一九三八年,卡繆擱置自己的第一本小說《快樂的死》,開始撰寫《異鄉人》。本書直至他逝世後才出版。這本處女作小說富含對大自然栩栩如生的描述和對既有常規的批判省思。主角梅爾索一心追求快樂,哪怕必須以犯罪做為代價。卡繆本身艱困而充滿熱情的青春時期孕育了本書主角的經歷;他的抉擇和省思,也預告了卡繆日後的其他小說和論述。
作者介紹
卡繆Albert Camus
菸不離手、笑看人世、洞悉人性、擁抱荒謬的性格大師
◆一九一三年生於北非阿爾及利亞,一九六○年於法國車禍驟逝。
◆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與沙特並稱為二十世紀法國文壇雙璧。
◆文學上為存在主義大師,哲學上提出荒謬論,政治上曾先後投入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陣營。
◆著有小說《異鄉人》(L'Etranger)、《鼠疫》(La Peste)、《墮落》(La Chute)、《快樂的死》(La mort heureuse)、《第一人》(Le premier homme);短篇小說集《放逐與王國》(L'exil et le royaume);文集《非此非彼》(L'Envers et l'endroit)、《婚禮》(Noces)、《夏日》(L'Ete)、《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札記》(Carnets);劇作《卡利古拉》(Caligula)、《修女安魂曲》(Requiem pour une nonne)、《誤會》(Le Malentendu)、《戒嚴》(L'État de siège)、《正義之士》(Les Justes)、《附魔者》(Les Possédés)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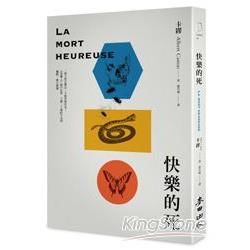
 2021/05/24
2021/05/24 2019/07/29
2019/0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