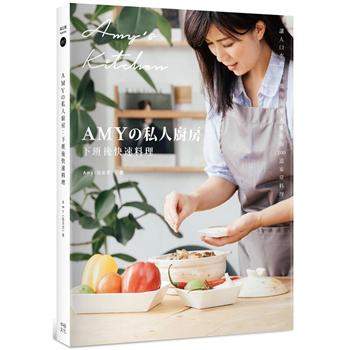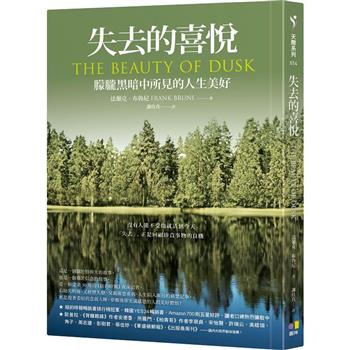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忠於自己靈魂的人:卡繆與《異鄉人》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當代華文世界解讀諾貝爾獎得主卡繆、《異鄉人》、「荒謬三部曲」最權威文本
知名作家楊照誠品講堂經典重現
何謂「荒謬」?何謂「存在」?「存在先於本質」又是什麼呢?存在主義是20世紀影響歐美的重要哲學思潮,當時法國文學的佼佼者幾乎皆是存在主義的大師,卡繆即為代表人物之一。相較於沙特的著作而言,即便是哲學論著的作品,卡繆的作品也都充滿了文學的風格與樂趣。
從卡繆知名作品《異鄉人》來看,他的思想體系最想要呈現的,就是「荒謬」。人的「存在」,常會尋找各種藉口,讓自己懷抱希望活下去──人因自由而活著,但關進監牢的囚犯還是繼續活著;人因財富而活著,但一貧如洗還是繼續活著──因此,在卡繆的觀點中,懷抱希望而活就是「荒謬」而非「誠實」的生活態度。
那麼,人有沒有可能不荒謬地活著?沒有了藉口、沒有了希望,還能忠於自己的靈魂而活?本書以「荒謬三部曲」的《薛西弗斯的神話》、《異鄉人》、《卡利古拉》為主軸,從文集、小說和戲劇等不同體裁,標示出潛藏在日常生活底下的「荒謬」,點出「存在主義」的真正本質,是理解卡繆與《異鄉人》的權威文本。
作者簡介
楊照
本名李明駿,一九六三年生,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曾任《明日報》總主筆、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台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新新聞》週報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等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News98電台「一點照新聞」、BRAVO FM91.3電台「閱讀音樂」、公共電視「人間相對論」節目主持人,並固定在「誠品講堂」、「敏隆講堂」、「趨勢講堂」及「天下文化人文空間」開設長期課程。
著有:
長篇小說──
《吹薩克斯風的革命者》、《大愛》、《暗巷迷夜》。
中短篇小說集──
《星星的末裔》、《黯魂》、《獨白》、《紅顏》、《往事追憶錄》、《背過身的瞬間》。
散文──
《軍旅札記》、《悲歡球場》、《場邊楊照》、《迷路的詩》、《Cafe Monday》、《新世紀散文家:楊照精選集》、《為了詩》、《故事效應》、《尋路青春》、《我想遇見你的人生:給女兒愛的書寫》。
文學文化評論集──
《流離觀點》、《文學的原像》、《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夢與灰燼》、《那些人那些故事》、《Taiwan Dreamer》、《知識分子的炫麗黃昏》、《問題年代》、《十年後的台灣》、《我的二十一世紀》、《在閱讀的密林中》、《理性的人》、《霧與畫:戰後台 灣文學史散論》、《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想樂》、《想樂2》,與馬家輝和胡洪俠合著《對照記@1963:22個日常生活詞彙》與《忽然懂了:對照記 @1963》。
現代經典細讀系列──
《還原演化論:重讀達爾文物種起源》、《頹廢、壓抑與昇華:解析夢的解析》、《永遠的少年:村上春樹與海邊的卡夫卡》、《馬奎斯與他的百年孤寂:活著是為了說故事》、《推理之門由此進:推理的四門必修課》、《對決人生:解讀海明威》、「中國傳統經典選讀系列叢書」。
譯作──
《老人與海》。
個人部落格:
tw.myblog.yahoo.com/mclee632008/
blog.roodo.com/yangzh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