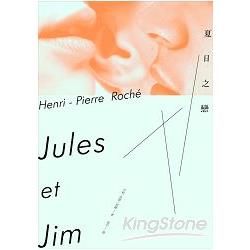亨利-皮耶.侯歇原著X楚浮導演X詩人夏宇譯作
2014年新版收錄〈詩人譯者夏宇答問:我為什麼翻譯《夏日之戀》〉
2014年新版收錄〈詩人譯者夏宇答問:我為什麼翻譯《夏日之戀》〉
法國新浪潮經典電影《夏日之戀》原著小說
從第一行開始,我對亨利-皮耶.侯歇的文筆一見傾心。──法國新浪潮導演楚浮
改編電影與原著的天作之合 楚浮與侯歇都讓對方更加燦爛──夏宇
她的微笑飄著。強大、青春、渴求吻,也渴求血,可能。
他們曾經見過這樣的微笑嗎?
如果有一天他們遇到了該怎麼辦呢?
《夏日之戀》是一部迷人緊湊的作品,既是小說,也以電報體般的文句談論愛情與友誼。法國新浪潮代表導演楚浮第一次看到此書時,驚為天人,「從第一行開始,我對亨利-皮耶.侯歇的文筆一見傾心。」本書改編電影並獲法國影藝學院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
本書描述兩個男人對同一個女人的愛,讀者難以因角色的善與惡做出抉擇,這種多面向的書寫觸動了楚浮改編電影,也誠如珍摩露在電影裡演唱的法國香頌:「如果我們注定邂逅,為何又要從彼此眼前消失?」《夏日之戀》的小說與電影將愛情的本質傳達得淋漓盡致,令人念念不忘。
從中歐來的居樂和法國人雋在巴黎相識後,開始了他們一見如故的情誼。兩人都是作家,在工作上互相幫助,也一同分享追求愛情的歷程。
他們的生活裡有許多談戀愛的機會,那些女人像是他們的母親,也可能是寵愛的女兒。他們有時候自己尋找情感的寄託,有時候互相介紹女性給對方認識,體會嫉妒、學會包容。在他們先後愛上凱茨的生活裡,三個人展開了含有純潔感情,且夾雜人性欲望的夏日戀曲……本書談論愛情的句子,尤其令人低迴不已:
「幸福很難以言辭描述,它被用舊磨損,而使用的人並不知道。」
「在愛情關係裡,至少要有一個人是忠實的,而那絕不是自己。」
「如果你願意,老的時候我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