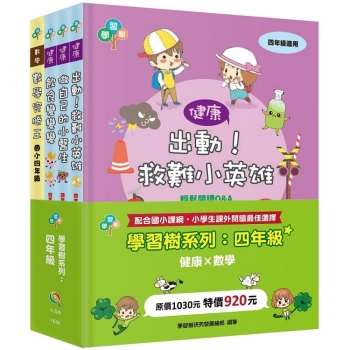我出生時就是人生的高峰。先父是貴族院議員,他用牛奶洗臉。他的兒子過得一天不如一天,需要靠寫文章掙錢。因此我可以理解所羅門王無盡的憂愁以及賤民的骯髒。──太宰治
太宰治的散文精華箴言集
收錄太宰治的重要語錄,集結成人生、文學與太宰治個人的三個面向,是一本適合從文字認識太宰治的精練札記。
太宰治最「不得已」的短篇
太宰治自述是為了創作《晚年》而生,若之後多活了些時間,不得已又再出了短篇集,他將為那本書取名為《歌留多》。
附錄有太宰治年表、關於太宰治及相關紀念場域介紹。
| FindBook |
有 18 項符合
太宰治的人生筆記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太宰治的人生筆記
內容簡介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