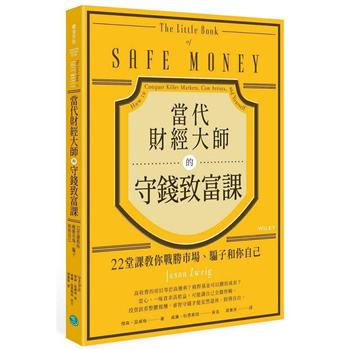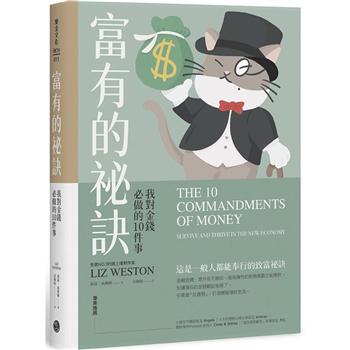食衣住行育樂,生活大小瑣事,人間事唯一法則,大概只有「累積」兩字。
人在公共場合,其實是眾目睽睽的。
活力十足的編劇家、作家袁瓊瓊,《壹周刊》專欄犀利觀察結集。
喜歡旅館勝於家,沒有手稿的作家,去個菜市場也感到振奮人心?!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我們整個人,無論外在內在,也不是一天造成的。
走過生命許多情感風暴,生活,在好玩也愛玩的袁瓊瓊眼裡,看見的是新鮮與有趣!
★我寫東西多半和當下時光與環境連結。我會把我的人物放在我正在寫稿的咖啡座旁,放在我正注視著的街道上。我會寫我感受到的天候溫度,身旁的聲音,色彩,氣味。於我,雖然在寫虛構的小說,但是一切其實就發生在當下。所以,注視自己的舊稿,注視過去的「舊自己」,真正的感覺其實往往是陌生,對那個人有點驚奇:「呀!原來我曾經這樣喔。」
當然,那一定還是你自己,只是大部分被自己遺忘了的。 ──袁瓊瓊
從一位宅男的死亡,到網路個人直播台的興起,自己孩子在校園中被霸凌的經驗,袁瓊瓊通曉「孤獨」的滋味,在其中卻也找到所謂「為人」的滋味與出口。
大量閱讀各類書籍、嗜愛電影,認為人生無法像電影,就算已經蓋棺論定,就算是已經結束的一段感情。因為跟我們有關,我們總是看不到全部,因為我們活在其中。有時候很難感覺生命是連貫的,一切似乎只存在於片段中,許多的碎片;我們經歷過的,或者在想像裡決定要經歷的那些人生,像放在拼圖盒子裡的小塊拼圖,只是個別的,不成畫面的小塊。
如果要喪失一種知覺?你會選擇什麼?
也許看世界的方式應該是不看。或說:看到「看」之外。
作者簡介:
袁瓊瓊
一九五○年出生於新竹市,原籍四川省眉山縣人。專業作家與電視編劇。早期曾以「朱陵」的筆名發表散文及新詩,更兼及童話故事。曾獲中外文學散文獎、聯合報小說獎、聯合報徵文散文首獎、時報文學獎首獎。著有散文《繾綣情書》、《孤單情書》、《紅塵心事》、《隨意》、《青春的天空》,小說《春水船》、《自己的天空》、《滄桑》、《或許,與愛無關》等多部作品,極短篇《袁瓊瓊極短篇》、《恐怖時代》等。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jade.yuan.14
電子書:https://readmoo.com/search/publisher/41
章節試閱
生活
有報刊採訪,需要拍照片,問說能不能來家裡拍?我正好最近準備搬家,屋子裡實在不成樣子,就說去咖啡館拍吧。對方很為難表示要拍的是「生活照」。意思似乎是:在家裡的影像會比較「生活」,或說在一個像是家的環境裡比較容易帶出被拍攝者的生活感,所以後來就去我母親家裡拍。雖然現在這個娘家,我幾乎不曾在其間生活過。我生長之地在台南。父母親把整個家搬到台北來時,我已經結婚,有了自己的家。
關於「生活照」,一般的看法大約是「非」登記照(護照和身分證上那種),或「非」藝術照(在攝影棚,有背景片和打光的那種)。「生活照」顧名思義是當事人在「生活」中的模樣。如果定義是這樣的話,說實話,泡咖啡館比較是我的「生活」,至少我在咖啡館裡待的時間比在娘家多。某些特定期間,甚至也比我待在自己居處時多。
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養成在咖啡館裡「生活」的習慣的,說實話時間太久,已經忘了。最初也是在家裡寫作的。在自己的桌前,看著自己的窗外。但是後來就成為在咖啡館裡寫稿的人。只要有稿紙和筆,幾乎就可以處處為家。從使用紙筆到使用電腦,從一張桌子到另一張桌子。雖然時常換桌子,很少換咖啡館。有一件事我百思不解。我會固定在某幾家咖啡館遊走,我是固定客人,但是幾乎不曾在咖啡館裡看到任何其他的「固定」客人。每天到咖啡館去就好像遊歷到新的社區或國度,除了店主,「風景」全部換新。
之所以喜歡泡咖啡館,跟寫劇本有關。寫劇本比寫小說「繁重」,不但量大,通常還得在一定時間內完成。往往忙得沒時間吃東西。在咖啡館寫稿的好處是一定有吃的,有喝的。到後來就發現還有另一項福利:可以看戲。
人在公共場合,其實是眾目睽睽的,被所有人看見,聽見。然而這種看見和聽見似乎當事人並不察覺,或不在乎。每次看到媒體記者拍到了一些應當是非常私密的影像時,我總是好奇那些人在做那些舉止時到底心裡在想什麼?是完全相信自己是隱形的?還是有輕微的表演心態?我猜人人都有多少戲劇性。有些人隱性,有些人顯性。以前陪模特兒到大陸拍泳裝照時,攝影師要某個小麻豆全裸出鏡。敝人女性意識稍強些,感覺這是莫大的對於女體的剝奪和侮辱。小麻豆拍完了照之後,我簡直快哭出來了,上前安慰她,問她是什麼感覺。小麻豆挺胸昂然回答:「我覺得我很美。」
我從此就明白果然每個人腦袋的構造是不一樣的。
我時常在咖啡館裡看見並且聽見故事。都是些斷片,適可以提供想像空間。兩個人低聲親密的嘁嘁窣窣,且說且笑,都不必聽清楚談話內容,就可以猜知必是在共享什麼祕密。也看過男女面對面坐,男方一臉沉重,然而明顯的心不在焉,女方卻含淚低訴,緊要處聲量拔高又放低,臉部表情在怒與悲之間來回。這種時候我總好奇他們在談判什麼。男女關係中,每一對情侶都多少會有這樣的時刻。而在那樣短的時間中,人的面部能夠變化出那樣多複雜和深刻的表情,尤其讓我覺得人人都有做演員的潛力。
在我,「生活」和家,並不必然有關聯。我大約這一兩年才比較常待在家裡。前些年都在外地。那個容納我的生活的場景,多半是旅館和飯店。每次出門,越來越簡單,頂多兩個皮箱。到了目的地之後才開始補一些必需物品。而離開的時候,那些物件便留在原地,並不跟我走。
會這樣簡潔,是因為多次出門的經驗。知道物件是依附於環境的,把甲地的東西帶到乙地去,除了紀念價值,真正用得上的,很少。而人是這樣容易遺忘,那些帶回來的「紀念品」,過了幾年,便渾忘了那些物品是哪裡來的,是為了什麼買的。而物品如果遺失了與自身相關的記憶,便成為廢物。而且是非常煩人的廢物,已然遺忘了它的意義,卻無法遺棄它。
我個人很喜歡飯店的生活。覺得它至少有以下的優點:有人來打掃清潔鋪床疊被。無論把房間弄亂到如何地步,出門一趟回來便煥然如新。當然用個菲傭也可以做到這點。但還是飯店這種「隱性」的僕人比較好。另外,因為空間不可能太大,會節制自己不要胡亂瞎拚,不小心買了一堆東西,放都沒地方放。我這些年生活在旅館,總是驚異於一個人需要的東西可以那麼少。只要有地方吃飯,有張床睡覺,有個電腦可以上網。幾乎就可以窩在旅館房間裡天長地久。
歐美偵探小說裡主角總是住在旅館。廉價的,破爛的小旅館,綠色的牆板,起毛的,骯髒的地毯。晚上睡覺時,窗外綠的紅的霓虹燈招牌一閃一閃。醉漢在窗外大聲叫囂,把酒瓶扔到窗玻璃上。隔壁房間裡尋歡的房客撞擊床板,發出哼叫。那是充滿慾望與情感的衝擊之地。福克納說過,一個小說家最適合居住的地方是「妓院樓上」。我相信住在這種廉價小旅館也是適合寫小說的。我認識一個人,在旅館裡住了快十年。我對他的旅館生活充滿幻想,後來他邀我去他住的地方。旅館已經被他住成了家。堆了他十年間累積的一切雜物,堆著他的衣服書籍碟片CD莫名其妙的小擺設他的酒他的菸他的垃圾。我很失望。
某方面來說,我的家這兩天的情形:到處堆疊著箱子布袋,家具打包綁在一塊,床板豎起來,書架拆成一片片豎起來,櫃子空了,桌子也分拆為腿與桌面……這些組成「家」的物件,一一被分解,失去它們原來的形狀,也失去功能,的,這種狀態,其實比完全裝置好,穩妥,固定的,泊止在地板上的情形,要更生動的解說了我的生活。我好像總是有一種要打碎或重組的心理。靜止往往讓我不安。固定讓我厭煩。而這些家具因為被拆解,忽然「存在分外分明」,慣用的器具,物品,在此時,一一被審核檢驗,那些要棄哪些要留;而棄或留的標準也與新舊或昂貴廉價無關。只與記憶有關。搬家的時候,被我攜帶離去的物事,和我棄置不睬的,各自標示了我的人生段落。標示了我的依賴,和不再依賴。
高樓
我去算命。算命師很年輕,看上去不到三十,戴金絲邊眼鏡,留長髮,油光水滑的梳到腦後去。穿唐裝。他那外貌很難讓人信服他的功力,但是價錢可以。他很貴。我朋友說他神準,她每年都找他算。又說他是「現代」算法,跟其他算命師不一樣。我那陣子狀況不好,到處算命聽到的說法都差不多,很想聽點不一樣的。很好奇這位懂得「現代」算法的算命師,會不會忽然給了我推翻那些「古典」算法的命理師給的答案。
倒也沒到「一命難求」的程度。打電話掛號,隨即便排上了。去的時候發現前面兩個正在算。等他們算完,我就進去了。
朋友跟他似是很熟,立即小小簡報一下我是幹什麼的。把我的背景我的遭遇我的心情……就是那些命理師應該自己從我的生辰八字裡看出來的資料全說出來了。我還沒開始算,已經覺得虧本,所以等「老師」(現在流行叫命理師「老師」)開口的時候,我就決定採取不合作主義,絕不透露任何訊息,而且要面無表情,不要讓他知道他算得準還是不準。
不過這老師還真能人也。果然不是普通算法。他先看我姓名,出生年月日,自己在一張白紙上嘩嘩嘩寫字,在字上頭用紅筆和藍筆拉線,果然十分「現代」,連我這算命老手都摸不清他用的是哪一門算法。如是演練數分鐘後,他說:「你住的地方太高。」
這一說,敝人馬上就「咦」出聲來,「不合作主義」立即破功,馬上問:「你怎麼知道?」
我喜歡住高樓。越高越好。還有老公的時候沒辦法,得適應對方可以接受的高度。後來從婚姻裡出逃,自己找房子,就住到了大廈頂樓。為什麼喜歡往高處去呢?實在不知道。總之就是喜歡高處,連坐百貨公司電梯,不管真正要去的是哪裡,每次都會一口氣直坐到頂層。尤其喜歡那種全透明的,掛在大樓外層的。電梯上升的時候,腳底下景物逐漸縮小,面前一無阻隔,整個世界在面前,而自己正在飛升……坐透明電梯是最接近飛翔的經驗。人在電梯裡,逐步凌頂,看著世界漸漸小去,猜想老鷹在飛翔的時候,眼中的世界就是這樣吧。
我總覺得高處自由。住得越高越自由。在高樓上,從窗口望出去,除了別的高樓,什麼也看不見。某種程度那是無人地帶,住一般高度的樓層,多少要防著外界的人,不想被窺看就得拉窗簾,音樂放太大聲怕吵到鄰居。但是住高樓上,似乎就不會被窺看也不會吵到鄰居了。雖然理論上,所有的高樓依然有樓下鄰居,甚至高樓旁邊也有高樓,但是奇怪的是,你就是覺得不會干擾到別人,也不會被別人干擾。那或許是住在高樓上的人彼此之間的默契,只要上到了數十層上,便任由每個人成為遺世獨立的個體,像《小王子》裡的描述,住在各自的小小星球上,擁有自己的小宇宙。
我一直住高樓。最高的住過三十二樓,那是在香港寫劇本的時候。到了這種高度,思想都會變得不一樣。每天從窗外看出去,一片雲霧茫茫,完全沒有現實感。你不覺得那是香港,事實上不覺得那在地球上。傍晚風起,整棟樓會咯噔咯噔搖晃,搖得還十分劇烈呢。但是我信任它是不會倒的,就安然享受這種搖籃曲。如果確定不會死也不會傷,沒有比地震來的時候更有趣的了。住高樓上,幾乎每天都可以享受這種小地震。整個房子隨風飄搖,俯在窗口上可以感覺那晃動。我總是驚奇,居然鋼骨水泥可以柔軟成這樣。
高樓上特別安靜,可能高處空間有吸音的作用,總之,我住高樓上通常聽不到雜音。窗外就是馬路,可是這樣高,看不見人,只看到車輛。那些火柴盒似的車輛,非常緩慢,安靜無聲。好像另一個世界,會有一種自己在天上的感覺。呆呆注視著滾滾紅塵,一切都那樣安靜,緩慢,漸漸的自己會發起呆來,看著空氣可以看很久。腦袋一片空白,而心跟著寧靜下來。我可以體會修行者要到高山上築茅廬的心情,不止於高處更接近天堂,重要的是高處能夠遠離塵囂。
一直到找這位「現代」命理師算命之前,我找房子都是越高越好,但是這位「老師」居然說:「你不能住高樓。」他說我運氣不好都是因為住得太高的緣故。我回想我這陣子的確都住得太高,也的確運氣不好。於是算完了命,馬上搬家。自然,住的不是高樓。
這位命理師說的其餘事項,事後證明完全不準。這個不宜住高樓的「指示」也不準。我後來想,他鐵口直斷我不該住高樓,大約是從我名字那個「瓊」字推衍出來的。「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一句,凡識字的應該都耳熟能詳。總之,我在七樓公寓的三樓住了七年。運勢一塌糊塗,全家雞飛狗跳。想是住得離塵世太近,樓下鄰居總是來敲門,嫌我們晚上太吵。樓上公寓漏水,漏到樓下去,樓下又來吵。而且公寓外正是馬路,一到夜晚就有人飆車,排氣管轟隆作響。比較有趣的是會有人喝醉了在路上吵架,前因後果字字分明。聽一段罵架,兩個人一生情史都可以猜出來。
我這幾年來一直住「非高樓」。近日搬新家,終於又回到了高處。我臥房裡一扇大窗,躺在床上就可以隔窗外望,要樓層太低,恐怕得設法遮人耳目,幸而是高樓,就連晚上就寢時都可以不拉窗簾,整座大窗上星光點點,有紅有綠……那是路燈和交通號誌給我製造的「地面上的星光」。
最近看到一篇報導:瑞士伯爾尼大學(Bern University)在二○一三年發表一項研究報告,說住在高樓的人,壽命比較長。原因之一是住高樓上比較不易受到空氣和噪音的汙染。住在高樓上,僅這一點就該值回「房」價吧。
手稿
最近接連碰到幾個展出單位跟我要手稿,讓我開始疑惑自己大約多少是個人物了。否則為什麼要我的手稿呢?手稿和照片一樣,無法獨立產生重要性,必定得附屬於某個人或某個事件,如果這個人或事沒有意義,手稿或照片也就沒有意義。過去幾乎沒有人跟我要過手稿,但是現在有了,有一家還說如果同意捐贈的話,將「永久典藏」。聽上去很是隆重。
但是我沒有手稿。至少是開始用電腦寫字之後便沒有手稿了。就除非對方只是想要我的筆跡,那一類倒是很多。便條紙一大堆:「某月某日必須交某稿數千字」,或「如果再不倒垃圾,不給零用錢」,那是給小孩的留話。以及「衛生紙/牙膏/牙刷/洗髮精/洗衣粉/環保垃圾袋/咖啡/冰淇淋」,那是購物清單。毛姆說過:「如果會看,購物清單上也有許多故事。」但是拿去展覽,未免為難觀眾的想像力。而且也太普通了。
我很遺憾自己的購物清單沒有更為勁爆的東西,例如「大麻三斤,情趣內衣一打」之類之類,那樣可讀性可能會高一點,不過生活沒法編造。購物清單是最誠實的東西,列在上面的都是我們在生命中消耗的物品,是真正的生活。仔細觀看自己的購物清單,會讓人興起虛無之感。這些白紙黑字在幽幽宣告我的人生被乏味的物件所圍繞,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永遠逃不出去。
講到「手稿」,我個人認為,照道理,作家「應該」是沒有自己的手稿的。至少我從來沒有。如果投稿被採用,「手稿」大半進了報社或雜誌社。如果沒被採用,這種「手稿」,猜想也不會有多少人有興趣。有一段時期流行用傳真發稿,我自己的習慣,如果確定稿件送過去了,「手稿」就直接扔垃圾桶。手寫的年代,尤其寫劇本,每天至少要出產十張以上稿紙,都留下來的話,那還得了。故此,我沒有手稿。並且是很多年以來,從來就沒有過「手稿」這東西。
我跟對方說我沒有手稿。他們便問能不能重新謄寫一遍。把自己的文章抄寫到稿紙上。嚴格來說,這不是手稿了,只是「手抄稿」。我以為手稿的意義,跟畫家的素描本一樣,重點在於「過程」。看知名畫家的素描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練筆的,也可以看出他如何逐步修改構圖。對照素描本和完成的作品,更能觀察出他的取捨。手稿的意義應該也在這裡。從字句的刪改增添,看作家在寫作時是怎麼思考的。
不過,也有人投稿時是重新抄寫過的,那個琢磨的過程不在稿件上。我早期寫稿也這樣,非常講究稿件的整齊清潔。然而這種手稿依然有可觀處。林語堂談書法之美時說過:欣賞書法不是看字體的形貌,而是從筆畫中看書法家的當時心情。他說:站在整幅書帖面前,從第一筆開始,一撇一捺,或勾或曳,隨著筆勢直看到最後一筆,會彷彿跟著書家在運筆時的心態完整的走了一遭。這所以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奉橘帖》和蘇軾的《寒食帖》能夠有那樣高的評價。不在於書法優美與否,而是筆畫中流動的氣韻,能在千年之下,一樣讓觀者如同身受。
手稿,即使是當時重新抄寫的手稿,也多少有這樣的力量。那是尚未面世的文章,那抄寫中有期待,有慎重,或也有多少的猶疑,你完全不知道它會成為怎樣,到底是曠世之作,還是讓人讀過即忘的,都不知道。那時的手稿,或也像所有的初生之物,含帶一切可能。
安德烈.莫洛亞的《巴爾札克傳》裡描寫過巴爾札克寫作時喜歡一改再改,往往一篇稿子會改得體無完膚,整段整段被塗掉,卻又在段落隙縫中落落長的加寫文句,寫不完的便拉線標示,牽到頁邊又寫上一大堆。二○一一年臺灣博物館展出巴爾札克文物展,現場看到他的手稿,才真正感受到大文豪的氣魄。那真是會讓排字工人生不如死的「手稿」。他不僅改自己的原作,還會在校樣上修改,「一部書稿要修改六七次,大刀闊斧,隨心所欲地改動,直到滿意為止;有時還會要求更改出版後的內容。一部二百頁的書,校樣合計起來往往都在二千頁以上。」
巴爾札克的手稿,呈現的不但是他的才華橫逸,還有他那種不拘小節的任性。他不知道世界上有兩種東西叫做「糨糊」和「剪刀」嗎?像他那樣大幅度修改文章我也不是沒做過,不過都會非常恭謹的去剪剪貼貼,倒也不是如何體貼排字工人,實在是擔心自己在稿件上到處牽拖,讓排字工目眩神迷,以至於指鹿為馬張冠李戴……。如果是詩稿還無所謂,現代詩一直被形容為「打翻排字盤」,排錯字說不定還成了神來之筆,但是其他文類便沒有這樣便利。中國字又是怎麼連好像都會對得上……總之,我想我那時的剪剪貼貼的「手稿」,多少也顯現了我自己對人性沒有太大信心的性格。不過那是「小時候」,這些年就大剌剌了許多,知道排錯幾個字(或幾行字)死不了人的。年輕的時候總有一大堆事覺得重要得不得了,年紀大之後便理解得讓一些重要的事「不重要」,否則會活得很費力的。
總之,花了一個上午很認真的在抄寫自己的小說,一邊抄一邊很感激自己小說裡都是對話,因此可以一句就跳一行,留一大堆空白。因為邀展的單位要我提供兩頁。
我已經多年沒有認真寫字了,多半只是「塗」字,往往一點事就占一頁,字體大大小小,如果忘記筆畫怎麼寫(用電腦之後常常這樣)就發明「符號字」,或者畫圖代替。橫豎自己看得懂就行。在一開始抄寫的時候,很是疙瘩,要記住自己的書上寫的是什麼,因為是舊作,自己寫些什麼差不多全忘光了。抄一句看一句,進度十分緩慢,然而,逐漸的,記憶回來,想起了當時為什麼給角色取這些名字,而哪些描寫是真有其人其事。
我的抄寫稿讓我短暫的回到了從前。我想這手稿被展出的時候,不會有任何人能夠看出這一點:我重溫了自己的舊日,手稿上有現在的我和過去的我,同時存在。
生活
有報刊採訪,需要拍照片,問說能不能來家裡拍?我正好最近準備搬家,屋子裡實在不成樣子,就說去咖啡館拍吧。對方很為難表示要拍的是「生活照」。意思似乎是:在家裡的影像會比較「生活」,或說在一個像是家的環境裡比較容易帶出被拍攝者的生活感,所以後來就去我母親家裡拍。雖然現在這個娘家,我幾乎不曾在其間生活過。我生長之地在台南。父母親把整個家搬到台北來時,我已經結婚,有了自己的家。
關於「生活照」,一般的看法大約是「非」登記照(護照和身分證上那種),或「非」藝術照(在攝影棚,有背景片和打光的那種)。「生...
作者序
看到「看」之外
時常胡思亂想,通常是我一個人的時候。坐在捷運上,搭公車,或只是在電影院門口等入場。周圍有很多人,但是我自己一個人。一個人的時候我總覺得世界與我無關,不必去交際寒暄,不必等待某個人,不必期待任何事發生。我只是鑲嵌在人群中,像彩色鑲嵌玻璃中的一片,我可能是綠色,或許紫色,或許明黃,看我在圖片中的哪一個部位。那種時候很微妙的會產生一種融合之感。感覺自己是美麗的,與世界一起美麗,但又是獨特的,獨特於所有人之外。
我胡思亂想的思緒其中有一項,時常會想到;就是,如若我必須喪失一種知覺,我會願意失去哪一種呢?視覺,聽覺,或是嗅覺?或味覺?
嚴格來說,在接近晚年的現在,這幾種知覺,我都或多或少在喪失中。曾經有接近十年的時間,吃什麼都覺得很難吃。不是沒有胃口。只是覺得世間食物都極難吃。但是會餓,所以仍是無知無覺的吃下去。或許環境與心境影響我的味覺,那時候過得非常不愉快。倒不致在痛苦中……或許就是在痛苦中,但是痛太久了變成麻木。總之那段期間對許多事物的感受都非常鈍,依靠這種鈍,安然的存活下去。太敏感有時是麻煩的。
小兒子嗅覺非常強,他時常突然來問我:「聞到什麼味道沒有?」我什麼都沒聞到。他會形容那味道,並且小狗一般在家裡循味道搜尋。看到他的情況,我確知我的嗅覺,近幾年,如不是喪失,至少也退化了。年輕時我應該是有嗅覺的,其證明是我寫的一些描寫氣味的文字。如果不是真正嗅聞到那些,我不可能編造出那些詭異的形容。不過目前,置身於任何環境中,我其實什麼都聞不到。我聞不到花香,也聞不到狗大便。不過我倒還記得經過麵包房,如果正好麵包出爐,便在店面附近,摻雜奶油和蜜的甜香團團裹著整家店,似某種防護罩,或者結界,有明顯的界線,一步跨出那味道便消失了,退回來便又有了。後來知道了「氣味」並不像想像中(或漫畫中畫的)是一縷煙氣,它其實是顆粒狀,會附著在物體表面。因之,我的感受或許是真實的,氣味的確有其範圍。在範圍內,氣味顆粒像編織物,或像霉菌,緊密的編織在一塊。或許不同氣味有不同形狀。團聚的氣味鑲嵌成看不見的彩色玻璃。祕密的自己美著。
我也記得在咖啡店裡,現磨咖啡豆的香氣,似有魔性般的,一種黑色的,幾乎熾熱的味道,像惡魔或天使,出現時並不準備停留,在你面前晃一下便消失了。咖啡的香氣是很奇妙的,沒有任何方式可以留住它。它出現便是為了離去。
聽覺倒還可以。雖然用插入式耳機凌虐耳膜多年,理論上它應該已經退化了。但是想聽的音樂和歌曲還是聽得見,當然要靠耳機。而在無法使用耳機的現實世界中,就總是聽見許多奇妙的聲音,有時候好像別人都沒聽見。偶爾聽見孩子們喊我,聽見我明白知道他不在我旁邊的人的聲音。或者聽見美好的,鳥叫聲,遠方傳來口哨,在百貨公司嘈雜的叫賣和音樂聲中,聽見流水般的豎琴。聲音本質是頻率,理論上,只要頻率調對,是可以聽到遠方聲音的。可以聽到眾聲中,唯一的,獨特的高音。
聲音對我很重要,「聽」似是比「看」空間更大,更富於想像。傾聽的時候會胡思亂想,想像聲音有無數顏色,人聲則想像那擁有它的喉嚨與胸腔。想像這聲音所從屬的形貌。當然這部分誤差很大。時常美好的聲音配屬的是乏味的人。我不太明白為什麼聲音往往最不像我們。我們自身的個性脾氣甚至習慣(就除非職業是播音員),從來不會顯現在聲音裡。福爾摩斯如果是瞎子,恐怕辦不了案。
因為重視聲音,因之,我總覺得,如果有個致命時刻要求我必須做選擇的話,我願意放棄的,應該是視覺。雖然想像中失去視覺有許多不方便。不過或許世界會因此而廣大。
美國盲詩人史蒂芬.庫希斯托(Stephen Kuusisto)在書裡寫過他「散步」的方式,他對於世界的辨認是靠著風,靠著空氣的溫度,氣味,靠著聲音,靠著地面的凹凸,軟硬,靠著觸撫到的事物:行道樹堅硬可靠的樹幹,路燈柱冰冷帶了腐鏽味的身體。靠著樹枝椏間葉片的低語,靠著行人足底與地面摩擦的節奏與聲響……在讀他的詩集時,我總覺得他給我們的日常事物新的詮釋。火不僅止於是明亮的,有熱度的,而水也絕非柔軟滑涼以及「薄」,或「清」,或「透明」,可以完全解說。
他的世界給我巨大的驚奇。可慶幸的是,要感受這世界,我不必真正喪失什麼,我只要關閉自己的視覺,像把窗關上,之後安靜的坐下來。
有時候看世界的方式應該是不看。或說:看到「看」之外。
看到「看」之外
時常胡思亂想,通常是我一個人的時候。坐在捷運上,搭公車,或只是在電影院門口等入場。周圍有很多人,但是我自己一個人。一個人的時候我總覺得世界與我無關,不必去交際寒暄,不必等待某個人,不必期待任何事發生。我只是鑲嵌在人群中,像彩色鑲嵌玻璃中的一片,我可能是綠色,或許紫色,或許明黃,看我在圖片中的哪一個部位。那種時候很微妙的會產生一種融合之感。感覺自己是美麗的,與世界一起美麗,但又是獨特的,獨特於所有人之外。
我胡思亂想的思緒其中有一項,時常會想到;就是,如若我必須喪失一種知覺,我會願...
目錄
序 看到「看」之外
輯一 我我我
生活
計程車
小市場人生
簡單的小幸福
手稿
影像與閱讀
來日無多
食生活
吃糖
高樓
我我我
輯二 孤獨電視台
宅男之逝
愛玩
霸凌
鬼故事
浪費人生
化妝
看電影
一天死了三次
相信
遊戲人生
夢二
孤獨電視台
看
不可思議
無意義的意義
阿基佑
地平線
吃素
發現
歐巴桑一日記
伏藏
閒
楊宗緯
好人變成魔鬼
輯三 不在場的人
哥倫布的巨船
不在場的人
荒野生存
老男孩
母親與女人
大家都愛吸血鬼
第十張餅
天使
變色龍的故事
序 看到「看」之外
輯一 我我我
生活
計程車
小市場人生
簡單的小幸福
手稿
影像與閱讀
來日無多
食生活
吃糖
高樓
我我我
輯二 孤獨電視台
宅男之逝
愛玩
霸凌
鬼故事
浪費人生
化妝
看電影
一天死了三次
相信
遊戲人生
夢二
孤獨電視台
看
不可思議
無意義的意義
阿基佑
地平線
吃素
發現
歐巴桑一日記
伏藏
閒
楊宗緯
好人變成魔鬼
輯三 不在場的人
哥倫布的巨船
不在場的人
荒野生存
老男孩
母親與女人
大家都愛吸血鬼
第十張餅
天使
變色龍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