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的題目不必是最時新的,卻應該是最根本的議題。「時空—身體—譬喻」是我這十幾年來陸續展開的研究主題,其中「相互定義」的視野正是打開二元僵局的關鍵;人身在宇宙四時流轉中,體驗順逆、離反的處境,並且透過不斷對話與創化的譬喻,更新與時推移的身心姿態。──鄭毓瑜
本書完整呈現鄭毓瑜教授近年來針對中國人文傳統「空間」觀的系列研究。從城市意象、園林寓意到國族視域、自然的氣氛,鄭教授融會各種歷史、思想與文學材料於一爐,同時又能妥切化用現象學、人文地理學等西方觀點;藉助這些閱讀與思考的成果,不但為古典文學開創出諸如「自然」、「身體」等新穎的研究議題,更顯現了文學與哲學、地理學,甚至是古典體氣醫療等相關領域的深刻關連。在強調跨領域整合的當代,這本書對於鄭教授個人的研究或整個中國人文傳統的研究,都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本書為全新增訂版,除了內容重新修訂外,也新增了〈由修禊事論蘭亭詩、蘭亭序「達」與「未達」的意義〉、〈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 ,展現了作者對「文本風景」歷久彌新且更豐富的主題詮釋。
本書特色
華人世界「中國人文抒情傳統」論述的重要著作!本書提供了該領域更開闊的視野與研究觀點。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全新增訂版)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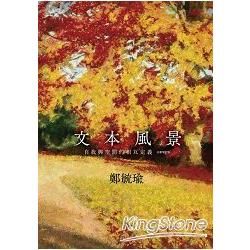 |
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全新增訂版) 作者:鄭毓瑜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14-12-2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48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增訂版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全新增訂版)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鄭毓瑜
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在學術研究方面,鄭教授擅長結合中西人文思潮,為古典文學開拓具有前瞻性與跨領域的視野,其中關於「空間」、「身體」與「抒情傳統」的論述尤為海內外注目。研究成果曾獲得教育部學術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國科會傑出學者研究計畫,胡適紀念講座,台大傑出專書獎,並曾獲美國Fulbright、國科會、蔣基會與Harvard、UCLA、UIUC、Princeton等著名學術機構獎助,出國研究與講學。著有《六朝文氣論探究》、《六朝情境美學》、《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等。
相關著作
《從摩羅到諾貝爾:文學‧經典‧現代意識》
鄭毓瑜
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在學術研究方面,鄭教授擅長結合中西人文思潮,為古典文學開拓具有前瞻性與跨領域的視野,其中關於「空間」、「身體」與「抒情傳統」的論述尤為海內外注目。研究成果曾獲得教育部學術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國科會傑出學者研究計畫,胡適紀念講座,台大傑出專書獎,並曾獲美國Fulbright、國科會、蔣基會與Harvard、UCLA、UIUC、Princeton等著名學術機構獎助,出國研究與講學。著有《六朝文氣論探究》、《六朝情境美學》、《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等。
相關著作
《從摩羅到諾貝爾:文學‧經典‧現代意識》
目錄
序:時空以外 ◎楊牧
導言:抒情自我的詮釋脈絡
單元一:意象化的城市
名士與都城-東晉「建康」論述
市井與圍城-南朝「建康」宮廷文化之一側面
單元二:文體與地方感
明清之際辭賦作品的「哀江南」論述--以夏完淳(大哀賦)為端緒的討論
流亡的風景--〈遊後樂園賦〉與朱舜水的遺民書寫
單元三:自然中的氣氛
(詩大序)的論釋界域--「抒情傳統」與類應世界觀
身體時氣感與漢魏「抒情」詩--漢魏文學與楚辭、月令的關係。
單元四: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
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
由修褉事論蘭亭詩、蘭亭序「達」與「未達」的意義
後記
附錄:《文本風景》書評/陳國球
導言:抒情自我的詮釋脈絡
單元一:意象化的城市
名士與都城-東晉「建康」論述
市井與圍城-南朝「建康」宮廷文化之一側面
單元二:文體與地方感
明清之際辭賦作品的「哀江南」論述--以夏完淳(大哀賦)為端緒的討論
流亡的風景--〈遊後樂園賦〉與朱舜水的遺民書寫
單元三:自然中的氣氛
(詩大序)的論釋界域--「抒情傳統」與類應世界觀
身體時氣感與漢魏「抒情」詩--漢魏文學與楚辭、月令的關係。
單元四:身體行動與地理種類
謝靈運〈山居賦〉與晉宋時期的「山川」、「山水」論述
由修褉事論蘭亭詩、蘭亭序「達」與「未達」的意義
後記
附錄:《文本風景》書評/陳國球
序
推薦序
序時空以外 / 楊牧
善讀書者一定看得見傳統文學之典麗幽微,透視文本,知道它是不孤立的,前有所承,後有所續,於嬗遞轉圜處產生意義。他揣摩作者謀篇的理路,試探其詞鋒,語躶,深入文章修辭規模的中心,有時甚至嘗試以意逆其志,是為閱讀策略之極致,一種令人神往的詮釋行為,接近了原初的創作動機。他看到層出無窮的意志和觀念在字裡行間流動,沸聲活活,洊勢潺潺,形象既繁複多樣,指涉復不失分明,都在他實踐的濾光鏡下各自擔負起語意折衝,勾勒,相互詮釋的責任--晷日繼之以黑夜的膏焚,使他得以通過深入比對和思考,把握到章句訓詁之鉅細而靡遺,認識時代地域的格調,風尚,以及文章賴以擴充完成的意象,進一步用來印證,說明典故和傳說等附屬,所以說他絕無懷疑,縱觀橫看,沒有一篇文章是孤立的。
雖然,我也聽到過有人埋怨,對早期漢文學異代互出的主題與風格不能容忍,視之為模仿重複,為思想與文體之退化、腐敗。有人讀杜詩「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認為是寫戰亂後植物蓊鬱豐美,一片繁榮新氣象,不知其所以然;再讀韋莊「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始覺悟到底詩人並不是著眼在寫春天美景,但國破怎能以「草木深」和「麥苗秀」表現?殊不知這正是傳統文學象徵系統準確,堅持的運作一例。其源出於王風:「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詩詠周東遷後,大夫行役過故都宗廟,見曩昔禮樂宮室盡皆荒蕪,為禾黍所取代,所以感嘆如此。簡言之,黍稷既不屬於宗周舊廟種植之農作,草木和麥苗也不屬於長安的大道街衢,目睹自然品物忽焉易位,更加重表達徬徨之心。而事實上,也唯有從古典原文考察,我們才能正確理解杜甫為什麼把「國」與「山河」齟齬錯置,反而造成最美麗,簡潔的文字效果,蓋國無非實際存在或存在過的城邑,即長安,如魏風「聊以行國」有限的範圍,和山河同樣是具體而非抽象,彼此的對應固然不可忽視,但須在人為聚落與自然界存在本體的異同處思考,才找到頭緒,領悟到古典的啟示。面對文本,不充足的詮釋固然可惜,過分閱讀也大可不必。若「池塘生春草」或「孟夏草木長」,前者無非就是蓄意於煩瑣處找到簡約,我們隨其上下文勉強進入那世界,感受它存在的理由或在其篇幅結構,但修辭學上的重要性竟無從說起。後者自然天成,彷彿就一筆帶過,不作勢深奧,不攀附,自成時序指示之規格,反而以無心機渲染更勝其餘,於六義中保留了一種介乎賦與興之間的祕密,還有一些比喻的因素,所以就不是孤立的。
我們把眼光轉到六朝都城的建康,就感覺到那三百餘年的歷史起伏,有一種幽遠的神詮秩序,初不僅只於宮室建築與地理形勢而已;綿亙成長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活動,以及它崇高的文化層面,我們風聞的傳說和深入的文章,更使我們相信,治文學史有習以時代分期解析共同主題與風格者,若是放在這個六朝「時期」來看,想當然是合理的。在建康都城的中心,郊野,邊緣,以及想像的空間與時間記憶最遙遠的夢之鄉陲,我們感覺到一些大雅人物共有的聲音,色彩,面貌,穿越不同的季候節氣,各自連結成黼黻有機之章,綰帶之以不朽的詩賦,環繞著那命運之城在永遠不斷地生長。
所以,當我們閱讀這大環境所催生的文化生命,揮之不去的當然是那些人物,勝過舊時代白下的軍壘或風景不殊的新亭,包括既賦〈遂初〉又諫遷都的孫綽,在清談與憂國間找到平衡的王導,庾亮,謝安,和雍容儀形,轉身又傲然嘯詠的周顗。他們和最完整的詩賦文章一樣,緣情體物有機進行,彼此詮釋。所以我們就在那一來一回的交談裡聽見微言大義,桓溫與孫綽,王羲之與謝安,因為言語論述到精妙處,智慧領先流露,而聲韻婉約,泠泠如絃上之音,是注定引起迴響,殆無可疑。
空間的設定如此,通過它可以讓我們回頭檢視那不世出的皇城,它的崛起和毀壞,再生,屈服,其規律圓融猶如一首五言詩,在江南的宮廷裡,市井中琢磨發光,如此確定不可移易的意象群,或持續自轉以導致變化的傳說和典故,隱喻與現實,廣泛的象徵體系,似乎都還不到完全定型的時候。但也好像有一天這一切都完成了,在我們來不及探明底細的時候,不知道是懷古,還是預言,無意間抬頭看到:一片降幡出石頭
若不是時間操縱它,難道我們可以說是空間以那俯視與仰望的巨眼,如此虛無地將時間限定,「築長圍以絕內外」,把所有斯文與側豔帶到一個終點?
鄭毓瑜教授將她近年環繞抒情傳統這個大題目所撰的論文六篇集成一帙,題為《文本風景》,其中第一單元兩篇的研究對象是東晉時代以及接下來南朝的建康,從一種紀律的角度檢視這金粉都城超越,繁複的意象世界,和它的宿命。我於閱讀之際,屢次為她冷肅的筆觸後點出的大量的同情體會覺得感動;想到有時面對古來的漢文學,還難免為其中的構成與敷衍動輒流於程式,為過度的鋪張,而產生反感,就知道我們需要的不一定是流行的批評理論,反而就是一貫的訓詁演練,和基本文學史觀的陶冶,以之推斷邏輯,找到詩的公理。這裡,我們看到一個方位分明的空間地域,一個無隱晦的光圈,被使用來照明特定時間裡多元的文化形態,突出人生的優遊和殘酷,終於又回歸文本,但不再僅是儼然禁錮的經典了。若第二單元所關注的,於一般騷賦瀏亮之外,又多了鉅大的勇毅和無窮悲憫,收束在晚明那一段悽惶無限的時間裡,指向江南,在更大的思想空間,體會烈士和遺民的意志,則文本裡舉哀的對象和虛設實有的園囿似乎更充滿了象徵張力,死難與流亡都是古來經典裡重複面對,思考的主題,也唯有在那持久延續的傳統裡最具意義。
上文提到傳統文學的構成與敷衍有時流於程式,甚至變成一種閱讀上的困擾。然則,我們又如何能將它順氣勢和傾向從頭整理,找到活力,並導向修辭學最上乘的表現體裁?創作者隨手之變,難以辭逮,但我們眼前攤開的文本傳承確定,不能增減,正在接受時間的考驗,普遍的質疑。況且,善讀書者更有責任為古典辯護,通過深刻精當的訓詁將它準確定位,繼之以解析,詮釋,還它活躍跳動的生氣,放置於調整的批評觀點之下,發現它所有典麗與幽微,彷彿是前所未有的,則甚至連續重出的章句,或近乎程式的表現方法,因為邏輯存在,正足以證明傳統文學之為想像和知識的累積,一種持平的創作方法,所以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的,前後有所繼承,產生美學和倫理的意義。
此書第三單元探討自然界的氣氛與詩的發生,展開,結束的關係,其中大篇幅評估漢魏時代抒情詩由無到有的過程,強調詩人對自然與文本的迎拒,於他的創作動機和方法,以及結果,具有一種辯證的力量。這就好像是說,所以,當陸士衡強調一個詩人的養成首先必須具有對時序推移的敏感──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恐怕只是一種隱喻修辭用語,細部結構仍有待參差的文本為他適時提供,其不可或無幾同於記載先人世德的大書,和一般「文章之林府」,而那有關時氣的文本特別令人覺得不可思議,例如: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氣奸陽。魚不上冰,甲冑私藏。驚蟄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雁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
這些近似農民曆的文字或許真介乎號稱夏代流傳下來的〈小正〉和《呂氏春秋》一類的月令之間,其實也可以說就是詩,如〈豳風‧七月〉云:「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𣵾下」,而詩是原來就有的,先於哲人之高瞻遠矚或深思熟慮而存在,或者如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所說,詩人就是秉諸神之志以探索,記述天地運作的睿智。從神詮的層次言,詩人創作的時氣感或從大自然季候變化的現實風景來,或自文本來,並無不同,其效果對他的詩的完成應該是一樣的。蓋文本曾經就是大自然風景的真實記載;唯其如此,詩人追求的時空就是無限,煙翳縹緲,訴諸具體的形象,付託給文字。毓瑜的論文集編就後,索序於我,可能因為她知道我早年曾作詩〈北斗行〉,試探天上星宿的預言奧祕,相對於人間玄想,至「搖光第七」遂以前引月令的季候節物檃栝度入,總結天樞以下七章之作。捧讀新書,愈增歲月之想。
(二○○五‧九‧台北)
序時空以外 / 楊牧
善讀書者一定看得見傳統文學之典麗幽微,透視文本,知道它是不孤立的,前有所承,後有所續,於嬗遞轉圜處產生意義。他揣摩作者謀篇的理路,試探其詞鋒,語躶,深入文章修辭規模的中心,有時甚至嘗試以意逆其志,是為閱讀策略之極致,一種令人神往的詮釋行為,接近了原初的創作動機。他看到層出無窮的意志和觀念在字裡行間流動,沸聲活活,洊勢潺潺,形象既繁複多樣,指涉復不失分明,都在他實踐的濾光鏡下各自擔負起語意折衝,勾勒,相互詮釋的責任--晷日繼之以黑夜的膏焚,使他得以通過深入比對和思考,把握到章句訓詁之鉅細而靡遺,認識時代地域的格調,風尚,以及文章賴以擴充完成的意象,進一步用來印證,說明典故和傳說等附屬,所以說他絕無懷疑,縱觀橫看,沒有一篇文章是孤立的。
雖然,我也聽到過有人埋怨,對早期漢文學異代互出的主題與風格不能容忍,視之為模仿重複,為思想與文體之退化、腐敗。有人讀杜詩「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認為是寫戰亂後植物蓊鬱豐美,一片繁榮新氣象,不知其所以然;再讀韋莊「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始覺悟到底詩人並不是著眼在寫春天美景,但國破怎能以「草木深」和「麥苗秀」表現?殊不知這正是傳統文學象徵系統準確,堅持的運作一例。其源出於王風:「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詩詠周東遷後,大夫行役過故都宗廟,見曩昔禮樂宮室盡皆荒蕪,為禾黍所取代,所以感嘆如此。簡言之,黍稷既不屬於宗周舊廟種植之農作,草木和麥苗也不屬於長安的大道街衢,目睹自然品物忽焉易位,更加重表達徬徨之心。而事實上,也唯有從古典原文考察,我們才能正確理解杜甫為什麼把「國」與「山河」齟齬錯置,反而造成最美麗,簡潔的文字效果,蓋國無非實際存在或存在過的城邑,即長安,如魏風「聊以行國」有限的範圍,和山河同樣是具體而非抽象,彼此的對應固然不可忽視,但須在人為聚落與自然界存在本體的異同處思考,才找到頭緒,領悟到古典的啟示。面對文本,不充足的詮釋固然可惜,過分閱讀也大可不必。若「池塘生春草」或「孟夏草木長」,前者無非就是蓄意於煩瑣處找到簡約,我們隨其上下文勉強進入那世界,感受它存在的理由或在其篇幅結構,但修辭學上的重要性竟無從說起。後者自然天成,彷彿就一筆帶過,不作勢深奧,不攀附,自成時序指示之規格,反而以無心機渲染更勝其餘,於六義中保留了一種介乎賦與興之間的祕密,還有一些比喻的因素,所以就不是孤立的。
我們把眼光轉到六朝都城的建康,就感覺到那三百餘年的歷史起伏,有一種幽遠的神詮秩序,初不僅只於宮室建築與地理形勢而已;綿亙成長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活動,以及它崇高的文化層面,我們風聞的傳說和深入的文章,更使我們相信,治文學史有習以時代分期解析共同主題與風格者,若是放在這個六朝「時期」來看,想當然是合理的。在建康都城的中心,郊野,邊緣,以及想像的空間與時間記憶最遙遠的夢之鄉陲,我們感覺到一些大雅人物共有的聲音,色彩,面貌,穿越不同的季候節氣,各自連結成黼黻有機之章,綰帶之以不朽的詩賦,環繞著那命運之城在永遠不斷地生長。
所以,當我們閱讀這大環境所催生的文化生命,揮之不去的當然是那些人物,勝過舊時代白下的軍壘或風景不殊的新亭,包括既賦〈遂初〉又諫遷都的孫綽,在清談與憂國間找到平衡的王導,庾亮,謝安,和雍容儀形,轉身又傲然嘯詠的周顗。他們和最完整的詩賦文章一樣,緣情體物有機進行,彼此詮釋。所以我們就在那一來一回的交談裡聽見微言大義,桓溫與孫綽,王羲之與謝安,因為言語論述到精妙處,智慧領先流露,而聲韻婉約,泠泠如絃上之音,是注定引起迴響,殆無可疑。
空間的設定如此,通過它可以讓我們回頭檢視那不世出的皇城,它的崛起和毀壞,再生,屈服,其規律圓融猶如一首五言詩,在江南的宮廷裡,市井中琢磨發光,如此確定不可移易的意象群,或持續自轉以導致變化的傳說和典故,隱喻與現實,廣泛的象徵體系,似乎都還不到完全定型的時候。但也好像有一天這一切都完成了,在我們來不及探明底細的時候,不知道是懷古,還是預言,無意間抬頭看到:一片降幡出石頭
若不是時間操縱它,難道我們可以說是空間以那俯視與仰望的巨眼,如此虛無地將時間限定,「築長圍以絕內外」,把所有斯文與側豔帶到一個終點?
鄭毓瑜教授將她近年環繞抒情傳統這個大題目所撰的論文六篇集成一帙,題為《文本風景》,其中第一單元兩篇的研究對象是東晉時代以及接下來南朝的建康,從一種紀律的角度檢視這金粉都城超越,繁複的意象世界,和它的宿命。我於閱讀之際,屢次為她冷肅的筆觸後點出的大量的同情體會覺得感動;想到有時面對古來的漢文學,還難免為其中的構成與敷衍動輒流於程式,為過度的鋪張,而產生反感,就知道我們需要的不一定是流行的批評理論,反而就是一貫的訓詁演練,和基本文學史觀的陶冶,以之推斷邏輯,找到詩的公理。這裡,我們看到一個方位分明的空間地域,一個無隱晦的光圈,被使用來照明特定時間裡多元的文化形態,突出人生的優遊和殘酷,終於又回歸文本,但不再僅是儼然禁錮的經典了。若第二單元所關注的,於一般騷賦瀏亮之外,又多了鉅大的勇毅和無窮悲憫,收束在晚明那一段悽惶無限的時間裡,指向江南,在更大的思想空間,體會烈士和遺民的意志,則文本裡舉哀的對象和虛設實有的園囿似乎更充滿了象徵張力,死難與流亡都是古來經典裡重複面對,思考的主題,也唯有在那持久延續的傳統裡最具意義。
上文提到傳統文學的構成與敷衍有時流於程式,甚至變成一種閱讀上的困擾。然則,我們又如何能將它順氣勢和傾向從頭整理,找到活力,並導向修辭學最上乘的表現體裁?創作者隨手之變,難以辭逮,但我們眼前攤開的文本傳承確定,不能增減,正在接受時間的考驗,普遍的質疑。況且,善讀書者更有責任為古典辯護,通過深刻精當的訓詁將它準確定位,繼之以解析,詮釋,還它活躍跳動的生氣,放置於調整的批評觀點之下,發現它所有典麗與幽微,彷彿是前所未有的,則甚至連續重出的章句,或近乎程式的表現方法,因為邏輯存在,正足以證明傳統文學之為想像和知識的累積,一種持平的創作方法,所以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的,前後有所繼承,產生美學和倫理的意義。
此書第三單元探討自然界的氣氛與詩的發生,展開,結束的關係,其中大篇幅評估漢魏時代抒情詩由無到有的過程,強調詩人對自然與文本的迎拒,於他的創作動機和方法,以及結果,具有一種辯證的力量。這就好像是說,所以,當陸士衡強調一個詩人的養成首先必須具有對時序推移的敏感──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恐怕只是一種隱喻修辭用語,細部結構仍有待參差的文本為他適時提供,其不可或無幾同於記載先人世德的大書,和一般「文章之林府」,而那有關時氣的文本特別令人覺得不可思議,例如: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氣奸陽。魚不上冰,甲冑私藏。驚蟄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雁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
這些近似農民曆的文字或許真介乎號稱夏代流傳下來的〈小正〉和《呂氏春秋》一類的月令之間,其實也可以說就是詩,如〈豳風‧七月〉云:「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𣵾下」,而詩是原來就有的,先於哲人之高瞻遠矚或深思熟慮而存在,或者如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所說,詩人就是秉諸神之志以探索,記述天地運作的睿智。從神詮的層次言,詩人創作的時氣感或從大自然季候變化的現實風景來,或自文本來,並無不同,其效果對他的詩的完成應該是一樣的。蓋文本曾經就是大自然風景的真實記載;唯其如此,詩人追求的時空就是無限,煙翳縹緲,訴諸具體的形象,付託給文字。毓瑜的論文集編就後,索序於我,可能因為她知道我早年曾作詩〈北斗行〉,試探天上星宿的預言奧祕,相對於人間玄想,至「搖光第七」遂以前引月令的季候節物檃栝度入,總結天樞以下七章之作。捧讀新書,愈增歲月之想。
(二○○五‧九‧台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