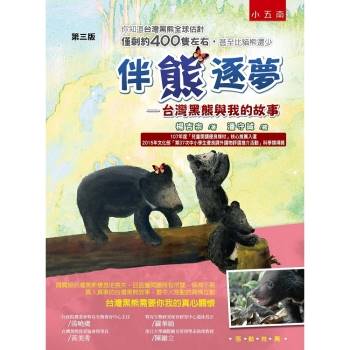我寫日記,憑弔從生命中消失無蹤的人,
然而,無論怎麼眨眼,他們的身影都無法再出現在我的視網膜上。
《博士熱愛的算式》、《人質朗讀會》作者
本屋大獎、芥川獎、谷崎潤一郎獎得主
小川洋子藉由平凡深入人心,從虛幻尋找真實的動人之作。
即使眷戀的都已離去,在一無所有前,也要用文字記錄屬於我自己的回憶。
計畫撰寫長篇小說的女作家,預計創作的作品遲遲沒有進展,卻在日記裡記下了一年內許多奇異的體驗。原本只是記錄日常生活的文字,卻意外讓她遁入虛幻的回憶之中,遺失了現實與幻想的界線……
為小說構思路途上的溫泉旅館,享用了長在動物屍體上的苔癬大餐;
偷偷潛入附近小學觀賞運動會,竟然意外上場參加賽跑;
在報紙上看見有關剽竊的新聞,想起自己也曾剽竊文學大師的作品,但沒人發現;
參觀神社舉辦的「嬰兒哭泣相撲」比賽,差點成功偷走一名男嬰;
重複閱讀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腦海則不斷浮現小時候弟弟吸吮她手指的畫面;
到遙遠的城市參訪現代藝術節,六個人在導遊的帶領下出發,卻只有兩人回來;
到醫院探視失去語言能力的母親,為她剪指甲,接著燃燒指甲,散發出焚屍的味道;
在失去靈感的夜晚抄寫深海魚圖鑑,想像自己在陽光照射不到的海底悠游,漸漸融入四周的黑暗之中......
作者簡介:
小川洋子
一九六二年出生於日本岡山縣,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院文藝系畢業。一九八八年,《毀滅黃粉蝶的時候》獲第七屆海燕新人文學獎;一九九一年,〈妊娠月曆〉獲得第一○四屆芥川獎;二○○四年,以《博士熱愛的算式》獲得讀賣文學獎、本屋大獎,以《婆羅門的埋葬》獲得泉鏡花文學獎;二○○六年,以《米娜的行進》獲得谷崎潤一郎獎。主要著作有《人質朗讀會》、《沉默博物館》、《博士熱愛的算式》、《祕密結晶》、《貴婦人Α的甦醒》、《無名指的標本》、《抱著貓,與大象一起游泳》、《米娜的行進》等多部作品。
其筆鋒冷歛,早期作品多描寫人性的陰暗和殘酷,三十歲之後有所轉變,特別是為《安妮.法蘭克的記憶》前往波蘭奧許維茲集中營採訪時,感受到「人類是如此殘酷,卻也如此偉大」,寫作風格因而轉變,「不再尖銳地刻畫、暴露人類深藏的惡意」,而能夠以「人類是善惡共同體」的態度看待他人,並且開始撰寫與記憶有關的主題。
小川洋子是繼村上春樹之後最受日本國內外文壇矚目的文學作家,其作品在歐洲受到極大的迴響,法、德、西、義均有譯本,且經常舉辦朗讀會朗讀其作品,《無名指的標本》原著更在法國改拍成電影,受喜愛程度可見一斑。
譯者簡介:
王蘊潔
在翻譯領域打滾十幾年,曾經譯介山崎豐子、小川洋子、白石一文等多位文壇重量級作家的著作,用心對待經手的每一部作品。譯有《博士熱愛的算式》、《永遠在身邊》、《宛如阿修羅》等,翻譯的文學作品數量已超越體重。部落格:綿羊的譯心譯意translation.pixnet.net/blog
章節試閱
九月某日(星期五)
為了長篇小說的採訪工作,參觀完宇宙射線研究所後,去F溫泉旅館投宿。
計程車在山裡開了很久很久,彷彿這一路永遠都開不到盡頭。沿途幾乎沒有遇到任何車子,兩側車窗外,只看到重重疊疊的巨樹林,即使水壩湖、飼養熊的牧場和養魚場偶爾從樹幹的縫隙中探出頭,也很快再度消失在樹木後方。層巒疊嶂之間的天空只剩下一小片,呈現出混濁的灰色。
「秋天落葉季節時,這一帶也很熱鬧吧?」
「不,也沒有。」
沉默寡言的司機只會說這句話。
「這裡的海拔差不多有一千五百公尺吧?」
「不,也沒有。」
「還要開很久嗎?」
「不,也沒有。」
當我沉默不語時,車內只有偶爾響起計費表跳表的喀滴、喀滴聲。
終於看到F溫泉旅館的指引牌時,太陽已經西沉到很低的位置。指引牌毫不客氣地掛在比道路標識更高的地方,一隻張大鼻孔的山豬用三叉的前爪指向F溫泉旅館的方向。牠的大腿到腋下之間都被紅褐色的鏽斑侵蝕,感覺好像又痛又癢。計程車按照山豬指示的方向駛離了國道,經過一座橋,行駛在碎石子路上。
旅館建在河畔,好像很用力地抱住凹凸不平的岩石。前院疏於修剪的胡枝子、敗醬草恣意綻放,有的已經枯黃飄落。玄關的拉門上,停了一隻漂亮的飛蛾,身上的花紋令人情不自禁地想用眼神撫摸,看著牠出了神。
「歡迎您遠道而來。」
出來迎接的竟然是一名年輕女生,但感覺不像是來打工幫忙的,舉手投足都很有深諳世事的女當家風格。她穿了一件簡單的襯衫和褶裙,腳上是一雙襪子。襯衫、裙子和襪子都是相同的深綠色,不知道是不是這家旅館的代表色。
我覺得她的臉似曾相識。她和某個我並不是很熟,也不知道名字,只知道長相的人長得很像。
「請進,請跟我來。」
女當家拎起行李袋,走向長長的走廊。走廊彎彎曲曲,被好幾個階梯分成了好幾段。往下走兩級階梯後,又往上走五級;往下走了八級,再往上走三級;之後又往上走六級,再往下走了十級。沿途一直都沿著階梯上上下下,可以感受到當初費了多大工夫,在幾乎沒有平面的地面上建造這家旅館的辛苦。
女當家走在走廊上時,完全感受不到她的腳下有階梯。雖然她的身體配合階梯上下起伏,但肩膀始終保持一條筆直的線。放有宇宙射線研究所參考資料的行李袋相當沉重,她的步伐絲毫不受影響,以稍微彎曲的膝蓋為起點,身體維持一定的速度向前滑行,我甚至懷疑她腳下踩著什麼未來的交通工具。我在她身後,好不容易才能跟上她的腳步,很快就忘了要思考她到底像誰這件事。
左側的幾個房間都關著門,隔著右側的落地窗外可以看到河岸。走廊的天花板很低,地上鋪著深褐色的毛皮。這種深褐色和女當家的深綠色襪子相互輝映。
「這是山豬的毛皮。」
女當家彷彿看透了我的心思,在絕佳的時機對我說了這句話。
她帶我來到一間很普通的、差不多有十張榻榻米大的和室。榻榻米冰冰涼涼,感覺有點冷。
「請問您幾點用晚餐?」
「我想七點半吃飯,麻煩你了。」
「遵命。」
「晚餐之前,我想去附近散散步。」
「河邊的潺潺小徑是最適合散步的地方。」
我聽從了女當家的建議,泡完溫泉後,換上浴衣,借了旅館的木屐,走在潺潺小徑上。河流的水量豐沛,流速也很快,撞向岩石和倒下的樹木時產生了白色的水浪,和「潺潺」如此悠閒的字眼完全搭不上調。水聲夾雜著風聲,翻轉著漩渦,一路嘩嘩流向山林深處。只有夕陽映照的山巒閃著光,山的另一側、天空的邊緣,以及四處溫泉的裊裊熱氣,都快要被暮色吞噬了。
我沿著滿地石塊的小徑走向上游的方向。這裡只有一條路,照理說不必擔心迷路,但穿著浴衣,踩著木屐走在陌生的地方令人出奇地不安,忍不住頻頻回首確認旅館的位置。旅館的屋頂在落葉松的樹梢中若隱若現,不斷改變著形狀越來越小,同時,兩側的芒草漸漸逼近,擋住了去路。最後,我不得不用雙手撥開,並踩住芒草根,否則無法繼續前進。浴衣的裙擺亂了,袖子翻了起來,芒草的針穗刺在小腿和手臂上隱隱作痛。仔細一看,發現留下了不少刮傷的痕跡,有些地方紅紅的,皮膚上出現了花紋,很像緊緊附在旅館大門那隻飛蛾翅膀上的花紋。這時不管我怎麼回頭眺望,都看不見旅館的屋頂了。
小徑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偏離了河畔,水聲漸遠,原本滿地碎石的地面也漸漸變得柔軟。抬起視線,白樺樹突然出現在一片芒草的後方,驚訝的我忍不住整了整衣襟,重新繫好腰帶。
兩棵白樺樹之間保持了適當的距離,筆直的樹幹伸向天空。兩棵樹不僅高度相同,樹幹的粗細、樹枝的伸展,和黃綠色的樹葉形成等腰三角形的輪廓也都呈現完美的對稱,完全無法區別。夕陽剛好落在樹頂,被風吹起的每一片樹葉都閃著光,剛才那麼煩人的芒草在白樺樹的周圍也乖巧順從地低下了頭。
我走過兩棵白樺樹之間,好像穿越了一道大門。木屐下的泥土越來越鬆軟。
沒想到前方是一片開闊的空間,我深信潺潺小徑已經走到了盡頭。葉子還沒有泛紅的花揪樹、楓樹和杜鵑隆起的樹根、即將倒塌的石垣,還有小廟、道祖神 ,和大小形狀各異的岩石,放眼望去,所有的一切都爬滿了苔蘚。
照亮白樺樹的夕陽不知道被什麼擋住了,四周暗濛濛的,沒有風,只有苔蘚吐出的陰濕纏繞在腳下。眼前所有的景物沒有任何動靜,從枯葉到岩石的縫隙,以及不小心迷失到這裡的所有一切,都被苔蘚覆蓋,緊緊擁抱,被封閉在這裡的世界。所有的一切被苔蘚奪走了輪廓,失去了原本的形狀,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圓滾滾的東西。綠色在地上蔓延,自在地變化著不同的深淺,屏氣斂息,東張西望,窺視是否還有任何遺漏之處。
親眼目睹這樣的景象,難道會有人不想在那些苔蘚上踩踩看嗎?我小心翼翼地把木屐向前踏出一步。動作絕對不能粗暴。苔蘚試圖削弱他人的意志,具備了既不是花,也不是樹木的曖昧模糊;又有著微小生物並肩作戰,攜手合作,努力活下去的堅韌;雖有毫不抵抗的柔弱,卻又具備了毫不留情的侵蝕精神。這些因素使我格外小心謹慎。
我將注意力集中在腳尖,慢慢調整身體重心,一步、兩步地向前走。腳底充分感受著踩在不該踩的東西上的感覺,回頭一看,發現自己踩過的痕跡並沒有造成太大的破壞,不由得鬆了一口氣。苔蘚佯裝無動於衷。
當眼睛逐漸適應後,終於發現石垣後方有一棟木造的平房。不知道原本是不是燒炭的小屋,或只是倉庫而已,那棟平房很簡陋,好幾處牆板都腐爛彎曲,整棟房子當然也都長滿了青苔。只有舖在屋頂的銅皮爬滿銅綠,但和周圍的蒼苔融為一體,幾乎分不清哪裡是銅綠,哪裡是蒼苔。
苔料理專門店
門牌上寫著這幾個字。蒼苔蔓延,爬滿裂痕的小型門牌上,居然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六個字,實在太不可思議了。也許這是用蒼苔寫的門牌。
「歡迎光臨。」
拉開玄關不太靈活的門時,發出了刺耳的聲音,突如其來的招呼聲嚇得我往後倒退。
「我在此恭候您的大駕。」
老婦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不,我只是剛好路過而已……」
「請不必客氣。」
「嗯,好,那個……」
「料理已經準備好了。」
「不,我已經請旅館幫我準備了。」
「您是說那家旅館嗎?」
一看到老婦人看向潺潺小徑的臉,我又忍不住向後退了一步。老婦人和旅館的女當家相差五十歲,但兩個人的臉長得一模一樣,而且,也同樣穿著深綠色的襯衫、深綠色的褶裙和深綠色的襪子。這些深綠色融入了周圍的苔蘚,模糊了老婦人的輪廓。
「這裡和那家旅館是親戚關係,也可以說是那裡的分館,您不必擔心。即使在這裡用餐也一樣。」
老婦人和我聊這些話時,我已經不知不覺脫下木屐,跟著她走到了和室大房間。雖然這棟房子的外觀很簡陋,但這間和室很氣派,雕刻精細的氣窗、古董字畫和擦得光可鑑人的裝飾柱都映入眼簾。這裡比旅館的房間大了好幾倍,四周隱入昏暗中,看不太清楚,中央已經備妥了矮桌、和室座椅、靠肘和坐墊,坐在過度膨脹的大坐墊上,參觀宇宙射線研究所之後的疲勞頓時湧向全身,雖然沒試過苔料理,但在這裡用餐似乎也不壞。
餐點都由那位老婦人一手張羅。首先是用水苔榨出來的水製成的開胃酒,在利口酒杯中倒了一口的開胃酒幾乎呈現透明,輕輕晃動時,杯底的水苔碎片在酒中飄舞。
「長水苔代表水質很乾淨。」
「很符合它的名字。」
「對,並不是很罕見的種類,顏色也比較淺,形狀有點像海藻。如果您有興趣,可以看看這個。」
老婦人把裝了水苔的培養皿和放大鏡遞到我面前。
「用這個觀察一下實物,品嚐料理時,可以嚐到更深奧的味道。」
我聽從老婦人的建議,用放大鏡觀察著培養皿。可以單手拿的十倍放大鏡很有歷史,握把上吸收了人的油脂。
「可以把放大鏡固定在眼睛上,更靠近青苔觀察,對,還可以更近一點。」
「哇,看得真清楚。」
原本以為只是普通的苔蘚,沒想到放大鏡下看到的身影並不普通。雖然不知道那些部分該稱為莖還是葉,總之,放大鏡下的苔蘚由各種不同形狀的部分組成,複雜的結構和苔蘚這麼冷漠的名字完全不相吻合。糾結的曲線、透明的平面、極小的囊、瘤、蓋、粉、毛連成一體,躺在培養皿的底部。一看就知道是新鮮摘採下來的,每個細微的部分都很滋潤,飽含水滴,隨著我的呼吸微微顫動。水滴也被染成了青苔色。
我把目光從放大鏡上移開,喝了一口開胃酒。
老婦人的服務貼心周到。每次送菜上來的時機都拿捏得恰到好處,關於苔蘚的說明也簡潔精確,既不馬虎,也不多說廢話;她總是可以預料接下來發生的事,但不會催促搶先,而是站在我的視野角落,舉手投足都不會讓人感受到她的存在。最令人佩服的是她端著餐盤走路的方式,碗盤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深綠色的襪子宛如有生命的動物般,在榻榻米上悄然無聲地滑動。也就是說,她走路的方式和旅館的女當家如出一轍。如果苔蘚會走路,走起路來絕對就像她們那樣。
煙燻莢蘚、醋味噌拌銀葉針蘚、清蒸絨蘚、滷蛇蘚、珠蘚湯、馬杉苔天婦羅……料理一道接著一道,每一道都別具匠心地裝在高級器皿中,老婦人也會同時附上培養皿。我用放大鏡觀察,品嚐著料理,然後再度用放大鏡觀察。
我無法正確判斷料理的味道,不適合用好不好吃的基準來衡量。用醋味噌拌的苔蘚有醋味噌的味道,天麩羅也有天麩羅的味道,但苔蘚本身躲在這些味道後面不願出來。不用害怕,來,出來吧。當我用舌頭探索時,才好不容易感受到苔蘚的風味,但也在轉眼之間就消失了,一點都不能鬆懈。
種類不同時,放大鏡下的風景也有不同的風貌。有的剛釋放出孢子,也有的排列了好幾個藏卵器,拼命張大了嘴巴。有的像黏乎乎的油紙,有的像蓬鬆的羽毛,有的像滋潤的果凍,形態各異,不勝枚舉。有蕈菇躲在孢子體後方,也有小蟲想要伺機逃逸。看到苔蘚以外的其他生物時,放大鏡下的觀察頓時變得樂趣無窮。
老婦人說的沒錯,觀察苔蘚後再食用可以慢慢刺激食慾。在重複觀察和品嚐的過程中,舌頭、鼻子和眼睛的功能交織在一起,渾然一體,體內萌生出食用苔蘚必不可缺的特殊感覺。
「這一帶有很多家苔料理專門店嗎?」
「不,有兩、三家幾可亂真的仿冒店,但只有這裡才是真正的苔料理專門店。」
「仿冒店?」
「就是用綠藻、蕨類和地皮菜之類的假冒苔蘚給客人吃,也有的摻雜海藻增加份量,或是使用顏料著色,看起來像苔蘚,真是令人難過。」
「使用假貨有什麼好處呢?」
「食用真正的苔蘚需要祖傳技術,並不是隨便找一些苔蘚摘採下來就可以直接食用的,技術不成熟的人想要處理苔蘚,也不知道怎麼下手,所以只能靠偽裝了。反正這種店很快就會倒閉。」
「這裡創業多少年了?」
「無法考究,據說從這裡開始長青苔的時候就開始了。」
老婦人收拾了天麩羅的盤子和馬杉苔的培養皿,走出了大房間。
四周的幽暗漸漸擴大,就連氣窗、字畫和裝飾柱都看不清楚了,燈光照亮了餐桌。我的吃相太差,苔蘚的碎片、湯汁和天婦羅的沾醬濺得滿桌都是,只有放大鏡始終保持著毅然的態度,等待下一個培養皿的到來。這裡可能沒有其他客人,老婦人離開後,完全聽不到任何動靜。雖然我並沒有吃很多,但可以感受到苔蘚吸收了消化液,在胃裡漸漸膨脹起來。我摸著肚子,寬了浴衣的腰帶,想像著雨後的傍晚,在森林深處,苔蘚就是像這樣不斷增生。
主餐最後端上了桌。
「這是石燒並齒蘚。」
老婦人的話音未落,平坦石盤上的油脂就發出滋滋的聲音。這是至今為止最熱鬧的一道料理。
「這種苔蘚長在比較特別的地方。」
「特別的地方是指……?」
「長在動物的屍體上。」
「是喔。」
「今天的是長在山豬屍體上。」
老婦人欠了欠身,走去燈泡的燈光照不到的昏暗中。我拿起放大鏡。我的動作已經練得很嫻熟,不需要任何多餘的動作,一下子就對準焦點。
採集並齒蘚時,維持了它長在屍體上的狀態。是屍體的後背、大腿還是胯下?到底是從哪個部分割下的?培養皿被血染紅了,紅色反而更襯托了那些苔蘚。放大鏡清楚地看到了山豬的肉、脂肪、皮膚和毛,以及剖面的粗糙和糾結的山豬毛。並齒蘚覆蓋在肉片上,纖細的孢子囊感覺很脆弱,無助地晃動著,但牢牢地在屍體上紮根。無論屍體有多麼微妙的凹凸起伏,都可以不慌不忙地應對,孢子囊擠在狹小的空間內,填補所有的空隙。無論再怎麼仔細檢查任何一個角落,都完全找不到遺漏的部分。石燒的石板仍然滋滋作響,冒著煙,散發出燒屍體的味道。
我回想起指向F溫泉旅館方向的那隻山豬,想像他踮腳踮得太累了,不願意再擠出滿面笑容,噗通一聲累壞倒地的樣子。山豬最後一次心跳才剛停止,血液的溫度還沒有冷卻,第一顆孢子已經飛落。落在深褐色毛根上的孢子靠著留在皮膚上的濕氣,萌發出原絲體。其他孢子也立刻收到了秘密暗號,接二連三地飛來,相互合作,相互幫忙。原絲體發芽後,終於出現了苔蘚的樣子,漸漸覆蓋屍體。這時,屍體上的溫度已經冷卻,蛆也開始活動,內臟開始腐爛,但苔蘚絲毫不為所動,只是默默完成自己的使命。
在沒有人煙的密林深處,一頭離群索居的山豬死去。沒有人送終的死亡,只有苔蘚的陪伴。苔蘚為山豬的屍體蓋上一條柔軟的深綠色毛毯。
「來,趕快趁熱吃了吧。」
老婦人在幽暗中對我說。
晚上八點剛過,我回到了旅館。雖然去的時候覺得走了不少路,但回程時,很快就看到了旅館的燈光。「苔料理專門店』似乎事先為我聯絡了,我沒有解釋任何事,女當家已經了然於心。回到房間時,被子已經舖好了。
我向女當家借了小收音機,趴在被褥上。今天要在甲子園球場和巨人隊打最後一戰,這場比賽非贏不可,上次在東京巨蛋球場的三連戰連輸三場,形勢的發展越來越不利了。
打開收音機,轉動旋鈕。如果在家,就會看電視,但在這裡無法奢求。我很少外出採訪旅行,卻總是在有重要比賽的日子出門,上次日本棒球聯盟的第一戰,和儂特利隊對戰時,我也因為出席一場文學研討會,被關在箕面的深山裡,結果,阪神隊四連敗。
我事先看了報紙,知道當地電台會實況轉播棒球比賽,所以,我轉動旋鈕,調到那個電台。收音機打開之後,一直滋滋嗡嗡地響個不停。每次把旋鈕向左、向右轉動,滋滋嗡嗡的聲音就忽大忽小,時叫時停,完全聽不到人的說話聲。我豎起耳朵,耐著性子等待金本擊出一支全壘打、藤川三振了對方選手、播音員興奮的尖叫、觀眾的歡呼聲這些令人懷念的聲音。我把收音機轉向,打開窗戶,拿在手上搖了搖,擦掉上面的灰塵,甚至對它吹氣,試了我能夠想到的所有事,但事態並沒有因此改善。
一定是宇宙線搞的鬼。
我突然想到這件事。今天在研究所時,不是才得知宇宙不斷向地球發出宇宙線,光是手掌大小的空間,每秒鐘就有六兆個微中子嗎?我身處一個嘈雜而又令人心煩的世界,因為整天呆頭呆腦,所以看不見,其實數億、數兆、數京 的粒子不斷從天空降落,以驚人的速度畫出人類無法畫出的完美直線,穿越我的身體。
我的手掌這麼小,怎麼能夠相信自己的手掌拿了六兆個東西? 如果我死在森林深處,覆蓋在我手掌上的苔蘚孢子會有六兆個嗎?宇宙線會覆蓋我的屍體,為我的死亡憑弔嗎?
這是宇宙線降落在甲子園球場的銀傘 上的聲音。我鬆開了旋鈕,聲音立刻增加了密度。我放棄了,把收音機丟到一旁,躺成了大字。浴衣亂了,手腳露了出來。我發現手臂和小腿上原本留下的飛蛾花紋不知何時消失了。我沒有整理採訪筆記,倒頭大睡。
(文稿零頁)
隔日(星期六)
看早報得知阪神隊輸了。四比六。
我在櫃檯結帳,女當家穿著和昨天相同的衣服。
「啊。」
我打算從皮夾拿錢出來時,忍不住叫出了聲音。我的指甲被染成了蒼苔色。
好像隔了一晚好像就年輕了五十歲的女當家說。
我從M機場搭螺旋槳飛機回到家中。
(文稿零頁)
九月某日(星期五)
為了長篇小說的採訪工作,參觀完宇宙射線研究所後,去F溫泉旅館投宿。
計程車在山裡開了很久很久,彷彿這一路永遠都開不到盡頭。沿途幾乎沒有遇到任何車子,兩側車窗外,只看到重重疊疊的巨樹林,即使水壩湖、飼養熊的牧場和養魚場偶爾從樹幹的縫隙中探出頭,也很快再度消失在樹木後方。層巒疊嶂之間的天空只剩下一小片,呈現出混濁的灰色。
「秋天落葉季節時,這一帶也很熱鬧吧?」
「不,也沒有。」
沉默寡言的司機只會說這句話。
「這裡的海拔差不多有一千五百公尺吧?」
「不,也沒有。」
「還要開很久嗎?...
目錄
九月某日 (星期五) 為長篇小說進行採訪工作,參觀了宇宙射線研究所,住在F溫泉旅館。
隔日 (星期六) 看早報得知阪神隊輸球。四比六。
十月某日 (星期二) 接受周刊雜誌採訪,回憶孩提時代住的房子。
隔日 (星期三) 傍晚準備晚餐時,看本地新聞。
十月某日 (星期日) 去鄰町參觀L小學的運動會。
隔日 (星期一) 下雨。超大的雨,無情的雨。
十一月某日(星期四) 在晚報上發現剽竊的新聞。
十一月某日(星期一) 和母親一起搭地鐵去百貨公司。
隔日 (星期二) 去醫院。西棟二二二病房。母親在沉睡。
十二月某日(星期一) 上午,公所生活改善課的R先生來家訪。
十二月某日(星期三) 收到「素寒貧心會」同意我入會的通知和會員徽章。
一月某日 (星期二) 公民館事務室打來電話,委託我擔任「概要教室」的講師。
一月某日 (星期四) 第一次戴著臭鼬的徽章外出。
二月某日 (星期三) 深夜,接到來自編輯部的傳真。
三月某日 (星期一) 車站前搭長途巴士前往健康水療天地。
隔日 (星期二) 翻開相簿,回味八歲時的照片。
四月某日 (星期六) 和生活改善課的R先生、作家W小姐一起去參觀盆栽嘉年華。
隔日 (星期日) 一整天都在書架上翻找W小姐的小說。
四月某日 (星期三) 參加了睽違三年的U文學新人獎的宴會。
四月某日 (星期一) 收到市公所生活改善課的通知。
五月某日 (星期日) 很久之前就在月曆上做了記號,滿心期待的嬰兒哭哭相撲大賽。
隔日 (星期一) 一整天都在看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
六月某日 (星期三) 接到「背誦俱樂部的創始人G老師追思會通知」。
七月某日 (星期日) 搭飛機後轉新幹線,前往遙遠的T鎮。
八月某日 (星期五) 去探視母親。
八月某日 (星期二) 夜晚輾轉難眠,抄寫圖鑑打發時間。
九月某日 (星期五) 為長篇小說進行採訪工作,參觀了宇宙射線研究所,住在F溫泉旅館。
隔日 (星期六) 看早報得知阪神隊輸球。四比六。
十月某日 (星期二) 接受周刊雜誌採訪,回憶孩提時代住的房子。
隔日 (星期三) 傍晚準備晚餐時,看本地新聞。
十月某日 (星期日) 去鄰町參觀L小學的運動會。
隔日 (星期一) 下雨。超大的雨,無情的雨。
十一月某日(星期四) 在晚報上發現剽竊的新聞。
十一月某日(星期一) 和母親一起搭地鐵去百貨公司。
隔日 (星期二) 去醫院。西棟二二二病房。母親在沉睡。
十二月某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