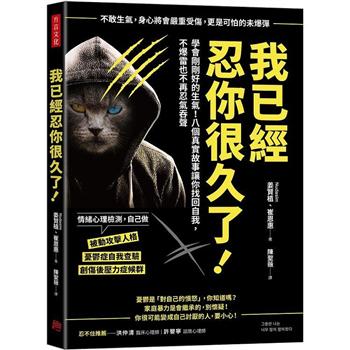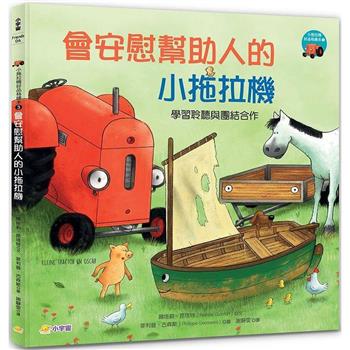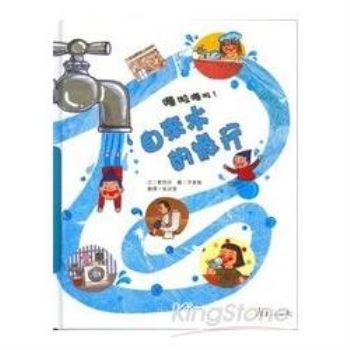推薦序
文有別趣 /黃錦樹
有段時期,我的夢經常經常具有某種連續性和預示性,而且是彩色的。有好幾回,我發現我身邊正在進行的事曾在我的夢境中出現,我幾乎吐出身旁的人即將吐露的下一句話。
出國前兩夜,我夢見五根金色巨鉤嵌在自己無頭無足水晶明澈的軀幹裡,像件美麗的雕刻,沒有痛楚,也沒有激情焦慮;而後我的手(我的意識告訴我那是我自己的手)探入體內,循著鉤的倒刺將鉤一一退了出來,夢便結束。
我曾張目看過死亡的花朵開放。「死」是沒有顏色的。--黃翰荻,《止舞草》
《人雉》是本相當有趣的書,甚至可說是近年散文界罕見的一朵奇葩。雖然某些文章文類的歸屬容或有些疑慮——就一本書而言,這幾乎是個無關痛癢的問題——我們還是籠統的把它歸於散文吧。散文在最寬廣的意義上即是對立於詩的總類。
黃翰萩的文章別有異趣,有一股難得的野趣、古趣。它的有趣一方面來自於表達方式上的與眾不同,再則是來自它的語言風格,二者當然是緊密相關的。表達方式之所以與眾不同,來自於作者的文學觀、世界觀和當今文壇的風尚有相當的差異,那又立基於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我們的時代,散文可能是被馴化得特別嚴重、也最能反映民國-台灣國民教育成果的一個領域。那多半還是得歸咎於師範國文系的文學想像﹙典雅、溫柔敦厚、文﹚,對語文表達的規範(符合各種部定的修辭格),經由大、中、小學教育長期的教學規訓,再經由文學獎、選集這些承認機制的進一步規範,「野」這東西就和雉一樣,已很難在這島上生存。要「野」,就必須拒絕體制,也意味著被體制拒絕,但那可能是個性化、個體化的極致。用書中的表述,即是必須採取一種「退步主義」(「帶病的退步主義之身」﹙〈病與觀音〉﹚),一種積極的逆俗﹙〈退步主義〉﹚。而在這個被持續的工業革命發達資本主義時代,往往就意味著退隱鄉間,「小隱於野」,採取不同的生活方式過日子。「彼時我因震駭自己淪為島人無情貪婪血汗工廠的劊子手,處於一種身心俱廢狀態,……年齒正壯的我在養病中成了一個空心人。」﹙〈病與觀音〉﹚故選擇「抽身而退」。因而書中每多憤世之言--有時竟有幾分舞鶴的廢人調。
「打開信箱,盡是這時代特有的無趣……名人忙,沒有時間一再深潛,所以在不知不覺中退步。名人總是應運而生應運而死。」(〈老頭與鬼〉)
「然此蕞陋小島的許多觀念藝術都和尿死一株草差不多。」﹙〈尿死一株草〉﹚
「攝影進入荒誕的所謂「民主化」之後,便失去了真正的讀者,大家都當「作者」去了,包括我在內。」﹙〈拍攝墳墓的人〉﹚
「我們想擁有一塊怎麼樣的地?如果我們種的是自己。」﹙〈假如我有一塊地〉﹚
《人雉》野性難馴的文體,就源自那樣的生活方式和自我定位。時而荒誕、時而執拗、時而奇幻、時而悲憤,時而抒情;行文汪洋曼衍,不拘一格,頗有《莊》、《列》遺風。時見寓言筆調,所以敘述者不一定是你、我、他這類代詞,可以是黃欣、禺耼、笑栽、卯生……有的還像人名但有的就是個寓言的敘事者。而人與雉、人與鬼、芭蕉與鳥之間都能對談,螳螂會唱大戲……,都饒富古風,古代筆記小說如《太平廣記》中亦常見此類筆法。那也源於作者對觀察這個世界的濃烈興趣(所以會有「賞了一陣子野草」這樣的句子),而別有體會。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對墳墓的興趣,他認為墳墓可以「顯現這個島嶼的文化地層」,移民文化從墓場確可看出一些端倪。確實,墳墓也會說故事。「墓場常洩露時代的歷史狀態……你走過越多不同的地方,看過越多不同的墳墓,你越了解它們的歌吟。」﹙〈拍攝墳墓的人〉﹚那對死亡還得有一種豁達。但即便是對生態浩劫苦澀的反思,表達上也與眾不同:「一隻盆地特有種,專以耳朵獵殺蟲子的大耳怪蛙游近,跳在他頭上,一人一蛙開始認真思考:在這資源有限的世界遊戲場上,不倚賴耳朵,當怎麼活下去?」(〈耳人〉)或如〈勸世歌〉般的〈毋貽盲者鏡〉廣用排比,以散文裡罕見的筆法,文言白話錯雜,諷世勸世:「盲者雖不能見有形之形,可以見無形之形,教之以『金目』,便知『人各哀其所生』。」
筆法的怪異使得黃翰荻的文章不會流於平淡無趣,而是處處波瀾,宛如郵票的鋸齒,鈍刀裁出的毛邊,「散文家」看了只怕要皺眉頭的。對我這樣的一個讀者而言,卻是怪得有趣,集子中大部分的文章都堪稱妙文。作者本身具備的多種藝術涵養很顯然有力的輔濟他的寫作,彷彿可以隨時打開不同的窗,迎風觀月。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對台語文字化的堅持。不是那種自我殖民化的傳教士羅馬字台語,而是晚清國學大師章太炎《新方言》主張的,為方言今音找回它遠古的肉身(字形,詞。中古,甚至上古漢語)的白話文。相較於向傳教士借洋殼,這是條非常難走的路,對當道的本土意識型態而言,也相對的政治不正確--它預設了漢語古籍是「台語」的根源,難免有「統傾」之嫌。但正因為作者的堅持和實踐,借用俄國形式主義的語彙,這其實是場難得的詞的復活的文體實驗;而這一點讓黃翰荻的文體帶著一層怪異的古意,甚至一種苦澀。從現代中文書寫的歷史來看,這是我所謂的華文的有趣個案--拒絕走向平順流麗、剔盡方言詞彙的純正中文 。閩粵兩地的方言遺產特別有可能讓有心人藉由援引方言,一定程度的忠於自己的口語,為自己的文學建立一種相異於北方天朝的獨特性。代價之一當然是不被他們承認。
但身為閩南人,有好些詞我還原不出方音,得從註解去揣度。蚼蟻(螞蟻)爪鼠色(老鼠色)飰釭(飯鍋)「敧在樹下」(站在樹下)「野雞髻花」(野雞冠花)……這些都沒問題。但有的沒註就如對古文,茫然不解。如「憃愚」,如「這谽谺的幽壑還座落在醭光裡」,如〈蜩甲〉。我上網略查一下,「憃愚」原來是我們都很熟的愚蠢,「憃」是異體字,典出《一切經音義》;谽谺,唐詩屢見,山谷空曠或山石險峻。〈蜩甲〉,《莊子•寓言》:『予蜩甲也,蛇蜕也。』 成玄英疏:『蜩甲,蟬殼也。』」都不在我既有的閩南語詞庫裡,多半是我自己的詞庫還不夠豐富。
另一方面,作者這樣的寫作路徑,又讓他像個本土現代主義者,語詞坑坑窟窟或多石礫的,只能讀普通話的讀者只怕會望而卻步。「錢,當時在外公家,是每日自己會生腳行入來的」〈第一間房子〉「女人腹如白雪、兩腿似蛤深納他的慾望,像海一般激烈波動起來,他則自恃為帆又自恃釣者,等女人化為魚。」(〈半日〉)「鳥頭長了一顆老人斑」(〈尿死一株草〉)這樣的句子像不像舞鶴?但黃翰荻和後者的決定性差異在於,舞鶴的世界幾乎被性的土石流淹沒了,被放大的男女生殖器成了本土的絕對象徵。而黃翰荻這裡,山川草木並沒有淪為次要、甚至微不足道的佈景陪襯,作者對草木蟲豸是有情的。論異色感,有時會讓人想起雷驤,但雷驤的筆調其實非常陰柔,黃翰荻卻時而暴烈。內視的開啟上,黃也更為頻繁,更為狂野或明淨。別忘了,《止舞草》還曾經啟發《妻夢狗》作者開啟夢的眼睛。其文生猛有力處,令人想起邱剛健〈再淫蕩出發的時候〉那類詩。
《人雉》中夢的強而有力,如〈病與觀音〉,一段剛開始就結束的昔日情緣,一個夢替代了一種可能的未來結局,提前終結另一種可能的人生。如此而能在敘述上開啟一個幻境或童趣的向度,和夢的調度功能相似,那也常是這些文章裡最美的片刻。從詭麗的世相、幻相,有時可以引渡向片刻的了悟,如夢:「一截佛指墜落在澹明搖曳的燭影下,雖朽壞了,卻猶柔軟、流麗、靜寂,髣如佛的本體。」﹙〈佛指〉及諸如此類不可思議的段落:
「爸爸,你的眼睛吃了什麼?」
「眼睛當然是吃它看見的東西。」
「它發亮。」
他伸手摘下右眼,照著月看……啊!目珠中有一顆金樹,莖幹上停滿鬼面天蛾吶!﹙〈鬼面天蛾與公木瓜〉﹚
那種詭麗、超現實的畫面感,時而妖仙乍現而近乎《聊齋誌異》,或許源於作者的繪畫訓練,那是一種特殊的視覺能力,藝術家天啟般的內視,一種敏銳的直觀,彷彿可以看出超出現象之物。在最表面的意義上,那當然也是一種陌生化的敘事策略,就像作者常引介西洋古典樂。或藉由「由李漁的傳奇《蜃中樓》走出來的」耳朵被養得特別大的畸人,來陌生化我們熟悉的世界。
作者當然也在尋找詩意、營造意境。而回憶童年住處、宛如一部家族史大長篇之餘光殘骸的〈第一間房子〉,某個抒情的瞬間(內在風景)可作為概括。像一幅發光的油畫,詩意盎然--
「窄巷和大溝垂直交叉處有一方小空地,地面上用成人手腕粗的竹子搭了一座葡萄架,春日裡葡萄藤涓出的嫩綠,以及夏盛熟果中碧酸夾揉的一包青甜,幾十年都用一只水晶碗盛放在記憶裡。」
猶如〈佛指〉裡「某個寒天,半夜醒來,他看見他的大畫桌上不知何來一只大白盤,盤中所盛正是那截佛指。」也是幅明淨的畫。恰可隱喻作者運用如此獨特而蕪雜的文體寫作所追尋的某種純粹的藝境。
附記:
我並不認識黃翰荻先生,為前輩的書寫〈推薦序〉感覺也不太像話。我和他的因緣除了同姓之外,大概就是十多年前都曾在楊淑慧的元尊出版社那裡出過書(彼《止舞草》;我,《馬華文學與中國性》)。
但我們也不乏共同處。我也持「退步主義」,選擇住在鄉間。愛書,蓄書數千,然猶未屆散書之齡。對墳場也感興趣,雖沒見過鬼。租了小塊地栽花種樹,不施藥,但也得忍受愛噴殺草劑的本土鄰居時時飄來惡臭的殺氣。
兒子一歲多時曾以單指大戰好鬥的綠螳螂雙鎌數百回合,不分勝負。彼時居處左近多樹蛙與竹節蟲,夜來蛙鳴如雨林,雨後花香醉人。
近年養了一窩晚上堅持住高樹上的白雉,凶狠的大公雞且曾以飛啄打敗我唸國中的大棵女兒,一瞬間,伊的粗壯「豬跤」上留下深深的喙痕。
年輕時讀過章炳麟《新方言》,思考過方言寫作的問題。自己多年來也寫一些「有的沒的」,但方言古字並不熟悉,閩南語詞彙亦不足以支撐寫作。受出版社委託讀黃先生文章時,習得「飰」字,故將甫完稿之散文〈鹹飯〉易為〈鹹飰〉,方捕獲鄉音,那也是先人遺音。
寫完本文初稿後得讀《翰荻草》,始知黃先生曾親炙民國-台灣學界傳說時代諸名師(鄭騫、魯實先、君毅、牟宗三等),那些先生都我老師的老師輩了。無怪乎作者時而能重新賦某些傳統文論的概念予活力,也能洞見傳統抒情主義的深刻處(如〈懷念呂璞石〉中所言的「『限制』使『自由之力』往一個點上深掘」,以致顯現出「『簡潔、重複』兩大聖像特質」);汲取古人的詩情,詮注當代巨匠的畫意。
在我唸台大中文系時,已是「雞棲於塒」的黃昏時刻了,當然那也可能只是我自己的主觀感受。
昔年楊淑慧贈予的《止舞草》不知流落何方,只好上網重購一本,赫然還是一九九六年的初版本。躺在書庫裡近二十年,還是新的。晚兩年出版的《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庫存多半早已壓成紙漿,流轉生滅不知幾回了。
2014/12/24初稿,2015/1/15補於埔里牛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