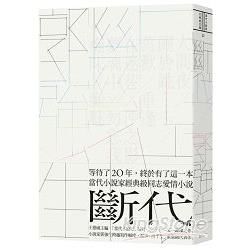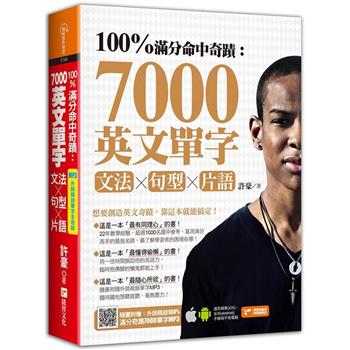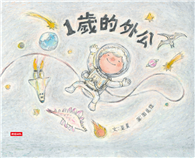「我需要愛情故事——這不過是我求生的本能,無須逃脫。」
等待了二十年,終於有了一本當代小說家經典級同志愛情小說!
王德威主編、「當代小說家」系列又一璀璨之作。
小說家郭強生跨越寫作幅度,淚別「前半生」重量級代表作。
郭強生是臺灣中堅代的重要小説家,最近幾年因爲同志議題小説《夜行之子》(2010)、《惑鄉之人》(2012)以及散文專欄而廣受好評。即將推出的《斷代》代表他創作的又一重要突破。在這些作品裏,郭強生狀寫同志世界的痴嗔貪怨、探勘情欲版圖的曲折詭譎;行有餘力,他更將禁色之戀延伸到歷史國族層面,作爲隱喻,也作爲生命最爲尖銳的見證。郭強生喜歡說故事。他的敍事綫索綿密,充滿劇場風格的衝突與巧合,甚至帶有推理意味。然而他的故事内容總是陰鬱穠麗的,千迴百轉,充滿幽幽鬼氣。這些特徵在新作《斷代》裏達到一個臨界點。 ──王德威
=內容簡介=
「我們未來的路已經夠難走了,不要再自尋煩惱了好不好?做你相信的事就對了!」
人生再複雜再深奧的道理,其實最後都可以簡化成這兩個字:時機。
絕大多數的失望之所以會發生,則是因為這兩個字:錯過。
雖然是爛命一條,至少知道生錯的是時代,不是自己。
深夜裡一家名為「MELODY」的酒館亮着剛剛好的燈火,
老朋友喊店長「老七」,新加入的客人稱他「Andy」。
在酒館中,無分你我各自帶着自己的身世,進入或離開……
歷經上世紀的喧嘩,好歹我們都精彩地活過一把。
「我第一次發現到,男生在一塊兒不一定就得成群結夥吃冰打球。」
年少時的選擇成為現在的故事,所謂的未來,原來總隱藏在我們不願正視的過去裡。
沒有人是婊子,只有輸不起的遜咖。
雖然那年夏天的我們都在虛幻的感情中自苦,其實仍有愛情柔軟的羽翼在眷護著。短暫的曲折,小小的忌妒與孤獨,不貪想更多,以為情愛就是帶著咖啡的微苦,加速著心跳,讓自己在夜裡清醒地作著無聊的夢。
那是此生再也不會有的奢侈。
拒絕了任何字符將我們命名,我們永遠也成不了彼此生命中真正的,同志。
在未來都只能各自上路,生存之道存乎一念之間,誰也唸不了誰的經。
就讓同學的歸同學,同志的歸同志。 ──郭強生《斷代》
作者簡介:
郭強生
1964年生,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紐約大學(NYU)戲劇博士,目前為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高中時期便於「聯副」發表小說進入文壇,二十二歲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作伴》。留美期間又陸續獲得時報文學獎戲劇首獎與文建會劇本創作首獎。2000年結束美國教職返台,協助成立華文世界第一間「文學創作研究所」,培育當前台灣新銳作家無數。2010年再度推出小說作品《夜行之子》,立即獲得廣大迴響與矚目,入圍台北國際書展大獎。2012年出版長篇小說《惑鄉之人》,榮獲第37屆金鼎獎。
近年作品多次入選「年度散文選」與「年度小說選」,同時主編《九十九年年度小說》、《作家與海》台灣海洋書寫文集等。其他出版作品包括散文集《我是我自己的新郎》、《就是捨不得》、日記文學《2003/郭強生》,以及評論文集《如果文學很簡單,我們也不用這麼辛苦》、《文學公民》、《在文學徬徨的年代》。劇場編導作品計有《非關男女》《慾可慾非常慾》、《給我一顆星星》、《慾望街車》等多部。優遊於文學與文化不同領域,其文字美學與創作視角成熟沉穩,冷冽華麗,從激昂與憂鬱之人性衝突中淬取恣放與純情,澎湃中見深厚底蘊。
章節試閱
1 人間夜
一切仍得謹慎提防的一九八五年—換言之,彩虹旗紅緞帶搖頭丸這些玩藝兒根本還沒問世的三份之一個世紀前。
在台灣當時的報紙只有三張,離國際化還很遠,資訊就像尚未開放進口的洋菸酒一樣,這方面的事更極為稀有也鮮為人知。連在台北市,百姓普遍英文程度仍屬低落,所以千萬別隨便開口,請問哪裡有ㄍㄟ ㄅˋㄚ,他可能會以為你是在用器官粗話罵人。同志?別忘了還是戒嚴時期,「愛人同志」是共產黨用語,罪加一等。
那麼,要怎麼定義MELODY呢?
就乾脆不必明說了。沒錯,若非熟人帶路,還會被小心盤查以防滋事。別招搖,得學會故布疑陣,教外人一眼識不破狐狸尾巴那才是上策。所以也別期待MELODY店裡有什麼風格或設計。店剛開張的時候,這地方連個卡拉OK設備都沒有。台北那時的經濟還落後馬尼拉吉隆坡,想當年能有這麼個場子已經很不錯了,就別挑剔太多。
BTW,還記得卡拉OK機器剛出現的時候,沒有電視螢幕,只能看歌詞本,而且用的還是那種匣式錄音帶?一匣十六首歌,有一本書那麼厚。MELODY才十五坪的店面,去掉吧台與座椅,站人都嫌擠,哪來的多餘空間堆放?想來這裡高歌?還是等數位化點歌系統出現再說吧!
不過說也奇怪,即使日後有了錢櫃這種全民歡唱出現,每家同志酒吧不論規模大小,仍少不了卡拉OK娛興。這恐怕是三十年滄海桑田過程中唯一還保留下來的傳統。歌唱得好壞倒是其次,有個上台亮相的機會才是重點,否則黑麻麻一屋子人哪能贏來目光,出門前的一番精心打扮豈不浪費?
不是說那時候的人英文水準不高嗎?那又為什麼取了個這樣裝模作樣的英文名字MELODY?且慢,寫成了「美樂地」,就別有一番滋味了不是?這就是所謂的故布疑陣,外人看起來覺得是做洋人生意的,員警都要敬畏三分。就像二十年後曾轟動一時、卻又曇花一現的搖頭吧TEXOUND,這名字在店卡上寫寫就好,私下大家都說「台客爽」,反倒俗而有力,挺風騷傳神的。
與「美樂地」同期的,還有其他這幾家場子。
「同心橋」應該是最早裝設了卡拉OK的。「重慶」的小舞池裡,男男翩翩,夜夜跳著探戈吉魯巴。中山北路上的「第一酒店」還沒歇業,旁邊那條小巷裡平日窄暗幽僻,到了周末就突然多了成群少年郎鬼頭鬼腦忙進忙出。位於那巷底某大樓地下室的「TEN」,一與○暗語私藏其中的店名堪稱經典。那可是當年第一家走迪斯可風的,開幕時鋒頭最健,影劇圈裡私下盛傳的幾位男星竟然現身捧場,讓剛出道的小傢伙們個個看得目瞪口呆。
彼時,老七年方二十,高高帥帥壞壞,浪子膏堆滿頭,出現在TEN的舞池,總能濺起四面傳情目光沐身好不虛榮。
當兵退伍回來,遇著原來在TEN當領班經理的老三,告訴他喬哥現在已從電視台基本簽約小歌星,躍上文藝愛情片大銀幕成了二線男主角,想出資弄個自己的小聚會所,提供熟朋友帶自己的朋友來認識彼此的朋友。沒兩年文藝愛情片開始退燒,癡情小生未雨綢繆移民加拿大,聽說還在那兒結了婚。只剩下老七還願意留下幫老三繼續接手,這才是「美樂地」正式掛牌的開始。
和同業相較之下,他們這店當年真是陽春得可以。可任誰也想不到,MELODY竟能如此長命,跨世紀存活至今。
那年頭談戀愛走的是日久生情路線,客人來店,不唱歌純聊天,沒有手機,沒有Line,常有人把情書留給吧台代傳,不像後來網路交友百無禁忌讓人眼花撩亂。年輕的時候,老七從沒去想過,屬於他們這種人的愛情能維持多久,這種自欺欺人還有幾年光景,總以為年少輕狂,這兒打工不過是個中途站,時候到了就會乖乖就範成家去。從沒料到,自己竟然是如此這般地過完大半生,每天傍晚來開店打掃然後忙到四點打烊收工,日復一日,這樣的生活已是第二十五個年頭。
老七更沒想到的是,自己能活著看見「同志婚姻」這名詞出現,並且三天兩頭被堂而皇之拿出來討論。雖然,那已經跟他沒太大關係了。
在他成長的年代裡,自求多福,方是立足境。要婚不婚,就讓下一代去操心吧!年年的大遊行他也一次沒去湊過熱鬧,每天累到睡眠都不夠,哪有那樣的閒工夫?
他已年過百半,最壞的年代也都走過來了。可憐當年的趙媽,還會因一張變裝照片被警察以「人妖」罪名逮捕入獄。搞運動?不是該為那些當年因風化罪入獄的老皇后們向政府申請國賠什麼的?這事從來也沒人管。
得了,小傢伙們只圖自己開心最重要,遊行不過是場嘉年華會,鰥寡孤疾老怪者,頂好躲一邊去。結束後要慶祝狂歡,小傢伙們也不會挑上來他這裡。現在他們要去的地方會是紅樓小熊村,FUNKY,JUMP
時代不一樣了。二十五年前若有人鎖定玻璃圈,說這個消費市場潛力無限是塊大餅,怕不笑掉人的大牙。
這陣子每有新生代蹦蹦跳跳推門進來,看見一屋子歐吉桑,無不吐舌做鬼臉,轉身就摔門撤腿,毫不給面子。早個幾些年,小伙子們都還懂點禮貌,既然推了門進來,也好歹點杯飲料坐坐。大家同病相憐,聽聽前輩們的故事,暖暖彼此的回憶,犯不著驕縱作態。如今不必遮遮掩掩,名目張膽多出了個身份,叫消費者。多的是一個晚上喝完酒,唱完歌跳完舞,最後再加三溫暖一遊才覺盡興的圈內玩家。這些玩都膩了也不愁,還有轟趴伺候。
曾經一度,沒人再管這地方叫美樂地,直接都說「老七的店」。現在卻只有老客人還在喊他老七,後來的客人則喊他Andy。
世代差異?不如說是他們這代在凋零吧!為了在這行生存,他也曾求新求變。那一年,各家酒吧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經營進入戰國時期,他一咬牙重新改裝,把店裡裡外外塗了個漆黑,國外進口的男體海報掛它個滿牆,決心來好好幹他一票。有錢不賺,難道是想上天堂?再怎麼也輪不到他們這種人吧?
他那年三十五,意識到老來沒依沒靠,此刻不存點老本更待何時?看多了圈內的老病殘窮,連當年秀場炙手可熱的諧星,到最後也只剩西門町小套房裡潦倒等死。老三得了那圈內人聞之色變的病,最後把店託給他的時候兩人哭成一團。老七不想如此,Andy更不甘。
接下來那幾年,Andy以人肉市場豔幟高張聞名圈內,來到店裡如進烏漆麻黑的盤絲洞,愛怎麼玩,能怎麼敢,照單全收。然而美樂地的店名終還是沒改,因為心裡不捨。老七總記得自己當年啥事不懂,若沒碰上幾位前輩哥哥們,弄出了這塊小避風港,否則若在新公園裡繼續鬼混,還不知道會被怎麼作賤。
幾起幾落,少不得風風雨雨,MELODY早成了同業間的一則傳奇。
在這吧檯後一站就是二十五年,除了那幾年裡身邊多了湯哥幫忙,他一個人扛起一家店,生意再忙也不曾有過算錯帳或送錯酒,只能說,天生是幹這行的料。
再怎麼能幹,現在的老七不得不承認,自己真的是有點年紀了。像昨天夜裡,打烊後收杯掃地不過才進行了一半,他一陣頭昏,再睜眼竟發現自己懷裡揣著掃帚,踡在牆角已睏了一覺。
睜眼醒來時心還怦跳著,一看牆上的電子時鐘閃的是04:20,不過才過了半個鐘點,卻好像去了很遠的地方一直在趕路,整個人弛軟在地,一時間不曉得自己身在何處。
眼前守了半輩子的這家店,仍是每晚打烊後的相同景象。吧檯上東倒西歪的啤酒瓶,關了聲音的電視螢幕繼續播著卡拉OK影帶。整個密閉的空間沒有窗戶,看不見外頭的雨究竟停了沒有。
寒流過境,冰雨已經連下了好幾天。
他這兒本就不是小朋友跑趴的熱門點,反倒是這樣的壞天氣時,不怕沒有熟客上門。雨夜孤燈誰都怕,不如來吧裡打發時間也好。老七這店裡別的沒有,就是卡拉OK歌曲比任何一家吧都多,二十多年前的陳年金曲他都保留著。在別處找不著的記憶,適合在又冷又雨的夜裡來他這裡重溫。
昨晚不過六七個客人,點歌單卻厚厚一疊,還有很多曲子在機器裡等著播放,客人卻不知何時都悄悄撤了。老七眨眨眼,看著電視螢幕上是林慧萍的哀怨特寫,少說也快二十年前的一首歌。不知是哪個客人點的,沒等到歌出來就先離去了。
等不了那麼久。多少銘心的盼望都讓人最後不得不放棄了,何況只是一首歌?
時序入冬後,近來非假日的晚上都是這樣落寞地結束。客人獨來自去,時候到了就走,不會出現兩人看對眼可以成雙離去的場面。
冬雨寒夜裡會出門的客人通常是另一種。
若只是期待豔遇那還比較好哄,但另種客人的心情就跟外頭的陰雨一樣難捉摸。唱了一曲又一曲,時而借酒裝瘋,時而又陷入沉思,午夜心事特別難熬。總算,又一個生命中寂寞的夜晚終於耗完,這些人臨走時並未顯得比較開心,甚至有可能在心底暗暗鄙斥自己的意志軟弱。為何雙腳總是不聽使喚?到底何時才能夠不必再踏進這地方?這樣的日子還要過多久?
老七收下酒錢的同時,彷彿也聽見了他們心底對MELODY的愛恨交織。在某些人的眼中,老七不過是利用了同志的寂寞飽了自己的荷包,他們的自怨往往轉成了對老七的不屑,老七並非沒感覺。但越是這種時候,老七越要提醒自己別被他們的情緒影響,所以總是左一聲「晚安喔」,右一句「再來啊」,喊得格外賣力。
雨還在滴滴答答下沒完。
空闇的酒吧裡,全是菸味不散,像看不見的記憶。
還沒完全清醒的老七,突然想起來,林慧萍的這首歌應該是小安點的。(早就該叫老安了吧那傢伙!)那人與BF在一起十五年,至今是紀錄保持人。畢竟是在老七這裡認識才開始交往的,兩人沒有過河拆橋,一年裡偶爾還是會來店裡露個臉。昨晚也是,他們看完了午夜場電影,散場吃完消夜路過老七這兒,丟下幾包滷味與香雞排,嘰嘰喳喳跟熟人打完一輪招呼,沒坐多久便走了。
小安碰到剛退伍的阿祥時已經四十,自然把身高一八三當過憲兵的阿祥當成了寶來寵。阿祥如今已是小安那時的歲數,早胖成了當年兩個大的龐然巨物。他們前腳才離開,麥可那個勢利鬼就忍不住開口發表起意見來。
真是老天幫忙,讓阿祥胖成這德性,麥可說。除了小安還把他當寶,現在還有誰會多看他兩眼?不然的話早份了。
老七懶得搭理,心想當初你不是還對憲兵阿祥心癢癢?可惜人家不要你。
麥可也算在圈裡打滾一段時間了,可是到現在都還搞不清楚狀況。他的長相有點吃虧是沒錯,人矮,鼻子又扁塌,但有比他長得更差的,還不是後來碰到了對象在一起?可是他每次就愛拿出自己醫生的名片來,很讓人倒胃口。
男配男,沒有誰高誰低,都得打心底是心甘情願才行。兩個美女相見只能爭豔較勁,成了紅眼宿敵。兩個帥哥反其道,不相妒反相愛,這算不算得是一種人性昇華?想用異性戀那套死纏爛打都是自掘墳墓。如果自知不是帥哥等級,那就盡量個性好一點,做人大方一點,身段放低一點,總有某個玩累了的帥哥,到了見帥不帥的人生階段,哪天反看中了你的成熟穩重。最怕的就是老來嬌。要知道,年輕貨色再不起眼的,也比一個老姊姊強。要不就安份找個平凡順眼的,拿醫生名片出來嚇唬誰呢?眼看也一把年紀了,這以後只會每下愈況,看他還能自我感覺良好到幾時。
(等等,麥可不是跟自己同年?)
老七迅速朝玻璃牆中的那個折映出的人影多端詳了兩眼。
(還過得去嗎?都有在健身呢)
年輕的時候,仗著自己有幾份皮相,專喜歡跟害羞的客人說上兩句露骨調情的話,看對方羞得滿臉帶春真是有趣。如今再怎麼說,在業界都算是媽媽桑等級了,過個兩年,也許真該考慮退休了,總不能讓客人看見吧檯後站了一個年華殘敗的老皇后。
(退休之後要幹嘛呢?)
從一九八○年代出道算起,老七他們這一代也差不多屆臨退役之年了。哪天他們要是走上了街頭抗爭,並非不可能的事。青春年華都在噤聲躲藏中度過了,老來也許撒手一搏,不為別的,為的正是同志該怎樣老有所終。
到底是要學學老榮民找個安養院?還是假裝自己是被子女棄養的獨居老人?小朋友把結婚權看成第一,哪想得到年老這回事。又不是有了婚姻權就一定有人願意跟你成家,真是的。
所以得要有專設給同志的老人院才行,老七常跟客人這麼抱怨:難道七老八十了,還要他們跟院裡其他的老太婆們搞聯誼不成?
1 人間夜
一切仍得謹慎提防的一九八五年—換言之,彩虹旗紅緞帶搖頭丸這些玩藝兒根本還沒問世的三份之一個世紀前。
在台灣當時的報紙只有三張,離國際化還很遠,資訊就像尚未開放進口的洋菸酒一樣,這方面的事更極為稀有也鮮為人知。連在台北市,百姓普遍英文程度仍屬低落,所以千萬別隨便開口,請問哪裡有ㄍㄟ ㄅˋㄚ,他可能會以為你是在用器官粗話罵人。同志?別忘了還是戒嚴時期,「愛人同志」是共產黨用語,罪加一等。
那麼,要怎麼定義MELODY呢?
就乾脆不必明說了。沒錯,若非熟人帶路,還會被小心盤查以防滋事。別招搖,得...
推薦序
彷彿在痴昧/魑魅的城邦
──郭強生的同志愛情倫(推)理故事/王德威
「我需要愛情故事——這不過是我求生的本能,無須逃脫。」
郭強生是臺灣中堅代的重要小説家,最近幾年因爲同志議題小説《夜行之子》(2010)、《惑鄉之人》(2012)以及散文專欄而廣受好評。即將推出的《斷代》代表他創作的又一重要突破。在這些作品裏,郭強生狀寫同志世界的痴嗔貪怨、探勘情欲版圖的曲折詭譎;行有餘力,他更將禁色之戀延伸到歷史國族層面,作爲隱喻,也作爲生命最爲尖銳的見證。郭強生喜歡說故事。他的敍事綫索綿密,充滿劇場風格的衝突與巧合,甚至帶有推理意味。然而他的故事内容總是陰鬱穠麗的,千迴百轉,充滿幽幽鬼氣。這些特徵在新作《斷代》裏達到一個臨界點。
郭強生的寫作起步很早,一九八七年就出版了第一本小説集《作伴》。這本小説集收有他高中到大學的創作,不乏習作痕跡,但筆下透露的青春氣息令人感動。之後《掏出你的手帕》、《傷心時不要跳舞》題材擴大,基本仍屬於都會愛情風格。九零年代中郭強生赴美深造戲劇,學成歸來後在劇場方面打開知名度。他雖未曾離開文學圈,但一直要到《夜行之子》才算正式重新以小説家身份亮相。
《夜行之子》是郭強生暌違創作十三年後的創作結集,由十三篇短片組成。故事從紐約華洋雜處的同志世界開始,時間點則是九一一世貿中心大樓爆炸的前夕。這個世界上演轟趴、嗑葯、扮裝、還有無止無休的情欲爭逐。但索多瑪的狂歡驅散不了人人心中的抑鬱浮躁,不祥之感由一個臺灣留學生的失蹤展開,蔓延到其他故事。這些故事若斷若續,場景則由紐約轉回臺北的七條通,二二八公園。郭強生筆下的「夜行之子」在黑暗的淵藪裏放縱他們的欲望,舔舐他們的傷痕。青春即逝的焦慮、所遇非人的悲哀,無不摧折人心。他們渴望愛情,但他們的愛情見不得天日。就像鬼魅一般,他們尋尋覓覓,無所依歸。
《惑鄉之人》是郭強生第一部長篇小説。藉由一位「灣生」日籍導演在七十年代重回臺灣拍片的綫索,郭強生鋪陳出一則從殖民到後殖民時期的故事。時間從一九四一年延續到二零零七年,人物則包括「灣生」的日本人、大陸父親、原住民母親的外省第二代、再到美籍日裔「二世」。他們屬於不同的時代背景,但都深受國族身份認同的困擾。他們不是原鄉人,而是「惑」鄉人。
而在身份不斷變幻的過程裏,郭強生更大膽以同志情欲凸顯殖民、世代、血緣的錯位關係。對他而言,只有同性之間那種相濡以沫的欲望或禁忌,才真正直搗殖民與被殖民者之間相互擬仿(mimicry)的情意結。 誰是施虐者,誰是受虐者,耐人尋味。《惑鄉之人》也是一部俱有鬼魅色彩的小説。真實與靈異此消彼長,與小説裏電影作爲一種魅幻的媒介互為表裏。
至此,我們不難看出郭強生經營同志題材的野心。他一方面呈現當代、跨國同志眾生相,一方面從歷史的縱深裏,發掘湮沒深處的記憶。當年以《作伴》、《傷心時不要跳舞》知名的青年作家儘管異性愛情寫(起來)得心應手??,但下筆似乎難逃啼笑因緣的公式。閲讀《夜行之子》、《惑鄉之人》這樣的小説,我們陡然感覺作家現在有了年紀,有了懺情的衝動。他的故事誇張艷異之餘,每每流露無何奈何的淒涼。他不僅訴説熾熱的愛情,更冷眼看待愛情的苦果。荒謬與虛無彌漫在他的字裏行間。隱隱之間,我們感覺這是「傷心」之人的故事,仿佛一切的一切不足爲外人道矣。
*
也許正是這樣「傷心」著書情懷,促使郭強生短短幾年又寫出另一本長篇小説《斷代》吧。不論就風格,人物,以及情節安排而言,《斷代》都更上一層樓。《夜行之子》儘管已經打造了他同志三書陰鬱的基調,畢竟是片段組合,難以刻畫人物内心轉折深度。《惑鄉之人》雖有龐大的歷史向度,而且獲得大獎(金鼎獎)的肯定,卻過於鋪陳主題和綫索,寓言性大過一切。在《斷代》裏,郭強生選擇有所不為。他仍然要訴説一則——不,三則——動聽的故事,但選擇聚焦在特定人物上。他也不再汲汲於《惑鄉之人》式的歷史敍事,但對時間、生命流逝的省思,反而更勝以往。
《斷代》的主人翁小鍾曾是名民歌手,轉任音樂制作人。小鍾也是愛滋病陽性帶原者。早在高中時期,小鍾在懵懂的情況下被同學姚誘惑了。小鍾暗戀姚,後者卻難以捉摸,而且男女通吃。多年以後兩人重逢,一切不堪回首。有病在身的小鍾萬念俱灰,而姚婚姻幸福,而且貴為國會要員。但事實果真如此麽?
與此同時,臺北七條通裏一個破落的同志酒吧發生異象。老闆老七突然中風,酒吧裏人鬼交雜。小説另外介紹超商收銀員阿龍的故事。阿龍愛戀風塵女子小閔,但是對同志酒吧的風風雨雨保持興趣,陰錯陽差的捲入老七中風的意外裏…
如果讀者覺得這三條綫索已經十分複雜,這還是故事的梗概而已。各個綫索又延伸出副綫索,其中人物相互交錯,形成一個信不信由你的情節網絡,環環相扣,頗有推理小説的趣味。郭強生喜歡說故事,由此可見一斑。識者或要認爲郭的故事似乎太過傳奇,但我們不妨從另一個方向思考。用郭強生的話來説,「我需要愛情故事——這不過是我求生的本能,無須逃脫。」------
戀一個人的折磨不是來自得不到,而是因為說不出,不斷自語,害怕兩人之間不再有故事。符號大師把愛情變成了語意,語意變成了文本,又將文本轉成了系統,只因終有一個說不出的故事而已。
———《 夜行之子》,p 92
愛情何以必須以故事般的方式演繹?就他的作品看來,有一種愛情如此「一言難盡」,以至只能以最迂回的方式說出。或者說愛情力量如此神秘,不正如故事般的難以置信?或更存在主義式的,不論多麽驚天動地的愛情,一旦說出口,也不過就是故事,或「故」事罷了。
在《斷代》裏,郭強生儼然有意將他的故事更加自我化。儘管表面情節繁複,他最終要處理的是筆下人物如何面對自己過去的往事——甚或是前世。小説的標題《斷代》顧名思義,已經點出時間的 「惘惘的威脅」。以第一人稱出現的小鍾儼然是敍事者的分身。小鍾自知來日無多,回顧前半生跌跌撞撞的冒險,只有滿目瘡痍的喟嘆——一切都要過去了。檢索往事,他理解高中那年一場羞辱的性邂逅,竟是此生最刻骨銘心的愛的啓蒙。剪不斷,理還亂的愛慾是痛苦和迷惘的根源,也是敍事的起點。
但小説真正的関鍵人物是姚。相對於小鍾,姚周旋在同性與異性世界,執政黨與反對黨,還有上流與底層社會間,是個迷樣的人物。他一樣難以告別過去,也以最激烈甚至扭曲的方式找尋和解之道。姚是強勢的,但在欲望深處,他卻有難言之「癮」。小説最後,故事急轉直下,姚竟然和所有綫索都沾上瓜葛。如果時光倒流,小鍾與姚未必不能成爲伴侶。然而俱往矣。小鍾和姚不僅分道揚鑣,也就要人鬼殊途。
就此我們回到郭強生一九八七年的《作伴》,那青年作家初試啼聲之作。故事中的主人翁無不帶有阿多尼斯 (Adonis) 美少年的雙性丰采,而當時的少年果然不識愁滋味。一切的羅曼蒂克不過是有情的呢喃。然而就著二零一五的《斷代》往回看,我們有了後見之明。原來《作伴》那樣清麗的文字是日後悲傷敍事的前奏,而那些美少年注定要在情場打滾,成爲難以超生的孤魂野鬼。回首三十年來的創作之路,有如前世與今生的碰撞,難怪郭強生覺得不勝滄桑了。
*
現代中國文學對同志題材的描寫可以追溯到五四時代。葉鼎洛(1897-1958)的《男友》(1927)寫一個男教員和男學生之間的曖昧情愫,既真切又感傷。廬隱(1898-1934)的《海濱故人》(1925)則寫大學女生相濡以沫的感情以及必然的失落,淡淡點出同性友誼的惘然。以今天的角度而言,這些作品游走情愛想像的邊緣,只是點到爲止。主流論述對同志關係的描述,基本不脫道德窠臼。重要的例子包括老舍(1899-1966)的《兔》(1943)和姜貴的《重陽》(1960)等。後者將一九二零年代國共兩黨合作投射到同性戀愛的關係裏,熔情欲與政治於一爐,在現代中國小説獨樹一幟。
但論當代同志小説的突破,我們不得不歸功白先勇。從一九六、七零年代《台北人》系列的〈那滿天亮晶晶的星星〉、《紐約客》系列的〈火島之行〉等, 白先勇寫出一個時代躁動不安的欲望,以及這種欲望的倫理、政治坐標。一九八三年《孽子》出版是同志文學的里程碑,也預示九十年代同志文學異軍突起。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如何看待郭強生的作品?如果並列《孽子》和郭的同志三書,我們不難發現世代之間的異同。《孽子》處理同志圈的聚散離合,仍然難以擺脫家國倫理的分野。相形之下,郭強生的同志關係則像水銀般的流淌,他的人物滲入社會各階層,以各種身份進行多重人生。兩位作家都描寫疏離、放逐、不倫、以及無可逃必的罪孽感,但是白先勇慈悲得太多。他總能想像某種(未必見容主流的)倫理的力量,作爲筆下孽子們出走與回歸的輻輳點。郭強生的夜行之子不願或不能找尋安頓的方式。在世紀末與世紀初的喧嘩裏,他們貌似有了更多的自為的空間,卻也同時曝露更深的孤獨與悲哀-------
夜晚降臨,族人聚於穴居洞前,大家交換了躊躇的眼神。手中的火把與四面的黑暗洪荒相較,那點光幅何其微弱。沒有數據參考,只能憑感受臆斷。改變會不會更好,永遠是未知的冒險。
有人留下,有人上路。流散遷徙,各自於不同的落腳處形成新的部落,跳起不同的舞,祭拜起各自的神。
有人決定出櫃,有人決定不出櫃;有人不出櫃卻也平穩過完大半生,有人出櫃後卻傷痕累累。無法面對被指指點點寧願娶妻生子的人不少。寧願一次又一次愛得赴湯蹈火也無法忍受形隻影單的人更多。所有的決定,倒頭來並非真正選擇了哪一種幸福,而更像是,選擇究竟寧願受哪一種苦……
《斷代》,P XXX
郭強生的寫作其實更讓我們想到九十年代兩部重要作品,朱天文的《荒人手記》(1994) 以及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1997)。兩作都以自我告白形式,演繹同志世界的他(她)/我關係。《荒人手記》思索色慾形上與形下的消長互動,《蒙馬特遺書》則自剖情之為物最誘人、也兇險的可能。兩部作品在辯證情欲和書寫的邏輯上有極大不同。《荒人手記》叩問書寫作爲救贖的可能,「我寫故我在」的可能。《蒙馬特遺書》則是不折不扣死亡書簡,因爲作者以自身的隕滅來完成文字的銘刻。 兩部作品都有相當自覺的表演性。前者以女作家「變裝」為男同志的書寫,演繹性別角色的流動性;後者則將書寫醖釀成爲一樁(真實)死亡事件。
如上所述,郭強生的作品充滿表演性,也藉這一表演性也(刪)通向他的倫理關懷。但他在意的不是朱天文式的文學形上劇場,也不是邱妙津式的告別生命/寫作演出。他的對同志倫理的推衍,表現在對推理小説這一文類的興趣上。《夜行之子》、《惑鄉之人》已經可見推理元素的使用。是在《斷代》裏,郭真正將這一文類抽絲剝繭的特徵提升成對小説人物關係、身份認同的隱喻。在同志的世界裏,人人都扮演著或是社會認可,或是自己欲想的角色。這是表演甚至扮裝的世界,也是一個諜對諜的世界。雙方就算是裸裎相見,也難以認清互相的底綫。
對郭強生而言,推理的底綫不是誰是同志與否,而是愛情的真相。這是《斷代》著墨最深的地方。如果「愛情」代表的是現代人生「親密」關係的終極表現,郭強生所刻畫的卻是一種吊詭。同志圈的愛慾流轉,往往以肉體、以青春作爲籌碼,哪有什麽真情可言?同志來往「真相大白」的時刻,不帶來愛情的宣示,而是不堪,是放逐,甚至是死亡。但相對的,郭強生也認爲正因爲這樣的愛情如此不可恃,那些鋌而走險、死而後已的戀人,不是更見證愛情摧枯拉朽的力量?
擺盪在這兩種極端之間,《斷代》的故事多頭並進。結局意義如何,必須由讀者自行領會。對郭強生而言,《斷代》應該標誌自己創作經驗的盤整。青春的創痛、中年的憂傷成爲一層又一層的積澱,如何挖掘剖析,不是易事。早在《夜行之子》裏,他已經向西方現代同志作家如王爾德(Oscar Wilde)、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以及佛斯特(E. M. Foster)等頻頻致意,反思他們在書寫和欲望之間的艱難歷程。藉著《斷代》,他有意見賢思齊,也回顧自己所來之路。荒唐言中有著往事歷歷,再囘首已是百年身。他創造了一個痴昧的城邦——也是充滿魑魅的城邦。
後記
郭強生十八嵗進入台大外文系,我有幸曾擔任他的導師。大學四年,強生給我的印象是極聰明、極乖巧,不愧是校園才子,讀書則力求「適可而止」。大四畢業那年,強生出版《作伴》,應他所請,我欣然為之作序,期許有加。哪裏知道當時的老師和學生其實一樣天真。
九十年代中期強生赴紐約大學深造,我適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於是又有了見面機會。記得他邀請我看了好幾場百老匯戲劇,聚會場合也常看到他。我甚至曾安排他到哥大教了幾年課。之後他回到臺灣,我轉往哈佛,逐漸斷了聯絡。
強生囘台後曾經熱衷劇場編導,未料這幾年他重拾小説創作,而且迭獲好評。看強生的作品我每每覺得不安,倒不是内容有多少聳動之處,而是敍述者的姿態如此陰鬱蒼涼,和印象中那個年輕的、仿佛不識愁滋味的大學生判若兩人。我不禁關心起來:這些年,他過的好麽?
在新作中他對自己成長的世代頻頻致意,不禁讓我心有慼慼焉。想起他大學英文作文寫的就是小説,而且内容悲傷,以致我十分不解。我們的師生關係是一回事,但顯然有另一個做為小說家的強生,這些年經過了更多我所不知道的生命歷練。虛構與真實永遠難以釐清。閲讀他的小説,還有他更貼近自己生活的散文,我似乎正在重新認識——想像——一個作家的前世今生。
也許這正是文學迷人之處吧。強生的新作定名為《斷代》,似乎呼應了我們的今昔之感。曾經的少年已經是中年,誰又沒有難言的往事?唯有文字見證著一路走來的歡樂與悲傷。謹綴數語,聊記三十年師生緣分。祝福強生。
彷彿在痴昧/魑魅的城邦
──郭強生的同志愛情倫(推)理故事/王德威
「我需要愛情故事——這不過是我求生的本能,無須逃脫。」
郭強生是臺灣中堅代的重要小説家,最近幾年因爲同志議題小説《夜行之子》(2010)、《惑鄉之人》(2012)以及散文專欄而廣受好評。即將推出的《斷代》代表他創作的又一重要突破。在這些作品裏,郭強生狀寫同志世界的痴嗔貪怨、探勘情欲版圖的曲折詭譎;行有餘力,他更將禁色之戀延伸到歷史國族層面,作爲隱喻,也作爲生命最爲尖銳的見證。郭強生喜歡說故事。他的敍事綫索綿密,充滿劇場風格的衝突與巧合,甚至帶...
目錄
彷彿在痴昧/魑魅的城邦──郭強生的同志愛情倫(推)理故事/王德威
1 人間夜
2 關於姚……
3 舊歡
4 重逢
5 在迷巷
6 沙之影
7 夢魂中
8 勿忘我
9 痴昧
10 痴魅
附錄/在純真失落的痛苦中覺醒──郭強生專訪/何敬堯 採訪
彷彿在痴昧/魑魅的城邦──郭強生的同志愛情倫(推)理故事/王德威
1 人間夜
2 關於姚……
3 舊歡
4 重逢
5 在迷巷
6 沙之影
7 夢魂中
8 勿忘我
9 痴昧
10 痴魅
附錄/在純真失落的痛苦中覺醒──郭強生專訪/何敬堯 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