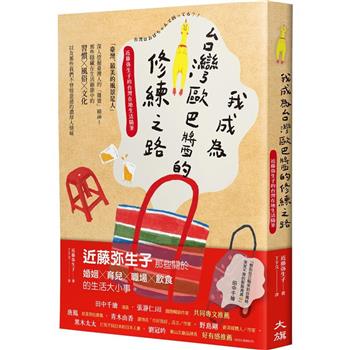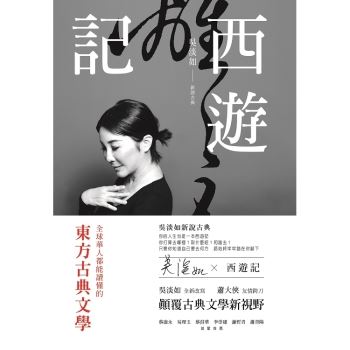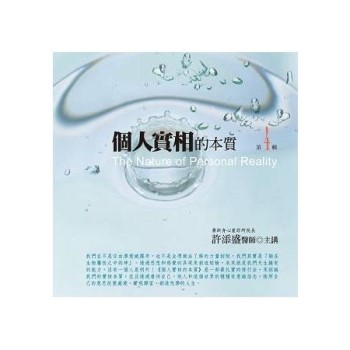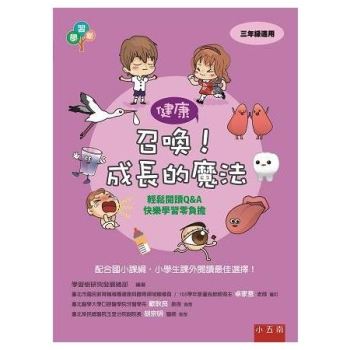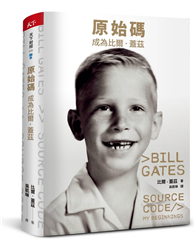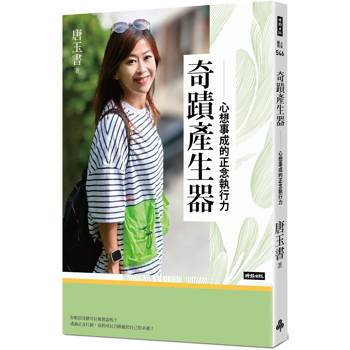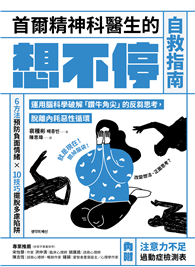緒論
馬華文學與民族─國家
嚴格來說,這是我第二本馬華文學論文集──近年重印的《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增訂版(麥田,2012)終於可以還原它該有的樣子──那是我的第一本馬華文學論文集,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視之為一本「專書」。如果從元尊版《馬華文學與中國性》(1998)算起,第一本與第二本馬華文學論文集的出版的時間相距十七年,但其間出版了三本其他性質的論文集。收入本書的主要論文分別發表於二○○三至二○一四年這十二年間,曾經為了讓它更像「專書」,個別論文做了不同程度的文字調整。組稿甚至早於《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增訂版,因故而拖延了兩年多(包括送審)。因此我的想法也一再改變,有的篇章拿掉了又放回去,有的放進去了又拿掉。
論文的寫作對我而言有一定的行動的意義,是我「介入」歷史的一種方式。這是和那些隔岸觀火,甚至隔靴搔癢的歷史的局外人的情況是全然不同的。
以下的第一部分甚至作為單篇文章應莊華興之邀(以〈我們的馬華文學〉)為題(《當代評論》2〔二○一二年六月(吉隆坡:林連玉基金會)〕)發表了。這部分交代了馬華文學研究對我而言何以不可能不預設文學性,而這文學性的思想資源來自何方。這也算是對那位一再批評我的「昔日之友」的部分回應。第三部分是簡略的交代收進的論文的身世,篇章順序對我而言一向是一種敘述方式。
一、我們的馬華文學
多年來,我們 的馬華文學研究嘗試從馬華文學的根源處做刨根究柢似的探討,包括「馬華文學」的基礎定義、屬性及它究竟能做怎樣的擴大(譬如關於「華馬文學」的策略思考)或翻轉(「華人少數文學」、「無國籍華文文學」、「旅臺的在地」);當然,這樣的探索,必然得進入文學史。然而,什麼是馬華文學史?它不正是我們要重新解釋(重寫)的對象嗎?是的,我們的研究一樣得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縱使這領域裡的前人並非巨人,肩膀也沒那麼寬大。然而,或許也因為這樣,所有的論述必然是在爭議中展開。不只是「馬華」、「文學史」,甚至還涉及「文學」。
譬如說,在馬華文學的場域裡,文學究竟是什麼?
這樣的提問表面上似乎毫無必要。如果謝詩堅的研究是對的,馬華文學的主流不就是以社會─政治功能為絕對優先的革命文學嗎?
而我們的研究不也是以具體的文學現象、文學作品為觀察分析的對象嗎?然而這樣的提問涉及我們從事研究的基礎預設:我們自己是怎麼看待文學的?我們認為文學是什麼,或該是什麼?沒有特定的基礎預設,研究是不可能展開的。雖然我們討論的作品大都早已被文學社群視為文學作品閱讀,相關的文學現象也早已被認可為文學事實。因而問題並不在於這一基礎層面的確認,而是更進一步的評價問題。對特定文學作品的價值認同往往有著嚴重的分歧,連帶的涉及對文學現象的解釋。而這些,都必得涉及理論的參照。
因為馬華文學畢竟是現代的產物,和所有殖民地新文學的狀況類似。那和西方的殖民擴張、民族國家的創立、大規模移民脫離不了干係。因而我們調動的學術資源幾乎都是西方的,縱使流派有所不同。換言之,還是必須站在西洋巨人的肩膀上,不論是贊同還是反駁,其實都離不開「大國理論」。
二十年前我還在大學念書時,買了甫中譯出版的保加利亞裔法國文學理論家托多洛夫(Tzvetan Todarov)的《批評的批評:教育小說》(Critique De La Critique) ,該書選擇若干二十世紀文學理論大家作為對話的對象,問題正是圍繞著諸家對「文學」的不同處理上。這些大家毫無例外的受惠於德國浪漫主義,並嘗試超越它。開宗第一章〈詩的語言〉即詳細梳理了俄國形式主義的詩學。托多洛夫有說服力的指出,形式主義詩學的背景除了康德美學之外,還應考慮康德以後德國浪漫主義的實踐,後者只怕更為關鍵。而在形式主義的後期,浪漫主義之詩的語言是「自在目的」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語言藝術的特殊性其實離不開歷史的參照。「所謂的特殊並不存在,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只存在於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中,而不是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它只存在於某些特殊的歷史時刻。在嚴格意義上,也難以截然劃分文學與非文學,因為並沒有「適用於而且只適用於所有文學類別的規則」 。然而從事實際研究的我們,並不需要那樣「適用於而且只適用於所有文學類別的規則」,因為我們研究的不是「文學本身」,而是具體歷史─社會中的文學生產。即使似乎立場最為形式主義的學者,也不會愚昧到不知道文學是一種社會生產。譬如在韋勒克、沃倫(Rene Wellek & Austin Warren)《文學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這本英美新批評的總結之作中,也會有這樣的話:「文學是一種社會性的實踐,它以語言這一社會創造物作為自己的媒介。……文學的產生通常與某些特殊的社會實踐有關;……文學具有一定的社會功能或效用,它不單純是個人的事情。因此,文學研究中提出的大多數問題是社會問題。」 雖然韋沃二氏強調的還是文學傳統和形式規範,相對輕視文學生產的外部條件(該書以文學的內在/外緣的劃分,在學術上是站不住腳的)。對我們而言,知識社會學(及形形色色的歐陸社會學)卻一直是必要的參照。然而形式主義的文學訓練是基本的,它讓我們有可能對具體作品做風格判斷、進行細緻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必須有那樣的基礎預設方可能參與文學研究,去辨識它自在目的的歷史瞬間(縱使只是烏托邦的瞬間),或者界定它的社會功能(或者形式的意識形態)。
況且,就我們置身的文學科系而言,它原就是近代的產物──不論是中國、港、臺還是東南亞新興民族國家,近代大學都是參考歐美的體制而建立。以我置身的科系而言,縱使中國自先秦以來就有「文章博學」的觀念,但在現代大學的建立過程中,還是選擇了西方近代的文學觀念(浪漫主義式的──辭章之學)以做為自我界定 ,並以之構造文學學科、「發明」文學史。因而自五四以來的文學科系均有相當數量的課程是凝注於審美客體自身的,那些被列為必讀的詩選文選詞曲選小說選,都是經由特定學術社群集體討論出來的經典。縱使從一種相對主義的立場來看,
所謂的「文學經典」,以及「民族文學」的無可懷疑的「偉大的傳統」,卻不得不被認為是個由特定人群出於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時代形成的構造物。文學作品或傳統的價值並不在其本身,……﹝價值﹞意謂某些人在特定境況中依據特殊標準和按給定目的而賦予價值的任何事物。
上引文否定任何內在的本質,認為必須訴諸群體(往往以階級、性別、族群、教育背景、世代,甚至性取向為切分指標)與群體間在文學場域裡的角力爭戰,以形成各自的共識。在那樣的過程中,相關價值預設甚至被凝固為慣例規範。藉由教學、各自編的選集、大系、論述,製作各自認定的文學團塊(或文學史)。如果它獲得學術社群的普遍接受,那就有了延續性,可以說是相對成功的經典化。如果得到一代又一代學人與文學人的認可,它就有了同一性,反面也論證了支撐它的價值體系還沒有受到顛覆。近代以來,「古典中國文學」的同一性就是那樣被建構起來的。縱使曾受到反傳統主義、極左意識形態(民粹政治的極致)的衝擊,究竟還是挺過來了。
馬華革命文學自然也是特殊歷史境遇的產物,它曾以凌越一切的霸權形式統馭馬華文壇。以自身群體的意識形態設定文學的價值,並藉由文學批評、雜文頒布法則、清算異己,製作文學經典(「大系」)。縱使有當代新左思潮的奧援,但我覺得它畢竟一樣是「由特定人群出於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時代形成的構造物」,它預設的文學慣例當然是可以爭論的。總而言之,針對文學的看法的論爭必然涉及價值立場,因此不免是場價值之爭。馬華文學的歷史還很短淺,我們介入的時間也很短,一切都還有待歷史的裁決。
而我的這些論文,更非純文學的賞析之作,涉及的問題毋寧是決定馬華文學的形態及其解釋架構的那特定的歷史─社會現實。於內,涉及的是它與馬來民族國家的緊張關係;於外,涉及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的關係。自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分裂成兩部分,馬華文學同時與兩者產生了關聯:人民共和國──左傾運動與革命文學;中華民國(臺灣)──旅臺文學。這兩個民族國家之外,還有一個虛擬式的民族國家:臺灣共和國。「我們的馬華文學」便是生存在這樣的夾縫之中。
二、重新編次
本書經過多年整理修訂,我增加了三篇這兩年新寫的論文,〈在或不在南方〉、〈審理開端〉和〈馬華文學與馬共小說〉。原為十二篇論文,現為十五篇,感覺完整些。次第也稍稍調整,〈審理開端〉、〈反思「南洋論述」〉、〈兼語國民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字」〉這三篇,都是反思馬華文學研究本身的方法論、理論預設之類的相關問題。算是「後設馬華文學」的問題(模仿佛洛依德「後設心理學」的修辭)。列在前頭,總結這十多年對相關問題的反思。方法是後來的,是多年的爭辯中衍生出來的。部分論文也增添隱喻式的主標題。另一個變化是把三十多篇短論約九萬字抽出,另成一小書,在大馬有人出版社那裡出版。馬華文學的議題,在馬來西亞出版應該比在臺灣出版有意義,我不認為臺灣讀者會對它感興趣。其他十一篇論文為第二卷,附錄一篇談華文教科書的。
書名也改了,原題《馬華文學與民族─國家》,改為《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當做是另一個版本,修訂版。小文學和少數文學都是同一個英文minor literature的中譯,小文學是錦忠的譯名,而少數文學對應的是王賡武他們「東南亞華人少數族裔」的華人史論述。不妨兩存之。minor literature也是我們開始思考馬華文學的理論參照之一。
三、敘述方式
收在這集子的十五篇論文,大部分先作為研討會論文口頭發表,再刊於學報或收入研討會論文集;部分且發表於報章副刊或文學雜誌,而被歸類為「文學批評」。這十多年來學術場域最大的變化之一是,文學刊物上的文學批評在學術上已變得毫無價值,因為文學刊物並不是「有匿名外審制」的「學術刊物」(更別說學術刊物還有分等級)。換言之,這是個文學批評的學術價值被摧毀的年代,學術在學術化、形式化、客體化。實質如何不再那麼受關注。
十五篇論文裡,有半數以上都在處理文學史,以及馬華文學的屬性、它的政治境遇,及可能的未來。卷一的第一篇〈重審開端〉我希望是和林某對話的終篇,一個再次告別的手勢。分歧一開始就存在了,但我終究難以理解:這麼多年過去了,為什麼那些什麼都不做、袖手旁觀的人反而可以自認站在較高的倫理位置?重讀舊文〈回歸方修〉,早在二○○一年我就已看出這不可調和的分歧了,因此多年沒與他對話,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譬如製作我的馬華文學。不料他還是緊咬「文學性」不放,只好再做個總的清理。
〈反思「南洋論述」〉,原是為張錦忠《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寫的緒論,檢討了馬華文學的基本認識論、方法論問題,針對我們已開展出來的諸視角(華馬文學、複系統、在地知識等)展開反思;也檢討了在臺馬華文學論述何以會遲到,這些提問今天看來依然尖銳──因此我很難理解何以此書的審查人之一竟然建議我拿掉它──或許他竟是這篇論文批評的對象之一?
這篇二○○三年的論文還有另一層意義,當初原以為我、林建國、張錦忠都會各出一本論文集,以作為「我們的『共圖』」、小小的紀念碑。我的《馬華文學與中國性》於一九九八年率先出版,時在美國念博士的林建國為它寫了篇批判性的導論;二○○三年錦忠的《南洋論述》出版,我也為它寫了篇批判性的導論。預期中的林建國的論文集卻遲遲未見,而錦忠的導論〈再論述──一個馬華文學論述在臺灣的系譜(或抒情)敘事〉(去國.汶化.華文祭:二○○五年華文文化研究會議,二○○五年一月八至九日,臺灣新竹,國交通大學)早在二○○五年就寫就發表了 。和林之間昔年那種「共圖」之誼,不知怎的煙消雲散,他大概忙於更雄偉更有野心更有學術價值的計畫去了。
〈兼語國民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馬華文學史及其不滿〉則是原題為〈國家、語言、民族─馬華─民族文學史及其相關問題〉,刪去與本書論文重複的一節後的樣態。一方面回應莊華興的馬來西亞國民文學「兼語」論──我覺得那是徒勞的──不過是重複了大馬國家文學的單語邏輯。再則是一探中國大陸近年來馬華文學研究中的中華民族主義預設,那是馬來民族主義的有趣對照。它同樣涉及了兩種民族主義,與〈華文少數文學〉恰恰構成一對照。
對於大陸的馬華文學研究,我想勾勒出它們的模式及意識形態局限就夠了,不必逐個兒指名道姓的去談。他們自己學術場域的問題,也得由他們自己去反思、解決。而那些被派到新、馬的青年學者,到目前為止普遍上都還提不出像樣的論題,有幾位態度卻非常囂張,不知道仗的是什麼勢。
近年許多大馬華裔青年學者留學中國取得博士學位,在馬華文學這領域一樣有受困之感,也沒能開創出什麼的局面。我同意錦忠的意見,還有大量的馬華文學史料沒有整理。在地的應利用地利優勢好好的從史料下手,做出一番成績來。別迷信中國學者的能力,沒能力的多得是。
卷二的十一篇,〈華文少數文學──離散現代性的未竟之旅〉是應大陸一個研討會之邀而寫的(因故未出席),從「離散」及「小文學」的角度概括了馬華文學(作為一種現代產物)的命運,參照卡夫卡(Franz Kafka)、奈波爾(V. S. Naipaul)等西方的案例,勾勒出它的未竟之旅,或可能的未來。作為開篇,有為馬華文學定調的意味。
它和本卷的第二篇〈另類租借,境外中文,現代性──論馬華文學史之前的馬華文學〉均是企圖超出國家、國民身分、國土邊界及新舊文學之分而重寫馬華文學史的一個嘗試,企圖打破現有馬華文學史的民族國家視域。它更以「南來」的流動及面臨的歷史災難為焦點,以康有為與郁達夫這兩個不同時代的南來案例,描述馬華文學歷史的複雜度。收在這裡的新版是兩篇論文的合併,即除了原題論文之外,併入另一篇討論康有為南洋詩的論文〈過客詩人的南洋色彩贅論──以康有為等為例〉。意在指出:如果沒有民族國家做意識形態後盾,即使是南洋色彩也不可能自然延伸出一種本土論。
〈馬華文學的國籍〉則直面馬華文學與馬來西亞民族國家、民族主義之間的複雜關聯。討論的正是處理馬華文學時不可迴避的主題,馬來西亞馬來國族主義(馬來民族主義)及華人民族主義下,馬華文學是處於怎樣的被限定狀態,在國家文學與非國家文學之間,在民族文學與非國家民族文學之間。如此可以理解馬華文學的基本格局是怎麼被設定的。不知不覺間,兩種民族主義限定了馬華文學。因此我建議,無妨技術性的擱置國家文學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裡,可以進而探勘被馬華文學論者視為命根的馬華文學本土論。
〈無國籍華文文學〉是讓馬華文學與臺灣民族主義對撞的一個嘗試。這篇文章寫於臺灣本土化的歷史最高峰,也可說是直接的回應了當時的「政治現實」。在策略上,把臺灣(一九四九後處於怪異民國情境、一九八○年代以來深陷兩種民族主義生死搏鬥的臺灣)納入視野,同樣作為移民社會,因冷戰與僑生政策而與馬華文學有了深刻的交集。本文以臺、馬華人移民史為背景,試著提出一個「無國籍華文文學」的解釋方案,企圖在馬、臺民族國家文學之外尋求解釋的可能。看似不可能的比較,意在指出,作為漢移民社會的衍生物,即使偶然的歷史境遇不同,馬華文學與臺灣文學仍有諸多結構上的相似之處:對中國的離心與向心──與中國之間緊張的互動、對抗性的本土化(自訴為本質化的「鄉土」),兼之用不用中文的煩惱、自身族群方言文字化的困難、對殖民語言的固著愛戀、族群分化……而在一九六○年代後,冷戰結構藉由留學管道為兩地華人建立了個文學通道,得以一定程度的讓馬華文學在馬來西亞國族主義之外找到一種補充性的寄生形式,同時歸屬與不歸屬兩地的華文文學,且與後者有持續的、間或緊張的對話關係。簡言之,多年來最令我不解的是,那些以馬華文學為敵的台灣本土論者,怎麼竟然看不出我們原該是他們最有力的盟友?
〈土與牆〉(原題〈東南亞華人少數民族的華文文學──政治的馬來西亞個案──論大馬華人本地意識的限度〉)可能是迄今為止對馬華文學本土論最有力的挑戰。這篇文章企圖論證,對馬華文學而言,構成它最深刻焦慮的本土恰恰是不可能的:語文、國家意識形態限制了它可能性的地平線。在馬來西亞國族主義的前提下,只有用馬來文寫作方有資格談論本土,此外任何關於本土的討論都是一廂情願的。或者說,只能以強迫性妄想的形式。如果說《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較為集中的處理「中國性」這樣的徵狀形式──過往一般被稱為中國意識、中國情懷,甚至僑民意識──在臺灣文學的語境裡,即祖國情懷,甚至是遺民意識,那本書最核心的論題即是「本土」這一對應的徵狀形式。
早在馬來亞建國前的一九三○年代,在英殖民的環境裡,有識之士即提出了「馬來亞化」的主張,雖然彼時政治的考量(在地鬥爭、反殖、爭取獨立)遠大於文學(馬華文學史上的「文學」始終是個問題),然而認同的問題還是急迫的被歷史提了出來。
建國以來,因為華文爭取為官方媒介語的失敗──符合國家意識─國民意識的講法是,華人以獲得馬來亞公民權交換承認馬來語為馬來(西)亞唯一的官方媒介語、政治權力的「馬來至上」。華文文學和華文私立中學一樣,因不受國家承認而被迫處於體制之外。在文學的場域,這樣的處境反而加強了自身的「本土」訴求,總是從題材、國家民族意識、在地腔調等方面強調,放大了馬華文學的馬字,棄兒似的,深怕稍稍遠離了就不被承認──即使事實上它早已(且是現在進行式的)不被承認。因被遺棄而更強烈的固著戀慕,甚至常常表現為對小社群內部異己者的無情砍殺攻擊。他們無意識的預設了它的可能性,而從未嘗試去思考它的不可能性,更別說去思考本土的不可能性帶來的文學的可能性。那樣的挫敗內化後,讓馬華文學反覆的呈現出它的雙極性──交替的憤懣與憂鬱。雖然後者,在革命文學的雄偉意志裡總是被壓抑下來,但在非革命文學那裡找到它長遠的棲地。
〈重寫自畫像──馬華現代主義者溫祥英的寫作及其困境〉討論的溫祥英是馬華現代主義的重要作家之一,有很好的英語能力,文學教養遠在一般的馬華作家之上。但作品並不多,可以看到在那個社會環境裡,寫作被生活的嚴重擠壓。溫老近年退休後復出後寫了若干篇佳作,猶是可以期待的新人。本文從他的作品及文論詳細的分析了他的寫作困境。他是馬華「盆栽境遇」的具體個案之一。
〈Negaraku──旅臺與馬共〉可以說是對〈無國籍華文文學〉及〈馬華文學的國籍〉另一種意義上的補充。一樣涉及國族認同、民族主義,更帶進過往討論馬華文學較少涉及的一個面向:馬共的歷史存在本身。它對華人史的意義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對文學史呢?本文的新意或許在於指出旅臺是冷戰情境下的一種交換,以符合美國利益的民國─臺灣的中華想像交換左翼的革命中國想像。這和馬共(在政治上華人總是被迫與它緊緊的捆綁在一起)在馬來亞建國後的處境有直接的關聯,可是這層面過去的討論都忽略了。而本文借用一些晚近的影片材料(一旅臺人關於馬來西亞國家──國歌Negaraku諧謔的饒舌歌、一馬來導演略帶嘲諷的馬共「紀錄片」),以帶出相關問題。馬華文學的「盆栽境遇」一如馬共的受困叢林,它受困於國家意識形態、民族主義,也受困於徹底商業化的移民文化。這篇論文和〈無國籍華文文學〉在刊於《文化研究》時,都有認真的審查人寫了詳細的審查意見,雖然部分意見我並不贊同,且在註解裡做了詳細的答覆,因有助於澄清論文中某些論點,也就保留了下來。我珍惜這樣的對話。
〈最後的戰役──論金枝芒的《饑餓》〉討論的是馬共陣營最有才華的作家見證馬共困境的長篇遺作《饑餓》。以晚近的馬共回憶錄做對照,詳細的分析它的文學特性與意識形態特性,藉以思考馬共對馬華文學的介入。也探觸馬共文學在文學上的根本局限,它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
〈馬華文學與馬共小說〉處理的是嚴格意義上的左翼的文學生產。最主要的部分應是討論韓素英的,她以英文撰寫、寫於馬來亞建國前夕的「馬共小說」,將近七十年來並沒有被超越。這另一方面反映的是,馬華文學自身創造力的低落。本文也約略稍微全面的回顧一下《餐風飲露》之後,馬共陣營內外不同的馬共題材小說,包括我自身的相關寫作。
〈李永平與民國〉討論了「我們旅臺」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李永平與民國─臺灣的複雜勾連。四十年的旅臺,有著強烈的中國認同,也難免受臺灣本土化的嚴峻考驗。經歷了臺灣四十年來的種種變化,他的處境、他的認同困境本身足以說明「旅臺」本身的複雜性。多年來我寫了多篇論文討論李永平,也一再違反他的意願把他強拉進「我們的」馬華文學,雖然他也許更願意被認定為是一個中國作家,境外歸僑。這可能也是我的李永平論的終篇。我們對馬華文學的思考,一開始就緊貼著李永平的寫作實踐。二十多年過去了,那些圍繞李永平的問題對我而言也不再是重要問題了。李永平已經走到他自己的大河盡頭,我還有自己的崎嶇山路要走。
本書的最後一篇論文〈在或不在南方〉透過王嘯平和賀巾這兩個離境(而非留臺)個案,回頭反思文學的國籍的荒謬,為全書的主題做個迂迴的總結。
附錄的〈製作華文,想像華人──馬來西亞獨中華文中學初中華文課本三種版本分析〉多次放進來又拿出去,總覺棄之可惜。是篇應特定研討會(「華文教學」)之邀而寫的論文(心太軟),是篇用笨方法寫的笨論文,令人疲憊。這大概也是本書中最無趣的一篇論文,卻費去我最多工夫。可見笨是很花時間和精力的。但它其實涉及大馬華校的重要問題。去國多年,沒想到我們的「華文」課竟爾客體化為準外語了。當中小學教科書外包給中國團隊,從中原的立場來看,那不過是「對外漢語教學」的另一種類型罷了。馬華文學在華校教育體系裡必得有一個重要的位置,這種必要的經典化是一種承認的程式。(當然,也不能亂選)自詡捍衛華教的董教總袞袞諸公真的不知道在想什麼。當然,自民國以來中小學華文課本本來就是個戰場,既有龐大的商機,又涉及文化上的意識形態角力,民國與人民共和國,名與利──好名好利好鬥的華人領袖和他們搖搖擺擺的價值認同,從教科書體質的變遷或許多少也可看得出來。
三、墳墓邊的小路
從最早的一篇馬華文學論文(1989)到現在,二十五、六年過去了,寫的並不算多,但主要的問題幾乎都談到了。重讀一遍後我對錦忠說:我們其實已經走得很遠了。雖然和大學術產業相比,實在微不足道,但似乎也只能這樣。但同行有能力參與對話的卻很少。〈重審開端〉新增的主標題「墳與路」均典出魯迅。有的路通向墳地,有的路根本是「死路」。相較之下,多年來我們走的這條,應可說是墓邊的小路,灌木雜草夾道。
我常對同鄉朋友說,其實馬華文學最為急迫的不是論述,而是好作品的生產,是寫作。畢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雖然,火候沒控制好難免煮得「夾生」或燒焦。而現今的學術體制強迫學者們(包括那群大陸學者)不斷的生產學院式論文,現有的馬華文學作品累積其實是不堪負荷的。馬華文學或許將被那些排山倒海的空洞論述給燒成一鍋炭。因此我其實非常同意張景雲先生的呼籲:我們需要的是不那麼學院化的文學研究,而是較自由的文學批評,它本身必須具備一定的溫度與可讀性。有力的論述還是必要的。
十五篇論文中有六篇刊於《香港文學》,特別感謝陶然先生。張錦忠、王德威、莊華興、高嘉謙等朋友,或提供若干資料,或商榷疑義、提供不同意見,或撰寫序文,均不同程度的參予了本書的「製作」。感謝麥田出版社,感謝那些還關心這本書的人。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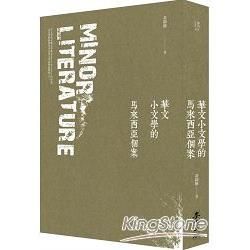 |
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 作者:黃錦樹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15-03-07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80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98 |
小說/文學 |
二手書 |
$ 270 |
二手中文書 |
$ 411 |
其他類型文學 |
$ 411 |
閱讀/賞析 |
$ 458 |
華文文學研究 |
$ 468 |
文學 |
$ 520 |
華文文學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
彷彿分歧與告別才是黃錦樹這本《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論文集的主調。是的,告別,才不會原地踏步。作為時間的倖存者,我們唯有向前走,繼續工作與生活。馬華文學史裏頭的「華文小文學作家」,在過去的時間與空間裏,想必也是這樣。──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華語中心主任 張錦忠
黃錦樹第二本馬華文學論文集,行動版《馬華文學與中國性》。
這些論文,於內,涉及的是它與馬來民族國家的緊張關係;於外,涉及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的關係。自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分裂成兩部分,馬華文學同時與兩者產生了關聯:人民共和國──左傾運動與革命文學;中華民國(台灣)──旅台文學。這兩個民族國家之外,還有一個虛擬式的民族國家:台灣共和國。「我們的馬華文學」便是生存在這樣的夾縫之中。
本書共收錄十五篇論文,第一卷〈重審開端〉、〈反思「南洋論述」〉、〈馬華文學史及其不滿〉是反思馬華文學研究本身的方法論、理論預設之類的相關問題。第二卷收錄其他十一篇論文,附錄一篇談華文教科書。
作者簡介:
黃錦樹,馬來西亞華裔,一九六七年生,祖籍福建南安。一九八六年來台求學,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碩士、清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曾獲多種文學獎。著有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烏暗暝》、《刻背》、《土與火》、《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猶見扶餘》,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文與魂與體:論現代中國性》等,並與友人合編《回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故事總要開始:馬華當代小說選》等。一九九六年迄今任教於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
相關著作
《馬華文學與中國性》
章節試閱
緒論
馬華文學與民族─國家
嚴格來說,這是我第二本馬華文學論文集──近年重印的《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增訂版(麥田,2012)終於可以還原它該有的樣子──那是我的第一本馬華文學論文集,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視之為一本「專書」。如果從元尊版《馬華文學與中國性》(1998)算起,第一本與第二本馬華文學論文集的出版的時間相距十七年,但其間出版了三本其他性質的論文集。收入本書的主要論文分別發表於二○○三至二○一四年這十二年間,曾經為了讓它更像「專書」,個別論文做了不同程度的文字調整。組稿甚至早於《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增...
馬華文學與民族─國家
嚴格來說,這是我第二本馬華文學論文集──近年重印的《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增訂版(麥田,2012)終於可以還原它該有的樣子──那是我的第一本馬華文學論文集,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視之為一本「專書」。如果從元尊版《馬華文學與中國性》(1998)算起,第一本與第二本馬華文學論文集的出版的時間相距十七年,但其間出版了三本其他性質的論文集。收入本書的主要論文分別發表於二○○三至二○一四年這十二年間,曾經為了讓它更像「專書」,個別論文做了不同程度的文字調整。組稿甚至早於《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增...
»看全部
推薦序
始於分歧,終於告別,或,告別(不了)的分歧敘事
──序黃錦樹的馬華文學論文集
張錦忠
黃錦樹收入這本《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集子中的論文,關注對象大多為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馬華文學──的現象、本質、屬性、場域位置、文學史、作家論、文學活動,大致上可以歸納為集體的「馬華文學(史)」、書寫馬共、與國家文學這三個議題。在論述闡述前兩個議題的過程中,難免涉及他和林建國──以及莊華興──對馬華文學史與國家文學的對話,或三人看法間的差異性。這些文章中最早的一篇,應是他給我的書《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
──序黃錦樹的馬華文學論文集
張錦忠
黃錦樹收入這本《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集子中的論文,關注對象大多為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馬華文學──的現象、本質、屬性、場域位置、文學史、作家論、文學活動,大致上可以歸納為集體的「馬華文學(史)」、書寫馬共、與國家文學這三個議題。在論述闡述前兩個議題的過程中,難免涉及他和林建國──以及莊華興──對馬華文學史與國家文學的對話,或三人看法間的差異性。這些文章中最早的一篇,應是他給我的書《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
»看全部
目錄
代序/張錦忠
緒論
卷一:重審開端
1墳與路──重審開端、重返「為什麼馬華文學」
2反思「南洋論述」──華馬文學、複系統與人類學視域
3兼語國民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馬華文學史及其不滿
卷二:華文小文學
4華文少數文學──離散現代性的未竟之旅
5另類租借,境外中文,現代性──論馬華文學史之前的馬華文學
6無國籍華文文學──在台馬華文學的史前史,或台灣文學史上的非台灣文學:一個文學史的比較綱領
7馬華文學的國籍:論馬華文學與(國家)民族主義
8土與牆:論馬華文學本土論的限度
9重寫自畫像──馬華現代主...
緒論
卷一:重審開端
1墳與路──重審開端、重返「為什麼馬華文學」
2反思「南洋論述」──華馬文學、複系統與人類學視域
3兼語國民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馬華文學史及其不滿
卷二:華文小文學
4華文少數文學──離散現代性的未竟之旅
5另類租借,境外中文,現代性──論馬華文學史之前的馬華文學
6無國籍華文文學──在台馬華文學的史前史,或台灣文學史上的非台灣文學:一個文學史的比較綱領
7馬華文學的國籍:論馬華文學與(國家)民族主義
8土與牆:論馬華文學本土論的限度
9重寫自畫像──馬華現代主...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黃錦樹
- 出版社: 麥田 出版日期:2015-03-08 ISBN/ISSN:978986344215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80頁 開數:14.80 * 21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華文文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