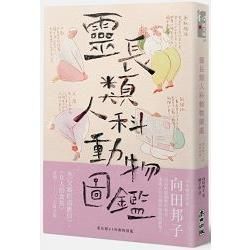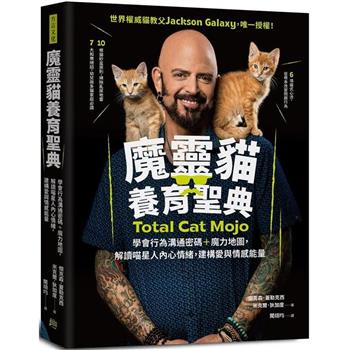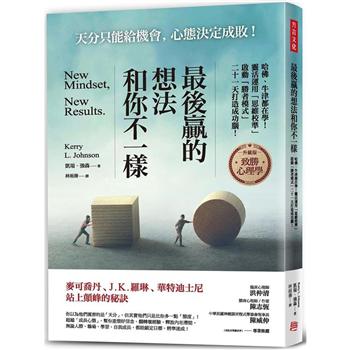在回憶上頭添加一點微笑,把人生綴成一幅幅美麗的插畫。
可悲的、可愛的,都是無可取代的。
可悲的、可愛的,都是無可取代的。
二十世紀曠世才女
大和民族的張愛玲
向田邦子眼光犀利獨到,將世界看作一本有趣的圖鑑,
從童年、男女、家庭到社會政治,一個個看似天真的提問,無不直擊人心。
「安全別針」或「安全保障條約」,真能確保「安全」?
軟綿綿、沒有顏色、看似心機很深的白豆腐,到底哪裡好吃?
到喪家做法事的和尚,收取費用時會不會害羞?
鍋子、打火機、電話亭都已變成透明的,為什麼唯獨郵筒不能透明?
彩色褲襪能在曼谷流行,東京為何就沒有味噌豬排?
下雨天用跑的和小心翼翼地走,哪種方式比較不會淋濕?
為什麼每到截稿日逼近,總是會想好好做菜?
向田邦子的散文藏著鄉愁,
有如翻閱年底的舊日曆,每一張泛黃的紙頁都是成長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