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甩虎媽兩條街,獨立自主小獅子,看他如何爬「升學」這條階梯。
「我感到昏眩,因為這就好像是我,我的童年是那麼短暫。甚至還沒有享受到那四個字『無憂無慮』,就要開始沒完沒了地讀書和考試。還好小時候我做過『壞小孩』,那時候的闖禍搗蛋變成了我最好的回憶。」
他的同班同學大路是他的第一競爭對手,身邊還有最會放大絕的讓老師,
小獅子的屁股永遠把辦公室外面那條所有同學都想閃的「反思凳」坐得熱熱的,
每個科目都拿A,義務服務,零蛋。
竟成為小獅子升學「爬藤」路的死穴?
TEEN,十三歲到十九歲,青少年。
所有的爸媽都知道,這是個「麻煩大了的」時候。
無論是台灣的指考,中國的高考,
所謂的自由美國,要上大學,
SAT後面更跟著一聯串的SATⅡ、AP等等,這裡面還沒有包括PSAT……
面對考試怪獸,無論是美國的孩子還是中國的孩子都是一樣,都在拚命。
只是美國的孩子拚得很釋放,中國的孩子很壓抑。
什麼才是正確的答案?
去了小獅子媽媽「祖國」服務的那個女孩,越洋捎來了一封手寫信,
關於人生,小獅子看見了更多的「選擇」……
※小獅子打怪第一關:大學進學面試
其中有一個問題很讓我費腦筋,竟然問我:「你最喜歡什麼?」看似簡單。但是後面有一條好幾行字的解說:「不可以和你的學習有關,不可以和你的課外活動有關、不可以和你的義務勞動有關,不可以和你的交友有關,不可以和你申請學校有關……」最後還有一句話:「五十個字回答。」
※小獅子打怪第二關:文科?還是理科?
前面是懸崖峭壁,後面是萬丈深淵,我走到了岔路上。我怎麼會落到這樣的境地?我沒有辦法停息,這裡沒有停息的落腳地。我也沒有辦法後退,那是死的靈魂。我只有手腳並用,像一隻壁虎一樣緊緊貼在蒼白的石英岩上向前。我知道任何一個小小的疏忽都會導致失敗,甚至滅亡。
沒有路,這就是我的前程!
這些年來,我不是一直都在朝著沒有路的方向攀岩嗎?常常感覺到一頭撞進了無縫的石壁被Bounce回來,咬了咬牙齒又重新開始。
這就是我自己選擇的科學。
溫馨推薦(按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小 野|作家
王浩威|作家、精神科醫師
李偉文|作家、牙醫、環保工作者
莫 言|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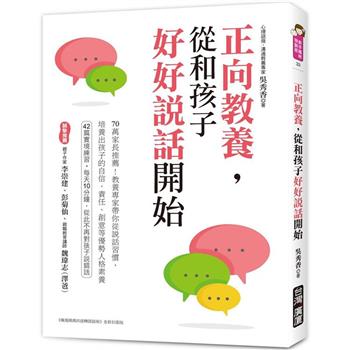








(不動產經紀人) 2025【粗體關鍵字標示必背重點】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條文解析+歷屆試題](八版)(不動產經紀人)](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24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