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張相片,我們要不是不予理會,就是得靠我們自己去把它的意義填滿。這張影像就和所有無法用言語表達的影像一樣,召喚觀看者做出決定。──約翰.伯格
傑夫.代爾,選編約翰.伯格的影像散文集
伯格的批評文字與創作某種虛構的真實故事攜手並進。當伯格悉心檢視照片裡的故事,包括明白揭露與隱藏其下的故事,並將它們哄誘出來時,說故事者的天職與懷抱便取代了影像評論家與質問者的工作。伯格書寫的不只是相片的意義,也說出了異義。
本書收錄的文章包括伯格出版過的書籍,以及先前未曾集結出版的展覽文章或是為展覽專刊撰寫的前言和後記。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攝影的異義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攝影的異義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約翰.伯格 John Berger
一九二六年出生於倫敦。文化藝術評論家、作家、詩人、劇作家,並於一九七二年贏得英國布克獎。一九六二年離開英國,長住在靠近法國邊境阿爾卑斯山的小村鎮裡。
相關重要著作還有《觀看的方式》、《班托的素描簿》、《影像的閱讀》、《藝術與革命》、《另類的出口》、《另一種影像敘事》、《我們在此相遇》、《留住一切親愛的》、《觀看的視界》等。
相關著作
《留住一切親愛的:生存.反抗.欲望與愛的限時信》
譯者簡介
吳莉君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譯有《觀看的方式》、《我們在此相遇》、《留住一切親愛的》、《霍布斯邦看21世紀:全球化,民主與恐怖主義》、《建築的法則》等。任職出版社多年,現為自由工作者。
張世倫
藝評人,攝影研究者,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
劉惠媛
實踐大學工業設計系兼任副教授。
曾任ArtChina藝術雜誌總編輯、世界宗教博物館副館長、公共電視「大家來逛博物館」主持人,從事藝術評論多年。並以《沒有圍牆的美術館》一書榮獲2003年金鼎獎優良圖書獎。
約翰.伯格 John Berger
一九二六年出生於倫敦。文化藝術評論家、作家、詩人、劇作家,並於一九七二年贏得英國布克獎。一九六二年離開英國,長住在靠近法國邊境阿爾卑斯山的小村鎮裡。
相關重要著作還有《觀看的方式》、《班托的素描簿》、《影像的閱讀》、《藝術與革命》、《另類的出口》、《另一種影像敘事》、《我們在此相遇》、《留住一切親愛的》、《觀看的視界》等。
相關著作
《留住一切親愛的:生存.反抗.欲望與愛的限時信》
譯者簡介
吳莉君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譯有《觀看的方式》、《我們在此相遇》、《留住一切親愛的》、《霍布斯邦看21世紀:全球化,民主與恐怖主義》、《建築的法則》等。任職出版社多年,現為自由工作者。
張世倫
藝評人,攝影研究者,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
劉惠媛
實踐大學工業設計系兼任副教授。
曾任ArtChina藝術雜誌總編輯、世界宗教博物館副館長、公共電視「大家來逛博物館」主持人,從事藝術評論多年。並以《沒有圍牆的美術館》一書榮獲2003年金鼎獎優良圖書獎。
目錄
插圖列表
導言
帝國主義的影像
理解一張照片
攝影蒙太奇的政治用途
痛苦的相片
西裝與相片
保羅.史川德
攝影術的使用
外貌
故事
農民的基督
瑪卡塔‧魯斯卡索娃的《朝聖者》
尤金‧史密斯
為協助紀錄片導演柯克‧莫里斯拍攝以史密斯為主角之影片所作的筆記
走路回家
克里斯‧基利普:《在現場》(與希薇雅‧葛蘭特合著)
活著的意思
尼克‧瓦普林頓:《起居室》
安德烈‧柯特茲:《關於閱讀》
地鐵裡的行乞男
亨利‧卡提耶布列松
瑪婷妮‧弗蘭克
《日復一日》傳真前言
尚‧摩爾
肖像速寫
一齣全球級的悲劇
與薩爾加多對談
認同
摩伊拉‧佩拉塔:《近乎無形》
向卡提耶布列松致敬
此地與彼時之間
馬克‧特西維:《我的美》
吉忒卡•漢茲洛瓦:《森林》
阿赫蘭•希伯里:《追蹤兵》
導言
帝國主義的影像
理解一張照片
攝影蒙太奇的政治用途
痛苦的相片
西裝與相片
保羅.史川德
攝影術的使用
外貌
故事
農民的基督
瑪卡塔‧魯斯卡索娃的《朝聖者》
尤金‧史密斯
為協助紀錄片導演柯克‧莫里斯拍攝以史密斯為主角之影片所作的筆記
走路回家
克里斯‧基利普:《在現場》(與希薇雅‧葛蘭特合著)
活著的意思
尼克‧瓦普林頓:《起居室》
安德烈‧柯特茲:《關於閱讀》
地鐵裡的行乞男
亨利‧卡提耶布列松
瑪婷妮‧弗蘭克
《日復一日》傳真前言
尚‧摩爾
肖像速寫
一齣全球級的悲劇
與薩爾加多對談
認同
摩伊拉‧佩拉塔:《近乎無形》
向卡提耶布列松致敬
此地與彼時之間
馬克‧特西維:《我的美》
吉忒卡•漢茲洛瓦:《森林》
阿赫蘭•希伯里:《追蹤兵》
圖書評論 - 評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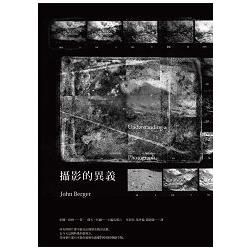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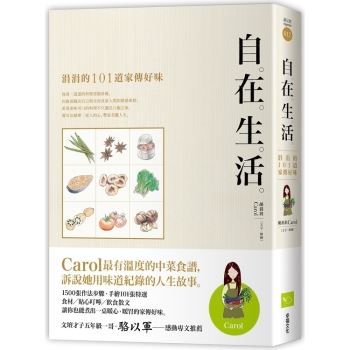








書名原文是Understanding a Photograph,了解攝影。作者約翰.伯格John Berger。是英國文化藝術評論家、作家、詩人、劇作家。行文方式想到之前閱讀的文化批評家,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文學評論的書籍,散文化的書寫,引用例證說明。但是如果一開始被太多瑣碎的文字理論所困,那會延緩閱讀的速度。 依照中文編輯所說,本書為為《持續進行的瞬間》作者傑夫.代爾(Geoff Dyer)從作者近半世紀寫作歷程裡,精煉出二十四篇影像散文,按年代順序選編而成。 只要關心攝影理論與文化批評的人,一定無法閃避這幾個人及他們的作品,分別是: 攝影小史。華特.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班雅明隨筆集》 (Walter Benjamin Essais)內收錄。 論攝影 ON PHOTOGRAPHY。 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明室‧ 攝影札記 La chambre claire。 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及本書作者的《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視覺藝術評論領域的必讀經典。 作者一開始是開始說明觀看的方式與角度,通常攝影作品與文學作品類似,作者已死。引述如下: 面對這張相片,我們要不是不予理會,就是得靠我們自己去把它的意義填滿。這張影像就和所有無法用言語表達的影像一樣,召喚觀看者做出決定。──約翰.伯格 這也是如果相關背景知識不足下,觀看攝影作飲不一定可以達到原作者賦予的目的。創造者選擇角度與時間,凍結下時光下的產物,照片。觀者的解讀。觀者透過作品延伸自己的想法,建構觀賞後的評論與心得,進而拓展了作品的意義範圍。但也可能扭曲。 攝影與美術繪畫很大的不同,就是作者的剪裁,中古世紀很多肖像畫,是沒有背景,背後不是全黑就是在優雅的室內。照片的作品剛好是對所有範圍內的景物一體適用,雖然可以加大景深,強化主體,但是意外載入的資訊不少,可能成為解讀作品的依據之一。 作品一定有觀點,以《鏡頭背後的勇者:用生命與勇氣走過的戰地紀實之路》為例。作者有關點的紀錄戰爭,進而反戰,這才是觀點。避免《旁觀他人之痛苦》中,所提出的質疑:「通過攝影這媒體,現代生活提供了無數機會讓人去旁觀去利用他人的痛苦。」如果沒有觀點,旁觀他人之痛苦的目的只剩下「窺視的淫慾和麻木不仁」。消費他人。這也是飢餓的蘇丹 The vulture and the little girl 這個照片,在得普立茲攝影獎後,攝影者自殺的原因,因為他太過旁觀,而非人道支援被攝影者。攝影者永遠要將主觀紀實與客觀平衡,介入關懷與獨立報導之間時時縈懷於心。 在閱讀文章之中,一開始是閱讀攝影的這件事,這個行為,這個藝術(雖然討論與爭論不少),但是後來角度慢慢延伸到不同攝影集,不同照片的批評者和閱讀者,獨樹一格的關注與時常懷抱的溫柔,悉心檢視照片裡的故事,向每一張照片提問。藝術閱讀也是這樣,這些人,何時,何地,為何,那個角度,什麼方式而有了這張照片。等於讀者必須要重構攝影當時及背後的故事。但是如果攝影集很大,版權或印刷問題,沒有了照片,那問題出現,有點類似隔靴搔癢,無從著力與建構故事。 在這麼多篇文章中,慢慢翻閱,不管是人像照片,大自然,參加宴會的穿著,政治宣傳照片,系列照片,深睡中的男人標題卻是朝聖者,討論攝影師的取角觀點,行乞男,藝術作品美等,翻閱翻閱到最後,有一篇阿赫蘭•希伯里:《追蹤兵》,引起特別關注,這個是在以色列這個國家出生的阿拉伯人,貝因都人。以色列國籍,但是不被猶太人所信任,但是必須服兵役,所以他們任務都是斥侯兵,往往去檢查阿拉伯人家都是他們先,這張照片道盡他們的無奈,報國至少才能讓家人好過,但是必須面對另ㄧ群人的責難。攝影作品也是具體而微的說明社會現象,但是照片以外的故事,必須要很多資訊補足,這也是作品雖好,但很多時候可能誤解讀的一個狀況。在越戰中,有一個很有名的照片,一個將軍在大街上槍殺一個看起來無辜的人民。實際上卻是那個人民是北越間諜,間接殺害將軍的很多同袍,將軍大怒,開槍槍決此間諜,反而成了反戰宣傳最後的照片,照片解讀不可不慎。 可以這麼說,相片的意義,或是相片的異義。最後引述: 我們只看見自己凝視的東西。『凝視』(gaze)是一種選擇的行為......我們關注的從來不只是事物本身,我們凝視的永遠是事物和我們之間的關係。──伯格《觀看的方式》 閱讀的觀點,同一時間閱讀,書的演化史 :六千年來人類知識載體大變遷,平鋪直述,主要是印刷與知識推廣,因為書籍的照片多,上手更快,引起注意的是西方由1750年起識字率皆超過一半,引發興趣,找了一下資料,同一時間的清朝,約為30-20之間,當然通常女性比例更低,閱讀像解連環鎖一般,一個接一個的連接,無窮無盡的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