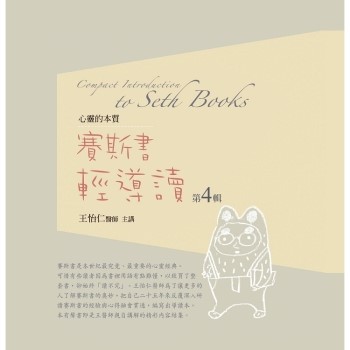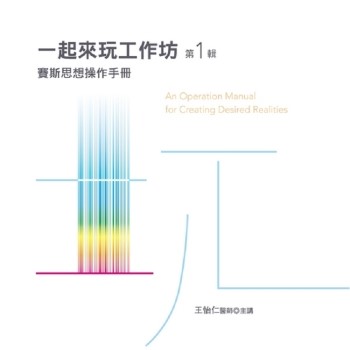推薦序
給一切明明是對的錯———閱讀吉田修一《最後的兒子》
孫梓評
香港填詞人周耀輝一首獻給尚.考克多(Jean Cocteau, 1889~1963)的歌〈給你〉裡寫到,「給世上搖搖欲墜的我/給一切明明是對的錯」,彷彿恰好可以用來總結吉田修一這冊處女作《最後的兒子》。三個中、短篇故事,發表於一九九七~一九九九年間,同名作品〈最後的兒子〉獲一九九七年日本文學界新人賞、芥川賞候補。有趣的是,時間經過,吉田修一將與松浦壽輝等人共同擔任二○○八年「文學界新人賞」評審。此時回頭閱讀他初顯身手的作品,頗生一絲後見之明的趣味。
被譽為與山田詠美一樣,同時跨足嚴肅文學與大眾文學的吉田修一,其作品確也露出這兩種表情:除了慣性在小說裡試探原鄉長崎(《長崎亂樂》、《7月24日大道》),也常疏離地書寫異鄉東京(《同棲生活》、《公園生活》、《東京灣景》、《地標》),吉田修一筆下的鏡頭冷暖兼具,既能夠近身拍出情感的搏動,亦能走遠,到一等距之處,冷眼觀察世間百態。這幾年他的中譯本有系統地問世,都不是什麼厚重的巨著,但在書店的平台上,相較於其他被熱力炒作的翻譯書,他的作品看似輕薄,卻不失深廣,側身於大量被翻譯、引介到台灣,而終究面目模糊、口氣相仿的日本作家之中,吉田修一也始終有別於他人。
幾乎沒有一次,是翻開吉田修一而感到失望。
除了以線條清楚的故事,緊緊抓住閱讀者的目光,我心裡對於美好故事的嚮往,也總能在吉田修一的小說裡獲得滿足:泡沫經濟後,城市裡徬徨無狀的頹廢世代;感情繫絆的兩造,如何使出本質的親密與野蠻;舊鄉記憶追索,家族枝狀圖與歷史勾纏的微妙對話……吉田修一不疾不徐,置身事外又踏火其中地,讓那些線索集中,在一次次有效的結構中,輕快地搬運著閱讀者。
回想起來,吉田修一的姿態總是相當優雅,他不涉入,不評判。「搖搖欲墜的我」所將遇見與遭遇的那些「明明是對的錯」,對他來說,只是(寄居於虛構的)事實的陳述。他的價值並不在於說服,而在於展現;不在於耽視,而在於如何能像泳者水中換氣那樣,使整體呼息均勻———宛如一種述事的工藝。
屬於吉田修一的誠實,並淡然直揭愛情的暴力層面的故事,曾經在他蒐錄於《熱帶魚》一書的短篇小說〈綠色豌豆〉中,讀見且驚豔。那一顆顆扔擲在戀人身上的豌豆,就像被具體化的微小情緒攻擊,製造出斷斷續續、惡意搔擾的痛。而類似的基調,也發揮在〈最後的兒子〉裡。
何謂「最後的兒子」?朱天文在《荒人手記》裡劃分為畸零族群、無法繁殖下一代的;白先勇稱為「孽子」,大膽逃出族譜所授予的宿命,而自成星圖的 ……然而吉田修一更「叛逆」或「靈活」,他的主角雖不像三島由紀夫《禁色》的悠一那樣人間亂樂,卻多少也有幾分《假面的告白》的況味。我們曾經隱隱約約在《同棲生活》或《長崎亂樂坂》裡讀見的性/別,在〈最後的兒子〉裡,可說是直擊了核心。一名從長崎來到東京的男人,歷經對青春同儕的詩意想望,與女性談過一段無疾而終的愛情後,為了可以獲得「什麼都不做的時間」,與第三性公關展開同居生活。稠熱夜晚,公園裡有男同志被惡意獵殺;新宿二丁目的酒吧,夜夜笙歌;這個刷牙總像「第一次要接吻的男孩」的男人,如何迎向有「戀病人癖」的第三性公關的包養?作者敘述時故做輕快的腔調,讓故事讀來生猛活潑,溫柔藏刀:誠實,總是深深地劃開了一些什麼。
第二個短篇〈碎片〉,也與兒子有關。鰥夫帶著兩個兒子,經營酒行工作。由於同樣是描寫藍領階級,不免聯想起〈熱帶魚〉裡的木工兄弟。那樣細微地臨摹著身體細部感受,彷彿在海岸邊亦可嗅聞到空氣中飄散的荷爾蒙氣味,九州有異於東京的日常作息,無出口的愛意與聊賴,都有效地收編在時空交錯的畫面之中,節制,有序,碎片的拼湊,為的是「得其情」。
讀至最末篇〈Water〉,一下子被青春的鯨尾給擊中。大學畢業後曾經在游泳教室打工(擔任教練?)的吉田修一,想必細細觀察過泳池旁的水紋光影,年輕孩子們嬉笑與認真的表情,或則他自己的成長經驗中,也有某深刻難忘的年輪吧。閱讀〈Water〉,處理青春期內心戲、一意往既定目標前傾的傻勁,都那麼使人心折。沒有例外地,當然也觸及對性與性別的好奇,一點點「男孩限定」的惡作劇……當體內漲潮的夏天淹沒了視野,一切卻又出奇地平靜,彷彿只有蟬聲是欲望的代言人。
閱讀〈最後的兒子〉時,讓我想起了橋口亮輔的電影《Hush》;好讀又動人的〈Water〉,則使我想起犬童一心拍《Jose與虎與魚們》的寂寞光影,燦亮天空下,殘忍和體諒該如何藏放?邊讀,邊感覺,這具有強烈畫面感覺的故事不拍成電影太可惜了。在網路上略微蒐尋後,驚喜地發現有著更好的結果———二○○六年,吉田修一已經將這個故事自編自導成為電影(www.wisepolicy.com/ water),二○○七年於日本上映。
〈Water〉裡的主角圭一郎,原想藉由尚.考克多的《白色之書》(Le Livre Blanc)暗示友伴,卻是徒勞;就像〈最後的兒子〉裡鍾愛維斯康提電影的右近,他們都是多麼地寂寞呢。「給世上搖搖欲墜的我/給一切明明是對的錯」……所幸,寂寞的時候,還可以躲進吉田修一筆下的熱帶夜,在搖搖欲墜的存在感中,細細咀嚼那一切是對的錯。
(本文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