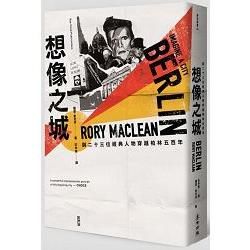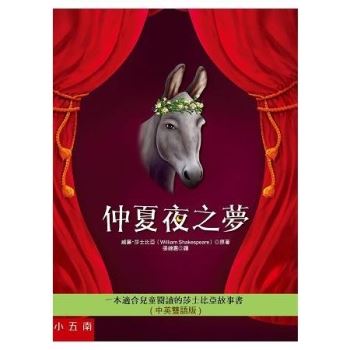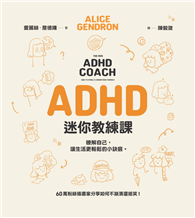自腓特烈大帝夏宮窗畔 俯看約翰.甘迺迪匆匆行過
從瑪琳.黛德麗裙飄袖搖間 傳來大衛.鮑伊激昂樂聲
二十三位古今人物行吟遊唱 吹響五世紀柏林頌歌
巴黎、倫敦、羅馬也豔羨的帝都風華軼史
本書透過五百年來發生在柏林的二十三個生動鮮明人物故事,呈現該城繽紛多元之歷史。我們將看到:一位欲躋身上流社會的青樓女子,如何將自己塑造成嬌貴仕女;德國老牌女星瑪琳.黛德麗如何誇示自己的性感;納粹頭子希特勒如何幻想將首都柏林打造成超級城市「日爾曼尼亞」;傳奇歌手大衛.鮑伊如何在其中優游歌唱。從政治家、國君,到攝影師、建築師、舞蹈家,乃至歌手、演員、劇作家,代代行過的身影,刻鏤柏林偉岸風跡。這座傳奇之都曾在二戰期間遭盟軍炸毀,戰後又被柏林圍牆一分為二,隨著東、西德統一才又合而為一,重獲新生。柏林人所發出的生命感觸,至今依然在此回響。
世界上沒有一座城市如同柏林這般,曾如此強盛地崛起,卻又落入如此悲慘境地;也少有城市如柏林這般,曾如此深受個人創造力與想像力的感染形塑。柏林是全世界最富變化與創意的都會之一,她塑造了許多人,人們也回頭塑造了她。二十三位人物在古今縱橫、軼聞頻生的娓娓敘事中,共繪出一幅筆法多變、瀟灑淋漓的德國名都肖像畫,鼓勵每一位平凡者,勇敢地在這座城市想像。
作者簡介:
羅里‧麥克林Rory MacLean
一九五四年出生於加拿大溫哥華,成長於多倫多,畢業於該市萊爾森大學(Ryerson University)。而後長期定居英國,曾數度落腳德國柏林,通曉德語。職業生涯最初十年,曾先後為電影導演大衛.海明斯與肯.羅素撰寫影片腳本,還曾在柏林與英國搖滾歌手大衛.鮑伊、在巴黎與德國老牌女星瑪琳.黛德麗共同拍攝電影。之後他由電影編劇轉為報導文學作家,一九九二年發表第一本著作《史達林的鼻子》(Stalin’s Nose),甫出版便榮登英國暢銷書排行榜前十名。其他著作曾分別榮獲加拿大總督文學獎、英國藝術局文學獎;入圍國際都柏林文學獎;兩度入圍庫克旅行文學獎,並獲邱吉爾藝術考察基金贊助。亦曾為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撰錄廣播節目。現為英國皇家文學學會院士。
譯者簡介:
莊仲黎
一九六九年生,女,德國漢堡大學民族學碩士、博士候選人。目前從事英、德語譯介工作,譯有《怎麼有人研究這個?》、《看懂了!超簡單有趣的現代藝術指南》、《讀書別靠意志力:風靡德國的邏輯K書法》、《心理韌性訓練》、《守護者的凝視:八個不放棄生命的動人故事》、《達爾文密碼》、《香料之王:胡椒的世界史與美味料理》、《七天學會用哲學思考》、《帶著兩隻大象翻越阿爾卑斯山》、《德意志領導:足球場的哲學家-勒夫,德國足球金盃路》、《柏林:歐洲灰姑娘的重生與蛻變》等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文化界名家盛讚推薦
何曼莊(小說家.換日線首席專欄作家)
胡晴舫(作家)
莊祖欣(作家)
鴻鴻(詩人.劇場導演)
(依姓名筆畫排序)
這部充滿企圖心的歷史著作藉由想像與藝術手法,全面再現柏林這座偉大德國首都從古至今的歷史面貌。本書令人佩服不已的原因,並非因為作者能以僅僅數百個字詞總結回顧某段歷史,而是能在一場混亂糾結的夢境裡,以縈繞人心的書寫方式描述將近六百年的柏林史。
~ 英國威爾斯女作家揚.莫莉絲(Jan Morris),《週日電訊報》
本書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人物紀實、一幅圖案豐富多樣的織錦,以細膩深入的手法,將五百多年來曾出現在柏林的二十三位人物 - 無論是赫赫有名或沒沒無聞 - 羅織在一起,共同映現柏林歷史。一本引人入勝的著作。
~《觀察家報》
羅里.麥克林透過本書傳達關於柏林的想像、深思、崇敬、困惑與批評,顯露出他對自己所熱愛的這座城市一些成熟思維。這本著作最深刻的特點在於它行文之優美。文章中那些絕妙的聲韻總令人忍不住反覆閱讀玩味,堪稱是完美的散文體。
~ 英國聖安德魯大學歷史學教授杰拉德.德.葛魯特(Gerard De Groot),《華盛頓郵報》
名人推薦:文化界名家盛讚推薦
何曼莊(小說家.換日線首席專欄作家)
胡晴舫(作家)
莊祖欣(作家)
鴻鴻(詩人.劇場導演)
(依姓名筆畫排序)
這部充滿企圖心的歷史著作藉由想像與藝術手法,全面再現柏林這座偉大德國首都從古至今的歷史面貌。本書令人佩服不已的原因,並非因為作者能以僅僅數百個字詞總結回顧某段歷史,而是能在一場混亂糾結的夢境裡,以縈繞人心的書寫方式描述將近六百年的柏林史。
~ 英國威爾斯女作家揚.莫莉絲(Jan Morris),《週日電訊報》
本書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人物紀實、一幅圖案豐富多樣的織錦,以...
作者序
前言
黎明的曙光在霧靄中投射出一個已消失的柏林皇宮的暗影。一位普魯士國王吹奏的長笛樂音飄盪在空氣裡。一些樹苗已在被遺忘的柏林鐵路支線上發芽生根,蘇聯共產黨領導人列寧在潛回俄國發動革命之前,曾在那兒歇腳休息。兀立於紀念柱上方的勝利女神像所閃耀的金色光芒穿透了周邊的動物公園(Tierpark)茂密的樹木與枝葉。柏林北邊的薩克森豪森集中營(KZ Sachsenhausen)的骨灰從焚化爐飄往南方,而在市中心的歐洲受難猶太人紀念碑園區(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的上空被捲入一陣帶著灰塵的旋風裡。孩童們的笑聲在建造於柏林圍牆遺跡上的那些缺少植被與綠意的帶狀公園裡迴響著。一群遊客在柏林城中區(Mitte)的一處單調無趣的停車場駐足發呆,他們站立的地面下正是希特勒的秘密地下碉堡的所在。
為何我們會特別受到某些城市的吸引?也許是因為,我們在孩提時期曾讀過某個故事,或在十幾歲時曾偶然地造訪,或純粹因為那個地方的居民、塔樓與歷史具體的表現出我們所認為的人生意義的觀點而深受觸動。在世人的眼裡,法國的巴黎是關於浪漫的愛情,南法鄰近西班牙的天主教朝聖地盧爾德(Lourdes)已與宗教奉獻畫上等號,美國的紐約意味著豐沛的能量,英國的倫敦總是講究流行時尚。
至於德國的柏林,則是「變動」的代名詞。它的認同並非植基於穩定,而是變化。沒有一座城市像柏林這般,處於如此強大、卻又如此消頹的輪迴裡。沒有一座城市像柏林這般,如此令人厭惡、如此令人恐懼,卻又如此令人迷戀。沒有一座城市像柏林這般,在橫跨五個世紀的雙邊衝突裡,曾被如此地扭曲與撕裂:從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所引發的新、舊教陣營的宗教戰爭到二十世紀後葉的美蘇冷戰,柏林始終處於西方兩股對立的意識形態的交鋒地帶。
柏林這座城市永遠處於改變之中,從未定型,所以能擁有更活潑的想像力。未曾造訪柏林的人們在親睹柏林之前,早已同時感受到它那些痛苦的欠缺以及亮麗的擁有:生命的意義已經存在、夢境已經實現,連邪惡也曾被密集地執行。它們曾響徹雲霄,撼動人類社會,而令人膽顫心驚。這座城市曾蒙受如此多的喪失,卻也曾經歷如此多的創造,因為,人們內心的想法能快速地填補真空,讓無形的東西具體化,並以想像連結真實。既然在柏林沒有什麼是固定不變的,在現在與過去之間,在被觀察的實體城市與上萬份書籍、電影、畫作以及充滿幻想力的建築烏托邦所虛構的地域之間,便出現了熱烈的對話。昨日的種種仍然在今天迴響著,那些活躍於柏林的夢想家與獨裁者所提出的構想似乎跟它的磚頭與灰泥一樣地牢固。這座深具魅力、且充滿變動的城市在精神層面總是顯得生機盎然。
很久很久以前,我揹著背包從加拿大來到歐洲四處旅行時,還是個未滿二十歲的青年。在那個開心愉快、無拘無束的夏季,我曾吃力地爬上巴黎的艾菲爾鐵塔,曾以輕快的步伐走下羅馬的「西班牙階梯」,並在希臘愛琴海的一處沙灘的星空下感受地球的運轉。然後,我在這趟旅行的最後一週來到柏林,並看到了柏林圍牆。這道可憎的水泥障礙物打從心底震撼了我,因為,在這個歐洲大陸的心臟地區竟然遍布著警衛瞭望塔、帶刺鐵絲網以及一群東德邊防士兵。他們已受上級指示,一律射殺想逃往西柏林、想在不同政權之下生活的東德同胞。
我那時當然知道二戰後的歷史,我也了解冷戰時期發生了什麼事,但我卻無法想像眼前的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那些分裂德國與歐洲的個人-戰爭的規劃者、蘇聯人民委員(相當於行政部會的部長)、東德情報組織史塔西(Stasi)的幹員-並不是什麼妖魔鬼怪,他們都是有血有肉的男人和女人,因此,當時的我很想了解他們的動機,了解他們為何會有這樣的作為。不過,同時我又對他們的罪行感到厭惡,而覺得應該去感受他們的受害者所承受的痛苦。
在柏林停留的那個星期,我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柏林圍牆的吸引。我經常爬上圍牆邊的一座木造瞭望台,而且一待就好幾個小時。我站在那個高處俯瞰荒涼的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Platz),並沉默地望著柏林圍牆雙牆之間那個布有地雷的死亡地帶。年少的我對於人們竟會因為理念的衝突而直接在市中心設置一道水泥牆、把一座城市硬生生地隔成兩半,著實感到訝異不已。
在那場夏季之旅的最後一天,我穿越了邊界而進入東柏林。我在查理檢查哨旁邊跨過一道白線後,便從柏林圍牆的一道出入口進入雙牆結構的圍牆內。入口的大門升起,接著便在我後頭關上,所有準備進入東柏林的車輛與行人全被趕入一處雙重急轉彎的水泥迴旋通道。就在那一刻,一架蘇聯米格戰鬥機飛過已沒有人跡的布蘭登堡門的上空,超音速所造成的空氣振動不僅讓窗戶震盪,也撼搖了我對於人性本善的信念。
我把護照交給一位全副武裝、沉默寡言的東德軍官。繳付簽證費用之後,便在一位穿著灰綠色制服的東德人民軍中尉的注視下,站在細雨中等候。他揹著一把子彈已上膛的步槍,在他戍守的那座矮小的警戒崗哨的另一側就是東柏林,周邊建築物的門已全被磚塊砌封住,附近地鐵站的入口也已封閉。腓特烈大街-曾經是柏林市中心最繁華的商業街-出現一條陰暗而狹窄的、表面塗上水泥的過境通道。柏林居民的魂魄與記憶似乎已在這條過道裡被吸走了!
在這場歐洲之旅的最後一天-同時也是我在東柏林的第一天-我離開柏林圍牆附近那個監控嚴密的邊界地帶,直接走向颳著強風的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東柏林的市中心。我隨身帶著一本阿弗烈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於一九二〇年代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在二戰爆發以及柏林圍牆興建之前,這位曾為柏林留下最重要的文學作品的作家早已蹓躂過這座廣場上那些舖石地面的天井與布料行,並以手中那支妙筆描繪那裡的鐘錶匠、戴著便帽、游手好閒的年輕人以及「非常廉價的女人」。廣場上的生意人以喉音大聲地說著猶太人的依地語 (Jiddisch)。商店的魚販們將肥美的鯡魚擺在冰塊上販賣,並把各種魚類的價格以粉筆寫在窄擠的店面裡的那扇通往地窖的門片上。穆恩茲街(Münzstraße)的那些電影院的外頭有幾位街頭藝人搖著他們推來的手搖風琴,樂聲此起彼落,非常熱鬧。一家勞工書籍專賣店的上方架設著一幅看板,裡面畫著一隻手擺在一本打開的書上,下面還有一把鐮刀與幾穗玉米的圖案以及一行文字:「如果你想增加生產量,就需要知道更多。」。
那是我第一次造訪亞歷山大廣場,時間是一九七〇年代。當我看到盤據在廣場周邊的那些灰暗的鋼筋水泥建築時,簡直無法和五十年前猶太裔德語小說家德布林筆下所描繪的那個「柏林令人震撼的心臟地帶」聯想在一起。這個老柏林的中心點的舊建築後來因為不敵納粹首席建築師亞伯特.許倍爾(Albert Speer)在首都展開的的日耳曼尼亞的大建設、英國蘭卡斯特轟炸機的空襲以及東德都市計畫專家的規畫,而逐一被拆除或炸毀殆盡。我那時站在亞歷山大廣場上,四周既聽不到人聲,也聽不到鳥鳴。位於廣場中央、基座貼著瓷磚的「民族友誼噴泉」(Brunnen der Völkerfreundschaft;Fountain of Friendship among People)看起來實在「很枯燥」(bone dry)。旁邊的東德國營連鎖百貨公司「中央百貨」 (Centrum Warenhaus)的建築表面布滿凹洞、設計毫無特色,裡面除了蘇聯錄音公司Melodiya出品的黑膠唱片之外,似乎沒有販售什麼值得購買的商品。燃燒褐媒的黑煙不斷朝空中噴出,外觀覆滿黑垢的車站發出陣陣濃厚的塵埃味。一列塗裝棕紅色和灰褐色的雙色電車嘎嘎作響地駛過拱橋。那時我由於緊緊地握住德布林的那本小說,連關節都因為使力過度而發白。亞歷山大廣場看起來就像被廢棄一般,只剩下一對推著嬰兒車的年輕男女在那裡走動著。他們在廣場上那座已經生鏽、造型非常類似原子構造的「世界鐘」(Weltzeituhr;World Time Clock)-裡面運行的那幾顆行星就像瀕臨毀滅的電子繞著一個原子核(恆星太陽)旋轉-下面停了下來,然後幫車內的嬰兒調整毛毯。我朝嬰兒車裡瞥了一眼,卻驚然發現,裡面竟躺著一個塑膠娃娃,而不是人類的嬰孩。
在廣場西側邊緣那座電車候車亭的另一頭,有一棟符合黃金比例的建築吸引了我的目光。它就是柏林的聖母教堂(St. Marienkirche),也是柏林第二古老的教堂,於十三世紀興建在該處的沙丘上,確切的建造年份並沒有文獻紀錄。這座教堂的斜向方位(未依循正南北方向)正好反映出老柏林的市街規劃。然而,當我朝它飛奔過去時,卻看到它的紅磚牆上仍遍布戰火留下的彈孔。從骯髒的大玻璃窗透入的微弱光線將聖靈往下拉進教堂潛藏的陰暗處,而不是向上帶往天國。一位孤獨的婦人坐在這座教堂的門口顫抖著,她的雙腳只穿著一雙已磨損的長襪,身旁的那位補鞋匠正磨著他的小刀,準備為她脫下的靴子打造新的鞋跟。
死神站在後面的走廊裡,祂向前抓住了紅衣樞機主教與教宗、國王與騎士、行政首長與宮廷弄臣的手,引領他們走完生命最後的旅程。我隨著他們在教堂裡移動,沿著那幅畫風蒼白暗淡、總長二十公尺的哥德式壁畫走著。這幅<死亡之舞>(Totentanz)繪於一四六九前後,簡單的作畫技巧頗似兒童繪畫,它躲過了火災與盟軍的空襲,而且還因為在中世紀晚期被塗上石灰水而默默地在聖母教堂裡存在了將近五百年。因此-舉例來說-當尼采走過這幅壁畫上的舞者的面前時,雖首次感受到柏林具有「走向死亡的潛在意志」,但他卻看不到隱藏在石灰之下描繪舞者的那些筆觸笨拙的線條。歌德、伏爾泰及格林兄弟也曾參訪聖母教堂,後來契訶夫、卡夫卡、德布林、弗拉迪米.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與鈞特.葛拉斯(Günter Grass)-不論是柏林的居民或訪客-也跟隨這些文學前輩的腳蹤走進這座教堂,然而,他們都只能用直覺感受<死亡之舞>的存在,並無法用眼目觀看。同樣地,活躍於威瑪共和時期的柏林裸體舞蹈家阿妮塔.貝柏(Anita Berber)-德國畫家奧托.迪克斯(Otto Dix)畫作裡的那位嘴唇塗黑的色情舞者-也曾在這條走廊裡受到莫名的啟發而創造出她自己的裸體死亡之舞。澳洲搖滾創作歌手尼克.凱夫(Nick Cave)在造訪聖母教堂,並在這幅隱藏的壁畫前停下腳步時,突然在他的腦子裡聽到他的歌曲<死亡不是結束>(Death is Not the End)的歌詞。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在柏林逗留期間甚至曾經想像,這座城市是一個死者與活人共存的世界,活人雖然看不見死者,但死者也無法觸摸活人。
「你們大家都一起來,跟著我加入這場死亡之舞!」這幅壁畫裡的那位模樣恐怖、穿著壽衣的主舞者以低地德語的韻文呼喚著。當他指示大家一起跳舞時,還回頭一瞥,我發現他正在注視我,正如他也曾注視經過這條走廊的每一個人,而且還把我們全部拉進這支舞蹈中。
頃刻間,我想像自己正握住這些難逃死亡命運的舞者的手。當太陽從浮雲的後方出現時,我正和他們一起步出聖母教堂。此時的亞歷山大廣場已不再荒涼,它忽然變得人擠人,到處都是黑死病的患者和哈布斯堡王朝軍隊的妓女。一群中世紀的說書人與喋喋不休的賣魚婦已重新回到這個生活場域。意圖報復納粹德國的蘇聯紅軍辱罵著那些必須彎腰清除瓦礫、並協助戰後重建的「廢墟中的女人」(Trümmerfrau)。在人羣中,我發現一些嚼著口香糖的美國大兵和已被燒得全身烏黑的英國轟炸機的投彈手緊抓住著火的降落傘,而且我還看見拿破崙跨騎在他的白色戰馬上,納粹親衛隊裝甲擲彈兵在被殺害的猶太兒童的四周昂首闊步地行走,在西柏林發表「我是柏林人」這場演講的甘迺迪總統命令他的車隊停在路邊一個烘培攤前面,一口氣購買了十幾個「柏林人甜甜圈」(Berliner)-一種灑上糖粉、內含李子餡的非圈狀的圓形甜甜圈。
關於柏林的想像還不只這些,因為,這座城市的一些標誌性的奇想其實或多或少都與死亡有關:英國搖滾歌手大衛.鮑伊歌曲裡的英雄們在柏林圍牆邊親吻著;德國大導演文.溫德斯電影裡的天使在持著火炬的納粹遊行隊伍的上方飛翔;英國小說家克里斯多福.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小說女主人翁莎莉.鮑爾絲曾與德國女星瑪琳.黛德麗一起逛街血拼;還有諜報小說大師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作品中的主角喬治.斯麥雷(George Smilely)曾目擊一列塞滿猶太人的火車駛往奧許維茲集中營(KZ Auschwitz)。放眼望去,眼目所及之處,柏林的那些真實的與想像的傳奇已跟我一樣,全加入了這場<死亡之舞>!
燈光轉換,我的幻想與夏日假期也隨之結束。我離開東柏林市中心的聖母教堂,搭機返回加拿大家中以及我所歸屬的那個平凡的世界。然而,我內在的某個部分卻相信,即使我們已離開某個地方,卻仍舊留在那兒。所以,沒過多久,我便感受到一股力量的驅使而重回柏林。在接下來那十年裡,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柏林從事電影工作並開始撰寫我的第一本書-一份關於東歐與蘇聯鐵幕國家的著作。我試圖剝除那層遮蓋壁畫的白石灰以及銅器表面的綠銹,而看清人們日常的生活世界,並與這座飄盪著鬼魂、令人著迷而善變的城市墜入情網,之後從中抽離,後來又回到熱戀的狀態。
一九八九年,太陽又再度露臉!東德人和西德人一起在柏林圍牆上跳舞,大家手牽著手,有的人手上還搖著燃燒的仙女棒。這場戶外的派對當然不是人們與死神共舞的最後一支華爾滋,而是在歡騰地慶祝一個嶄新的開始!當時我特地在柏林圍牆東、西牆之間那片柔軟的沙地-原先埋設地雷的無人地帶-上,留下一道連結東、西柏林的腳印。數千名柏林人為了剷除這道障礙物,正在我的周圍拿著十字鎬和鐵錘賣力地敲敲打打。一羣東德人開著東德的小型國民車「特拉比」(Trabi)-板金較薄,有時會拋錨,而必須下來推車-在那些忙著拆除圍牆厚重的水泥塊的士兵身邊繞行轉圈。曾被蘇聯騷擾、恐嚇並剝奪公民權的俄國大提琴家羅斯托波維奇(Mstislav Rostropovich)還特地前來共襄盛舉。他在查理檢查哨即席演奏一首巴赫無伴奏大提琴組曲時,旁邊還有一個老人跪地痛哭。馬路保養人員重新讓已阻斷將近三十年的街道恢復暢通。柏林圍牆周邊那些地鐵「鬼站」也因為開始營運而出現來來往往的人潮。長達一百五十五公里長的柏林圍牆在一年之內便已被拆除殆盡,狹帶狀的原地只留下一道不起眼的舖石線以及部分路段會彎扭的腳踏車道。在這座城市裡,我本身的行動不僅成為回憶,還成為柏林歷史的一部分,這並非因為我曾對它有重要的貢獻,而是許多其他人所立下的功績深深地進入我的生命中。
在認識柏林四十年之後,此刻居住柏林的我試圖描繪這座城市的形貌,試圖區分它的過去與現在、順從與反叛、有形與無形。我站在亞歷山大廣場上,忙碌地看著那些身上刺青的遊客以及沐浴在陽光下、手裡拿著iPhone、抱著小寵物狗、手上帶著鮮豔的霓虹色彩的腕帶、或是在咖啡廳外頭用毛毯把自己包住的老柏林人。我轉身離開他們,卻又在廣場上來來回回地逡巡,然後繞出了廣場而走進附近的街區裡。我知道,光是在城市裡走馬看花並記下一些有趣的見聞,並無法展現柏林的真面貌。為了呈顯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柏林,以及蓬勃活潑的柏林神話的力量,人們有必要了解這些神話的創造者,諸如藝術家、思想家以及那些擁有廣被接受、因而富有高度真實性的觀點的活躍份子。柏林造就了他們,同時他們也造就了柏林,並將這個原本在歷史上平庸且樸拙的邊陲地區改造成為歐洲的首都。
我在本書裡,透過一些男性與女性的故事描繪柏林這座城市的歷史變遷:政治人物、畫家、心碎的普魯士國王、重獲新生的搖滾巨星、惡魔般的天才-不過,至少還有一個天使。此外,這些故事裡還伴隨著多不勝數的、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他們的生平根本無人知曉:德國人與外國人、本地出生的女兒與從外地收養的兒子……他們每個人都不一樣,都是獨立的個體,但全都跟現代的柏林人擁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在這座創造與邪惡的實驗室,在這個幻想與死亡的原鄉,柏林敢讓他們盡情地創造與發揮想像!
前言
黎明的曙光在霧靄中投射出一個已消失的柏林皇宮的暗影。一位普魯士國王吹奏的長笛樂音飄盪在空氣裡。一些樹苗已在被遺忘的柏林鐵路支線上發芽生根,蘇聯共產黨領導人列寧在潛回俄國發動革命之前,曾在那兒歇腳休息。兀立於紀念柱上方的勝利女神像所閃耀的金色光芒穿透了周邊的動物公園(Tierpark)茂密的樹木與枝葉。柏林北邊的薩克森豪森集中營(KZ Sachsenhausen)的骨灰從焚化爐飄往南方,而在市中心的歐洲受難猶太人紀念碑園區(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的上空被捲入一陣帶著灰塵的旋風裡。孩童們的笑聲在建...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孔拉德.馮.寇恩:聖母教堂,一四六九年
第二章 科林.阿巴尼:柏林皇宮,一六一八年
第三章 腓特烈大帝:忘憂宮,一七六二年
第四章 卡爾.辛克爾:皇宮大花園,一八一六年
第五章 莉莉.諾伊斯:老莫阿比特街,一八五八年
第六章 華爾特.拉特瑙:大道街,一八八一年
第七章 艾爾莎.喜爾緒:王儲河岸大道,一八七三年
第八章 瑪格麗特.波瑪:羅納貝格街,一九〇五年
第九章 弗立茲.哈伯:達冷區,一九一五年
第十章 凱特.柯爾維茲:威爾特廣場,一九〇三年
第十一章 克里斯多福.伊舍伍德:諾倫朵夫街,一九二七年
第十二章 貝爾托.布萊希特:造船工人大道劇院,一九二八年
第十三章 瑪琳.黛德麗:巴伯斯貝格製片廠,一九二九年
第十四章 蘭妮.萊芬斯坦:選帝侯大道,一九三五年
第十五章 亞伯特.許倍爾:菩提樹街,一九三八年
第十六章 約瑟夫.戈培爾:佛斯街,一九四五年
第十七章 迪特.威爾納:貝瑙爾大街,一九六一年
第十八章 比爾.哈維:魯鐸夫區,一九五五年
第十九章 約翰.甘迺迪:西柏林市政府,一九六三年
第二十章 大衛.鮑伊:科特納街,一九七七年
第二十一章 廖文河:軒尼菲德機場,一九八六年
第二十二章 我們去跳舞吧:柏林動物園,二〇一一年
第二十三章 伊爾絲.菲利普斯:基瑟勒街,二〇一三年
終章
後記及參考資料
謝辭
前言
第一章 孔拉德.馮.寇恩:聖母教堂,一四六九年
第二章 科林.阿巴尼:柏林皇宮,一六一八年
第三章 腓特烈大帝:忘憂宮,一七六二年
第四章 卡爾.辛克爾:皇宮大花園,一八一六年
第五章 莉莉.諾伊斯:老莫阿比特街,一八五八年
第六章 華爾特.拉特瑙:大道街,一八八一年
第七章 艾爾莎.喜爾緒:王儲河岸大道,一八七三年
第八章 瑪格麗特.波瑪:羅納貝格街,一九〇五年
第九章 弗立茲.哈伯:達冷區,一九一五年
第十章 凱特.柯爾維茲:威爾特廣場,一九〇三年
第十一章 克里斯多福.伊舍伍德:諾倫朵夫街,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