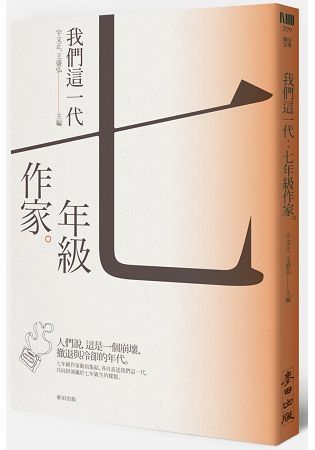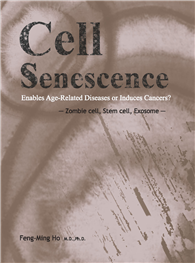主編序
意義已經飛出書頁……
先從源頭說起吧。二○一三年的青年節,聯副做過一個「新青年專輯」,邀請不同世代彼此對話。當時羅毓嘉一篇〈青年為什麼憤怒〉創下極高的點閱率及大量社群網站的分享,連新聞部的同事都跑來問我:「哇,今天副刊怎麼回事?」我也訝異。而就像在廚房裡,我看著鍋蓋的震動便知道裡面的湯要滾沸了,年輕人(大致也就是七年級世代)有話要說。
年輕人有話要說,這念頭一直放在心上,思考過,還可以在副刊做什麼樣的對話?後來決定,不要兩兩對話,也不要主題辯詰了,就做一個「我們這一代──七年級作家」大專輯吧,廣邀這個世代的作家,空出一整個月版面(二○一五年五-六月),讓他們自由發揮。有作家著眼於世代論述,也有作家從自己的成長、當下的處境(我不想用「困境」這個詞)書寫,簡直是一串鞭炮,霹靂啪啦響了一個多月。一向稿擠、始終債台高築的聯副很少做這麼大手筆的專輯,但是很過癮,回響出乎預期。之後頗有其他年齡層的作家躍躍欲試,於是我們便陸續向不同的年齡層「世代交替」,目前為止有了六年級、五年級、四年級作家的專輯,清明上河圖似地,各世代許多作家都繪下了屬於自己世代的畫卷。
當然會有人(包括參與的作家)質疑:這種以十年為一代的粗略劃分有意義嗎?要說沒意義也真的沒意義。光是「為什麼是十年?」這一句我就回答不出來了,除了習慣十進位,還有別的道理嗎?但出發點本來就不是在定義世代上打轉,原意就是想給剛經歷過太陽花運動(二○一四年三月)這件大事,猶處在亢奮狀態的七年級世代一個專屬的舞台,把內心的騷動(即便未參與、不參與者,我相信心裡可能也有波動),透過文字宣洩出來,當初的立意便是如此。
相互理解,並不是理所當然、容易的事。猶記得在我差不多、甚至更年輕的時候,我們這一代(五年級)被前輩作家批評為「幼稚園」大學生(見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人間副刊》龍應台〈幼稚園大學〉)。我當時五內翻騰,但是我沉默,所有的大學生皆沉默(如果當年有臉書……)。我的辯駁只存在於自己的腦海之中,未曾行於文字的,便是不存在。但這個深刻的記憶教會我一件事:莫以自己偏狹管窺,輕易論斷、標籤化,尤其是貶抑一群我並不理解的人,不僅是不同世代,亦包括不同種族、不同國家、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性別、不同性取向……各種不同族群的人們。
也因此,為這一本七年級作家專書作序,我並不想從中「歸納」任何我所以為的共通點,反而是期盼讀者從這些篇章裡看出歧異,那才是相互理解的開始吧。
全書分成三卷。卷一是「青春斷片:當記憶漸行漸遠」,我不禁想著,對他們來說,青春還在啊。
黃崇凱〈廣州朋友〉,寫一起長大的朋友阿義,那逸出記憶的面孔輪廓、離分岔點已經太遙遠的彼此人生。「你寫這個的價值在哪裡?」文中阿義問作者,也彷彿問著全書所有的人。
祁立峰〈天橋時間〉走過通往少年時光的橋,美好卻倉促的九○年代,騷動的青春,一回首,橋已不見!
劉思坊〈我會變成這樣都是你害的〉,回憶青春期不明原因的過敏,重新召回一度盤踞體內的惡獸,牠帶來羞辱、恐慌,牠無預警地侵略,又無原因地離開。留下陰影,也留下對無常的感知與所有溫暖的感恩。
李時雍〈方舟〉乘載一位敏感的少年,他澄澈之眼,映照雪白的心靈世界。楊隸亞的〈純真年代〉,是一個音樂豐饒的年代,開始窺見隱喻、初識憂鬱的詩的年代,交友形式仍然可稱「含蓄」的年代。忽然換下制服,穿上了便服,她自問:「我們有沒有變成更好的大人」呢?
楊富閔〈烏陰烏陰〉記敘年少的微叛逆,潛伏體內的躁動,隱隱的倔強,籠罩在悶雷未發、大雨要下不下的烏陰氣象裡。少年練習「出門」,父親練習對話,父子都在陰霾下。
林佑軒〈青春已是強弩之末〉,一一指認中學時代的男校男孩,鮮奶、白虎、黑色土狗……陽光下,八十個男孩的相處、衝撞。從最近的距離──鏡頭拉遠,當年男孩同盟,如今男人女人。幸福就要啟程,青春已是強弩之末。
楊婕〈色盲島〉,回望畫畫的自己,童年畫中的畸怪人形,預告了真實的人生。那冷酷而純真的線條,她正以文字接續,以敏銳雙眼捕捉。
卷二「社會思辨:草莓、魯蛇、太陽花」展現七年級世代的批判力量。
賴志穎〈世界是葷的〉從食安憂慮入題,一個擁有博士學位的生命科技研究員,面對這整個世界的集體詐騙,「連食物都背叛他了」,人生,還能執著什麼?湖南蟲〈活得像一句流行語〉,流行語轉瞬成為死語,世界的油門一催到底,連在資訊大爆炸世代裡誕生的七年級,都只能奮力加大守備範圍……「不公平」是這世代對時代最大的指責,最深的怨嘆。
黃信恩〈穿行,在訴訟、防禦與責任間〉寫出今日醫者深沉的無奈。訴訟的年代裡,「防禦性醫療」只是一層薄弱的牆,能否抵擋絕望、出走的醫界土石流滾滾而下?阿布〈有病〉則是另一角度──精神科的醫生絮語。探索「失序」者的心靈世界,塑成人格之謎的創傷,痛。醫師走在「同理心」這座橋梁之上,遙望這個社會;這座橋梁,也能打通失序的台灣嗎?
羅毓嘉〈七、七〉,寫給「你們七」,表面辛辣,實則哀涼,哀惋角落裡的浪人七、便利商店七、魯蛇七、虔誠七……仍舊期盼能夠擁有快樂的,正要長大的所有少年七。
翟翱的〈舊鎮消息〉,昔日從故鄉玉里小鎮眺望天空,想像翻山之外的島,想望著未來;而今在「島的中心」生活,回頭看故鄉,新建案、煙囪、標語布條、違法集會舉牌,山的兩邊沒有不同,那是比慨嘆「城鄉差距」還恐怖的慨嘆。
朱宥勳〈其實我也想原地解散〉反擊不公平的「世代論述」,抵抗「外面」的壓制,抵抗「大人」。真正的抵抗,來自實質的建構,二○一一年一套「台灣七年級文學金典」問世,做為主編之一的朱宥勳,在此不斷自問:(集結)可以喊停了嗎?是否已經完成了階段性任務?
林禹瑄〈都是自由惹的禍〉嘆息「新世代變成崩世代,太陽花變成曇花,烏托邦卻依然還是烏托邦」,然而潘朵拉的盒子已經打開,窮忙而疲憊的世代啊,試圖越活越清醒寬容,「還好,你們還有時間。」
卷三主題是「身分尋索:摹寫失焦的輪廓」。
吳妮民〈脫胎〉是全書裡少見陳述對於母性、對於「生」的迷惑、思索,誠懇寫出這一代女性於此腳步滯重的深層憂傷。
曾琮琇〈流動的課室〉,追溯今日這一代體制外的抗爭,火藥早早於少女時埋藏,此時此刻,被點燃,被喚醒。
言叔夏〈賣夢的人〉是另一個課室,那鼴鼠的地洞時光,譬如夜遊,書本、電影、教授的話語……已是遙遠混沌的夢。宛如沿途賣夢的言叔夏,捕捉終要被曝曬、魄散魂飛的夢,捉得住的,捉不住的,皆在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裡逸散了。
黃文鉅〈魔山〉攀爬一座現實的山,這一代高學歷高失業的處境,憂鬱,留下遺書的朋友梅姬沒有攀越過去,詠懷搭檔凋零的作者,可還在山中?神小風〈三十一歲無業小姐〉亦是寫職場,寫夢想,寫其中的衝突與孤獨感,自由勝利,其他再說吧!
陳栢青〈我們九○年代初萌芽的性〉,性在這裡,是身體的啟蒙,也是隱喻,個人成長的隱喻,整個島嶼、整個時代快速劇變的隱喻。快速滑過的事物,令人錯愕,令人哀愁。周紘立的〈熱日熱夜〉更具象地寫性,寫身體,寫情感和欲望。「熱日熱夜」的欲望,卻寫得冷靜,連背叛亦冷靜;你和我是「被截斷的蚯蚓」之兩端,把對你的想像,做為我失去的部分,纏綿的冷靜。
許亞歷寫〈造臉〉,「大眾臉」誘發對臉的思索。一張臉,一個人的象徵;臉與臉之間,畫出的連結線,是人際,是網絡。作者在芸芸眾生裡探究臉部辨識的密碼,面具的密碼,臉書世界裡隱性的臉面生活之密碼,一如童年時掌握畫臉的祕訣。
顏訥〈世界妙妙妙搜奇博覽會〉,速寫曾經參觀過同一場搜奇博覽會,同感於童話摧毀而忽焉早熟的朋友毛毛,她的夢想,她的經歷,她的力不從心,乃至於她的逃遁,「這難道會是我們這一代女性的宿命嗎?」也或者,她們只是共享了某個震撼少女心的記憶罷了?
陳又津〈你媽媽是外勞嗎?〉寫出「新二代」的感受,成長的處境,身分的困惑。「我們現在一起扛起新二代這面旗子……你絕對不是孤獨一人,你看,我們都好好長大了,你一定也可以。」身分、認同,在全書裡穿針引線,而這是最揪心的一篇。
我拿著麥田出版編輯給我的書稿,為了便於檢索,隨手用螢光筆一路塗上閱讀過程中特別吸引我的字眼:抄經/都更/過敏原/雪崩/男孩同盟/死語/防禦/憤怒的鱗/同理心/黑掉/賣夢/大數據/新二代……
這些詞彙在我眼裡,像是這一群年輕作家此時此刻的印記,輻射出去,隱隱略可交織成這本書的觀照面吧。但我又想著,對於這遠比我當年具備行動力的一代,當我闔上書稿時,這些螢光的詞彙早已長出了翅翼……
宇文正(作家、《聯合報》副刊組主任)
推薦序
性‧謊言‧(反)彼得潘
以十年為一代的「年級」說不大能說服我。例如,黃崇凱一九八一年出生,從精神光譜、閱讀地圖到笑哏,我們差異不是太大(拜託才差三歲!);許亞歷一九八四年出生,從社交媒介臉部辨識系統衍伸思索人之存在,想法也頗類似;朱宥勳一九八八年出生,不無解構意味地告訴讀者「七年級」是在怎樣的世代壓抑中建構出來,且頗帶威嚇地(畢竟年長世代也常威嚇年輕人)宣示,網路是未來的社會,「七年級」才是網路如魚得水的一群,那姿態恍惚讓我想起現當代文學史上接連不斷出來宣示的苦悶者們。
宣示些什麼呢?通常是對前代或同代的怒目與質疑。縱向的抗爭:血氣強一點直接呼喊打倒老賊與一切反動勢力,客氣一點的會說什麼什麼經典也影響了我們但是新的時代已經來臨云云。不管哪種說法,目標都是新陳代謝。再來,則是要在紛紜場域裡突出自我,這是橫向的抗爭,舉個早一點的例子罷:徐志摩一向被視為「抒情」,其實戰意超強,看看他在〈《新月》的態度〉(一九二八,這一年他三十一歲了)裡說了什麼--「不妨把思想(廣義的,現代刊物的內容的一個簡稱)比做一個市場,我們來看看現代我們這市場上看得見的是什麼?如同在別的市場上,這思想的市場也是擺滿了攤子,開滿了店鋪,掛滿了招牌,扯滿了旗號,貼滿了廣告,這一眼看去辨認得清的至少有十來種行業」--他列舉了十二派,然後一次打倒,告訴讀者,那些都是「妨害健康」與「折辱尊嚴」的黑心商品,從而確立自己(的這一派)的位置(買這個才是對的)。
二○一一年出版了分文類編纂的「七年級金典」系列,五年後看來,提供的名單並不非常精確,有些作者顯然後繼乏力,有些後發者則來不及被辨認。這種「代表名單」本來就跟波赫士的沙之書一樣,總在流變之中,容易誤判與遺漏。有人說,戲棚子底下站久了就是你的,不見得是定理,沒天分與修為,站久了也不會成仙,然而,只站五分鐘,即使那五分鐘再耀眼,也一樣不成事。這一次,《我們這一代》全書收羅二十六位「七年級」作家,相對完整,卻非定論;指定文體為散文(散文親人,不代表人人會寫),指定題材與自身世代定位有關,原先是副刊企畫,種種條件考量可能造成限制。這份名單,我認為主要遺憾有二:第一,少了湯舒雯,第二,詩人所占比例太低。
「七年級」創作者裡,不少人已是獨當一面的作家或專業人士,或已經在職場裡打滾了幾年,或深刻感受知識的空轉與背負,因此,毫不意外會在書裡讀到一種微近中年心境:和昔日友人相聚時的雲泥或隔膜感,專業崗位上的社會與道德思索,文學與乾燥日常的拉鋸,是否要將自己擺進社會期許位置的掙扎,女性無論有何才華有何專精到底還是被問:「那妳這樣誰要娶妳?」如黃崇凱〈廣州朋友〉、賴志穎〈世界是葷的〉、吳妮民〈脫胎〉、黃文鉅〈魔山〉等,均使我動容。然後,羅毓嘉〈七、七〉可視為一則七年級小史,踢踢踏踏,昂揚著下巴講浪人七魯蛇七頂尖七解放七的歸途,就在此時此地。
再者,性的自省,也成為打開自我的鑰匙。我愛林佑軒〈青春已是強弩之末〉,不無自溺,可是自溺裡有清冷,「男校的男同志永遠應嬰兒,永遠男孩。男校的男同志:彼得潘,守著長不大之國--有些人變成了比莉」,稱自己彼得潘,那這位彼得潘顯然已經生出時間意識,純情大觀園正如煙消逝,變成記憶的幻燈。還有陳栢青,戴著彼得潘面具的老靈魂,懷念從前的心跳,「很髒,髒得很乾淨」,〈我們九○年代初萌芽的性〉詫異於下一代男孩們變成了無菌好學生,冷淡新人種:「下一代把衛生當禮貌,不只帶套,無菌到像有病,且身體是身體,精神是精神,分得清楚,才脫得大方。才沒經歷,先有經驗。」
全書很有意味地終止在陳又津〈你媽媽是外勞嗎?〉,追溯「新移民」這樣合宜正確名詞出現之前,母親是來自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孩子們,如何向人解釋自己,且通常並非說明「是」什麼,而是「不是」什麼,不是確立邊界,是摘掉標籤。然而,就在這樣有些顛躓的成長中,變成了一個和大家一樣,普通得不得了的台灣人。「新」台灣之子的異質,是情願保留以標誌自我複雜歷史、以張力對應偏見,還是情願從外顯到內蘊,終至看不出痕跡?
二十六位作者裡,四位學者,至少五位博士班在讀,三位線上醫師,數位媒體工作者與自由寫作者……台灣迎來了普遍學歷最高的一代文學作家,然而,面對真實人生,崩壞社會,也是極辛苦的一代。應和夏宇多年前的詩句,「有一天醒來突然問自己╱這就是未來嗎╱這就是從前╱所耿耿於懷的未來嗎」,神小風〈三十一歲無業小姐〉替所有人惶然:「現在就是未來嗎?不是正身處在那個想像中,耿耿於懷的未來裡?」拚命推向岸上、被教育著以足換鰭才能腳踏實地的漫長青春結束後,會不會發現,整個世界其實是個「極清澈的謊」呢?
楊佳嫻(作家、清大中文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