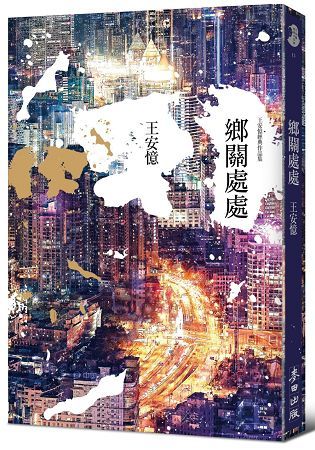圖書名稱:鄉關處處
上海的人就是海裡針,手一鬆就沒有了。
世界風水在轉,老上海人成邊緣人,
世事轉瞬翻新,現在有一種人,叫做新上海人……
《鄉關處處》收入王安憶最新三部中篇小說,三個故事分別發生在上海、紐約和香港,講述了生活在這三個城市的移民故事。
〈鄉關處處〉講述上海花花世界的急速變化,讓人措手不及去面對。這城市容納了老上海人、新上海人、討生活的異地人、台灣人等。藉由月娥的移工生活軌跡,王安憶絲絲入扣地寫下上海人的新頁,引領讀者識見上海新面貌。
〈向西,向西,向南〉,描寫兩個萍水相逢的中國女子在西方世界的生活處境。王安憶筆下看似不慍不火的紀實書寫兩個女人的情感故事,然而,小說更深刻觸及中國在經濟翻轉後,二十一世紀華人浮華的生活,以及世代與世代間隔閡的哀愁。
〈紅豆生南國〉寫的是一個內地出生的男孩在香港落地生根的故事,他在生恩與養恩,離鄉與還鄉,事業沉浮、婚姻成敗中跌宕起伏。講述了從青春至老年,男子「相思」的情事百態。
王安憶擅長對個體生命及日常生活,以其針腳綿密的書寫方式,從各個角落的煙火氣裡挖掘打撈出世態人情。《鄉關處處》深刻勾勒出人性最狂烈的風暴,以及命運裡最荒涼的景色;故事於平淡中滲出一抹參透人情事故的遼闊世界。
作者簡介
王安憶
王安憶,1954年生於南京,55年隨母親遷至上海,文革時期曾至安徽插隊落戶。曾任演奏員、編輯,現專事寫作。作品曾多次獲得多項優秀小說獎。
《長恨歌》榮獲九○代最有影響力的中國作品、1998第四屆上海文學藝術獎、1999年亞洲週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100強、2000年第五屆茅盾文學獎、2001年第六屆星洲日報「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富萍》榮獲2003年第六屆「上海長中篇小說優秀作品大獎」長篇小說二等獎、《天香》獲2012年第四屆紅樓夢文學獎。
著有《紀實與虛構》、《長恨歌》、《憂傷的年代》、《處女蛋》、《隱居的時代》、《獨語》、《妹頭》、《富萍》、《香港情與愛》、《剃度》、《我讀我看》、《現代生活》、《逐鹿中街》、《兒女英雄傳》、《叔叔的故事》、《遍地梟雄》、《上種紅菱下種藕》、《小說家的讀書密碼》、《啟蒙時代》、《月色撩人》、《茜紗窗下》、《天香》、《眾聲喧嘩》、《匿名》等。
作品被翻譯成英、德、荷、法、捷、日、韓、希伯來文等多種文字,是一位在海內外享有廣泛聲譽的中國作家。
相關著作:《匿名》《天香》《眾聲喧嘩》《茜紗窗下》《月色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