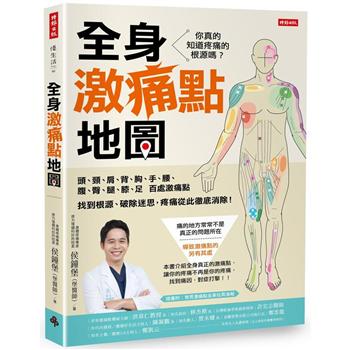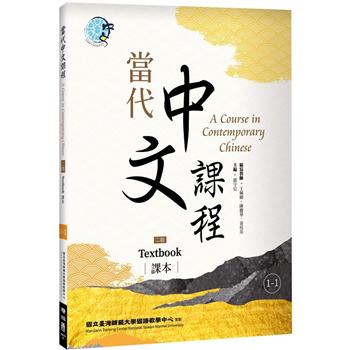我該從哪裡開始。故事可以從任何一個點開始。「我」,這個敘述者,也可以是任何人。在古典的小說世界,「我」是作者創造出來的角色;網路的虛擬宇宙裡,「我」是作者啟動的一個假帳號。你不認識「我」,然而,你將認識「我」,因為「我」將成為這個故事的敘述者。隱身於假帳號的作者設定了「我」是這本小說的作者,而不是她。「我」才是登錄帳號、貼了頭像、開地球文的那個人。你將認識的作者,是「我」。
作者的手指在鍵盤敲下第一個句子,你的手指滑開閱讀器的面板(就像你曾經翻開紙本的書頁),「我」開口說第一句話,嶄新的頁面亮了起來,好似一條腹部銀白的飛魚,突然躍出浩瀚無垠的深藍海洋,魚身閃耀光亮的鱗片,如閃亮流星般劃過你和我的瞳孔,立即攫取了我們的注意力,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個骨架纖細、膚質凝脂的年輕女性叫莉蓮,她站在公寓中,黑髮,小而巧的鼻梁,碎花紫襯衫,車黃線的深藍牛仔褲,帶高跟的棕色短靴,畫眼線、夾睫毛,嘴唇塗了薄薄的亮彩護唇膏,正踮起腳。
就從這裡開始。
且讓這個故事從無生有,由黑暗中浮現。一秒之前,不存在;一秒之後,不僅出世,而且彷彿存在已久,我描述的全部事情都是真的。
莉蓮,她站在自己的腳尖上,吃力地伸長手臂,要從衣櫥頂端取下一頂駝色寬邊呢帽。憲宏不斷傳短訊來,她急著出門。
說是公寓,其實只是一間附帶簡單衛浴的八坪大房間,台北市捷運朝南跑,最後一站,幾叢公寓蓋得歪七扭八,像一口長壞了的牙齒,留下不多空隙當巷弄,一輛車子開進來都嫌侷促。她的租處就在最邊間靠山那棟公寓的頂樓,電梯只到七樓,接著往上爬一層,推開整棟大樓的公共逃生門,走過水泥磚不平的灰色地面,小房間就在那裡,工法草率,四面貼滿白色瓷磚,鐵皮頂,拉過兩條電線,像間公共廁所,顯然由房東自行加蓋,說不定違法。房東千叮萬囑她馬桶容易堵塞,千萬小心,禁止她煮飯,頂多用電器燒燒水,泡泡茶或咖啡還行。她認為自己還算幸運,因為房租夠低,頭一次她負擔得起沒有室友,出入獨立,相對隱私。二十七歲了,她幾乎感覺像個擁有私生活的成人。這一帶正好地勢較高,打開窗口,她就能飽覽城市的全景。
她住進來,馬上自拍。一片扁平的灰海,全是加蓋的鐵皮屋。全台北的建築都像是背了鐵盾甲,藍空再明亮,也無法反映陽光的雀躍。
「這是我的窗口。」她上載照片,附註。隨即一堆網友留言,喔,好美噢。整座城市都在妳腳下。真羨慕。她早拍一張,晚拍一張,持續一百天,記錄這座城市的晨昏,這系列照片網友喜歡得不得了。自稱凱撒大帝的網友留話,希望有一天能有機會與妳並肩站在全世界的屋頂。
憲宏皺眉問這個人到底是誰,老第一個按讚,他有沒有自己的生活,成天掛在網上,不做其他事。她聳聳肩,她也不認識。
「妳讓陌生人窺視妳的私生活?」憲宏不可思議。
「那只是個窗口。」但她上傳的照片不只窗口,還有朋友聚會、購物戰績、閱讀清單、旅遊景點、電影票根,四處吃飯打卡,而且每張照片都有她自己。
「妳不怕他憑照片找到妳的住處?」
「我這間房就在網路上找的。網上還有當初招租的照片呢,全世界都看得到我家。」
「現在外頭瘋子那麼多。」
「阿宅不代表是瘋子。」
「他叫他自己凱撒大帝,我看是夠瘋了。」憲宏嘀咕。
她取出那頂帽子,斜戴在右額上。天氣並不冷,但她待會要去跟瓊瓊她們喝一杯,那是間潮店,她想看起來時髦。她進了宛如飛機洗手間的浴室,對鏡調整帽子,出來,自拍。
臉書留言如海面泡沫浮上來,美女,仙女,女神,妳這樣犯法喔,一堆驚嘆號、紅心圖案。凱撒大帝留言,妳可以不可以停止美麗,我知道很難,為了我這顆衰弱的心臟,請妳試著不要這麼美,妳這名謀殺犯。
她微笑。手機螢幕亮了一下。又是憲宏發來的短訊。她的朋友都用社交軟體,只有憲宏還在發短訊。憲宏拒上社交媒體,為了加入她的網路社群,不得不使用,但他從不參與討論,自己也不發文,找她還是發短訊。短訊老派,不免笨重,憲宏發起短訊總是一條接一條,好像遠方天邊在打雷,轟隆隆,只覺得吵,妳在家吧,我想妳了,別出門,我帶晚餐來,等我,妳在哪裡,為什麼不回話。她趁光亮消失前,瞄了一眼憲宏的問句,將手機收進大衣口袋,掛上耳機,背起袋子,帶上門。
自從她搬進了這間頂樓加蓋,憲宏幾乎天天來。房間太小,房東給了她一張單人床,一個小櫃子,一張小桌子和一把椅,她住了四個月,床上床下已堆滿衣服書籍,幾乎沒有走路的空間,更容不下兩人同時活動,她站在桌子前手沖咖啡,他就坐在床上,像小男孩仰頭看著媽媽一樣跟她說話,而他坐下來之前,還得先把床上高高的衣衫塚,牛仔褲、大衣、運動衫、胸罩、內褲等等,先小心翼翼移到椅子去,騰出床面才有得坐。晚上兩人擠在她的單人床上,背靠著牆,用她的十三吋電腦看片子。他總拎來啤酒滷味,吃剩了從來不收拾,擱在床底下過夜,有時候忘了幾天,還會長蟑螂。她想要房東至少裝台空調,他嗤之以鼻,說頂樓加蓋就該這般滋味,冬日冰箱,夏天暖爐,日子寒愴而淒涼,他緊緊摟住她,用懷念的語調說,喔,當年唸大學就這樣子,每個離家求學的男孩都住在台北市頂樓加蓋,都有個女友當他馴養的貓,寂寞的夜裡,靜靜窩在他身旁,用她柔軟的身子撫慰男孩思家的心情。台北的頂樓加蓋如同巴黎灰色屋頂上的女傭房,迷你,幽靜,躲開了眾人的視線,遺世獨立,情人飄浮在城市上空,忘我溫存。
莉蓮的頂樓加蓋,既小又窄,像間衣櫥,對憲宏來說,那是魔法衣櫥,只要打開門走進去,立刻遁入奇幻空間。不用離開這座城市,只要登高,搭七樓電梯,再爬一層,光線已豁然明亮,空氣清新,微風濕潤拂面,那已是另一個迥異的時空。雖然他上來時總是氣喘吁吁,他的神情愉快,雙眸閃耀,面頰紅潤,他看上去幾乎是青春的。
躲到莉蓮的頂樓加蓋,他就暫時逃開了他的現實。他的現實就是他腳下的城市,每條街道,每棟建物,每間辦公室,每家餐廳,每座公園,每張報紙,每台電視,每張臉,每句話,每道車鳴,都在擠壓他,質詢他,壓榨他,逼得他無處可逃。他住在兩百坪多豪宅,背對象山,面對台北101,四間臥房、三套衛浴、兩間客廳,廚房寬敞,飯廳擺了十二人桌,足以夜夜筵席,他卻在家裡一刻也待不住。城裡幾乎每個人都認識他,他也認識每個人,他卻嫌他們個個虛情假意,毫無真心,沒有真正的友情,只有一條社交梯子擠滿了人,下面的人想把上面的人拉下來,上面的人想把下面的人踢下去。窮的想要有錢,有錢的想要更有錢,有名的想要用名賺錢,有權的想要用權搞錢,錢錢錢,什麼人都要錢。他寧可懸空坐在莉蓮的頂樓加蓋,回到年輕時代的窮,當時他什麼都沒有,卻自我感覺富足得不得了。
他告訴莉蓮,「我什麼都沒有,就有理想。不是對社會,而是對自己。我對自己有理想。我深信自己會做出一番轟動的事業。」
他果然幹出一番轟動的事業,讓他有間位居城中精華區的豪宅供他百般聊賴,身陷權貴圈子抱怨出不來,今天北京明天柏林後天紐約地飛,美酒佳餚吃到牙酸反胃,車子朋友情人房產股票公司榮耀,他什麼都有了,卻失掉了自己,他只有跑到莉蓮的頂樓加蓋來,才能找回一點自己。
「狗屁。」莉蓮翻了個大白眼。
她問憲宏可不可再陳腔濫調一點,「你要當那個腰纏萬貫可是年老力衰到了要喝紅酒才能勃起的中年大叔,別拉我下水當那個貧窮柔弱但純潔性感的年輕情婦。」
頂樓加蓋不是莉蓮的魔法衣櫥,而是她的現實。莉蓮每天起床,現實就像四面牆,向她逼近,令她窒息,她只想跳下床,盡速逃離這個棺材似的小房間。頂樓加蓋底下的城市是憲宏唾棄不屑的現實,卻是莉蓮之所以願意棲身頂樓加蓋的原因,因為她還想留在這裡,靠近下面那些擁擠污穢的街道。
「因為妳有理想,對自己有理想。」憲宏眨眼。
她翻了另一個白眼。憲宏哈哈大笑。讓她不斷羞辱他,對他的一切冷嘲熱諷,是他們調情的方式。他們的關係從一開始就如此不對等。彷彿她口頭上越貶低他的觀點,越踐踏他的價值,她越能證明她的青春勝過他的智慧,她尚未受污染的純真高過他全部加總起來的人生經驗,她的世代比他的世代更聰明更自由,更懂世界是怎麼一回事。她證明他們之間至少是平等的,因為她雖然只有二十七歲,她卻能隨心所欲羞辱這個五十六歲的男人。甚至,她略勝一籌,因為時間站在她這一邊。她的人生還不夠長到足以留下污點,就算犯了錯,她還有時間可以彌補。畢竟她離老朽仍遠,他卻已經必須思考不朽的意義了。
莉蓮邊聽音樂邊沿著歪掉了的巷子走往地鐵站,手機再度震動了一下。瓊瓊他們在等她喝酒,她實在不想理會憲宏,然而她的指頭反射性地把手機從口袋掏出來。
「人在台北。」四個字。不是李憲宏。
她的呼吸停住。腳步也停了。她眼前又出現那天的日出。他們坐在國父紀念館的草地聊了一夜,快天亮時,臨時起意去走一條古道,據說能從台北一路到金山,古早魚販每天從漁港送新鮮漁獲穿過草嶺進城販賣的小徑。走到一半,天已大光,又累又渴,藍天壯麗,高草颯颯,大風呼呼吹雲跑。他們一到大路上就攔車。中午回到了台北,疲倦地連搖手再見的氣力都沒有,就各自回家了。那張笑臉,那雙炯炯燃燒的眼眸,泛白嘴唇全裂了,瘦長的竹竿子腿,那麼熱的天,還裹在深色牛仔褲裡。她一路逆風跟他說話,隔天嗓子都啞了。
又一條短訊進來,憲宏的,把莉蓮拉回台北市南邊的這條巷子。她續行,進了捷運站,站在月台上,列車來了一輛,她沒上。她在回訊。
「待多久?」她寄了出去。
等她轉車,到了瓊瓊他們約的店,對方再沒回信。
她正要進去找瓊瓊,突然,訊息提示聲響了。嗶。
只有一行字。
停止。莉蓮轉過身來,瞪著我。
請你停止寫我。她的手護住手機螢幕,不讓我看那個筆畫少於憲宏的名字。
她一揮手,打掉我的視線。雖然我知道誰傳訊給她,從哪裡傳給她,為何憲宏冗長而充滿綿密愛意的訊息令她心煩,這條短得不能再短的一行字卻加速她心跳。她還是遮住那行字,不讓我吐露那個名字,也就是不讓讀者你知道。她堅持我沒資格代她暴露這項細節。
小說裡角色沒有隱私。實情是無論小說家如何創造了一個受限的視角,他還是處於全知的位置,他知道每一個角色的動機,他因而設定了每一句話背後的意義,他只是故意不講,慢慢、慢慢揭露畫面,讓話語響起、手勢起落,讀者就像是一名被他用手遮蔽雙眼進入一個不知名的房間,只能用感官去猜測周圍事物的變化,直到最後一刻,也就是最後一頁,他才拿開雙手,讓讀者親眼看見整間屋子的全貌。
但莉蓮不吃這一套。不是她不相信小說故布疑陣的樂趣,而是她不認為這個世上誰能代表其他人發言,因為沒有誰真的瞭解誰。即使她是作者腦中創造出來的角色,作者也不真的懂她,就像天底下的父母不見得瞭解自己的孩子。
現在,她冷著一張臉,像名叛逆青少女,對著我說,請停止寫我。你沒有資格寫我。你跟你的世界皆已經腐朽,你資訊嚴重落後,知道的東西太少,我一天得到的訊息量相當於你二十年的訊息量,你是活在地面上的舊人類,我是活在雲端的新人類,你這個古代人怎麼可能理解我這個現代人,怎麼有能力寫我的世界。你的讀者若要瞭解我,他們只要直接上網,跟隨我的動態,看我拍的照片,讀我貼的文字,關於我,讀者可以擁有第一手資訊,何必透過你這個差勁的仲介。
我向我的角色解釋,寫作是一門技藝,小說家的職責是觀察人性。
就像手沖黑白照片才叫藝術?莉蓮對我嗤之以鼻。我的手機就能拍出很好的照片,表達千言萬語。藝術,是一種存在方式。就像詩人是一種生活風格。我不寫詩,而是我卻活得比任何詩人更波西米亞。我比詩人更詩人。不信,你上網看看。
我一時無話可說。莉蓮不需要小說家替她虛構一個身分,她自己虛構了自己。不信,你上網看看。證明一個角色的存在,已經不是透過紙頁還是圖書館,而是網路。而網路的一望無際,其實就像大海,你最後什麼細節都看不見,尤其豔陽高照時,縱使你瞇緊眼皮,努力望遠,終究只能望見一條細細的海平線。一般人很少下海去撈,他們懶洋洋躺在船板上,等著有人潛水直接丟上船來給他們,一條魚、一顆珍珠、一枝珊瑚、一把海草,各式網站、各個臉書、素人名人,都在拚命往社會這條大船上丟懶人包。
我無可奈何,只好對莉蓮說,那麼,小說家能拿故事編織人性的懶人包嗎?
但這是我的故事,理應由我來說。莉蓮拿她兩隻閃爍如火的黑眼睛恫視我。我喜歡我的角色擁有一雙強勢的眼睛,不知道為什麼。
「停止。」嘿,莉蓮用兩根指頭彈出清脆的響聲,要我注意。
「別走神,聽著,我不是你創造出來的人。你不是佛蘭根斯坦,我不是你的怪物。單憑你從記憶大海打撈出來的破銅爛鐵,是拼湊不出來我這個活生生的人。你看待事物已有刻板觀點,形成自己的偏執,自以為對世界有一套深刻的理論。你說你關心我,對我好奇,其實你只是想藉由我來驗證你的看法。但我不服從。我不任你擺布。無論你想說什麼,那是你的價值觀,可不是我的。你對我有意見,你想要用小說教訓我,把我寫成一則道德寓言,嗯,作夢。你號稱寫作之人,以為你在觀察人性,但,你只不過是一名下流的偷窺者。你偷竊了別人的生命,假裝是你自己的想像力,你扮腔別人的說話語氣,以為那是自己發明出來的聲音,你比網路上那些每天潛水觀察我一舉一動的變態網友好不到哪裡去。你們都是沒有生活的人,踮腳尖趴在別人家籬笆上,竊視別人屋子裡的活動,僅憑零星印象,說三道四,妄下斷語。這是我的故事。我的。你要故事,寫你自己的事。」
莉蓮令我一時無話可說。唉,難道除了新聞報導和偽裝成小說的私人日記,其他文類皆已退了流行?
「不是退了流行,而是失去了功能,再也無力準確描述這個世界。」
所以,一個人除了寫自己,再也不能寫別人?我頹喪。
莉蓮對我聳聳肩,轉身,推門找瓊瓊他們喝酒。
莉蓮不讓我寫她,但我仍可以寫李憲宏,那個對他來說手機仍只是一具移動電話的男人。他屬於上世紀,仍然相信小說是一門藝術的時代。此刻他就坐在莉蓮即將進入的餐廳裡。
莉蓮進去,稍微張望,瓊瓊一群人十來個,坐在後頭靠洗手間的大圓桌。她一眼瞥見憲宏,雖然他染黑了髮,臉皮不皺,體形精瘦,夾在笑容輕盈的年輕人中間,他的輪廓硬是顯眼些,皮膚搓了時間的鹽,刻深了五官的陰影,臉部失去柔和線條,即便他正溫柔地淺笑,卻不知為何讓人覺得淡淡哀傷,彷彿生命的重量正沉沉壓在他心頭,想來正是所謂歲月的風霜。
他的雙眼瞥見莉蓮的身影,馬上像路燈突然點亮般放光。
他整個下午找不到莉蓮。只見莉蓮臉書不斷更新動態,但她沒接他電話也不回他短訊。傍晚,瓊瓊來敲他辦公室的門,問他還有沒有事,她有聚會,得準時下班。他隨口問,什麼聚會。果不其然,瓊瓊立刻央他晚上沒事就一起去。他臉露不置可否,任瓊瓊搖身五歲女孩,扭著身子用鼻音哀求他,來嘛來嘛。
他不介意跟年輕人混,年輕人還算喜歡他。像他這類社會名人,年輕人要的不多,只要一點點注意力就好了。與他在街上擦肩而過,來自於他的一句稱讚,坐下來喝過一杯酒,空泛聊幾句生活,會讓年輕人說嘴好久。他知道有些年輕人將他的名字不停掛在唇邊炫耀,誇大了他們之間的交情,以增加自己的文化資本,曾經有位資深導演耳聞某個年輕人到處用他的名字招搖撞騙,在一個場合終於撞見,這名導演一掌惡狠狠將這個浮誇不實的年輕人猛推到牆角,厲聲警告,不准拿他的名字在城裡騙吃騙喝,否則一定給他好看,但,李憲宏無所謂。他間接聽過年輕人轉述遇見他的經驗,宛如教徒感動敘述他們見到羅馬教宗、還是平民興奮描述跟美國總統握了手的軼事,他覺得很有趣,好像李憲宏不是他,而是小說裡的角色、歷史上的人物、神話中的神祇,李憲宏這個名字染上虛構的神秘色彩,成了一則偉大而遙遠的都市傳奇。當他自我介紹李憲宏,他用第一人稱,而人們口中不斷轉述的這個李憲宏,對他來說,已是個第三人稱,另一個陌生人,與他無關。名氣就是這麼回事,他很年輕便成名,早早習慣了當別人故事裡的第三人稱。
他剛闖出名氣時,起初不能接受失去李憲宏這個名字的所有權,那年他二十七歲,與此時的莉蓮同齡,一天早晨他慢跑完,穿著短褲,坐在早餐店喝豆漿嚼飯糰,聽見背後一桌陌生人以近乎親狎的方式在談論他,重複關於他的媒體報導,他不在乎他們議論他,真正讓他覺得毛骨悚然的是他們說話時的篤定語氣,百分之一百的權威口吻,彷彿因為讀了幾篇雜誌報導,看他上過幾次電視,得到零碎資訊,他們便摸透了他這個人,像摸骨師一樣不僅摸清了他整個人的筋骨,連他的前世今生全都一併摸出來了。後來他跟曉雯的緋聞鬧上檯面,他打開電視,看見一堆他這輩子從沒見過面的人,神情激動,口若懸河在講他這個人的品性,創意鬼才,趨勢專家,熱心公益,學問淵博,但無論如何就是逃不過美人關。他的一生宛如一捲清明上河圖攤開在他們面前,長長一條,供他們把玩細節,指指點點。他們講得信誓旦旦,比他的妻子情婦們更清楚他的生活怪癖,像是他上廁所會用掉幾張衛生紙這類私密細節,他霎時領悟他們講的那個人不是他,只是剛好跟他同名同姓,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的李憲宏。出名,就是進入大眾的記憶體,讓他們百分百擁有你,變成他們的一部分,當他們想起你,他們不是想起你這個人,而是動用社會的集體記憶,他們只是用你來錨定時代。
他不擁有李憲宏。就像現在,他任作者書寫他。傳奇需要轉述,轉述需要第三人稱。要進入社會記憶體,就不能介意當第三人稱,把詮釋權讓給別人,供人們說故事、報新聞、講八卦。
| FindBook |
有 12 項符合
群島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3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群島
「我在這裡。」
這是自我高張的時代,所以是自私的時代。
這也是自戀甚於戀人的時代,因而是苦戀的時代。
當無數的世界可以輕易召喚到眼前,
卻始終不能讓另一人成為自己的世界。
第一本長篇小說,為我們演繹當代台灣的網路眾相、世代流變
/
臉書時代的當代台灣,直指世代鴻溝與人心異境的解碼直播
一部關於徒勞的渴望之書,也是愛與語言的沙之書
身體不再是靈魂的居所,靈魂化為電流,奔入虛擬的時空,
愛情果真是名符其實的來電,而戀人的名字是一個帳號。
新戀情就是新頁面,開啓變按鍵,結束只須滑掉。
戀人的功能越來越像手機上的應用程式,用來增添生活的美妙與方便,
過段日子生膩,遺忘,一秒鐘空檔突然想起來,隨手刪掉。
網路令我們狀似無比親密,關係卻如此匱乏。
交友與絕交都只是一個按鍵的事。
臉書上的你、現實中的你,哪一個才是真的你?
「雖然這些人今晚才見面,但他們之間的互動卻是時時刻刻分分秒秒,時間綿延不絕,匯成一條斬不斷的長河。今晚只是網路大河掉出來的點滴。網路不再是實體世界的延伸,而是倒過來,實體世界才是網路的延續。」——胡晴舫
誰留連在誰的肉體,我們只交換體液與快感,不交換靈魂。網美林莉蓮可以是媒體名人李憲宏的情婦,也可以王世傑的情人。網路上,莉蓮與淑媚是朋友,但面對面是情敵,一個熱烈愛台灣,另一個只愛自己;現實中的聚會,是社群媒體溢出來的流動饗宴,指尖交談更甚於嘴巴說出來的無聊話語,一轉頭便成為明日的網路筆仗……
不論散文、時事評論或短篇小說,胡晴舫向來嫻熟於世代之別,人我之辨;她總能準確捕捉人們總自欺或不自知的幽微心思,盤根錯結的關係,道德難題,以為都在掌握中卻持續失控的處境,既理直氣壯又過分纖細怯懦的欲望。
在殊異個體間,胡晴舫也能犀利地指出共相,清晰看見每個人孵夢的侷促姿態,或對著其實無非自身鏡像的他人,「另一個我」,既嫌惡卻抄襲,既依賴又傷害,既憧憬復背叛的荒謬演出。
她筆下人物,多半是時代、城市或各種意義的浪遊者,遊走於隔閡間隙,處處無家處處家。
如今背景淹覆過一片浩瀚虛渺的網路汪洋,瀰漫末世逃亡感或探險氣息,新的時代族裔宛如大航海時代冒險者,降生於這片「電流即交流」的無邊海上並生活其中;而網路作為今日最大的生態系與生活圈,注定了人們無比自由又徬徨困陷的漂泊感。
在這部動員「小說中的小說」設計的她/他——創意教父,網紅女神,離群的憤青,隱抑自我的小說作者,在網路活得更精采的帶風向者,癡等情人的女強人……——始終是獨自一人,以求愛的熱望為槳、自身孤寂作筏,划入網海滔天巨浪;年齡跨度將近三十歲的他們,也從來都是一群人,無分新舊人類,幾乎無能脫出這片洶洶大海。包括書中「小說作者」在內,「沒有人是局外人」。
三一八學運,網路霸凌,媒體衰微,同婚入法……胡晴舫敏銳地將這幾年人們強烈共鳴或幾近公審的時事結合進小說,大格局地思索「台灣」的角色性格演化;同時見證科技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動搖對「真實」的認知;更是銳利指陳,我們如何輕易地棄守一己所有,甘願隨波逐流、習慣於鬱鬱寡歡。
世代、愛情與網路,終究都教我們活得卑鄙,自覺渺小。
藉由描述這個由指尖暴君創造,公私界線疾速泯滅、客觀讓位給主觀、備忘即是遺忘的「表面」世界,胡晴舫以其深情,讓人們在攢聚成群時,更意識到各自的內在孤寂;她也生動呈現每個人活成一座孤島的狀態,卻讓島與島之間,以目光、欲望、回憶、遺憾絲絲縷縷相連,耿耿懸念,在不可見的現實或網路海面下,形成彼此羈絆、需索、傾軋的複雜地脈。
作者簡介:
胡晴舫
台灣台北生,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戲劇碩士。寫作包括散文、小說、文化評論。1999年移居香港。固定專欄發表於兩岸三地以及新加坡各大中文媒體。作品《第三人》(麥田出版)獲第37屆金鼎獎圖書類文學獎。2010年起,旅居東京、紐約,現居香港。
著作:2000 旅人/2001 她/2001 機械時代/2002 濫情者/2005 辦公室/2008 人間喜劇/2010 我這一代人/2011 城市的憂鬱/2012 第三人/2014 懸浮/2017 無名者
相關著作:《群島(限量親簽版)》《懸浮》《第三人》《第三人(精裝)》
章節試閱
我該從哪裡開始。故事可以從任何一個點開始。「我」,這個敘述者,也可以是任何人。在古典的小說世界,「我」是作者創造出來的角色;網路的虛擬宇宙裡,「我」是作者啟動的一個假帳號。你不認識「我」,然而,你將認識「我」,因為「我」將成為這個故事的敘述者。隱身於假帳號的作者設定了「我」是這本小說的作者,而不是她。「我」才是登錄帳號、貼了頭像、開地球文的那個人。你將認識的作者,是「我」。
作者的手指在鍵盤敲下第一個句子,你的手指滑開閱讀器的面板(就像你曾經翻開紙本的書頁),「我」開口說第一句話,嶄新的頁面亮了...
作者的手指在鍵盤敲下第一個句子,你的手指滑開閱讀器的面板(就像你曾經翻開紙本的書頁),「我」開口說第一句話,嶄新的頁面亮了...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2019/07/09
2019/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