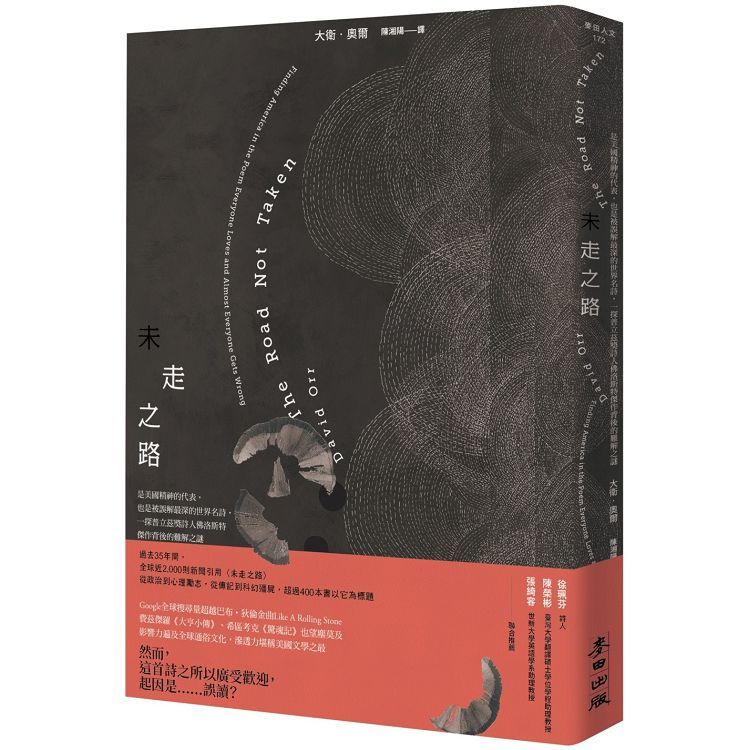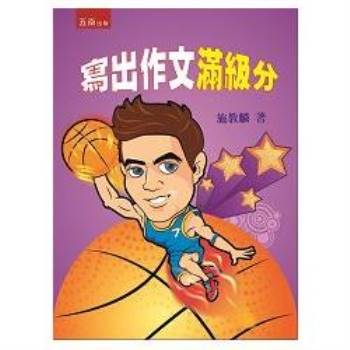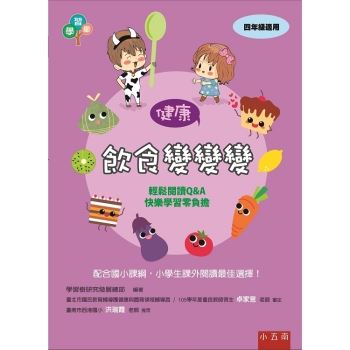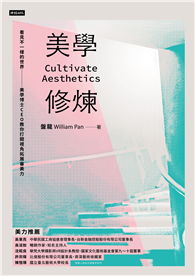多年以後時光某處
我會喟然長嘆,幽幽敘述:
黃葉林間岔出兩條小路,而我──
我選擇了人煙稀少的那條
往後的一切就此不同
過去 35 年間,全球近 2000 則新聞引用〈未走之路〉我會喟然長嘆,幽幽敘述:
黃葉林間岔出兩條小路,而我──
我選擇了人煙稀少的那條
往後的一切就此不同
從政治到心理勵志,從傳記到科幻殭屍,超過 400 本書以它為標題
Google 全球搜尋量超越巴布‧狄倫金曲〈Like A Rolling Stone〉
費茲傑羅《大亨小傳》、希區考克《驚魂記》也望塵莫及
影響力遍及全球通俗文化,滲透力堪稱美國文學之最
然而,這首詩之所以廣受歡迎,起因是……誤讀?
徐珮芬(詩人)、陳榮彬(臺大翻譯碩士學程助理教授)、張綺容(世新大學英語學系助理教授)
◎聯合推薦
揭開世界名詩〈未走之路〉的神祕面紗
一個「作者已死」的最佳範例
「我的詩——我應該說每個人的詩——
都是為了絆倒讀者,讓他一頭栽進那無邊無盡。」
──佛洛斯特的私人信件之一
「我跟你打賭,沒什麼人知道有人被我的〈未走之路〉騙了,
更說不出是哪裡被騙。」──佛洛斯特的私人信件之二
‧佛洛斯特,美國史上最偉大的田園詩人,其地位之崇高,連總統也敬他三分,但他過世後卻屢遭爆料,本人其實是個性格乖戾的「怪物」?
‧世人咸認其不朽名作〈未走之路〉中蘊含純正的美國精神,也都以為這就是一首讚揚個人選擇的頌歌,但它的原意,卻吊詭地與後世所流傳的大相逕庭?不僅不正面,還很……虛無主義?
一個世紀以來,文學評論家和眾多讀者不斷叩問〈未走之路〉這首名詩的真正意涵,而大衛‧奧爾在此則以專書探討此詩與美國文化的交互影響力,及其在詩歌結構上的複雜性。他逐句解析佛洛斯特其作,細膩探究此詩問世的時代背景,並藉由考證當時的文學圈內軼事以及佛洛斯特與他人的信件往返,試圖推敲詩人的心理狀態,還原其創作初衷:一個容納多重可能性的開放空間,一個被無意識的選擇所包覆的選擇。〈未走之路〉描繪了一個選擇中的自我,卻也隱約批判這個自我。選擇的難題,向來是西方哲學傳統中最源遠流長的難題,而作者揭示了詩中經典的「岔路口兩難」如何遙遙呼應了佛洛斯特的詩觀與傳奇一生,同時亦旁徵博引,援用哲學、心理學與腦科學等跨域觀點,指出美國精神的精髓如何蘊藏其中。
▎本書特色
關於〈未走之路〉的受歡迎程度
◎商業影響力遍及各類流行通俗文化
‧2008 年福特汽車曾以〈未走之路〉為題,拍攝品牌形象廣告。
‧曾被曼陀珠、尼古清口嚼錠、AIG 保險和全球最大求職網站 Monster.com 用於商業廣告。
‧無數音樂創作者借用詩中短語寫歌,十餘部電視影集以詩句作為標題。
‧電玩公司 Spry Fox 以「Road Not Taken」為名推出遊戲。
◎ 在新聞媒體和出版界超乎尋常的高引用率
‧在過去 35 年間,佛洛斯特的詩句出現在全球近 2000 則新聞報導裡,以每週不止一次的頻率出現;在超過 400 本其他作家的作品中,它被作為書中標題、副標題、章節標題。詩句的普及度之高,遠超出同時代的其他美國詩作。
‧詩人羅伯特‧賓斯基(Robert Pinsky)籌辦「Favorite Poem」計畫,邀請美國民眾以各種形式表達他們最愛的詩是哪一首,結果顯示最受歡迎的是〈未走之路〉,共收到超過八千封投稿信件。
◎ 驚人網路搜尋量
‧大衛‧奧爾以作品加作者名「未走之路 + 佛洛斯特」在 Google 搜尋,並將結果與同時代其他知名詩人比較後發現:它比艾茲拉‧龐德與其作品的搜尋量高出 24 倍,比「荒原 + 艾略特」高出至少 4 倍。當「未走之路 + 佛洛斯特」與其他更現代的非詩歌作品比較,搜尋量比「Like a Rolling Stone + 狄倫」高出不止 2 倍,比「大亨小傳 + 費茲傑羅」高出近 3 倍,也比「驚魂記 + 希區考克」高出 3 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