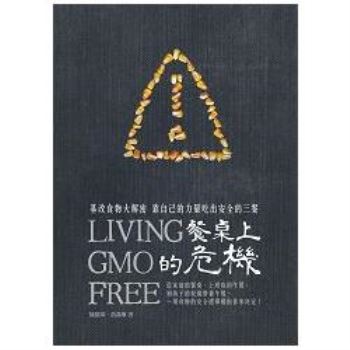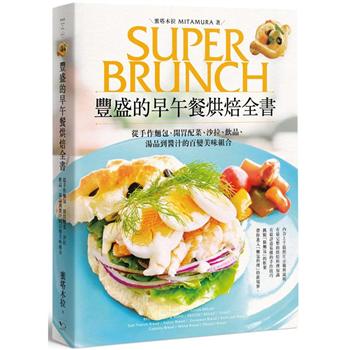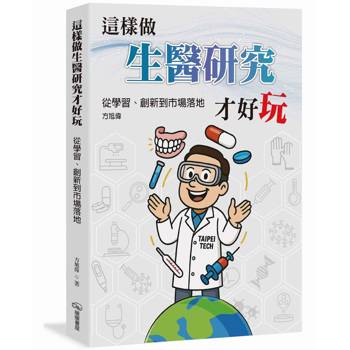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大宋之變1063-1086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中國歷史上第一場馬王政爭!
聚焦北宋英宗、神宗到哲宗的三朝政壇風雲,
看北宋政治家們如何從一場君子之爭,演變成朝野分裂的政治大對決!
北大歷史學系教授、宋史專家趙冬梅,破解百年大宋盛衰轉折的重磅之作!
揭露大宋之變的錯綜因果,探究帝國興衰的深層根源,
帶你讀懂北宋權力運作的歷史智慧!
這是一個朝代的轉折史,作為君王,他們奮發進取:
行新法、伐交趾、收河湟,改制元豐,伐夏開邊……卻無法阻止國家衰亡。
* * *
這是一群有識之士的時代悲歌,作為臣子,他們名震千古:
韓琦、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卻難解當下危機。
* * *
君臣遇合之際,他們積極尋求變革,
卻終將改革變成政治角力,將北宋推向危亡的深淵!
▌一出版即席捲大陸各大好書榜!各大知名公眾號、媒體強力推荐,當當網99.9%讀者五星好評!
▌羅輯思維、得到APP 創始人‧羅振宇‧重磅推荐
從來沒有哪個朝代像宋朝這樣飽受爭議,有人說它積貧積弱,有人說它文明輝煌。本書作者、北京大學趙冬梅教授認為,從一○六三年英宗即位,到一○八六年哲宗初司馬光離世,二十四年間,是宋朝政治由盛轉衰的關鍵轉折,堪稱「大宋之變」。
本書以司馬光的後半生為線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壇風雲,深入濮議之爭、王安石變法、司馬相業等歷史細節,以人物為經,以事件為緯,刻畫出鮮活的歷史人物與情境,充分展現韓琦、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文人政治家在歷史大變局中的抗爭與博弈,再現共治時代末期知識分子的榮光與屈辱。以抽絲剝繭的分析推理,典雅流暢的語言,探究大宋之變的錯綜因果和歷史真相,揭示朝代興衰、帝國統治的深層根源。
從宋朝這段風雲詭譎的政局中,我們清楚地看到,當士大夫群體分裂成利益集團,當集團的利益超越國家的整體利益,集團之間於是黨同伐異,互相攻擊,甚至水火不容,終致掌權者開始政治大清洗,鬥敗者淪為政治黑名單,國家領導人也失去了超越性的視野,不得不跟更擅於玩弄權勢的集團結合。北宋滅亡的禍根,也正是在這二十幾年間的國家紛擾中埋下。
▌本書特色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宋史專家、「百家講壇」特邀主講人趙冬梅治宋史之作。講透「大宋之變」的深層根源和歷史邏輯:在以皇權為根基的帝制時代,寬容政治消亡、君臣共治打破,北宋政治走向不可逆轉的腐敗。
◆以人物串聯歷史,以細節關照全局。以推動歷史發展的樞紐性人物司馬光後半生行跡為切入點,來勾勒北宋政治的演變軌跡,還原北宋由盛轉衰的歷史真相,探討帝制王朝的政權格局與歷史命運。
◆深入歷史過程,還原歷史事件中的「情與理」。對許多宋代歷史上的重要問題,如王安石變法、司馬相業等,重新回到歷史情境中去同情和理解,從宋代的歷史背景和實際運作的效果予以評析,為讀者提供新的看待歷史的方式。
◆以史料為據,從人性角度,充分還原了北宋君臣在歷史大時局的命運與選擇。
◆附有《大事記年》《宋朝官制簡表》,人物關係、歷史脈絡清晰可循。
▌以史為鑑
當朝野在政治正確的內鬥中逐漸淪喪,
政治糾錯批評的機制失效,終於埋下國破家亡的禍根!
◆宋朝如何從開國初期的包容走向皇帝和宰相的專制?
◆如何站在當時的歷史情境公平地評斷王安石變法?
◆宋神宗、王安石對宋朝政治文化造成哪些無可彌補的傷害?
◆一身正氣的司馬光在萬眾歡呼聲中登相,為何最終一事無成?
作者簡介
趙冬梅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大陸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特邀主講人,浙江大學公眾史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英國牛津大學高級訪問學者,曾任德國維爾茨堡大學漢學系客座教授、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美國史丹佛大學北大分校客座副教授,香港浸會大學「章群中國歷史講座」特邀主講人;致力於宋代制度史、政治文化史、歷史人物傳記的研究、寫作和傳播,主要著作有《文武之間:北宋武選官研究》《武道徬徨:中國古代的武舉和武學》《司馬光和他的時代》《千秋是非話寇準》,譯著《天潢貴冑:宋代宗室史》《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
| |||
|
|


 2020/12/26
2020/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