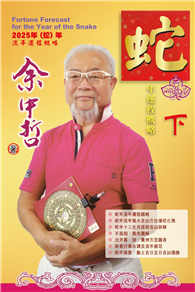前言
判決可能有助於修補破裂的世界。
──吉兒.史塔佛(Jill Stauffer)
這是一個無法寬恕的年代,一個憤慨的年代。這個世界缺乏原諒的理由。每當社會媒體平台允許大眾匿名評論,仇恨的言語就會在網上爆發。或許是受到經濟失調的刺激,又或者是領袖之間不擇手段地互相推諉,狹隘的公共政策與苦澀的政治鬥爭促使國籍、種族與背景不同的人相互懷疑。美國在判定、起訴與懲罰犯罪的時候特別嚴厲,尤其是起訴少數族裔時更是如此。二○一八年的美國是人類史上最多人入獄的國家。
反之,美國對於債務一般採取寬容的政策,尤其是商業上的債務,而且破產的程序允許公司可以重新開始。這個重新開始的概念事實上是任何場景之中寬恕的核心。但是,在美國,個別債務人面臨更多的阻礙,一九九八年以來,美國的破產法清楚地把學生貸款排除在外,但即使是提供學生貸款的公司,以及只想著賺錢而未能用心辦學的營利型學校,也可以藉由申請破產喘一口氣。而在國際上,歐洲、南美與非洲國家上演一連串經濟艱困的劇碼,隨之而來的,是還不出錢還有倉皇失措地尋找務實的解決之道。寬恕,也就是讓合理的憤恨(justified grievances)隨風而去──是人類在不同社會之間培養起來的能力,甚至已經融入法律體系之中。
法律何時會以及何時該寬恕?
法律所執行的寬恕改變了司法的結果。法律是一套管理人類行為的規則與制度,傳達合理憤恨的依據與結果,但是法律也提供方法讓人寬恕錯誤的行為。撤銷刑事控訴、藉著破產程序卸下債務,還有對人的赦免,都是透過法律給予寬恕的實例。法律本身有可能會藉著放棄追究司法責任以及盡量不責備,落實對人的寬恕。法律可能是一個把折磨轉為機會的工具。
藉著寬恕,我是指有意識且深思熟慮之後,決定撤銷對有過失或犯下傷害罪行的人宣洩不滿的正當理由。在此意義之下,寬恕會不斷擴大,它包含(但不限於)以下情況:犯錯的人認錯,並試著修補他們所造成的傷害,受害者與其他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或大局著想,決定把合理的憤恨放在一旁。入伍服役的人可能決定要寬恕他那個逃避徵召的兄弟,而他的兄弟接著也可能轉而放下他們對此事的爭執,使得兩人朝未來更好的關係邁進。如果沒有承認錯誤,就不可能有寬恕;對於個人來說,寬恕以及期待帶來傷害的人必須承受法律後果,這兩者並非無法並存。謀殺案受害者的母親可能會決定要原諒殺人兇手,但還是希望罪犯可以受到起訴與懲罰。法律的規則就是會處罰道歉的人,如此一來,便使得道歉與寬恕的可能性雙雙降低。法律制度與政府官員會避免使用不當行為的調查結果來起訴,但他們也不會消除調查結果。
本書要問的是,執法人員與制度何時會,以及何時應該鼓勵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寬恕?法律本身何時有可能寬恕?比較法律如何處理刑事犯罪與債務──幾百年來,不同文明在法律上要選擇寬恕,都要處理違法行為中這兩個根本領域──可以讓我們學到什麼?除此之外,比較美國法律與國際法在此面向的作法,帶來了任何有助益的觀點嗎?
提出上述問題,是為了邀請人們討論並檢證不同法律體系的比較以及人們之間的非正式互動。如果約會遲到、話沒聽到請人再說一遍,或是有什麼驚人之舉,我們會說「請見諒」。寬恕、容忍、仁慈以及善意在哲學與宗教傳統都有顯著的表現,包括人道主義(humanism)、基督教、猶太教(Judaism)、佛教、巴哈伊信仰(Baha’I)、印度教(Hinduism)以及儒教,還有在夏威夷、加拿大、紐西蘭與獅子山共和國(Sierra Leone)和其他等地原住民的古老實踐上面皆可看到。
因此許多傳統都有文字及儀式來培養人的寬恕能力。寬恕就是讓自己的內心不再把過錯算在犯錯的人身上,即使依然看得清所謂的過錯。人可以寬恕其他人而無須寬恕錯誤的行為。「寬恕就是一種承認我們跟其他人一樣的舉動。」反之,有些人呼籲寬恕,恰恰正是因為知道我們對於他人的行為動機理解有限。寬恕鼓勵人們站在別人的角度想,瞭解影響他人行動背後更大的壓力與結構,優先創造共享的未來,而不是陷入對過去的怨憤。
所以,反過來說,寬恕的能力是一種資源,讓個人有辦法超越積怨與衝突。曼德拉(Nelson Mandela)領導南非的社會運動反抗種族隔離制度,再引領國家和平過渡到一個擁抱人權的民主政府,塑造出關注未來的寬大胸懷,而非以過去為中心的怨恨。他曾經觀察到:「恨就像是自己喝下毒藥,然後希望你的敵人快死。」請求寬恕意味著在跟上帝、家人、鄰居、同事甚至是陌生人的互動中,往悔改及贖罪邁了一步;給予寬恕是人努力要追隨聖人的腳步。
雖然有些傳統把寬恕視為對道歉、悔改、賠償或接受處罰的回應,但有些傳統是無條件地支持寬恕。寬恕可能讓冒犯他人的人得益──減輕他的孤立感,或是提供撫慰與接納。「寬恕提供的是懲罰給不了的東西:寬恕的時候我們讓犯錯的人有真正洗心革面的機會;一切重新開始。」哲學家露西.阿萊伊斯(Lucy Allais)如此解釋道。倖存者可能希望寬恕犯錯者能夠以一種非個人懲罰所做不到的方式,讓犯錯之人有所轉變。有些人靠著重新邀請罪犯進入人性的道德社群,靠著展現關懷與連結,亟欲改變他們。當身分曝光的受害者想要寬恕,想要找到一份歉意,焦點就落在已經改變或有可能改變的犯罪者身上。
雖然有人只是單方面寬恕,不期待犯罪者的改變,但寬恕之舉不但可以給寬恕者一個心理解脫的可能,也讓他們有了道德提升的機會。由此看來,寬恕意味著打破冤冤相報並且拒絕眼睜睜看著犯錯之人受苦的欲望。夫妻可能會想:「我不會原諒,除非另一半道歉,」但是一方也可以在沒有道歉的情況下先行原諒。寬恕者可以用盡全力去應付他(她)無法理解或控制的事,而這樣做也可以提升個人、避免痛苦、防止冤冤相報,且能把他(她)從某種滿腦子都被扭曲自己生活與感性的錯誤感知所盤據的狀態中釋放出來。所以,寬恕為道德的自我改善創造了機會。
針對人類健康、憂鬱症和家庭諮商的研究指出,因他人言行受到傷害的人,寬恕增加了他們生理、情感與精神上的幸福感。放掉內心的不滿能帶給寬恕者的東西超過受到寬恕的人。寬恕做錯事的人讓犯罪或違犯承諾的受害者可以放下怨憤,重建關係,或是單純靠著選擇寬恕這個行動,就覺得獲得了力量。有一個替金恩博士遺孀科雷塔.金恩(Coretta Scott King)夫人工作的人解釋:「她的先生過世之後,我感覺到有些人試圖利用她的寬容,並想利用她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我很驚訝她面對這些情況時的沉著冷靜。她對我說,如果你不原諒別人,那種感覺會殺了你。」猶太教的拉比哈羅德.庫什納(Rabbi Harold Kushner)認為受害者應該寬恕,不是因為對方值得原諒,而是因為受害者不想變成一個痛苦、怨恨的人。作家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說得很生動:「寬恕不是一件你為其他人做的事,而是一件你為自己所做的事。這是在說:『你沒重要到可以讓我動彈不得。』也是在說:『你不能把我困在過去,我值得一個未來。』
選擇不寬恕也可以帶來力量。醫學與心理學領域的學者漸漸重視寬恕,政治學、衝突解決與哲學領域的學者也是一樣。人們可以鼓勵受到影響的人寬恕,但不能強迫他們寬恕。一名幼時受到虐待的大人,完全有憤恨的正當理由,而拒絕寬恕可能會感受到權威(authority)與自我價值(self-worth)──甚至是成熟,它讓當事人克服了試著取悅他人的後天傾向。寬恕一直是,而且絕對依然是個人獨一無二的特權;強迫、甚至是要求受害者寬恕,會造成他們又經歷到新的傷害、失去自主權,以及源自於先前傷害所產生的低人一等之感。不論是私底下或公開要求受害人寬恕,都能造成新的受害(victimization),否定受害者自己的選擇。它可能會痛苦地取消掉受害者自己是要寬恕(或不寬恕)的決定。事實上,強迫別人寬恕本身就有可能造成對方心理上的悲痛。
寬恕是許多文學作品的主軸。在托爾斯泰(Tolstoy)一八八七年的中篇小說《克羅伊策奏鳴曲》(The Kreutzer Sonata)之中,主角謀殺通姦的妻子獲判無罪,然後乞求火車上一同乘車的旅客原諒他。胡賽尼(Khaled Hossein)二○○三年的小說《追風箏的孩子》(The Kite Runner)裡的主角試圖原諒自己未對遭人毆打的朋友伸出援手。在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 一八七一──七二),多蘿西亞(Dorothea)努力不要太輕易寬恕,她悲天憫人的能力恰好也被充滿同情地描繪出來。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一九八七年的小說《寵兒》(Beloved)問的是一個蓄意殺害自己小孩的母親是否值得原諒,即使他們是在逃離奴隸制後被捕。乞求寬恕也不斷出現在流行音樂的歌詞之中,詳細刻畫戀人之間、親子之間、個人與上帝之間以及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過錯及道歉。
寬恕可以是集體的事。陌生人與彼此認識的人都可以並且確實給予了寬恕,例如有一群校園槍擊事件受害者的母親與兇手的母親(彼此並不認識)於二○○八年在華盛頓首府齊聚,為了和解與撫慰一起參加了「寬恕的母親下午茶」(Forgiving Mother’s Tea)。
寬恕不見得是阻止犯罪者受到起訴或承擔其他法律後果。當一個受委屈的人放下憤怒或主張懲戒,並不是要強迫其他人也這麼做;這種個人寬恕的行為,也不是要剝奪大眾透過習俗與規則落實社會規範的責任與權力。的確,寬恕的人也可以主張懲罰犯罪者是一項公共行為,堅持公共規範。這證明了法律與寬恕可能屬於完全不同的領域。寬恕屬於人際(interpersonal)領域,法律體系則是取決於無關個人(impersonal)的過程。藉著寬恕,我可以放下對那個傷害我之人的憤怒與仇恨,但我並不打算、也不可以改變秉公處理的需求,又或者是改變試著嚇阻未來類似犯罪者的政策。
因此,個人的寬恕行為可能與公開的刑事起訴並存;或者說有可能使寬恕者主張放棄起訴,或克制自己加入起訴。寬恕和法律的懲罰都認為:罪犯應被視為社群的正式成員,社群會要求所有成員為他們的行動負責。雖然,堅持寬恕的觀點可能會呼籲法律程序與法律條文本身進行改變。
修復式正義
隨著內戰或大規模的暴力過後,國家如果想要處理違背人性或侵略的罪行,有可能會尋求審判之外的替代方法。一九九五年,受到阿根廷一九八三年全國失踪人員調查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Disappearance of Persons)的啟發,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開始啟動,這是「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機制的重要實例。27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運作的三年期間,邀請受害者訴說個人遭遇,也請罪犯申請大赦,條件是他們要證明自己的行動是出於政治而非個人目的,而且他們使用的手段也符合政治目的之比例。接下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針對潛在的賠償舉辦聽證會,雖然僅有少數的賠償是來自聽證的過程。
屠圖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回想起自己擔任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的工作時說道:「寬恕意味著放棄對罪犯以牙還牙的權利,但這種損失能解放受害者。」 屠圖在聽證會上希望受害者能寬恕罪犯。有人因為他期待受害者給出寬恕而批評他,但他承認,受害者的寬恕不應該被視為理所當然,事實上是反映出他們的寬宏大度。波萊恩(Alex Boraine)這位曾主張設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部長擔任了委員會的副主席,後來也描述聽證會上作證的人普遍沒有復仇的想法。他想像和解是一種非暴力的共存,而屠圖想的是一種更為堅實的過程,過程中,犯罪者公開告解與懺悔,然後受害者寬恕。儘管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並未要求倖存者面對那些折磨及傷害他們的人,但有時候在委員會面前作證可能異常痛苦。南非暴力與酷刑受害者創傷中心(Trauma Centre for Victims of Violence and Torture)的專家估計,在自己服務的數百個對象中,有超過一半的人在作證之後產生嚴重的心理問題,或是後悔自己那樣做。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受到反對者的批評。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和比科(Steven Bantu Biko)的家人在法庭上提出異議,委員會的報告也引發前政府官員、警察和政治領袖的抨擊。一項研究表明,參加真相委員會聽證過程的四百二十九個人,只有七十二人討論到寬恕,只有百分之十的人願意原諒那些為自己行徑負責的人,只有七人說願意無條件寬恕。一份研究發現,有百分之三十的參與者表示感到原諒的壓力。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不大考慮賠償的問題。而且南非持續不斷的暴力和不信任將影響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最終的評估。政治漫畫家夏皮羅(Zapiro)生動地捕捉到問題所在,漫畫中,屠圖大主教站在代表「真相」的土地上,裂縫的另一邊則是寫著「和解」。
即使有缺陷,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提供了一個挖掘與揭露政府與反對者歷史罪刑的論壇。儘管擔心大規模的暴力,但這符合和平的政治轉型。這也在盧安達(Rwanda)、獅子山共和國、柬埔寨(Cambodia)、賴比瑞亞(Liberia)等近四十個國家激發出類似的努力。為了追究責任和往前走,北愛爾蘭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優先找回動亂時期(Troubles)的暴力真相。委員會確立了五種可行方法:在歷史上畫出一條線;參與衝突的組織進行內部調查;以社群為基礎的計畫(community-based projects);恢復真相委員會;歷史澄清委員會。
對於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成功與失敗所做的分析,正在從一些不為人知的軼事轉移到更嚴謹的研究。各個不同團體的公開看法都讚揚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帶來了真相。它的過程正好符合相對和平的民主轉型,民眾也表現出參議政治的高度意願,而且尊重法律制度。聯合國的一項倡議明確表達出賠償的原則,等於說明了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以及二○○六年十二月聯合國大會採行的「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踪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from Enforced Disappearances)所做的努力。
真相委員會和賠償是修復式正義的創舉,把受害者、侵犯者和社群裡的其他成員包含進來,使其參與另類、前瞻性的討論及行動。修復式正義渴望在司法過程中結合寬恕,而不僅僅是簡單地糾正其暴行,它試著結合受害者、侵犯者與社群成員,一起努力讓事情在現在與未來走向正軌。修復式正義的程序建立在北美原住民、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紐西蘭毛利人(Maori)與其他文化的傳統上,專注未來往往更甚於關注過去,關注社群以及當下的受害者與加害者。
屠圖大主教針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演講及著作中,提出了修復式正義的想法。他二○○○的作品《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彩虹之國的和解與重建之路》(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激發了芝加哥退休法官墨菲(Sheila Murphy)在校園中設立修復式正義的圈子,把受害者、加害者與其他人都納進,讓他們討論那些本來會走入職業懲戒程序(disciplinary proceeding)的事件。圈子裡的學生、老師、行政人員與其他受到影響的人一起討論事情 的真相、誰受到影響又如何影響、每個人承擔的責任、還有要採取什麼步驟來修復傷害。有些學校主動使用這樣的圈子,藉由建立社群意識與信任來防止霸凌與衝突。
地方社群正在實施的類似做法,既是回應衝突也是嘗試避免衝突。透過調解會、社群會議、鄰里修復委員會或調停的小圈圈,修復式正義的計畫要求受害者放下合理的憤恨,至少要能夠與加害者交流,幫助他們重新加入社群。這對受害者來說是很高的要求,即使是在受害者與相關社群的身分都已清楚定義的時候。根據英國的實證研究,受害者對於修復性過程的滿意度大於敵對性過程(adversarial processes),而且很急於幫助加害者扭轉人生,但他們幾乎不會使用寬恕這個字眼或概念。也許是因為如此,修復式正義一直以來主要都是針對一些小罪,像是蓄意破壞,儘管有些人也亟欲用修復式正義處理仇恨犯罪和其他重罪。
在此前提下,美國許多少年法庭會採用修復式正義的舉措。找到罪行以及認罪答辯(guilty plea)之後,他們可能會把加害者、受害者和其他社群成員都放進量刑協議之中,這份協議會反映加害者對於受害者受傷程度的理解、受害者對於加害者處境與需求的理解,還有社群成員幫助的意願。這一類的修復性努力經常可以拓寬人們對於社會與文化因素影響個人錯誤行為的認知。以屠圖大主教的話來說,修復式正義的努力「是要瞭解罪犯,所以會有同理心,並且試著設身處地,體會那些制約他們的壓力與影響力」。
針對青少年修復性司法的舉措,常見的其中一項元素是賠償(restitution):做錯事的人提供服務或工作來修補他或她所造成的傷害。重新粉刷房屋、美化環境,還有洗車和洗狗,都是青少年法庭判決賠償的例子。青少年司法中的修復性努力,都是在嘗試追究年輕的加害者對主要受害者應負的責任,同時也培養他們的技能。英國有個城市會在受到監督、控制以及安全的環境中舉辦修復性司法的會議,受害者可以在會上跟加害者說明罪行的影響,並且建議修補傷害的可行之道。參加者提議社區計畫,這類計畫可讓年輕人參與慈善事業或多種機構的(multiagency)付出,探索個人感興趣或是對受害者有實際好處的工作。
曼德拉和屠圖大主教留下的語言與領導風範,把激勵人心的話語和形象帶給渴望未來的社群。二○一四到二○一六年間,哥倫比亞與革命武裝部隊FARC協商出一份和平協議,針對前FARC以及國家軍隊的成員提供了一套赦免政治罪的程序。這與個人寬恕的例子一樣,把對過去的關注轉移到關注未來,而且不會把過去抹消掉。受到哥倫比亞政府指控為「叛亂」的人權行動主義者奧班朵(Liliany Obando)受到特赦,重新獲得自由,也有了找工作的機會。哥倫比亞的努力有如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反映出希望:一個向前看與寬恕的過程,藉著公開承認歷史錯誤、調查過去政府所行使的違反人性尊嚴之事以及靠著那些反抗政府的人,將能避免未來的冤冤相報。法律規則和程序可以鼓勵或至少不懲罰人們表達歉意或寬恕,而他們可以支持特定的受害者和整體社會採取更寬容的態度。
然而,法律的寬恕帶來進一步的問題:法律如何能夠寬恕?法律上的寬恕與個人的寬恕有何不同?支持和反對法律寬恕的理由是什麼?法律範圍內寬恕的限度在哪裡?又應該到哪裡?(未完)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法律何時該寬恕?:從赦免、修復式司法到轉型正義,前哈佛法學院院長寫給當代的法律思辨課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法律何時該寬恕?:從赦免、修復式司法到轉型正義,前哈佛法學院院長寫給當代的法律思辨課
我們認同懲罰的規範力,卻也看見寬恕的正向引導力量。
然而,要讓寬恕成為司法實務的一環,牽扯到極為複雜的衝突。
◇◇─────────◇◇
前哈佛法學院院長、美國大法官候選人、哈佛三百週年校級教授瑪莎‧米諾
給眼下這個動盪不安的世界一場充滿人性辯證的法律課
李茂生(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周宇修(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苗博雅(臺北市議員)、楊貴智(法律白話文網站站長)、葉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聯合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序)
誰有寬恕的權利?
誰應該被寬恕?
在哪些條件下才能夠寬恕?
如果法律不從懲罰的角度制定,而是原諒與寬恕,
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寬恕的能力是一種資源,讓個人有辦法超越積怨與衝突。曼德拉領導南非的社會運動反抗種族隔離,再引領國家和平過渡到一個擁抱人權的民主政府,塑造出關注未來的寬大胸懷,而非耽溺於過去的怨恨。他曾說:「恨就像是自己喝下毒藥,然後希望你的敵人快死。」
寬恕,意味著打破冤冤相報的輪迴,並且拒絕個人內心「親眼目睹犯錯的人受苦」的慾望。
然而,寬恕的概念非常複雜,需要層層剝開釐清:
△ 寬恕必須出自個人意願,強迫他人寬恕,會帶來二次傷害。
△ 當事人選擇不寬恕是一種賦權,同樣能獲得尊嚴與力量。
△ 我們可以寬恕他人,而無須寬恕錯誤的行為。
△ 個人受傷可以選擇寬恕,但若傷害的是整個社群,正義仍需司法維持。
寬恕的人也可以主張懲罰犯罪者是一項公共行為,堅持公共規範。這證明法律與寬恕可能屬於完全不同的領域。寬恕屬於「人際領域」,法律體系則是取決於無關個人的過程。藉著寬恕,人們可以放下對那個傷害他們之人的憤怒與仇恨,但人們同時可能並不打算、也不可以改變秉公處理的需求,又或者是改變政策,試著遏止未來有類似的犯罪者。法律體系的寬恕帶來進一步的問題:
△ 法律如何能夠寬恕犯錯之人?
△ 法律上的寬恕與個人的寬恕有何不同?
△ 支持和反對法律寬恕的理由各是什麼?
△ 法律範圍內寬恕的限度在哪裡?
法律反映一個社會的道德價值,而在一個比較不公正的社會裡,就會需要更多的法律。法律體系的目的本是用於懲罰違反者,但如果重新修正法律規則,將寬恕的可能性也納入的話,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前哈佛法學院院長瑪莎‧米諾在本書提出「寬恕的力量」所具有的種種潛能,一方面探討寬恕的前提,另一方面則承認有些錯誤絕對不可饒恕。她深入不同領域的議題在法律、正義,與文化傳統的複雜交界,並拋出一個當代最為困難的問題:法律是否應該鼓勵人們寬恕?
╱
米諾透過以下三大面向來處理法律中的寬恕議題:
1. 面對童兵與未成年犯罪者,修復式司法有何利弊?
2. 債務免除如何給予人們重新開始的機會?針對政府、企業與個別債權人,各國法律處理債務的方式有何不同?
3. 當赦免作為強大的法律工具,它何時能增強正義、和平與民主的價值,何時又會成為特權的打手,傷害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承諾?
有時候,放棄法律上的怨恨會讓法律更為公正。不過,由於法律是維護民主的重要框架,雖然宗教領袖、心理學家等都肯定寬恕是向善之動力,但要將寬恕落實為正式的法律施行細則,將牽涉到更為複雜的考量。瑪莎‧米諾身為鑽研寬恕議題數十年的哈佛法學院教授,藉由本書議題之探討,無論在實務與理論上都進一步提出了操作的輪廓與辯證。
【各界重磅推薦】
‧在這個充滿噪音以及困惑、由仇恨所賦予生氣的世界中,瑪莎‧米諾是一個具有道德清晰的聲音;她是一個鼓勵寬恕的律師,一名追求證據的學者,一個追求慈悲的人。
──吉兒.萊波爾(Jill Lepore),《真理的史詩》(These Truths)作者
‧在這個被反動與嗆聲文化所形塑,對於他人總是採取嚴厲、道德指向性譴責的時代中,這本傑出的作品帶來了一個深刻的提醒:為了能夠讓一個分歧社會融合成一個人性社會,必須要具有根植於法律的寬恕,以及和解的能力。本書針對法律該如何做到這點進行了啟發性的討論,讓本書成為一個更具人性社會的燈塔。
──克勞德‧史提爾(Claude Steele),《韋瓦第效應》(Whistling Vivaldi)作者
‧除了瑪莎‧米諾之外,沒人能針對寬恕在法律上的角色及原諒的相關法律寫出這樣傑出、可讀的靜思之作……本書展示出如何在同時記住過去之時,也拋開過去前進並重建。」
──勞倫斯‧特萊布(Laurence Tribe),《終結總統制》(To End a Presidency)作者
‧「如果一個人的手裡仍抓著他犯罪所得的贓物,那他能夠被赦免嗎?」(語出哈姆雷特)。在這本充滿慈悲、細緻並實際的著作中,瑪莎‧米諾將一組初見似乎毫無關聯的議題進行了具有啟發性的連結:童兵所犯下的恐怖罪行、公司與學生債務,以及總統對不思悔改的罪犯所進行的特赦。米諾以傑出手法展示了這些議題全都引導出同一個急迫且具爭議性的問題:一個正直的司法系統能夠針對哪些犯行、在哪些情況下進行寬恕?《法律何時該寬恕?》就這個法律難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指引。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普立茲獎得主
‧瑪莎‧米諾討論了社會如何從大規模的悲劇與違反人權事件中恢復的這部作品具有轉型正義的意義……她的見解根植於對司法要求的深入細緻理解,聰明而又深入。
──布萊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平等正義倡議組織(Equal Justice Initiative)創辦人
‧瑪莎‧米諾慈悲、淵博且細緻的檢驗……具有突破性,應該會為未來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架構。
──《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針對修復式正義的堅實可及文獻。
──《科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法律何時該寬恕?》將幫助讀者理解法律之下原諒與寬恕的棘手複雜性。
──《書單雜誌》(Booklist)
作者簡介:
瑪莎.米諾Martha Minow
哈佛三百週年校級教授,二○○九年至二○一七年間擔任哈佛法學院院長。在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翰‧保羅‧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退休後,米諾是繼任大法官的候選人之一。
數十年來,她研究並書寫關於法律與原諒的相關議題,研究範圍包括科索沃的獨立國際委員會以及聯合國高級難民署的想像共存計畫。著有Between Vengeance and Forgiveness: Facing History after Genocide and Mass Violence(暫譯:報復與諒解之間:在種族滅絕與大屠殺後面對歷史)等作。
譯者簡介:
李宗義
畢業於政治大學英語系、東亞所,清華大學社會所博士,現為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副教授,近年關注災難中的政府與災民的決策,翻譯的作品包括《叛離、抗議與忠誠》(商周)等近二十本。
許雅淑
畢業於台大圖資系、清華大學社會所,清華大學社會所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社會學、文化社會學、金融、文化財富等,翻譯作品包括《窮人的經濟學》等書。
章節試閱
前言
判決可能有助於修補破裂的世界。
──吉兒.史塔佛(Jill Stauffer)
這是一個無法寬恕的年代,一個憤慨的年代。這個世界缺乏原諒的理由。每當社會媒體平台允許大眾匿名評論,仇恨的言語就會在網上爆發。或許是受到經濟失調的刺激,又或者是領袖之間不擇手段地互相推諉,狹隘的公共政策與苦澀的政治鬥爭促使國籍、種族與背景不同的人相互懷疑。美國在判定、起訴與懲罰犯罪的時候特別嚴厲,尤其是起訴少數族裔時更是如此。二○一八年的美國是人類史上最多人入獄的國家。
反之,美國對於債務一般採取寬容的政策,尤其是商業上的債務...
判決可能有助於修補破裂的世界。
──吉兒.史塔佛(Jill Stauffer)
這是一個無法寬恕的年代,一個憤慨的年代。這個世界缺乏原諒的理由。每當社會媒體平台允許大眾匿名評論,仇恨的言語就會在網上爆發。或許是受到經濟失調的刺激,又或者是領袖之間不擇手段地互相推諉,狹隘的公共政策與苦澀的政治鬥爭促使國籍、種族與背景不同的人相互懷疑。美國在判定、起訴與懲罰犯罪的時候特別嚴厲,尤其是起訴少數族裔時更是如此。二○一八年的美國是人類史上最多人入獄的國家。
反之,美國對於債務一般採取寬容的政策,尤其是商業上的債務...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前言
寬恕年輕人
寬恕債務
大赦與特赦
反思
謝辭
註釋
寬恕年輕人
寬恕債務
大赦與特赦
反思
謝辭
註釋
|

![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2023全新增修版] 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2023全新增修版]](https://cdn.kingstone.com.tw/book/images/product/20156/2015630770320/2015630770320m.jpg?Q=263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