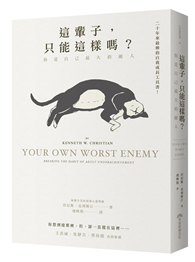圖書名稱:大象死去的河邊
思索南洋華人命運的重要小說
馬共對我而言是文學的實驗場域,甚至可能讓我抵達寫作本身。——黃錦樹
百年前兩頭公象纏鬥同歸於盡之河,惡臭持續,河魚翻肚,草木都枯死。兩張大象皮和四支象牙、象骨,被村大巫師取走當傳家寶,象牙則獻給紅毛鬼佬。兩張厚重象皮,輾轉賣到好萊塢,被剪裁成蝙蝠俠和羅賓的披風了。
〈遲到的青年〉小說開篇即被緊張肅殺的氣息扼住。這個神祕人物能夠遏制時間流動、甚至偷走時間的能力。青年所到之處,鐘表指針大亂,交通工具緩慢,赤道天寒地凍,孩童瞬間變成老人。透過在一切重要歷史節點中遲到的青年,講述了一個在時間中無家可歸的寓言。
國共內戰後,卯(毛)主席敗戰,被送至台灣,與老蔣同在島上。〈再會,福爾摩莎〉帶著喜劇色彩,描繪台灣島上二大獨裁強人之死,以及藏在小說虛實之間的黑色幽默。
大哥留學台灣爾後失蹤,經商的父親重金懸賞尋人;他告誡二戰後留在南洋的前台籍日本兵說,台灣已是共產主義實驗室,有任何不同想法都可能被「整」,或被送去勞改,挖礦、清除從中國海漂來的垃圾……〈似乎是〉裡提著老皮箱返家的青年,跟無人島上的青年會是同一人嗎?
馬來語「革莫」是胖子的意思,綽號叫革莫的人,人生遇見了五個名字都叫建國的人,其中包括一名女同學百合子。〈建國那回事〉描寫革莫叫建國的朋友與同學不同的生命際遇。
〈大象死去的河邊〉描述血月喚醒老婦伊尼的過往,童年的她居住在一個叫「大象死去的河邊」的小鎮。有一天,家中來了三個北方難民,是俄羅斯馬戲團的魔術師,由父親款待,在這場聚會後父親被帶走失蹤復現後,瘋了。長大後的伊尼結婚、工作於圖書館。有一天她收到一本書名《老虎革命潰敗後的山老鼠革命》的書,這本孤本書是否得以解開她的身世與父親失蹤之謎?而,父親真的有參與革命運動?那晚發生了什麼事?
〈匪夷所思〉怡保市郊一間名為「紅毛丹」的精神病院裡的精神病患,以囈語似的瘋言,正確道出當代人類的病徵。
寫作源於絕望,但在絕望中絕處逢生,創作更令人驚豔的小說。
儘管《大象死去的河邊》不全然涉及馬共,但身處於馬來西亞與台灣之間,作家黃錦樹在思索馬共議題的意義上,它留給我們的遺產是什麼――包括可能發生而實際上沒有發生的。
黃錦樹說:此刻過去、現在、未來同時呈現,在思索東南亞華人的命運的同時,很嘲諷的我將在時空中不著痕跡地消失,消失在歷史敘述的邊緣。我的「馬共寫作」本就是個沒有計畫的計畫,而且很可能一開始就在做「收尾的動作」,現在也還在繼續「收尾」……馬共對我而言是文學的實驗場域,甚至可能讓我抵達寫作本身。對實存的馬共和馬華革命文學的信仰者而言,那是不可理解的,個人主義,小資情緒。
作者簡介
黃錦樹
馬來西亞華裔。一九六七年生,一九八六年來台求學,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碩士、清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一九九六年迄今任教於埔里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曾榮獲多項文學獎。
著有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烏暗暝》、《刻背》、《土與火》、《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猶見扶餘》、《魚》、《雨》、《民國的慢船》;散文集《焚燒》、《火笑了》;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謊言或真理的技藝》、《文與魂與體》、《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