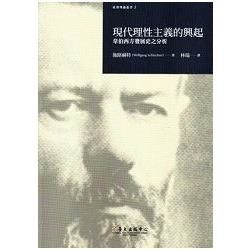韋伯解讀西方社會的發展,得出「理性主義的興起」的主旋律,
對臺灣而言,不僅是理論的啟迪,更具有現實的意義。
韋伯一生的學術研究,志在彰顯西方現代與西方理性主義的獨特性。身為德國新康德主義與歷史主義的後學,又是社會學的開基始祖之一,他以極其繁複的論證,在西方文化內以及跨文化間的比較下,縱橫上下論古今,突顯了西方現代與西方理性主義興起的非預期性結果。
本書作者施路赫特長期擔任《韋伯全集》的主編,他藉由《韋伯全集》的重新編撰、二手文獻的大量湧現,前所未有且全面性地回歸到韋伯作品,對韋伯的學說進行整體化與脈絡化的研究,企圖為「西方現代何以成為西方現代?西方特有的理性主義何以興起?」的複雜議題尋求答案。
作者運用韋伯作品裡提煉出的「發展史」概念,整合了社會學與歷史學、共時性的與貫時性的分析,並將韋伯研究計畫與當代德語世界兩大社會思想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與盧曼(Niklas Luhmann)的學說相提並論,將韋伯對西方現代與西方理性主義的興起之論證,定位為一種兼顧精神與物質的「進化理論的最小限度計畫」。
作者簡介:
沃夫岡.施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
1938年出生於德國的路德維希堡(Ludwigsburg)。1967年畢業於柏林自由大學(Doctor rer.pol.,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1972年在曼海姆大學(Universität Mannheim)取得教授資格(Habilitation),1973年起任教於杜塞爾多夫大學(Universität Düsseldorf),於1976年,與80(1896)年前的韋伯一樣,獲聘於海德堡大學(Universität Heidelberg)任教,從此使海德堡大學成為韋伯研究的重鎮。
施路赫特教授是世界著名的韋伯專家,著有多本有關韋伯的作品,在德語世界的社會學界裡,其聲望僅次於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盧曼(Niklas Luhmann)等人,對於韋伯的社會學理論,以及從古典到當代的社會學理論的分析與探討,有卓著的貢獻。他長期擔任《韋伯全集》的主編,為海德堡科學院院士,也曾擔任德國總統科技顧問教育委員會主席,主導德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多年,現任海德堡大學Marsilius高等研究院院長。
譯者簡介:
林端(1958-2013)
1980年畢業於臺灣大學社會學系,1989年畢業於德國哥廷根大學,並以優異的研究成果,獲得畢業論文獎學金。同年跟隨韋伯專家施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專攻韋伯社會學理論與儒家倫理,1994年獲得海德堡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
林端曾任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兼任教授、北京大學社會理論研究中心副理事長、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理論學報》主編。學術專長為:韋伯社會學理論、法律社會學、宗教社會學、儒家倫理研究、文化社會學、文化人類學。主要著作包括《儒家倫理與法律文化:社會學觀點的探索》(1994,2002增訂版)、Konfuzianische Ethik und Legitimation der Herrschaft im alten China: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vergleichenden Soziologie Max Webers(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7)、《韋伯論中國傳統法律:韋伯比較社會學的批判》(2003),以及論文六十多篇。
作者序
作者序
一本書要在二十年後重新出版,是一件冒險的事。當年這本書所要對應的問題與狀況,已經隨著時代而有所改變,不再是相同的場景,一些在彼時看來至關重要的問題,如今似乎顯得無足輕重了;相關的討論雖然仍繼續發展,但是討論的重點卻已經轉移,連身為作者的我也同樣在改變。
本書最初完成於1978 年。重新出版的版本除了下述小幅度的修改之外,並沒有作太大的變更:雖說採用了一個新的章節大綱,但也只是在某些辭句上作了改善;此外,並將部分排版印刷的錯誤加以校正。不過立基於實質的考量,書名從原來的《西方理性主義的發展:韋伯社會的歷史之分析》,更改為《現代理性主義的興起:韋伯西方發展史之分析》。其中原書名所透露的兩個概念:「發展」與「社會的歷史」,在新的書名裡都被避免掉了,因為這兩個詞彙不但引起誤解,而且也無法清楚地描繪我在此所要強調的特性。接著,我更建立了一個以韋伯為取向的研究計畫,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演變?一方面是從作品史的相關考量作為出發點;另外一方面,則跟韋伯對於「發展」的想法與「進化論」(不管是舊的或新的)之間的區別息息相關。我將在後文有更進一步的說明。
但是修改本書的書名,其實也不是新鮮的事情:早在1981年,這本書出美國版的時候,就已作了一些變更,當時書名訂為《西方理性主義的興起:韋伯的發展史》,至於現在的書名以及章節大綱,則是在1987年的日文版就已經使用了。在這種情形下,我想透過這本德文的新版作品,追溯一下我長久以來的想法。
本書首度嘗試闡明關於韋伯的研究計畫。這項計畫在當時有兩個重點:一是有關韋伯的討論,另外則是有關社會理論的討論。在對韋伯的討論上,其緊繃的範圍,是透過兩個學者的名字彰顯出來的:一是田布魯克(Friedrich H. Tenbruck),另一則是班迪克斯(Reinhard Bendix);而有關「德國的」社會理論的討論,則是藉由盧曼(Niklas Luhmann)與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論辯加以明晰。透過這本書,我嘗試在這兩者之間找出一條道路,把這些學者當成釐清韋伯研究計畫的邊界座標,並從該計畫的獨特性出發。後來我繼續擴大討論的層次,尤其是韋伯與康德的關係。
但本書的目的並非是為了填補這個缺憾。我所要表明的是:這個舊的版本從今日的角度來看,有哪些方面是需要加以擴充的?還有哪一小部分是需要加以改正的?接下來我將分成四個問題組合加以處理:首先是作品史上的,其次是概念策略的,第三是有關發展史的,第四是有關世界史的—比較的問題。
當我撰寫本書時,對於韋伯作品的歷史,還停留在一種初步的印象。但是,我也已經意識到《經濟與社會》以及《宗教社會學論文集》這兩大作品之間存在的互補性,以及由這些作品作為立論基礎建構而成、但仍未臻完備的價值論出發,尤其是有關《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的作品史,透過信件交換,我也建立了一個獲得支持的觀點。如今回顧起來,這是相當正確的,藉此我嘗試與田布魯克作品史的建構過程互相對話。至於有關《經濟與社會》的作品史,我在當時尚未形成同樣的意見,是直到後來的作品裡才逐漸成形。其間,有對這部作品更深入的認識產生,有些集結成冊出版了,有些則無,對此我將作進一步的說明。
在70年代,《經濟與社會》還普遍地被看作是韋伯的主要作品,甚至被當成一本書,裡面包含了兩個(或者多個)部分。而這本書是在他去世前很短的時間,才開始用這個書名加以出版。田布魯克攻擊這種主流的意見,而且對韋伯夫人與溫克曼的編輯策略加以批評,這種批評也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激起了當時的討論。到底《經濟與社會》是否是韋伯的主要作品?而且是否是一本包含兩個(亦或多個)部分被命名的書?正因為這牽涉到韋伯的重要作品之一,事關重大,田布魯克提出一種看法,就理智上來看,我認為這種看法是無法辯駁的。但是在其他一些重要問題上,我在1978年時還沒有獨特的立論基礎從事上述答案的研究工作,這是在後來才形成的。這不只是來自於語言學上的興趣,而且也直接牽涉到我的研究計畫。
當我進一步填補這些漏洞的時候,我確信田布魯克所謂「兩部分的問題」的答案是正確的。但是,他卻從這種深富價值的觀點跳脫,重新提出一些站不住腳的結論。《經濟與社會》的確不是一本書包含兩個(或者多個)部分,而且這個題目也不對,正確的題目應是《經濟與諸社會秩序及權力》。在這個名字之下,藏著隸屬於同一個計畫的兩個版本:比較早的版本是1914年,在這裡一個更早的,或者一些更早的,但是卻不可區分的;另一個是比較晚的、1920年的版本。後一個版本,韋伯自己還將之付印。但這兩種版本其實都不完全,之所以如此,前者咎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後者則歸因於韋伯的突然去世。(下略)
在這一方面,我已提到本書所採行的概念策略的一個面向:一方面太過迅速地把韋伯原來的概念,與《經濟與社會》的編者所做的建構與附加文句兩相等同;另外一方面,將韋伯原來的概念與新的社會學的概念語言兩相等同。針對編者所加上去的標題,根據韋伯的文字習慣,我們的確無法排除一兩個在韋伯的手稿裡面出現過。但更重要的是,我在本書主要致力建構韋伯與當代的概念之間的橋樑:一方面是現代的系統理論,另外一方面則是哈伯瑪斯所重建的歷史唯物論,後者朝向一個溝通行動理論的道路邁進。透過這樣的作法,我非全面性地提出韋伯研究計畫獨立自主性的說法(而且這正是相對於最近的社會理論的立場而言)。
當我撰寫本書的時候,哈伯瑪斯尚未出版他的《溝通行動理論》;而且盧曼尚未轉變到自我再製理論。但是哈伯瑪斯讓我有幸閱讀他的手稿,這也就是後來該書的第一冊。在其中,他很明白地既批判也採納韋伯的行動理論跟理性化理論。對我而言,他的行動理論的學說立場,尤其是在他與下列學說的串連,如皮亞傑與柯伯格(Lawrence Kohlberg)認知理論主義的發展心理學,而且是相當好的結合,將韋伯的理念――利害關心(或譯利益)――模型進一步加以發展(世界圖像發展與意識的發展)。
另外一方面,我也認為派深思與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很適合進一步地發展韋伯的秩序模型與分殊化模型(功能的分殊化)。就好像哈伯瑪斯在他的《溝通行動理論》一書中所做的一般,我從一個立基於行動取向的行動理論學說,以及立基於功能的系統理論學說出發,即使不一定能相互補充,但卻可以相互比較(我現在不再抱持類似的看法)。(下略)
我們現在來談第三個問題範圍。在這書裡,我強調韋伯的學說在某種意義下,是一種進化理論的最小計畫。當時我的嘗試是想要在介於進化理論以及類型學比較的世界史之間,找尋一條第三途徑(這或多或少是個無助的陳述)。當時我彰顯這個「第三條路」,就已經把它當成發展史的考察,但限定在它方法論的地位之下。因此我想再次描述這樣出發的用意,而且澄清一下這「第三條路」。
一個進化理論的特色何在?通常,它會把差異當成缺點來看待。此時差異被看成:從最進步的發展階段岔開出去。因此,一個進化理論必須陳述出一個方向的標準,而此標準可以允許將發展與進步相結合。一種發展卻沒有進步的情況,對進化理論而言,就其字面意義來看,終究是不存在的。
因此,人們可以區分兩種進化理論:第一類是具有強制發展性的,另外一類則是接受意外的狀況。前者發展的步驟是必要的,偶發事件有如干擾者;第二類發展的步驟則是偶發事件的產物,人們可以把這兩類進化理論的基本類型,跟黑格爾與達爾文連接起來。在此,我沒辦法詳細作說明。在最近有關進化理論的重要討論,從這兩個基本類型轉變出來,它們要麼立基在必然性,要麼立基在偶發性之上,但是卻解釋由此創造出來的發展步驟,且把它當成進步來看待。在此意義下,他們提出來的是階段的模型。(下略)
藉此,我已經討論到最後一個問題範圍,亦即世界史的、比較的觀點,而這必須要跟發展史的觀點連接起來看待。前者(世界史的—比較的觀點)在本書中只有部分的討論,這樣的缺失,我在80年代嘗試加以改進。其中包括有關討論韋伯對世界諸宗教的比較研究的書,韋伯當年有的已經寫出來,有的並沒有來得及完成。我透過這六本書而得的認識成果,收在《宗教與生活方式》的第二冊裡。此外,也有一個有關西方獨特性發展的完整陳述,那是對本書的細部的補充,而且在某些地方也加以改正。
當我們看到韋伯在他的《宗教論文集》,以及《經濟及諸社會秩序與權力》比較早的版本裡有關宗教社會學手稿的計畫時,我們會馬上明白,他的世界史的宗教比較,把重點擺在特勒爾齊所謂的文化宗教上。除此之外,他也把儒教當成一個精神整體文化的另一個承擔者,附加上去。正因為這樣,使他陷入了一些困境。我想在此作一個簡短的、階段性的考察,然後再回到發展史的面向來。
由軸心時代產生的理性主義,具有很多不同的承擔者,這種理性主義是一種以超驗為基礎的理性主義,主要是宗教的理性主義,因此有不同抉擇的理性主義形式出現:包括逃避現世的、克服現世的、支配現世的、適應現世的,還有對現世冷淡的理性主義。在此意義下,本書所刻劃的是一種比較柔軟的階段,而且具有不同抉擇的可能性。在這樣的情形下,也表明了西方特殊的發展,亦即西方宗教史上的特殊發展。這種宗教的核心在這些不同的抉擇裡,特別凸顯出一種可能性,亦即支配現世的宗教理性主義。它也形成一種文化的根源,藉此根源,現代的理性主義產生出來。因此,它具有文化的、制度的與心態的成分,這些不同成分,在本書中,被仔細地處理出來:支配現世的世俗的理性主義、現代的機構國家以及現代的資本主義,還有入世取向的職業禁欲主義的生活方式等等。將這些特徵聚攏起來,很確切地形成一個豐富意涵的「現代」概念。在此也給人一個印象,彷彿有別於軸心時代文化宗教的多元主義,在此只存在一種現代。
為了糾正本書分析所可能帶來的這種(錯誤)印象,我們應該把第一個軸心時代,主要是一種宗教式的,與第二個軸心時代,主要是一種世俗式的,兩者區別開來,然後應用在此發展出來的比較柔軟的階段概念。因此,西方的特殊發展,在前面提到特勒爾齊的意義之下,是具有普遍的意義以及有效性的,因為第二個軸心時代是以現代理性主義的興起為其濫觴。在此,並不是價值論的超驗基礎會減少,而是其原有的宗教基礎會減少。現代的理性主義,在西方的發展,文化上表現在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制度上表現在教皇國的、封建的、城市的以及科學的革命預作準備的,而且一開始就體現了不同抉擇的可能性。這不僅對歐洲有效,而且特別對歐洲與美洲的比較有效;北美洲甚至其他的美洲部分,一開始就不是歐洲的一個附屬品。它們一開始就把現代的理性主義,或者更普遍地說「現代的計畫」加以轉化,同時加以多元化,因此現代一開始就不只是反思性的,同時也是多元性的。就像諸文化宗教一般,它們也一樣不斷有創新出現。正如第一次軸心時代的文化,是跟前軸心時代的文化相關的,例如儒教與佛教跟日本的文化,或者伊斯蘭教跟許多非洲的文化相關一樣,第二次軸心時代的文化,也跟第一次軸心時代的文化息息相關。在這裡跟現代理性主義所達到的發展水準息息相關的不同抉擇,亦即一個支配現世的世俗理性主義及其制度上與心態上的相關因素,亦即理性的機構國家、理性的資本主義,以及入世的職業禁欲的生活方式等等,當時我在這本書中,強調得還不夠清楚。
在此意義下,本書過去是,現在也是,而且的的確確只是一個開始,這個開始,跟一段前期的歷史相關,這在其他兩本書中《官僚制支配的諸面向》以及另一本論文集《支配現世的理性主義》裡可以看到。這也跟一個比較長的後期歷史息息相關,這後期的歷史還在持續中,迄今集結在《宗教與生活方式》、《無法調和的現代》兩本書中。因此,就像我前面說過的,這本書的開始是需要補充與修正的。儘管如此,本書的開始,對我來說,仍然有著相當具體的意義,我希望且盼望對今天的讀者來說,一樣具有這個具體的意義。
作者序
一本書要在二十年後重新出版,是一件冒險的事。當年這本書所要對應的問題與狀況,已經隨著時代而有所改變,不再是相同的場景,一些在彼時看來至關重要的問題,如今似乎顯得無足輕重了;相關的討論雖然仍繼續發展,但是討論的重點卻已經轉移,連身為作者的我也同樣在改變。
本書最初完成於1978 年。重新出版的版本除了下述小幅度的修改之外,並沒有作太大的變更:雖說採用了一個新的章節大綱,但也只是在某些辭句上作了改善;此外,並將部分排版印刷的錯誤加以校正。不過立基於實質的考量,書名從原來的《西方理性主義的發展:韋伯...
目錄
韋伯著作縮寫對照
作者序
前言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韋伯世界史的問題
第一節 西方資本主義的特殊現象
第二節 第二節 西方理性主義的特殊現象
第三章 西方發展史意義下的韋伯社會學之哲學背景
第一節 與新康德學派價值論的關係
第二節 以價值衝突論為內容的價值論
第四章 西方發展史意義下的韋伯社會學之實質內容
第一節 諸基本假設與諸基本概念
一、價值領域與生活秩序(制度範疇)
二、社會關係的層次與面向
第二節 社會的諸結構原則
一、社會的諸結構原則的倫理成分
二、社會的結構原則的制度成分
第五章 法律的類型與支配的類型
第一節 諸基本假設與諸基本概念
第二節 法律社會學
一、法律的類型
二、法律在形式上的結構原則
三、法律在實質上的結構原則
四、法律實質領域的分殊化
五、倫理與法律的關係
第三節 支配社會學
一、傳統的支配:忠誠原則與個人關係化
二、理性的支配:合法性原則與即物化
三、傳統的支配與理性的支配之間的比較
四、卡理斯瑪的支配:介於個人關係化與即物化之間的使命原則
五、支配社會學的系統化
第四節 支配的類型論與行動的類型論
第五節 西方發展史意義下的韋伯社會學的實質內容之結論
第六章 歷史的解釋問題:過渡到現代時宗教改革扮演的角色
第一節 宗教社會學方法論的諸面向
第二節 禁欲的基督新教研究中對過渡之分析
第三節 宗教與經濟之關係的比較研究中對過渡之分析
第四節 基督教的文化意義:世界諸宗教的一個比較
第五節 禁欲的基督新教的文化意義:宗教改革期各救贖宗教的潮流之比較
第七章 結論
參考文獻
人名德中對照索引
事項索引
譯者跋
韋伯著作縮寫對照
作者序
前言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韋伯世界史的問題
第一節 西方資本主義的特殊現象
第二節 第二節 西方理性主義的特殊現象
第三章 西方發展史意義下的韋伯社會學之哲學背景
第一節 與新康德學派價值論的關係
第二節 以價值衝突論為內容的價值論
第四章 西方發展史意義下的韋伯社會學之實質內容
第一節 諸基本假設與諸基本概念
一、價值領域與生活秩序(制度範疇)
二、社會關係的層次與面向
第二節 社會的諸結構原則
一、社會的諸結構原則的倫理成分
二、社會的結構原則的制度成分
第五章 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