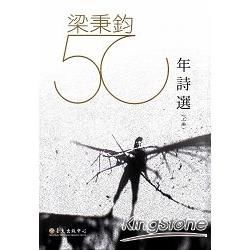代序
語言與風格的自覺――也斯(梁秉鈞)【摘錄】
我在七○年代初在香港先認識也斯(梁秉鈞)而成為好友,談了不少現代詩的種種問題。一九七二年,他(當時用梁新怡筆名)、覃權與小克訪問我,訪問稿發表在他編的《文林》(一九七三年九月),同一期,他選登了我翻譯的王維 Hiding the Universe: Poems of Wang Wei (Wushinshe, Tokyo -Grossman, New York, 1972) 中英對照十首詩。對我此前的作品、理論、道家美學和舊詩裏的靈活語法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這次對話不久,我勸他攻讀博士,隨後他到了聖地牙哥我任教的加州大學攻讀研究,有一段師生互動的交流,雖然我是老師,他在我心中一直是詩的伙伴。大抵因為我的詩最早成形於香港,我們有相同的背景,關心相同的問題,對三、四○年代的重要的、在文字藝術用功的詩人,在當時大陸的政治一言堂和臺灣以左傾為由的鎮壓下的消聲寂滅非常關心。他和我都曾利用香港這些書籍資料的健在,設法重建這個聯結,所以談得很開心,事實上,我、慈美和也斯、他太太吳煦斌的認識,是我們生命裏難得的機會,是非常寶貴的時段,生活在一起,聊天,出遊。也斯曾經寫過兩首詩,其一是〈大馬鎮的頌詩〉,大馬鎮,就是我們住的地方 Del Mar,原是「海緣」的意思,但該鎮夏天是出名的跑馬場,故音譯為大馬鎮,該詩裏有不少我們同遊看風景、因五葉松起興的懷鄉、在海邊抓小魚和論詩論藝術的痕跡;另外一首是〈樂海崖的月亮〉,「樂海崖」是我音譯大學所在地的 La Jolla(像 Del Mar 一樣,都是西班牙語,La Jolla 是珠寶、寶石的意思,讀音是 la hoiya),其海灣公園極為美麗,萬年海浪的拍岸,沖擊成沿岸奇岩怪洞,是遊人如鯽的勝地,故音譯為「樂海崖」。如果我沒有記錯,他到了不久是中秋,曾在那裏烤肉賞月。
我們師生如兄弟,時時為現代中國文化嘔心,他希望為現代中國文化找出一點曙光,他的論文 Aesthetics of Opposition: A Study of the Moderni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Poets, 1936-1949 是最重要的里程碑,因而在我一九九二年出版的英譯三、四○年代詩選 Lyrics from Shelters: Modern Chinese Poetry, 1930-1950 (Garland Publishing, New York) 時,我毫不遲疑地把該論文裏的一章, “Literary Modernity in Chinese Poetry” 作為我新書的第三篇序。但我更喜歡他的詩,或者應該說詩和散文互為推展下為香港披沙揀金地,帶著最純粹的未被污染的喜悅的心,呈現中國文化裏抒情式的堅韌的力量。我深信,他誠摯不被框限的文心,將是香港的典範,也是不同文化碰撞中蛻變的中國必須追隨的典範。
(也斯)他不但具有我說的語言的自覺――包括完全擺脫陳腔濫調的素樸洗煉和對「風格歷史」的兩種自覺,而且在事件呈現和語調存真上提供了變化多端的語言策略。尤有甚者,他承接了大陸三、四○年代到臺灣六○年代對語言刻骨鏤心的訴求、對結構精嚴的遵從,作了建設性的揚棄,而獲致一種相當灑脫、靈活的突破。這個突破不但包括了對現代主義本身在其求開放的過程中不自覺地落入封閉形式的挑戰,還包括把被霸權(或宰制)表達形式所壓制或邊緣化的經驗層面重新納入他詩的運作裏,把人生的瑣碎萬狀――尤其是不易納入所謂「純詩」的事物事件――給予它們一種平等而莊嚴的存現。為此,他在散文與詩的語言間摸索出一種敘述的抒情形式,在散漫與嚴謹中找出一個自由收放的運作空間,或者我應該更正確的說,在來回於散漫(指的是漫步式、遊目式,非散漫無章也)和嚴謹之間嘗試多種收放的呈現事物的方式。在許多方面,和臺灣現代主義後起的詩的運動同步地通某種重要的消息。
也斯的詩語氣自然、乾淨利落、沒有陳腔濫情的傾瀉是顯而易見的。他的聲音,不管傷愁不管騰躍的歡快(他是極其敏感的人,自然地也會有喜悅和愁苦),都是如壩上的水很緩慢的溢出,或如一種平靜中微微的顫抖,或如靜夜中火光一閃,讓我們觸然一覺而開始探入思索。在這裏,我想從他的突破談起。
現代主義出現的初期,是以突破傳統思想和語言的宰制來重新喚起被物化、被規則化社會壓制下去或消減化滅的生命世界的層面,開始時是開放性的,在形式上,在思想上,對傳統的讀者都有「駭人處」的創新。但物化、規則化社會發展中,在工具理性至上的推動下,語言的藝術性、語言的靈性層面受到最大的戕害(亦即是語言被看成只是一種工具,其靈性持護的角色則被輕視至忽略),所以在開放的同時又進行語言藝術的營造,也是語言自覺最尖銳的時期,企圖以此重現已失去的靈性。由於營造,便又在打破了傳統的結構和表意行為之後,另求新的結構,如利用「原始類型」、神話、曲喻、反諷等等。同時為了追求靈性的重建而又偏向於「純詩」,把其他的所謂「不純」的經驗(包括日常的所謂瑣碎的經驗)摒諸門外,而無意中又回復到「超越」(如「理體」、「神」)的追求。中國的現代主義者,由三、四○年代到六○年代,雖然不會迷失於「超越」的追索(中國傳統美學中這種取向不顯),但在結構上有時也變得極其複雜詭奇,到了成為私有象徵的地步。
現代主義後起思想,覺得這與原有的開放性相違,而且對於其中的排他性很有意見。在詩歌上,在一般藝術上,便開始再從新的封閉走向新的開放,從「崇高純粹」走向日常事物事件。在形式上,由濃縮緊扣走向放鬆自由,把過去很少寫的題材,包括偶發性的題材,加以美學的凝注,給它們莊嚴的凝視。關於這一點,也斯在他的詩與駱笑平的畫合展(一九八五年五月四─廿九日)的《游詩》後記裏有美學心跡的表白:
《游詩》這名字最先曾用在一九七四年一組寫廣州和肇慶的詩前面,那其實不是狹義的旅遊詩,因為所見的已經令人沒有心情遊山玩水,所以想透過城市和山水去寫一些永遠牽連人的問題,或者像卞之琳譯奧頓詩那樣說,希望「叫有山、有水、有房子的地方也可以有人。」那一組詩,無疑是第一次離開了熟悉的生活環境,強烈地感覺到另外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寫的。
這以後也有好幾次或長或短的離開原來的環境和熟悉的生活方式。其中最長的一次是一九七八至八四年在加州聖地牙哥。一個人置身陌生的文化之中,自然會忍不住對時間和空間的敏感,對文化和言語反省,對事事物物比較異同,一方面尖銳地感覺差距,一方面尋求是否有共通的規律。
廣義的旅遊文學往往有放逐的哀愁也有發現的喜悅……表現在詩裏通常有兩種模式: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象徵的詩學,詩人所感已經整理為一獨立自存的內心世界,對外在世界的所遇因而覺得不重要,有什麼也只是割截扭拗作為投射內心世界的象徵符號;一種我們可稱之為發現的詩學,即詩人並不強調把內心意識籠罩在萬物上,而是走入萬物,觀看感受所遇的一切,發現它們的道理。我自己比較接近後面的一種態度。
葉維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