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中國社會史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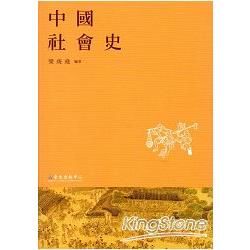 |
中國社會史 作者:梁庚堯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4-10-27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40 |
二手中文書 |
$ 395 |
中文書 |
$ 395 |
教育學習 |
電子書 |
$ 395 |
中國史地 |
$ 395 |
中國歷史 |
$ 395 |
社會學 |
$ 395 |
Others |
$ 450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社會史
本書內容兼顧各時代的社會特色與貫穿時序的整體脈絡,為深具敘事特色的中國社會史教科書。
本書起始於新石器時代華北、華南農業村落的興起,結束於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以社會組織與社會結構為重心,討論中國歷史上相關的重要問題,以明瞭其延續與變遷。
探討的問題諸如:農業村落的興起與土地制度、租佃制度的演進;封建社會、門第社會、科舉社會出現的時代背景,及士人、士族、士紳的社會角色;古代氏族與國家形成的關係和家族制度的變化;城市性質的演變與工商業的盛衰、復振;人口的變動及其對社會中心轉移的影響;漢末道教在傳統社會中的根源;中古到近世佛教社會力量的發展、限制;近世民間祕密宗教的活躍與其對社會的影響;宗教、家族、政府、士人、商人對推動社會福利與互助的貢獻;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在西方政治、經濟、文化影響下的劇變。
本書課題之選取,分歷史階段看,可得各時代的社會特色;合而觀之,則能掌握中國社會史的整體脈絡,有助於對傳統社會進行深層的思考,是為理解中國社會發展軌跡的入門書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