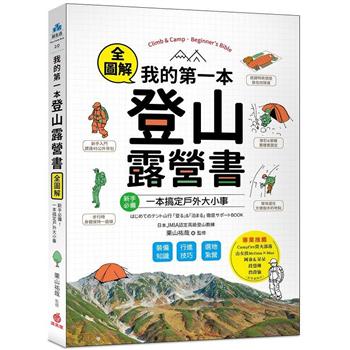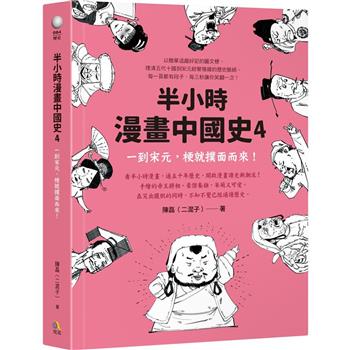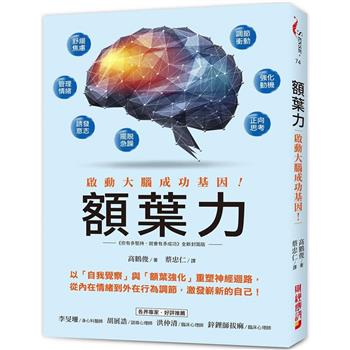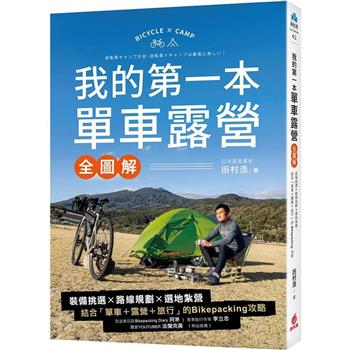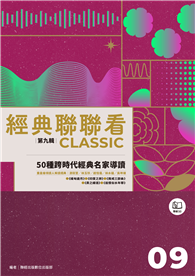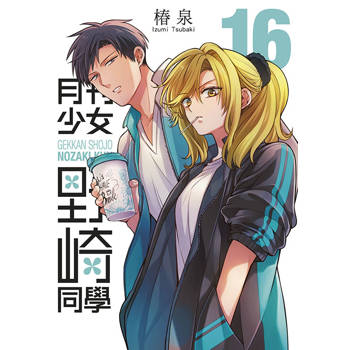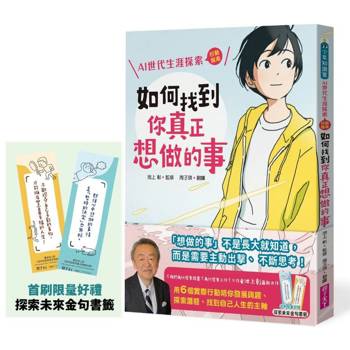〈桃花源記〉甚解(摘錄)
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已經是沉澱在民族潛意識裡的樂園象徵,逃避濁世暴政的洞天福地。歷來討論的大多是從避世的消極意義去理解,無論認為桃源是實有其地,或是純出於想像,都會欣賞它能讓人隱遁其中的造境;尤其是傾向於重視陶淵明道家思想的人,很容易跟陶淵明之為「隱逸詩人」聯想在一起。「隱逸」自然是遠離世間,不涉及現實問題。不過,近代開始有人從西方「烏托邦」的觀念來理解。如果視為「烏托邦」,在本質上雖然也是虛構,卻增添了積極的意義,就不完全是不涉及現實的想像。「桃花源」是神仙性質的樂園,還是「烏托邦」式的理想?是本文有興趣來討論的。
一、
〈桃花源記〉(以下或簡稱〈記〉)已經是膾炙人口,眾所熟知,不煩再引出全文;不過,〈記〉後所附的詩,一般或不注意,而兩者應該合看,才能有比較完整的理解,所以先錄於下: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跡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
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
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
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
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
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
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清風,高舉尋吾契。
這首詩(以下簡稱〈詩〉)中所表達的其實比〈記〉更直接,把故事性的外衣也脫掉了,因此不像〈記〉那麼生動有趣。然而作者的意旨則比較清楚,也補充了〈記〉中沒說出的話。歷來詮釋〈記〉和〈詩〉旨的大都以「避秦」為說,因為這在詩文中說得很清楚;但是,進一步的解釋就不一致了。歸納《陶淵明卷》中搜集到的資料,約略可有以下的說法:
(一)把桃源當成仙境
先是唐代的王維,在他的〈桃源行〉中說:「初為避地去人間,更聞成仙遂不還。」末云:「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後來韓愈和劉禹錫的詩裡也同樣的以為是「神仙」或「仙家」。這可能是出於對〈詩〉中「神界」的解讀,也可能只是更浪漫的想像。不過,〈詩〉中的「神界」恐怕只是形容語,並不是陶淵明真以為桃源是神人所居。〈記〉中也只說「絕境」,不說是仙境。無論〈記〉或〈詩〉中都只是寫現實生活中事,完全沒有辟穀、飛昇之類的嚮往。所以蘇東坡駁斥說:「殺雞作食,豈有神仙而殺者乎?」漁人所見的那些人,只是避秦亂來之人的後世子孫,決不是秦人不死的神仙;後來大多贊成東坡的意見。其實韓愈已經認為世俗「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由於那是他為人畫桃源圖的題畫詩,只能含糊其辭而已。即使有人當作仙境來描繪,也不過是好奇騁才之作,並不必真相信其有。然而這卻模糊了陶淵明寫作的意旨和焦點。
(二)以桃源是實境
自唐宋以降,大多認為桃源實有其地,而且相信就是現在湖南桃源縣境內。只有蘇東坡認為它就像「蜀青城山老人村」一樣(道極險遠,……溪水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嘗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但這只是不認為桃源是仙境,並未否認武陵或桃源縣境內亦有其處的可能性。陳寅恪因此廣蒐史籍,作〈桃花源記旁證〉。以為真實之桃花源是在北方之弘農,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這新奇的說法是他從《水經注》壹伍〈洛水〉找到劉裕西征時參軍戴延之至檀山,「其山四絕弧峙,上有塢聚。」陶淵明或聽說戴的聞見,「〈桃花源記〉之作即取材於此」。這雖然不無可能,但是陶淵明也可能是聽到別的傳聞(見下)。同時,陳說為了符合他鉤索出的史料,認為所避之秦是指苻堅之苻秦而言,「與始皇、胡亥之嬴秦絕無關涉」。這就得把〈記〉「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看成是「點綴」之語、或「寓意特加之筆」,如此,〈詩〉的「嬴氏亂天紀」也要解釋成影射性的語句,這實在是過為迂迴的詮釋。至於陶淵明是否因感「苻秦」虐政而興起作〈記〉之意,也沒有必然的證據。陳說的考徵新異有趣,卻難其必信。陳說強調他是「止就紀實立說,凡關於寓意者,概不涉及」,這恐怕是問題所在。〈記〉的可貴全在寓意,是否紀實並非重點。設想之境(紀實)本為寓意,歧為兩端,就像查案不問動機,必難周延。其實指秦為「苻秦」,已涉其寓意,只是為遷就史料中的「紀實」才推出的寓意而已。
(三)非仙境也非實有其地
桃源所在因〈記〉形成一個傳統,雖多以為就是現在的桃源縣境,但並非執泥於此實地。清代的邱嘉穗就說:「設想甚奇,直於污濁世界中另闢一天地,使人神遊於黃、農之代。公蓋厭塵網而慕淳風,故嘗自命為無懷、葛天之民,而此記即其寄託之意。如必求其人與地之所在而實之,則鑿矣。」這種說法就比蘇東坡更通達了。事實上,一般讀者也並不介意是否實有其地的問題。
不過,桃源雖然不必實有其人,或實有其地,這種「設想」卻可能是陶淵明聽到一些傳聞,再經過想像才構思成的。相傳是陶淵明著的《搜神後記》卷一,載「桃花源」一則之前後,就有四則類似的傳聞:
1.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一人誤墜穴中,……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
2. 會稽剡縣民袁項、根碩二人獵,經深山重嶺甚多。見一群山羊六七頭,逐之。經一石橋,甚狹而峻。羊去,根等亦隨,渡向絕崖。羊徑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既入內,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
3. 滎陽人姓何,……隱遁養志。常至田舍,人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丈餘,蕭疏單衣,角巾,來詣之。翩翩舉其兩手,並舞而來。語何云「君曾見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尋逐徑向一山,山有穴,纔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隨之入。初甚急,前輒閒曠,便失人。見有良田數十頃,何遂墾作,以為世業,子孫至今賴之。
4. 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見岸下土穴中……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間。
這些記述裡都是與世隔絕之境,經過隱密的洞穴才被發現,跟〈記〉中「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完全相同。通過後所見「平敞」、「閒曠」、「土地曠空」、「開明朗然」也大都類似。這些「傳聞」中的時、地、人,恐怕多是虛構的。〈記〉被記下來的時候,自然又經過想像和潤色。〈記〉的傳聞也一定被改寫過,《搜神後記》中的〈桃花源〉原只有「太守劉歆」之名,〈記〉中則刪去太守的名字,而增加了「南陽劉子驥」事。而今本《搜神後記》中〈桃花源〉一則之後,載有一則云:
南陽劉驎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欲還
失道。遇伐薪人,問徑,僅得還家。……欲更尋索,不復知處矣。
〈記〉的「定稿」顯然是移花接木,增入劉子驥事。可能是因為劉子驥「好遊山水」為人熟知,借來增強其真實性;也可能借以暗示自己之「高舉尋吾契」。而太守非如劉子驥「高尚士也」,故〈記〉中遂隱其名。因此,〈記〉的「傳聞」更極可能在陶淵明的「寓意」下被改動過,或者這本就是陶淵明的想像之作,如還要實指其事、其地,則不免膠柱鼓瑟。如果說〈記〉的構想是受到《搜神後記》中幾則傳聞的啟發,倒是自然的事。在魏晉亂世,這種傳聞應該還有許多。不過,上面引的前三則都有神仙異聞之意,而〈記〉顯然大異其趣,這必然跟作者的寫作意圖有關。
二、
如果把〈記〉跟〈詩〉合看,作者的寫作用意就比較清楚。所謂「厭塵網而慕淳風」固然可以是概括的說明,卻過於簡略。如細加尋繹,就會發現其「文本」會容許不同的歧義。
如〈記〉所云:「先世避秦時亂」「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詩〉亦云:「嬴氏亂天紀,」進一步的解釋就不一致。宋洪邁《容齋隨筆》據《宋書.陶淵明傳》和五臣注《文選》說他在劉裕篡晉之後,恥事二姓,所著文章,不書年號,惟云甲子。所以說:「予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為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於劉裕,託之於秦,借以為喻耳。」 這是以「嬴秦」喻劉裕。陳寅恪則以為秦指「苻秦」,「無論魏晉」只是「點綴語」。所喻不同,進一步的解釋就會有差異。實際上,「嬴秦」可喻任何暴亂的濁世,不必是苻秦,也不必是劉裕;歷史上幾乎每一個朝代都是專橫的統治者。王安石的〈桃源行〉詩說得最好:
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時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
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為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
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因相問。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為晉。
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沾巾。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
這並不是說超出歷史或時間之外,而是厭棄這些歷朝的虐政,希望走出「幾秦」的惡性循環。「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在語意上亦可暗示這些朝代都不足道,不僅是不知而已。王安石實在是個大政治家,所以能從這一角度去解讀,指出陶淵明嚮慕的是舜淳樸之世,〈記〉和〈詩〉的寓意就很明顯。比較蘇軾和陶此詩:「凡聖無異居,清濁共此世。心閑偶自見,念起忽已逝。欲知真一處,要使六用廢。桃源信不遠,杖藜可小憩……」雖然亦有深趣,卻完全從個人著眼,不如王詩宏大,能表出淵明心事。
又如〈詩〉中有「奇蹤隱五百」之句,也有異說。韓愈〈桃源圖詩〉作「六百年」。洪邁由秦算起,到太元十二年,乃及六百年。有人據以認為「六百載為近實」。有人把「太元」改為「太康」以求符合年數。其實陶淵明不可能精確的去計算,如「五百」不是傳寫之誤,他可能另有寓意。清鄭文焯就說:「此蓋隱寓五百年王者興之慨,何事苦算歲紀,以辯太元、太康元號耶?」近人古直也有相同的看法。如果〈記〉和〈詩〉本來是寄託作者的政治理想,因而聯想到孟子的說辭,有意借用,應該是合理的推想。
把〈記〉和〈詩〉的意旨說得最切要的還是王安石詩裡的一句「雖有父子無君臣」。這是從〈記〉的「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和〈詩〉「秋熟靡王稅」等句總結出來的。〈記〉和〈詩〉原是構想一個不需要完糧納稅的「無君臣」的社會。王安石一句點明出來,將退避逃隱的意思轉換成積極的政治理念。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思文論集: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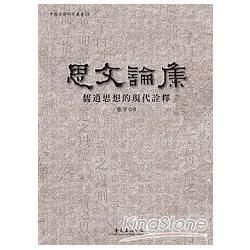 |
思文論集: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中國文學研叢書08【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出版日期:2014-11-01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10 |
Others |
二手書 |
$ 355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395 |
教育學習 |
$ 395 |
哲學 |
$ 440 |
中文書 |
$ 440 |
中國哲學 |
$ 450 |
社會人文 |
$ 475 |
教育學習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思文論集: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
本書從具體的、個別的問題為起始點,出入於文史經典之間;
在上友古人的筆端,投注現代人的情感與關懷。
本書選輯了十七篇論文,是作者張亨教授長期讀書和思考的累積。諸篇各自獨立,互不相屬,亦非一時之作,探討的問題雖然分散,但有以下三個基調:(一)大多試從具體的、個別的問題出發,思考其蘊涵的根源性的或思想史的意義。(二)儘可能依據原典或文本作直接的詮釋。(三)這些詮釋是在一個現代人的存在情境之下、無可解免的前理解中進行的。這必然會有個人理解上的限制,卻也寓寄自我傾注的關懷。
本書用思想史的研究方式,對選擇的論題作追根究柢、溯其淵源的了解。多篇是從較可信的文本中的一兩句話追問起,由微而顯,以期增加理解的深度,而不像一般哲學史或觀念史作周延的概括性的論述。
本書討論較多的是儒家思想,道家的比較少。多篇是從較可信的文本中的一兩句話追問起,由微而顯,以期增加理解的深度,並期使文本脫離異化,而不陷入論辯的泥沼。作者藉助於現代詮釋的觀念,探索所謂文本裡沒有說出的意義。〈說道家〉與〈說儒家〉兩篇尤多用之。另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討論道家時對於神話的重視,焦點放在莊子、老子如何運用神話;或者他們採取了神話中的那些意義而加以轉化。
作者簡介:
張亨
1931年生於山東泰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及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曾任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傅爾布萊特訪問教授。現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名譽教授。
章節試閱
〈桃花源記〉甚解(摘錄)
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已經是沉澱在民族潛意識裡的樂園象徵,逃避濁世暴政的洞天福地。歷來討論的大多是從避世的消極意義去理解,無論認為桃源是實有其地,或是純出於想像,都會欣賞它能讓人隱遁其中的造境;尤其是傾向於重視陶淵明道家思想的人,很容易跟陶淵明之為「隱逸詩人」聯想在一起。「隱逸」自然是遠離世間,不涉及現實問題。不過,近代開始有人從西方「烏托邦」的觀念來理解。如果視為「烏托邦」,在本質上雖然也是虛構,卻增添了積極的意義,就不完全是不涉及現實的想像。「桃花源」是神仙性質的樂園...
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已經是沉澱在民族潛意識裡的樂園象徵,逃避濁世暴政的洞天福地。歷來討論的大多是從避世的消極意義去理解,無論認為桃源是實有其地,或是純出於想像,都會欣賞它能讓人隱遁其中的造境;尤其是傾向於重視陶淵明道家思想的人,很容易跟陶淵明之為「隱逸詩人」聯想在一起。「隱逸」自然是遠離世間,不涉及現實問題。不過,近代開始有人從西方「烏托邦」的觀念來理解。如果視為「烏托邦」,在本質上雖然也是虛構,卻增添了積極的意義,就不完全是不涉及現實的想像。「桃花源」是神仙性質的樂園...
»看全部
作者序
本書選輯了十七篇論文。前十一篇曾以《思文之際論集》之名由允晨文化出版,今復增益六篇,簡化書名為《思文論集》。
這些論文是長期讀書和思考的累積,不像一般專書有完整的系統。諸篇各自獨立,先後次序也僅依寫成的年代,未加類別。因此若只看篇名,顯得雜亂無章。不過,在《思文之際論集》的〈序〉中曾說:
這些論文探討的問題雖然分散,但有三個基調可說:(一)大多試從具體的、個別的問題出發,思考其蘊涵的根源性的或思想史的意義。(二)儘可能依據原典或文本作直接的詮釋。(三)這些詮釋是在一個現代人的存在情境之下、無可解...
這些論文是長期讀書和思考的累積,不像一般專書有完整的系統。諸篇各自獨立,先後次序也僅依寫成的年代,未加類別。因此若只看篇名,顯得雜亂無章。不過,在《思文之際論集》的〈序〉中曾說:
這些論文探討的問題雖然分散,但有三個基調可說:(一)大多試從具體的、個別的問題出發,思考其蘊涵的根源性的或思想史的意義。(二)儘可能依據原典或文本作直接的詮釋。(三)這些詮釋是在一個現代人的存在情境之下、無可解...
»看全部
目錄
序
一、先秦思想中兩種對語言的省察
二、陸機論文學的創作過程
三、《論語》論詩
四、莊子哲學與神話思想──道家思想溯源
五、荀子的禮法思想試論
六、張載「太虛即氣」疏釋
七、「天人合一」的原始及其轉化
八、朱子的志業──建立道統意義之探討
九、試從黃宗羲的思想詮釋其文學視界
十、〈定性書〉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
十一、《論語》中的一首詩
十二、《莊子》中「化」的幾重涵義
十三、〈桃花源記〉甚解
十四、從「知之濠上」到「無心外之物」──戴靜山先生〈魚樂解〉述義
十五、《詩.桃夭》甚解
十六、說道家...
一、先秦思想中兩種對語言的省察
二、陸機論文學的創作過程
三、《論語》論詩
四、莊子哲學與神話思想──道家思想溯源
五、荀子的禮法思想試論
六、張載「太虛即氣」疏釋
七、「天人合一」的原始及其轉化
八、朱子的志業──建立道統意義之探討
九、試從黃宗羲的思想詮釋其文學視界
十、〈定性書〉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
十一、《論語》中的一首詩
十二、《莊子》中「化」的幾重涵義
十三、〈桃花源記〉甚解
十四、從「知之濠上」到「無心外之物」──戴靜山先生〈魚樂解〉述義
十五、《詩.桃夭》甚解
十六、說道家...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張亨
- 出版社: 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4-12-22 ISBN/ISSN:978986350044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中國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