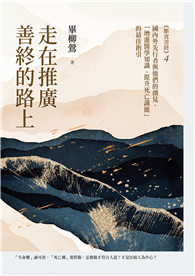序章 課題與方法――近代民族主義、「青年」與地域社會(摘錄)
本書是以臺灣近代「青年」的政治社會史為研究焦點,藉以闡明日治時期教化政策與殖民地社會變遷之間的相互關係。本書除序章和結論外共分成六章,第一章到第四章主要著眼於殖民政府「青年」教化政策的起源、意圖及半世紀當中演變的過程;第五章和第六章則以臺中州草屯地域社會的「青年像」為具體事例,探討殖民政府「青年」教化政策與地域社會變遷的相關性。
因此,本書首先將從目前為止通常被限定在師範教育脈絡中討論的「國語學校」入手,藉由「青年」概念的導入來重新檢視其定位,並試圖闡明長達半世紀以來,該校畢業生在殖民統治政策與殖民地社會變遷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換言之,從1896到1919年(1922年送出最後的畢業生),走過四分之一世紀歲月的國語學校,在日本殖民臺灣統治史上,不單單只是個教育機關,在近代化人才培育上,更是殖民地教育、教化的中樞。這與稍後設立專門以培育專業人士(醫師)的醫學校不同,國語學校一開始便定位為培養初等教育機關教員、實業家,以及地方行政低階官僚等,從事殖民地經營的綜合性人才培育機關。
如上所述,1919年以後,該校部分的畢業生轉身成為「臺灣青年」,並以殖民地宗主國首都為舞臺,反過來倡議要求臺灣人自治並嚴厲批評殖民政府的專制統治;然而大多數的畢業生,一直到日本戰敗為止始終留在地域社會中,作為殖民統治體制地方行政末端的協力者,從事於殖民地社會教育和社會教化的任務。而且這些人由於長期任教於初等教育機構,更是直接影響著下一代――即所謂「戰爭期世代」,扮演著重要的「政策仲介者」角色。
在上述既有的研究成果上,本書將以嶄新的視野搭配新出土的第一手史料和相關文獻,希望能解決先行研究所留下的難題及上述所設定的課題,進而對臺灣近代史和日本殖民地主義研究有所貢獻。因此雖覺冗長,接下來筆者在此希望將本書所欲探究和闡明的課題,進一步論述如下。
(一)近代化的孿生子――民族主義和「青年」
殖民地近代民族主義和「青年」之間到底有何種特殊性?班納迪克.安德森在其著名的近代民族主義論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中,對於近代民族主義和「青年」的關聯,有如下的陳述:
所以在殖民地,當我們說「青年」,我們所指的――至少在最初――是「受過教育的青年」(Schooled Youth)。這又再次提醒我們,殖民地的學校體系在促成殖民地民族主義興起中扮演了獨特的角色。
殖民地主義生下的孿生子――民族主義和「青年」――的關係,若就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而論,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為首的殖民地近代學校體系,即是扮演著培育日本帝國「官方民族主義」的「殖民地青年」之重要任務。雖然一直要等到1920年前後,才出現由「臺灣青年」所掀起的民間版臺灣人民族主義思潮;但是,很明確的共通點是,他們都是受過殖民地近代學校教育的「青年」,並擁有「雙語讀寫能力」。
殖民地「臺灣青年」運用「雙語讀寫能力」,而成為學習以歐美諸國為開端於世界各國所展開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將「國民」概念以及「國民國家」概念,移植到當地(即殖民地)的媒合者。換言之,民族主義和「青年」堪稱是殖民地主義在殖民地社會所產下的近代化孿生子。日本殖民地主義一再地反覆強調其與歐美諸國在殖民地統治體制上的差異(所謂「反殖民地主義的殖民地統治」);然而只要一窺殖民統治下臺灣社會有關「青年」論述的內涵,便可以體會到,即使就殖民地臺灣而言,班納迪克.安德森的觀點仍非常具有啟發性。
尤其,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從早已被視為近代臺灣民族意識覺醒的代表性刊物《臺灣青年》中,擷取出下列的一段話來進一步推敲:
青年為國柱石,何國何時皆然,尤其世局遷移之際可見多數青年當先驅活動,今日我島也甚為期盼青年自覺……不肖衷心切望我島青年諸君組織地方青年團則為地方文化啟發而奮志勉勵。
文中所稱的青年團,根據該文後續所述,亦即「團員之間要互相激勵,陶冶共同合作的精神,而且在培育健全國民的下一世代(後繼者)之同時,也必須在本島處於過渡時代之際,是直接或間接促進啟發本島社會文化」之青年團體;而青年團的會員則以「公學校畢業以上或是一般有志者」為預設對象。
由此可知,《臺灣青年》在該文中所主張的青年團,其成員必須是受過「社會文化啟發」的公學校以上畢業生,同時也被視為是「健全國民的後繼者」。該文論述當中不斷貫串其間的所謂「青年」,一開始便與「國家(我島)」相連結而率先成為一專屬且特異的社會範疇――「我島青年」;進而,透過「我島」、「地方文化」、「先驅」等詞彙來與臺灣連結並衍生出「青年(民族)自覺」的特殊意涵。亦即,在殖民地臺灣近代化的過程中,同樣可以清楚地看到,當其民族主義萌芽之際民族主義和「青年」的孿生關係。
但如上所述,與安德森所研究的西方殖民地發展不同,日本帝國統治下的殖民地臺灣,有別於「臺灣青年」的民族主義運動,很顯然在1920年以前,「俄國化」官方民族主義的模組不僅已被複製到日本帝國,並且透過國家主義信徒伊澤修二等殖民地官僚之擘劃,於第一個海外殖民地臺灣展開。
(二)「青年」教化政策的本質
因此,近代臺灣所看到的民族主義和「青年」的孿生關係,不是虛無飄渺的存在,而是實際鑲嵌在臺灣和日本殖民地主義之相互關係中誕生而展開的。因此,我們必須在此一層面,徹底揭開日本殖民地主義特殊性的真實面紗。
此處焦點所在,乃是基於日本殖民地主義下,人才培育的臺灣總督府之同化教育與「社會教化,亦即社會教育」的政策範疇,究竟與日本本土有何關係?臺灣總督府在移入本土的「青年」概念以後,便積極建構其「社會教化」政策。這裡所稱「社會教化」的政策概念,不僅是日本本土移入的概念,同時也正如宮坂廣作所解析的「日本的社會教育就是『青年團本位』」。
換句話說,「社會教化」的主要對象就是「青年」,也可以說,「社會教化」政策就等同於「青年」教化政策。若從結論來看,可以清楚看出臺灣總督府一開始並不是先從青年團著手,因為誠如近藤正己所述「漢民族社會原本就不曾存在相當於日本『若者宿』與青年團的組織」,而是先行透過殖民地近代學校教育體系,來培養近代國民國家的「殖民地青年」。至於青年團這樣的組織正式移入殖民地,除了學校教育成果的累積和延續外,其主要的背景,更與1920年前後臺灣青年所展開一連串的文化、政治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探究日本殖民地主義的特殊性之際,也正可清晰地映照出與之相抗衡的「臺灣青年」不同階段的面貌。
日本統治下殖民地時期臺灣「青年」教化政策的展開,並非一路暢行無阻,亦非按部就班,而是相對於殖民地社會和局勢變動的一種筆者稱之為「急就章式的補破網」因應策略。對此,本書歸納出三處具體政策轉換的觀察點:分別是1896年府國語學校、1926年府文教局,和1944年府青年師範學校之設立。
要言之,1895年日本領臺之後的所謂「青年教育」,主要是以1896年設立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為中心,而在學校體制中進行。亦即殖民統治者以將國語學校的學生培育成「新領土經營者」的「青年」,視為首要之急務。且從同時期展開的國語傳習所開始,讓這些前朝遺民的臺灣人年輕世代,從領有初期便透過近代學校教育賦予其最重要的能力――「雙語讀寫能力」,然後當他們一走出學校便賦予其在臺灣社會中肩負教育體系(公學校為主的初等教育為核心)、教化體系(官媒《臺灣日日新報》編輯和記者等)的經營管理職務之「義務」,並享有擔任公學校教師並兼具下級文官資格的特權。
即使到1919年改制為臺北師範學校後,這些人仍全心全力投注於公學校或各地方社會的國語普及工作,一直到殖民統治結束為止。換言之,當時殖民地臺灣所謂的社會教化只是學校教育的延續,而扮演主要角色的就是這些國語學校的校友們,而這些「國黌校友」在地方社會中,一則協助並推動各地公學校的設立,一方面也成為地方街庄役場街庄區長的預備軍,逐步歷練成為地域社會中「新進有為」的人物。可以說,直到1922年第二次《臺灣教育令》頒布――亦即所謂內臺人共學制實施為止,總督府「青年」教化政策的主軸始終以學校為施政重心。
然而當1919年東京「新民會」和1920年東京臺灣青年會等非武裝抗日運動團體,相繼在島外成立,殖民政府原有的「青年」教化政策逐漸受到嚴重挑戰。尤其1921年作為臺灣島內非武裝抗日統一戰線的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對於臺灣青年層的影響,更遠遠超乎總督府官僚的想像,而使得「青年」教化政策不得不改弦更張,決意移入日本本土官製青年團制度。
因此,官製青年團政策的轉換,正宣告了「青年」教化政策不僅強化「學校內部」的管制,更要針對「學校外部」的青年層進行思想統制與發展社會教化設施。1924年,當時擔任日本本土青年團運動核心人物之一的後藤文夫(詳第三章)被任命為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1926年,在其任內設立了作為青年教化總司令部的府文教局,強化對青年團指導者的培育、學校的監督指導(增加視學官的員額),以及對「青年」的思想統制。1930年,所謂的《臺灣青年團訓令》(即府令第七十二號)的公布,其實也是其任內「青年」教化政策的延續,在訓令中,「青年」被明確定位為「下一世代社會的擔當者」。
進入1930年代,在軍事色彩愈來愈濃的日本本土和殖民地,社會教育(教化)的必要性不斷被強化,而由總督府文教局社會教育部的主管官員所主辦的雜誌《社會教育》創刊,同時對於青年層的軍事訓練和社會教化動員也陸續強化。自1930年代中葉起,在皇民化運動和總力戰體制之下,「皇國民的培訓」不管在人力或是在人心動員上,皆成為刻不容緩的急務,於是連原先排除臺灣青年層加入的青年訓練所,到了這個時期也伴隨著青年學校的設立而被允許。
這些其實都是為了因應提升廣泛青年層國語能力的要求所致。於是,為了普及國語教育而相繼設立的各種社會教育(簡易)設施,對於學歷(是否公學校畢業)不再有所限制,因而造成宮崎聖子所指出的青年團員「中下層化」的現象。但另一方面,應急式的普及政策也同時暴露出擁有「雙語讀寫能力」教員的嚴重缺乏。
1944年隨著青年學校義務化之同時,臺灣總督府當局所提出的解決之道便是與本土同步,在原有的師範學校體系之內,增設了以培育青年學校師資為目的的青年師範學校,其主要職責便是「皇國民的育成」。諷刺的是,所召募而來的學生,對於當局的「美意」未必照單全收;相反的,有不少中等學校畢業的內、臺人應考生,是因為不想被徵兵或抽到志願兵而前來投考該校。只是人算不如天算,由於日本帝國的軍事作戰節節敗退,青年師範學校的修業年限被迫縮短,翌年先後被強制徵召入伍服役或充當學徒兵,並在根本來不及分發擔任教師一職之前,日本殖民地體制便正式宣告瓦解。其命運之乖舛,可說與領臺隔年設立的國語學校成為鮮明的對比。
僅有一年多壽命的青年師範學校,由於如曇花一現而未受到太大的重視。有關戰後臺灣的研究中,皇民化時期與戰爭時期的青年團或「臺籍日本兵」(原日本軍屬、軍夫),因為論及軍事動員和臺灣人的戰爭經驗而最受矚目;只是在殖民地教育史或制度史研究中,由於青年師範學校存在時間過於短暫,往往只被視為師範學校史中的註腳而遭一語帶過,導致以其為對象的研究可說一片空白。更遑論昔日充當學徒兵而被動員的青年師範學校臺灣人學生的事蹟,迄今也都被忽略。
筆者以為,不應僅將青年師範學校如狗尾續貂般放置在學校史研究的脈絡中,而應就其在殖民地「青年」教化政策史中的定位重新檢視,就其短暫如曇花一現的存在意義來看,其實正好印證了「青年」教化政策已走到窮途末路的象徵。何以故?因為此時所謂的臺灣人「青師青年」,已不再是之前擁有雙語讀寫能力的「國師青年」,而是1937年象徵漢族意識的漢文被官方表面禁絕下,在皇民化運動期成長而只能讀寫日語的「皇國青年」罷了。然而,儘管喪失了漢語能力,卻不等同於失去了漢族意識。毋寧說在皇國敗象昭然若揭的過程,同時也是讓這些「皇國青年」本身的臺灣人認同再度被激發出來的過程,官方民族主義「青年」教化政策的終結正體現於此。
不論是國語學校還是青年師範學校,其設立本身皆基於肩負特定任務――亦即以「青年」教育、教化的意圖為基本理念,而成立的「任務型學校」;而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的設立,更是殖民地「青年」教化政策大轉換的證據,此際殖民政府改弦更張,「青年」教化政策態度從消極轉趨積極,並以其作為青年層思想統制的司令塔,與「臺灣青年」展開一場青年爭奪戰。而即使在皇民化運動與戰爭動員時期,一連串有關青年社會教化政策積極推動之際,國語學校畢業生對於這些政策的進展,依舊在教化社會中扮演著承上啟下的重要角色。
綜上所述,在殖民政府長達半世紀的統治下,殖民地臺灣有關「青年」教化的應對措施,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內涵。首先殖民統治之初,率先由扮演著臺灣教育、教化總樞紐的國語學校,培育「青年」種子菁英部隊,派遣到各地協助公學校設立、國語教育普及,以及透過《臺灣日日新報》和《臺灣教育》等官方媒體來「教育社會」;到了中期,為了正面迎擊來自「臺灣青年」的激烈挑戰,而在中央層級新設文教局,試圖防止校外「青年」受到「惡思想」的汙染;末期,到了敗象已露之際,倉促新設府青年師範學校,以培育青年團和青年學校的師資,作為「皇國青年」總力戰體制的新指導者,但已時不我與。
但是在另一方面,相對於殖民政策綿密的教化規訓措施,我們也不能忽略如一開始所舉徐慶祥的事例。在地域社會當中,其實有一股濃得化不開,一種跨越殖民地政治、政策的制約而存在的國語學校畢業生關係網絡、同窗情誼,以至臺灣人國族認同意識的存在。而唯有透過這些突破各種制約的非制度性存在,才能讓殖民統治和「青年」教化政策的本質,以及以「青年」為主體的教化政策的實態,得以更清晰地浮現出來。
(三)臺灣社會中「協力機制」的結構――學歷、職業配套的特權與教師在地化
「青年」教化政策乍看之下似乎與「學歷」社會毫無關聯,然究其實際,作為近代國民國家文化統合政策的一環,透過以義務教育為開端的學校教育,「青年」和國民國家的關係一目了然,並且於國民統合時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就殖民地臺灣的實態而言,同化政策的種種論述當中,「青年」教化政策無疑才是殖民統治上最為核心的問題。在殖民政策中所謂「青年」,乃是具備「雙語讀寫能力」,並作為新領土經營者的新式人才。同時在殖民地社會中,「青年」所代表的意義,則是一群擁有殖民地「學校畢業」的新式學歷,而足以向外誇耀的新興階層。
殖民地社會中所謂的「學歷」,不單僅是學習知識的證明,更是受到殖民統治者認可,擁有「國語力」和「教化社會」能力,並具有資格足以擔當「新領土經營者」的最佳證明。若演繹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中對民族主義定義的說法,同樣的,近代國民國家中的「青年」,不只是單純的平面性概念,同時也是殖民統治下「文化的人造物」,而且一旦被創造出來,就會變成「模式化」。換言之,殖民統治者一則基於日本帝國官方民族主義的原理,二則將漢人的「科舉造士」的傳統奪胎換骨,以培育創造出這批近代學歷青年集團,並衍化成各種不同模組,培育不同專業需求的人才,來遂行其殖民統治與滲透殖民地社會的目的。
天野郁夫指出,近代國民國家從一開始便主導和統制包括自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為止的一貫性教育,同時授予學歷和職業所配套而成的資格認證制度。而就近代日本而言,最早且最具近代性的職業就是教師和醫師這兩項,且其中教師這項職業,更是國家要從初等教育中培育出新一代國民之際,不可或缺的「基層官僚」。若從這點來看,一開始便被嚴格限制在普遍只有初等教育的殖民地臺灣,殖民地教師培育的重要性更是一目了然。而體現這種近代國民國家統治權力思維而在殖民地臺灣體現的教育機關,不是別的,正是1896年設立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殖民政府透過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師範教育,結合了學歷與資格(職業)的配套,並使其成為一種特權性的存在,培育臺灣人「青年」菁英逐步將其納入這套遂行殖民統治的結構內。
因而在地域社會中,國語學校畢業生儼然成為統治者的代理人。首先藉由學校教育體系,透過殖民地教師將日本帝國官方民族主義,灌輸給招收臺灣人學齡兒童的初等教育機關――公學校,進行「國民」的生產與再生產;同時在社會教育中也發揮極大的影響力,殖民地教師尤其是內地人畢業生,更扮演著教育、教化地域社會的指導者角色。因此可說,殖民地教師的表現不僅攸關地域社會的統治,甚至與整個殖民統治的成敗互為表裡。這點,除了可從時人的回顧談中,往往不分立場對於殖民地時期臺灣教育成果的肯定以及高就學率的讚頌,抑或戰後對於日治時期日本人教師與臺灣人學生間的「教育無差別待遇」往往成為報章媒體「美談」的現象可知,「殖民地教師」這種跨越種族、跨越統治與被統治二元對立的社會現象,實有其特殊的社會意義。
第一章 殖民統治政策與「青年」的誕生――處在鎮壓與懷柔的夾縫中(節錄)
三、「青年」的誕生
日本帝國與清帝國簽下《馬關條約》而獲得殖民地臺灣,成為近代亞洲各國中第一個也是唯一的殖民地帝國。為了統治前所未有的海外殖民地,並標榜與西歐帝國殖民地統治的不同,日本殖民政府喊出「同文同種」的口號,而以全面「同化」(日本人化)臺灣的新附民為政策目標。然而,此一「同化」教化政策的對象是誰?而擔任這項政策推動的又是誰?這些問題的答案並非不言自明的。
以近代國家原理欲遂行直接統治的日本帝國,一開始便積極利用臺灣漢人鄉紳階層,保存舊慣,飴鞭並用,望能逐步建構殖民統治的基礎。然而,這些措施只不過是戰略性的一時之便,作為終極目標的,不用說乃是將臺灣新附民同化的方針。因此,1897年4月將原本日本內地體現天皇制國家統治原理的《教育敕語》,亦於海外殖民地臺灣頒布漢譯版,成為教化臺灣人的最高原則,而逐步地全面性植入殖民地社會。而且為了實現上述目標,非得培育殖民統治「必須的人才」不可。
所以,殖民政府一開始目光便停留在那批「數量有限」的鄉紳階層和他們的子弟身上。如上所述,殖民統治政策除了對武裝抗日勢力進行無情的軍事鎮壓和屠殺以儆效尤外,對於新式學校教育的推動以及舊鄉紳階層,則採取恩威並施的懷柔策略。換言之,殖民政府在統治之初,一方面軍事鎮壓抗日義士,另一方面則積極培育新學之「士」和攏絡尊重前清舊有科舉功名之「士」,亦即征討「義士」和「造(新)士」、「尊(舊)士」的殖民統治政策,幾乎同時在殖民地社會展開。
以往的研究成果當中,對於殖民統治前期武裝抗日的討論既多且繁,因此本小節主要以探討造「新士」的政策意圖,及兼論「舊士」等鄉紳階層的對應為焦點,藉此闡明殖民政府是如何利用「尊士」政策,而將日本內地的日本帝國官方民族主義相應而生的抽象概念「青年」,移植到具有漢人士大夫傳統的臺灣社會中,並透過近代學校教育進行奪胎換骨,進而讓此一抽象的新概念,與漢人社會的「造士」傳統揉合,而創造出安德森所稱之「殖民地青年」。究明此一殖民政策如何滲透入臺灣社會的過程和接受的機制為何,乃是本小節論述焦點之所在。
首先,近代學校教育與漢族「科舉造士」的傳統教育之間,最大的差異乃在於年齡――所謂學齡制度存在之有無。即在原本並未明顯區分學齡的漢人社會中,如何透過學齡制度的導入,來切割出不同的年齡社會集團,正是殖民地教育在臺灣展開之際,殖民政府首先所必須面臨的問題。
(一)學齡制度的遞嬗
「學齡」制度的規定乃是近代學校的特徵之一。由於學力上和生理上的差異,因此必須根據不同年齡階段的差異來進行學級編班。安德森以荷領印尼為例指出:「跟當地傳統現存的學校形成強烈鮮明的對照……,殖民政府所設立的新式學校,由一種龐大的、被高度合理化下嚴格的中央集權化的金字塔體制所組成,讓人不得不聯想到這根本就是國家官僚機構本身的複製品」,接著,對於殖民地學校的運作方式,安德森繼續描述如下:
被統一的教科書、標準化的畢業證書和教員證、並且根據不同的年齡集團所嚴格規制下的學年制、不同學級的編班和教材,透過這些事物,自然地創造出一種獨特風格而又具有同質性的經驗空間。
其中關於年齡集團所謂「年紀太大」的考量,在傳統教育制度裡原本就不存在,但就「殖民地西式學校來說,卻是一種根本不會意識到的基本原則」。
因此,隨著近代學校教育制度導入的同時,國民的概念也被帶入,國民依據不同的年齡(當然,也規定性別和財產的基準)而具有相關的權利和義務。其中最基本的,便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納稅、義務教育和徵兵等三大義務。但是正如同矢內原忠雄所指出的,殖民地人民雖然擔負納稅的義務,卻未實施徵兵制和義務教育,而臺灣更是專以國語教育為中心施行所謂的同化教育。因為不被認為是日本國民,因此即使到了殖民統治末期,為了全面動員臺灣人始不得不宣稱施行義務教育和徵兵制的殖民地臺灣,要如何克服傳統科舉制度下缺乏「年紀太大」觀念,按照實際需要制定新的年齡集團基準這件事,正是作為統治者在設立近代學校時,一開始所面臨的問題。
「士大夫巡禮圈」的臺灣漢人社會當中,對於儒教經典《論語》中孔子所言「十五而志於學」似乎已具備近代的學齡概念,但這只是指人格教養的開端而言,且是一生中持續不間斷。以儒教思想為中心所發展出來的科舉制度,在現實運作上,這套以任官為目的的傳統教育制度,也根本沒有年齡的上限。所以,傳統教育未限制年齡的舊慣,乃成為近代學校制度導入之際,首先必須加以克服和排除的對象,然後再藉由學齡的分段化作為殖民政府培育近代國民的機制,以從中形塑養成殖民地社會「青年」集團的原型。
(二)年齡集團的分段化
如前所述,殖民政府將1880年代於日本內地形成的、從小學校――中學校――高等學校――大學一貫完備的近代教育制度引進殖民地臺灣,但是一開始並未嚴格區分採取一定年齡分段化的作法,反而是極度遷就當時民學(書房義塾等傳統教育)設施的現狀進行調整。因此,初期所設立的國語傳習所、國語學校,以及1898年公學校所招募的學生,皆是以具備漢字學習經歷且沒有家業負擔的出身為要件,並限制年齡在30歲以下的臺灣青年層為新式教育推展的優先對象。以下將依據臺灣總督府所頒布的相關教育法令,來檢視實際規定於不同時期的遞嬗過程。
1898(明治三十一)年8月16日《公學校規則》(府令第七十八號)頒布,取代原有非制度性教育機關的國語傳習所,成為以臺灣人學齡兒童為招生對象的初等教育機關。根據該規則第三條的規定,「公學校的學生其年齡為8歲以上14歲以下」,公學校從此便成為繼續就讀國語學校和其他中等教育機關的基礎。
從1912年開始,由於日本領臺後出生的新世代陸續登場,以及產業和農村資源開發所需,公學校的入學者年齡大都限制在滿7歲到12歲以下,與日本內地沒有太大差異;然而由於臺灣人的中等教育機關遭到嚴格限制,12歲以上從公學校畢業的學生,只能繼續就讀有高等科設置的公學校,或相當於補習教育的實業教育機構。換言之,殖民政府雖讓臺灣青年層接受初等教育,卻又嚴格限制其接受初等教育以上的教育,觀其主要用意,乃是為了因應殖民地開發在產業、農業上所需的任務型人才培育。
在此情況下,數量有限的「青年子弟」升學的主要學校,除了1901年開設的專門教育機關(即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之外,當時初等教育以外的中等教育機關只有一所,即從一開始殖民政府為了培養殖民地官僚、實業家和公學校教師,也就是所謂「公務及自由業」人才培育機關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包括初期曾短暫存在的三所師範學校),以培養殖民統治所須的綜合性人才。
如上所述日治初期一度設置專收臺灣人學生的三所師範學校,其法源依據的《臺灣總督府師範學校規則》(府令第三十一號)在1899年4月13日頒布時,其第一條便規定「師範學校乃在於培養本島人成為國語傳習所及公學校教員」為目的,修業年限三年,「學生的年齡為18歲以上25歲以下」(第五條)為招生對象。至於入學條件的規定還另外加註:「入學學生的資格,必須通曉漢文,並且為官立學校或公學校畢業,以及具備同等以上學力之本島人。在學中沒有家事之累,從畢業後起十年間能保證擔任教職者。但是目前官立學校及公學校第三學年學科修了或具備同等以上學力者亦得以入學」(第十六條)。總之,臺灣人學生的入學資格主要在要求學生的學力(通曉漢文)、「無家事之累」,以及能宣誓保證「從畢業之日起十年間擔任教職者」。
由此可知殖民統治初期師範學校所招收的臺灣人學生,必須符合通曉漢文(具有書房教育經歷)且曾修業於公學校,年齡為18歲到25歲之間,沒有家事之累者,亦即多半為當時臺灣社會家財中等以上的鄉紳階層的青年子弟。就殖民政府而言,這些擁有「學歷和資產」的臺灣人青年世代,乃是當時臺灣人社會中優先接受日本化教育的主要對象。而具體要求該校畢業生須從事十年教職的義務,除了可確保教師人才、節省經費和保證就業等用意之外,殖民政府期待讓當時接受傳統書房教育的年輕世代,能順利轉換跑道,成為近代學校教育教師這項職業的一員,這些條件也發揮著讓傳統遞嬗至近代此一過渡時期人才培育無縫接軌的功能。
然而事與願違,1902年前後三所師範學校相繼廢校,結果三校學生先後被編入國語學校的師範部就讀。但在另一方面,當時國語學校卻曾經一度新增實業部。由此可看出國語學校逐步擴大規模,常設國語部和師範部以及視實際所需增設任務型的實業部,以培養殖民政府遂行公私業務人才和公學校教員為主要職能,一直到1919年改制為臺北師範學校為止,都不曾間斷。
1904年可說是臺灣近代初等教育的分水嶺,在這一年,臺灣人學齡兒童就讀書房教育的學生數,首次被公學校學生數超越,公學校畢業這道基準線,從此以後成為國語學校為首的中等教育機關招生資格的主要基本條件。因此從翌年(1905)起,國語學校對於臺灣人學生的學齡相關規定如下:「師範部設置甲科及乙科……申請就讀乙科的學生以年齡滿15歲以上、23歲以下的本島人為對象,具備公學校畢業以上的學力者」(第七條),以及「申請就讀國語部的學生為年齡滿15歲以上、22歲以下,具備公學校畢業以上的學力者」(第九條),不論何者,至此公學校畢業已成為基本學歷要求。
有關公學校的學齡規定,1907年左右,公學校的入學就讀年齡為滿7歲到20歲以下,當時公學校的修業年限有四年制也有八年制。根據1912年11月28日《公學校規則改正》(府令第四十號)的規定,八年制公學校被廢,新增設二年制的實業科,原則上公學校一律改為六年制。至於招生年齡也調整為滿7歲以上到12歲以下(含例外)。這項規定自1913年1月1日起施行。
在公學校逐步走向學齡基準化的情況下,殖民政府雖然一方面也容許傳統書房的漢文教育,但另一方面則積極推動將書房變成「公學校的輔助機關」,進行更全面性地奪胎換骨的措施。綜上所述,直到1910年代末期為止,對於臺灣社會來說,公學校大體上已成為培養具備基礎「雙語能力」的初等教育機關,並以7歲到12歲之間的臺灣人兒童為招生對象。相較於此,更具特權性格的中等教育機關――國語學校,為了培養人數更少的「新領土經營者」,在習得更進階而專業的「雙語讀寫能力」後,分發至殖民統治所需的近代部門任職。因此,其招收對象更限縮為以公學校出身(肄、畢業)且成績優秀者,年齡在23歲以下的臺灣青年菁英為主。
該校的畢業生,除了習得進階而專業的「雙語讀寫能力」以外,更不能忽視的是,當他們從殖民政府手中領到畢業證書的那一瞬間,亦可同時取得在殖民政府所轄(屬)各種公私業務機關任職的低階文官資格。換言之,這些接受殖民地教育、屬於某一特定年齡階層的臺灣青年菁英,正是一開始便擁有「學歷」和職業這項制度性配套的特權化「(殖民地)青年」。
(三)近代「學歷」與職業的擁有者
那麼隨著殖民政府近代學校教育的施行而被引進臺灣社會的「學歷」,究竟所指為何、又是如何融入傳統社會?原本在中華文化的傳統當中,並不存在今日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學歷」這個詞彙。學歷這個詞彙乃是與近代學校的發展同時並進,且密不可分。不過傳統當中雖未使用學歷一詞,但有一較接近的詞彙「履歷」,這個詞彙直到今日仍被普遍使用。然而,傳統中的「履歷」,與現代社會主要記載教育經歷和職業經歷的履歷表內容也並不一樣,而主要是記錄科舉制度下「任官的經歷」之含義:
﹝陔餘叢考.履歷﹞履歷二字,至宋時始為官場成語。﹝六部成語.吏部.履歷.注解﹞作官之出身及作官之地方及如何保舉,均謂之履歷。
總之,履歷原本與庶民無關,而是科舉制度下官僚們的任官紀錄。而一直到日本領臺為止,臺灣社會中先是由鄉紳階層傳統文人所使用,接著藉由書房教育擴散到臺灣社會而逐漸普及。
日本領臺之後,臺灣社會中傳統履歷的含義,便被近代學校教育的學歷所轉換並逐步取代。而且不僅限於傳統的鄉紳階層,從就讀近代學校的學生到在殖民政府等公私機關任職的臺灣人之間,亦漸漸地擴大,因此可以說學歷社會的原型很快地便在殖民地初期產生。儘管如此,真正生根落實,則要等到昭和時期各級學校體系的完備以及職業專業化後,才宣告成熟。因為即使在殖民地初期,仍非使用學歷而是沿用「學業」一詞。
根據日本教育社會學者天野郁夫指出,在日本本土「學歷此一語彙成為一般用語,是從邁入昭和時期開始的。而在此之前,表示與學業、學校相關履歷的一般性用語並不存在」。而天野郁夫也進一步指出:
「學歷」一詞原來只是表示教育(學問、學業)有關的履歷,或是與學校相關履歷的意思罷了。而後之所以成為教育社會學上的重要概念,乃是因為與學問和學校有所關聯的履歷,變成一種社會性的「資格」,並賦予取得這些(「資格」)的人們,保證擁有各式各樣的「特權」所致。
引文中明確指出近代的所謂「學歷」,已成為一種在特定的學校中、習得特定的學問和學業之證明,而且在取得這項證明的同時,也獲得各式各樣的「特權」,學歷已不僅是作為學問和學業的證明,同時是「作為一種資格的證明」。
若從此一角度觀之,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及其畢業生,對於殖民地臺灣社會而言,正合乎天野郁夫所指出的扮演著「特定的學校」而具有特權般的存在。甚且,居於異民族統治優勢的殖民政府,藉由活用資格與學歷這項配套化的「特權」之賦予,巧妙地將臺灣人社會中科舉任官「履歷」的傳統奪胎換骨,全面地展現出殖民地主義的特色,透過近代學校教育,將學歷的概念植入殖民地社會當中。
天野郁夫對於日本社會中象徵日本近代「學歷」社會的原點,即1872年(明治五年)明治政府頒布的《學制》所具有的時代意義,有如下的描述:
藉此〔明治五年《學制》的頒布促使近代學校制度的展開〕使得教育上的基本事物能在「學校」這樣的組織中展開,而在此間修習一定程度學問和學業的「證明」,透過修了證書、畢業證書、學位等形式,必須經由「學校」始得加以授予。
此外天野也指出,進入1880年代後,日本內地對於「學歷」這一概念雖然尚未廣泛認知,但是有關於各級學校制度的建置,卻是在此一時期幾乎宣告完成。而後1890年「明治憲法」的施行以及《教育敕語》的公布,最後到了1895年――日本領有殖民地臺灣的同一年,正式實施第一次高等文官考試,藉此從小學開始一直到接受大學教育的青年知識階層,都可藉由「學歷」或資格考試的管道,在政府所屬各項近代職業部門內任職,而此一晉升管道也是在這一年齊備。儘管要達到學歷社會的境界尚有一段路要走,但對於學歷的重視,則在1900年前後便已逐步落實成形。
檢視當時的殖民地臺灣社會,具有近代性「學歷」含意的學校機關,分別有1896年設立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以及繼承國語傳習所而在1898年起於臺灣全島各地陸續設立的公學校兩者。藉此,殖民地臺灣近代學校進階體制和「學歷」社會的建構也算是規模粗具。因為,若擁有這類學校的教育經歷,除了表示習得國語(即日語)的能力獲得承認而授予畢業證書之外,同時更可獲得保障,進入官廳或公學校等殖民政府機關任職(儘管都是低階文官或雇員)。也就是說,「學歷作為一種特權」,在殖民統治初期,便由殖民政府引進推行。
尤其在殖民統治初期,地方必須自籌教育經費且書房仍大量存在,如果沒有賦予「特權」(利益),抑或這些「利益」不足以吸引臺灣住民,那麼低迷的就學率恐怕根本無法拉抬。而事實上,殖民政府為了吸引臺灣住民將其子弟送入學校,也提供了包括獎學金、學費公費制、免費提供教科書和宿舍等優渥條件,並且動員鄉紳、警察和教師進行學生的招募,甚至連畢業後的工作都一併給予保障。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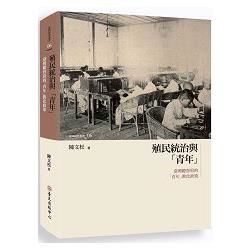 |
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 作者:陳文松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5-04-2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9 |
二手中文書 |
$ 378 |
中文書 |
$ 378 |
台灣研究 |
$ 387 |
教育學習 |
$ 387 |
社會人文 |
$ 387 |
社會人文 |
$ 387 |
歷史 |
電子書 |
$ 430 |
台灣史地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
殖民地青年是統治體制的協力者?或是反抗者?
本書自臺灣總督府教化政策的特殊視角切入,
呈現殖民地歷史中清流與濁流難以劃分的複雜面貌。
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意圖使臺灣人的子弟成為其殖民統治的協力者,賦予臺灣青年擔任「殖民地近代性」的仲介者角色,卻也同時孕育了反殖民的年輕力量。本書旨在探討日本統治下,殖民地臺灣長達半世紀的殖民政策,如何形塑一特權化「青年集團」,並藉由近代化的「青年」概念,闡明其與殖民地社會之間的互動和關聯。
「科舉造士」原是中華帝國科舉制度為國舉才之傳統;為了培育殖民統治所需人才,殖民政府透過1896年設立的臺灣第一所高等教育機構──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將此傳統換骨奪胎,並移入近代國民國家的「青年」概念,作為殖民地學校教育與社會教化的先鋒部隊。此一「青年集團」的內涵,隨著臺灣社會情勢之演變而變化,全島自主性的「臺灣青年」與地域社會的「官製青年集團」,在傳統與近代、統治與被統治之間,亦呈現多重的面貌。
作者簡介:
陳文松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曾任教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東華大學,現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講授臺灣政治文化史、日治臺灣史、區域研究。其研究領域包括殖民政策史、地域社會,以及日常生活(娛樂)史。著有〈從「總理」到「區長」:與日本帝國「推拖頑抗」的武秀才洪玉麟――以洪玉麟文書(1896-1897)為論述中心〉、〈日治臺灣麻雀的流行、「流毒」及其對應〉等。
章節試閱
序章 課題與方法――近代民族主義、「青年」與地域社會(摘錄)
本書是以臺灣近代「青年」的政治社會史為研究焦點,藉以闡明日治時期教化政策與殖民地社會變遷之間的相互關係。本書除序章和結論外共分成六章,第一章到第四章主要著眼於殖民政府「青年」教化政策的起源、意圖及半世紀當中演變的過程;第五章和第六章則以臺中州草屯地域社會的「青年像」為具體事例,探討殖民政府「青年」教化政策與地域社會變遷的相關性。
因此,本書首先將從目前為止通常被限定在師範教育脈絡中討論的「國語學校」入手,藉由「青年」概念的導入來重新檢視...
本書是以臺灣近代「青年」的政治社會史為研究焦點,藉以闡明日治時期教化政策與殖民地社會變遷之間的相互關係。本書除序章和結論外共分成六章,第一章到第四章主要著眼於殖民政府「青年」教化政策的起源、意圖及半世紀當中演變的過程;第五章和第六章則以臺中州草屯地域社會的「青年像」為具體事例,探討殖民政府「青年」教化政策與地域社會變遷的相關性。
因此,本書首先將從目前為止通常被限定在師範教育脈絡中討論的「國語學校」入手,藉由「青年」概念的導入來重新檢視...
»看全部
目錄
序章 課題和方法――近代民族主義、「青年」、地域社會
一、追問吳濁流「然而即便如此」(それでも)所留下的課題
二、先行研究
三、本書研究的目的和課題
四、研究對象、方法與史料介紹
第一章 殖民統治政策與「青年」的誕生――處在鎮壓與懷柔的夾縫中
一、問題所在
二、從「士」到「青年」的奪胎換骨
三、「青年」的誕生
四、享有特權性地位的「青年」
五、教師這項職業的誕生
小結
第二章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青年」教育、教化的中樞與「雙重語言讀寫能力」的訓練所
一、問題所在
二、「...
一、追問吳濁流「然而即便如此」(それでも)所留下的課題
二、先行研究
三、本書研究的目的和課題
四、研究對象、方法與史料介紹
第一章 殖民統治政策與「青年」的誕生――處在鎮壓與懷柔的夾縫中
一、問題所在
二、從「士」到「青年」的奪胎換骨
三、「青年」的誕生
四、享有特權性地位的「青年」
五、教師這項職業的誕生
小結
第二章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青年」教育、教化的中樞與「雙重語言讀寫能力」的訓練所
一、問題所在
二、「...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陳文松
- 出版社: 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5-04-28 ISBN/ISSN:978986350058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32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台灣研究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