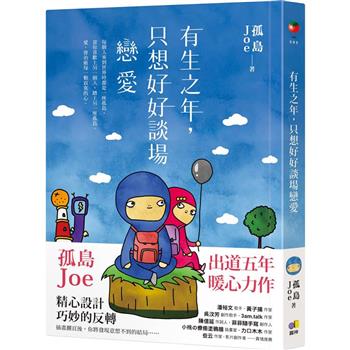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揚雄的範式研究的圖書 |
 |
揚雄的範式研究:西漢末年學術範式衝突的折中之例 作者:馮樹勳 出版社: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5-08-1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5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77 |
哲學 |
$ 277 |
📌哲學79折起 |
$ 308 |
中文書 |
$ 308 |
中國哲學 |
$ 315 |
教育學習 |
$ 315 |
社會人文 |
$ 315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揚雄的範式研究
鑑於學術史論及清中葉《易》學為了強調時代特色,皆以漢《易》派為代表,本書採取不同研究視角,強調彰顯《易》學發展的多元性,故針對清初及清中葉的《易》學,分別就圖書《易》學、漢《易》派、宋《易》派,及歸本《易》經傳、強調致用與建立體系的《易》家進行類型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