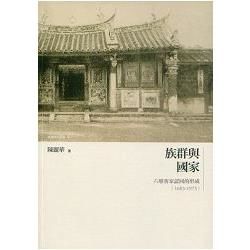「臺灣客家人的族群認同從何而來?」
本書採取歷史人類學的觀點,以六堆為研究對象,
重新思索近三百年來國家因素對臺灣客家族群認同形塑的影響。
六堆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客家聚落,也是桃竹苗地區之外的第二大客家聚居區。不過,「六堆」並不是一個可以在地圖上找到的地名,它其實是高雄市及屏東縣境內十二個鄉鎮的合稱。其地域名稱來自於清代當地人士組織的軍事性地域聯盟,至今還可清楚分辨不同地域的堆別。
本書採取歷史人類學的觀點與方法,試圖描繪及說明臺灣六堆地區的客家族群認同,如何經歷清帝國、日本到戰後中華民國三個不同政權的治理,在這近三百年的時間中逐漸形成與演變的歷史。臺灣客語群體的地方文化和認同在清帝國統治時期,已與其祖籍地華南社會存在差異。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則使得臺灣「客家」的想像逐步形成,只是更大程度和語言文化聯繫起來,血統色彩則較為淡漠。而血統色彩強烈的所謂「中原客家」族群觀念,則是在進入二戰末期以及戰後,才逐漸深入臺灣社會。
本書特別著重在「族群」與「國家」之間的互動,作者在本書指出,國家既是行政治理的機構,同時也是文化理念的集合體,而族群意識的衍生和表達,深深地植根於不斷變化的國家意識當中。它並不僅僅透過制度性因素表現出來,亦透過禮儀和象徵表現出來。不同國家政權治理下的禮儀和文化元素,如何在臺灣六堆巧妙地、選擇性地納入歷史記憶的框架,成為晚近表達客家認同的方式,亦為本書的論述重心。
作者簡介:
陳麗華
現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其目前的學術研究集中在臺灣社會史與客家族群史。2010年獲得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學位後,曾先後於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及中央研究院從事研究工作,其研究論文曾發表在《臺灣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歷史人類學學刊》等學術期刊上。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本書透過各類歷史材料的蒐集與整理,將具體的人物行動與反應鮮活地刻畫出來,但是又往往經過不同材料的交叉比對分析,而不致流於只是當事者的片面說詞。這些嚴謹的鋪陳與論證,往往是以流暢而引人入勝的敘說方式進行,而不會流於一般學術論文的艱澀。這充分展現歷史人類學取向的優點。……這是一本論證嚴謹、又有相當可讀性的著作,值得向客家研究、臺灣研究的學者,以及一般讀者推薦。
――王甫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作者)
名人推薦:本書透過各類歷史材料的蒐集與整理,將具體的人物行動與反應鮮活地刻畫出來,但是又往往經過不同材料的交叉比對分析,而不致流於只是當事者的片面說詞。這些嚴謹的鋪陳與論證,往往是以流暢而引人入勝的敘說方式進行,而不會流於一般學術論文的艱澀。這充分展現歷史人類學取向的優點。……這是一本論證嚴謹、又有相當可讀性的著作,值得向客家研究、臺灣研究的學者,以及一般讀者推薦。
――王甫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作者)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導論:六堆地區的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節錄)
本書要講述的,是族群認同如何從傳統時代至當代形成和演變的歷史。我關注的群體是臺灣的客家人,他們在近年來臺灣社會政治和學術轉向的潮流中,已經日益成為一個「顯形化」的群體。而反觀歷史,臺灣社會從清代以來經歷了三個不同國家政權的治理(清帝國、日本、中華民國),這一特殊歷史經驗對於客家族群認同形成的影響,便是本書的主題。
為了將這一關心落實到具體的地域社會脈絡中,我選擇臺灣南部的六堆地區作為研究地點。這是因為該地號稱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客家聚落,目前亦是除了北部桃竹苗地區之外的第二大客家聚居區。不過,「六堆」並不是一個可以在地圖上找到的地名,它其實是大高雄市及屏東縣境內十二個鄉鎮的合稱,分為前、後、左、右、中及先鋒六個不同的堆,每堆包含一至數個鄉鎮。其地域名稱的由來與清代當地人士組織的軍事性地域聯盟有關,現在地方人士還可以清楚分辨不同地域的堆別。
六堆的客家節慶
在六堆地區,現在每年都會舉辦盛大的「六堆嘉年華」活動。在今天的臺灣,節慶活動已經成為展演族群文化和認同的重要方式,這一活動亦不例外,還被歸入臺灣「客庄十二大節慶」之一。2006年10月,我曾赴當地參加首屆「六堆嘉年華」活動,試圖了解當地人用何種方式表達自己是客家人。我發現其中展示出來的豐富地方歷史文化元素,正是回答我關心問題的切入點。
我所參加的首屆「六堆嘉年華」,整個活動為期近十天。它主要由四大部分活動構成,其中最重要的兩部分,一是六堆忠義祠忠勇公出巡繞境活動,二是六堆運動會。此外則是由十二個鄉鎮分別舉辦的文化產業活動,以及屏東縣政府主辦的昌黎祠韓愈文化祭。
整個活動的重心,是圍繞六堆忠義祠進行的。它位於中堆屏東縣竹田鄉境內,是當地歷史最悠久的廟宇,始建於康熙末期。「忠勇公」則是這座廟宇的主要拜祭對象,也是當地人對清代曾協助清廷平亂的「義民」的稱呼。此次嘉年華活動最重要的典禮――第四十二屆六堆運動會聖火引燃及嘉年華忠勇公出巡起駕典禮,便在此舉辦。
典禮當日,我見到著藍衫白帽的廟方管理人員和工作人員、著灰色長衫的禮儀人員、白衫藍褲的當地鄉鎮長,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員和議員等,均齊集廟中進行祭祀。其後,地方人士將忠勇公迎至廟外的神轎上,我注意到迎出來的並非是一般廟宇常見的神像,而是一面中間寫著「六堆忠義祠先賢先烈之諸神位」的黑底金字牌位。隨後,聖火亦在廟中的香爐燃起,由各堆鄉鎮長舉起火炬進行接力,拉開了為期一週的忠勇公繞境和聖火傳遞的序幕。
其後,我在來自竹田鄉的葉先生一家幫助下,跟隨繞境隊伍走過了高屏一帶屬於「六堆」範圍的十餘個鄉鎮。整個繞境隊伍由一列蜿蜒了百餘公尺的車隊構成,隊伍前面也有一輛載著神轎和香案的小貨車,車上插著上書「六堆忠義祠忠勇公」黃底紅字的三角旗幟,一路亦伴隨著音樂和鑼鼓聲,與一般臺灣地方廟宇常見的神明繞境活動頗為類似。然而,它又和一般的繞境隊伍頗為不同,走在車隊最前面的並非神轎,而是一輛白色的「聖火車」;緊隨其後的也不是八家將、電音三太子等臺灣社會習見的陣頭,而是十幾輛由鮮花、燈光和各種裝飾物妝點的花車,上面寫著六堆當地各鄉鎮的名字,幾部車身上還寫著「六堆運動會」字樣。尾隨花車的,則是大小不一的私家轎車,葉先生一家的車便是其中之一。
如果我們把節日和儀式作為社會集體記憶的展現方式的話,早在數十年前,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等便曾提醒我們,社會記憶是一個不斷有意識地選擇的結果,某些古老或晚近的傳統會被挑選出來進行重構,原因乃是出於當代的需要。在六堆嘉年華精心選擇的傳統活動背後,展現的無疑是塑造「客家」的當代需要。我在六堆地區進行調查的時期,正是臺灣客家族群意識建構如火如荼的時期。所到各鄉鎮,我發現當地人亦會很自然地談起「我們客家人」,顯示「客家」族群認同已經具有廣泛基礎。而2005年我曾參加的忠義祠秋祭活動相比,最大的不同,便是國家力量已經深深介入,整個活動的大部分經費由民進黨執政之後次年成立,且宣稱以振興客家文化為目的的國家機構――客家委員會(當時名為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資助。此次的忠勇公出巡繞境活動,亦是六堆有史以來的頭一遭。
那麼,那些古老或晚近的傳統,又經過了怎樣的重構過程呢?一個跨越了清帝國時代、日本時代和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時代的地方禮儀集合,顯示出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之下,對於「六堆」的地域認同,堅韌地延續下來。然而,忠義祠和忠勇公拜祭,形成於六堆客家人的祖先被稱為「粵人」、「客民」的清帝國時代;運動會則可以追溯到他們被稱為「廣東種族」的日治時期。我們不禁好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地方人士透過禮儀拜祭要表達的是怎樣的認同?在客家族群意識興起的時代,為何它們可以迅速被整合進新的認同框架?
臺灣客家研究的脈絡
對於當代臺灣社會客家族群意識的晚近性,社會學家已經做了精闢的分析。王甫昌便曾指出,臺灣社會分為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和原住民四大族群的說法,實際上是上個世紀90年代才萌生的,它是將歷史上不同時期的分類方式,即原住民與漢人、本省人與外省人、閩南人與客家人的區分,放在同一個平面上的結果。在此基礎上,王甫昌認為「客家」族群認同亦是一種現代性的「想像」,是1980年代後期開始的客家社會運動動員的結果,這種想像所預設人群之間的關係,是以現代國家的公民權利為前提,而一些客家文化運動的訴求背後,實際上是針對臺灣走向民主化與本土化之後,來自強勢閩南文化的壓力,他將這種新的認同稱之為「泛臺灣客家認同」。80年代後期,臺灣興起客家族群運動,其最開始便是以保存「客家母語」,防止客家文化流失的方式,演變為愈來愈有實力的政治力量,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設置便是表徵之一。
不過,一個新興的族群建構之所以能夠如此迅速地滲透到地方社會,絕非一日之寒。我們可以想像,在臺灣社會內部,早已存在某種具有共性的認同觀念,當族群觀念進來的時候,這種認同觀念便被置入新的認同框架。事實上,王甫昌等社會學家也沒有否認,三百年前左右移入臺灣的客家人後代,在臺灣社會的歷史經驗(經過清朝、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中,已經形成某種「歷史基礎」。
試圖將歷史因素與當代族群進行連貫融通的,主要是臺灣歷史學、人類學、地理學及文學等領域學者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有幾種不同的回答方式,其中一種認為客家身分認同是移民從「原鄉」帶來的,在來臺之前,他們已經具有共同的語言、居住環境、信仰習俗及維生方式等。換句話說,他們在來臺灣之前便已經是客家人。最具理論色彩的敘述,是上個世紀末歷史地理學家施添福做出的,他發現客家移民到臺灣之後,多在靠山地區居住,以務農為主,在與「原鄉」相似的地理環境和生計方式之下,延續其客家認同。這樣的研究取向,在六堆地域研究中亦有所體現,如簡炯仁和施添福對於南部高屏地區的研究,均試圖對「客家」社區與「福佬」社區的差異提出解釋,前者認為二者拓墾路線的不同,聚落分布上亦逐漸呈現出族群差異。後者則從二者生計方式和社會結構的差別,提出了務本的「客家」社區與逐末的「福佬」社會的對照。林正慧對於清代六堆整體的歷史,做了最為深入而細緻的研究,其中便花兩章篇幅,探究客家人來臺的背景和路線,亦具有說服力地證明了他們本來便具有共同的來源和認同。
這種想法並非沒有所本,事實上,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羅香林等歷史學者便已經在建構一個理想化的「原鄉」客家人圖景了。在這幅圖景中,客家人具有文化上的共性,他們是由晉代以來,從中原地區經歷數次南遷過程的漢民族中的一個支系,融匯吸納南方不同群體而形成。他也具體勾畫出客家人「原鄉」分布,其核心地帶便在中國大陸福建、廣東及江西三省交界的地區,幾個省下面的縣級行政單位,被按照語言、來源等劃分為「純客縣」與「非純客縣」。他的研究在戰後的臺灣,便已經具有一定的影響力,1970年代以降,陳運棟更在其學說基礎上系統地加以引申,使得其客家觀念在臺灣社會得到更為廣泛而深入的傳播。早期學者在進行研究時,亦常假定客家人具有來源和文化上的共性,不過近年來隨著區域研究的深入,這一觀念已經漸漸修正。
至於作為共同文化因素之一的客家語言,它無疑是從原籍帶來的,並影響臺灣社會的群體劃分。早在1960年代,人類學家孔邁隆(Myron L. Cohen),與同時期的人類學家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便曾經在臺灣南部的六堆客家地區村落進行調查。他們意識到這些社區內的群體是客家人,而且講不一樣的語言。不過他們真正關心的,乃是透過這一群體所展現的漢人社會整體結構問題,尤其是要和英國人類學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對於中國東南沿海宗族組織結構和功能的研究對話。在1960年代末,孔邁隆在考察清後期,中國兩廣地區客家話與廣府話群體械鬥的歷史後,提出一個新的見解,即試圖將語言的差異變成一種分析工具,作為當時學者關注的宗族、地緣等差異之外,影響地方社會組織方式及區分社會群體的變量之一。 語言的差異性並未根本動搖漢人社會的整體性,其背後同樣隱含原籍與臺灣人群存在連續性的假設。
另外一種回答,則強調臺灣社會特殊的歷史經驗,對於客家認同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人類學家莊英章、羅烈師、賴玉玲等人的研究,便尤其關注北部新竹枋寮義民廟與客家地域社會建構的關係,羅烈師便認為十九世紀後期北部新竹地區已經形成以「粵人」表達的人群認同。基於竹塹地區政治、商業及拓墾空間分布等因素,人群組合最後形成以祖籍為界的狀態。他也具體分析廟中供奉對象的階序結構,如何與義民廟的財產管理體制結合,從而將祭典區內宗族和廟宇背後的人群,整合進一個龐大的信仰體系內。這一廟宇統合北部廣大地域的客語人群的背景和具體過程,也得到細緻的描述。
這一關懷背後,其實也繼承了人類學家對於臺灣漢人社會研究的傳統,即關注祭祀活動與地域組織的關係。其理論基礎可以追溯至用祭祀圈、信仰圈等概念研究臺灣民間信仰活動,「祭祀圈」由日本學者岡田謙提出,目的是為了將聚落中見到的寺廟,與人們的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聯繫起來,從而分析二者之間的關係。在1970年代臺灣社會科學興起的年代,這一理論引起臺灣學者很大的興趣,並應用到具體的地域研究中,後來亦不斷發展出修正性的理論。而近年來西方族群理論的發展,尤其是巴斯(Fredrik Barth)與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關於族群與民族建構過程的論述,也影響臺灣學者。前者將族群去本質化,認為應在社會組織及其關係中,觀察在不同群體接觸地帶個體的認同歸屬。後者則將民族視為想像的共同體,是現代社會政治、文化和物質條件的產物。
近年來,學者則日益認識到客家族群的建構性。這一轉移既是臺灣學科自身深化的背景下,對於之前不假思索地將客家族稱套用在歷史上的不滿,亦與客家意識高漲之後,試圖用更精緻的定義重新審視歷史上的人群分類有關。李文良對於清代康熙至乾隆時期六堆的研究,深入反思歷史上的「客」和今日客家的關係。他注意到清初有關「客民」的記載,歸納起來意味著祖籍潮州府(當時的潮州府包括雍正年間分治出來的嘉應州),維生方式以佃耕、傭工為主,並且健訟樂鬥。這與今日族群意義上的客家之間存在很大的距離。同時與一般臺灣史上的理解不同,他認為六堆客家人的先祖們早就先於閩南業主在當地生息了,雖然閩南地主們更易於憑藉與官府的關係取得地權,但是康熙時期地方經濟成長的成果主要由客家人獲取。康熙後期有關「客」、「客民」及「客仔」負面形象記載的大量出現,便與閩籍地主們對於社會結構變化的普遍焦慮有關。隨後,客語群體主要透過「義民」身分及科舉制度下的祖籍認同,不斷改變著自身的身分和認同。這一細緻深入的研究,為地域族群研究提供了更具反思性和動態的視角。
施添福在其最新的研究中,也試圖回答「客家到底是什麼」的問題。為了從名詞上追索「客家」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流傳過程,他首先將眼光轉向了中國,指出這一詞彙主要是在連接兩地的東江流域地區衍生和流傳。他也從國家制度、西方人書寫和民間口語等面向,勾勒了臺灣不同時代人群指稱的變化,以及「客家」一詞傳入和取代傳統詞彙的過程。林正慧的專著,則從歷史學的角度,對於清初至戰後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做了最為豐富和完整的文本追溯。她同樣首先追溯中國華南客家形塑的歷程,並細緻考察不同地域與方言人群移民臺灣後的情況,指出清代以來,方言一直是臺灣漢人分類的界線,然而清代其與省籍分類交錯,日治時期則透過國家的力量,以一省對應一種方言的認知方式,排除了清代省籍問題的干擾;戰後,客家方言群體則與華南經驗銜接,將自己重新定義為客家。
從這幾種回答方式上,可以看出學者們對於客家人的理解方式有很大的差異,它反映了在族群研究上學術範式的轉移。不過,這一轉移與其說反映了歷史解釋力的強弱,毋寧說是學者關注面向的變化:歷史學者在強調客家人共同來源時,並未否定他們在臺灣的共同經驗對認同有影響;人類學者在研究客家人在臺灣的共同經驗時,也沒有否認他們在來臺之前,在語言與生活上已經有互通的想法。而近年來的最新研究,在強調族群建構性的同時,也已經日益關注到國家(尤其是清帝國之下)行政制度和人群分類方式,對於地方人士認同的影響,因此,土地制度、租佃關係、學額問題及人口調查等,紛紛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國家、他者及我群觀念的差異,亦日漸受到關注。
以上研究無疑深具啟發性。然而在我看來,更為重要的,是臺灣歷史上具體地域社會的客語群體,如何在將地域認同和不同國家意識結合的過程中,逐漸接受和表達其客家族群自覺意識。事實上從清初客家人大量來臺以降,臺灣社會經歷了幾個國家轉變的特殊歷史經驗:清帝國曾經治理臺灣兩百餘年,近代以來崛起的日本,則曾經治理此地半個世紀,中華民國迄今亦治理達七十年。環顧整個東亞地區,雖然由眾多來源不同、形態各異的政權統治的經驗並非鮮見,但是尚無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與臺灣有著完全相同的軌跡。探究這一特殊經驗對於地方社會表達族群身分認同的詞彙,以及文化象徵上的深遠影響,不但有助於我們反思臺灣客家族群的建構過程,亦有助於觀察和比較它有別於中國及東南亞地區客家論述的根本原因。
國家與族群
如何處理從傳統政權至近代國家之下的族群建構問題,不同研究者亦有歧義的看法。有的學者認為將當代的學術概念引入歷史,有以今度古之嫌,詞彙轉換背後亦缺乏足夠的學理支持。如柯嬌燕(Pamela Crossley)便曾批評中國學界「族群」概念的流行,往往是之前「種族」、「少數民族」等概念替代物的反證。 有的學者則認為不同語言文化群體之間的差異既然已經存在,用族群概念進行分析並無不妥,韓起瀾(Emily Honig)關於上海蘇北人的研究便指出漢人的籍貫背後,其實隱藏著族群性。如何在前近代的人群分類和當代族群分野之間,建立歷史的連貫性,對於歷史學者而言的確是一大挑戰。
近二十年前,澳洲歷史學家梁肇庭對於客家族群的研究,為傳統至近代客家族群認同的建構,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他主要受到社會學家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人類學家巴斯族群理論的影響。人類學家關注「我群」和「他群」的差異與互動,並試圖把二者接觸的關係模式演化為族群分析概念;而社會學家則試圖在歷史中對於不同類型的群體認同,進行有意義的類型劃分。帕特森便曾經在1975年一本影響深遠的論文集中,以加勒比海的兩個中國人群體為例,提出他對於族群的看法。在他看來,一個群體有意無意地共享文化傳統,只能算是「文化的」群體,而只有當他們彼此接觸時,這些共有的標記被有意識地拿來增進內部團結,才能算是「族群的」。這種自覺意識存在與否,是判斷族群存在與否的關鍵要素;而文化群體中的某一部分變成了族群,亦不代表全體變成了族群。
深受帕特森影響的梁肇庭,便將其觀點引入了中國華南的客家研究,提出應該將「自覺的」客家族群,與尚沒有族群自覺意識的客家文化群體區分開來。事實上,他的專著可以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在討論華南一帶客家人如何從文化群體演變為族群,強調自覺意識衍生的過程;第二部分討論中國社會贛江流域、長江下游及漢水盆地棚民的際遇,則小心地避開使用「客家」的字眼。同時,作為著名中國市場體系研究者施堅雅(William Skinner)的學生,他也試圖從市場理論出發,將客家族群現象放到幾個世紀以來,中國內部區域經濟變遷與內部移民潮流的互動中去考慮,強調經濟因素是其移民的動因,而區域經濟週期的變化,亦影響他們和本地人關係的平和與否。
梁肇庭認為,傳統帝國時期的客家,可以視為是一種文化群體的建構。講客家話的人雖然一直在南中國大量存在,但他們被標籤和逐漸認同於「客家」,是在與其他語言群體的不斷接觸和衝突中形成的。明末和清初,客家人開始從廣東東北的山區向東江中下游移民。至十九世紀,當大量粵東客家人從山區向嶺南地區移民的時候,與同省講粵語的群體密切接觸,才導致客家人文化特性逐漸建立,而透過對於科舉成功的原籍梅州的建構,這一群體強化了對於共同來源和文化的認同。 客家族群自覺意識的衍生,則與晚清至近代以來,中國廣東區域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巨變有關。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民族主義興起時,客家族群意識亦開始在粵東客家知識分子和政治菁英群體中產生,它和民國政治緊密相關。但那些粵北、閩西乃至贛南同樣講客家話的人群,卻鮮有這樣的概念。
在我看來,這樣一種研究視角,在今日的族群研究中,應當是一種理解的前提,而非結果。在此基礎上,重新思索傳統國家至當代社會的巨變過程中,國家建構因素對於族群認同的影響,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值得進一步探究。
首先是作為行政和法律體系的國家,其所具有的人群分類觀念和戶籍登記制度,對於地方社會我群表達詞彙的影響。在明清之際社會秩序屢次巨變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國家是牽引這一變化的最關鍵力量,其影響不只表現在社會秩序建立與否,也表現在族類劃分的層面上。陳春聲近年來的研究,便將對於明清之際中國東南沿海地方社會變化的關注,延伸到廣東韓江流域的族類劃分上。他指出十五至十七世紀粵東地區的社會變遷,使得大量「畲人」、「猺人」和「蜑人」轉化為朝廷的編戶齊民,活躍於崇山峻嶺間的「山賊」、「流賊」及其後代亦逐漸納入官府的管治,清代該地「客家」社會的建構才成為可能。而康熙初年對沿海居民實行的「遷海」政策及其隨後的「復界」安排,對韓江流域不同語言群體的關係有著深遠影響,正是解除海禁之後臺灣大規模的開發,讓該流域上下游的群體均大量來到臺灣,不同群體的密切接觸,亦使得語言差異的感覺被凸顯出來。
同樣,將這個幾乎是客家人前史研究的視角,向其後的歷史脈絡延伸,便會發現曾經治理臺灣的清帝國、日本帝國和中華民國政府,都具有人口調查的概念,雖然清帝國之下實施的狀況頗為有限,日治時期及戰後卻建立了極為完整的戶籍制度,其中亦體現了族類劃分的觀點。而不同國家之下的制度安排和其所引起的社會變遷,同樣深深影響地方人士表達身分認同的詞彙。在清帝國之下,臺灣地方社會講客家話的群體,便必須透過強調自己的省籍身分(無論是粵還是閩),才能夠符合國家的觀念和制度安排;而在日治時期,西方種族觀念則與傳統省籍觀念妥協,創造出不同於中國的族群概念,即「廣東種族」;戰後省籍觀念再次復興,背後卻帶有強烈的族群色彩。對於地方人士而言,其認同無疑多元且視不同情境而變化,而當國家是其生活和意識中最為龐大而無法忽視的「他者」時,選擇契合國家觀念的詞彙來表達身分認同,便成為不同國家之下具有理性的策略性選擇。
其次,國家不僅是行政治理的單位,更是一種演化中的文化理念集合體。它影響地域文化的表現形式,亦影響地方社會人士的自我認同觀念。這一觀念可能表現為地域文化的差異,亦可能被視為是一種族群上的差異。關於這一點,近年來中國華南地域社會史的研究最富有啟發性。其研究顯示,這種文化理念經過數個世紀的發展,已經深深嵌入地方人士的意識當中,形成一種中國文化「大一統」的結構。這並不意味著地方社會的差異性逐漸消弭,實際上,地方社會不同歷史時期文化符號和意識形態的疊合交錯,正是這一結構的一體兩面,在地方社會千差萬別的禮儀拜祭中,在地方人士獨特的身分認同中,都可以找到作為文化理念的國家影響痕跡。 這並不是中國社會獨有的現象,近代以來英、法等民族國家的建構,便顯示出那些具有象徵意義的禮儀或傳統習俗活動的重要性,而它們往往是出於民族的目的,而逐漸被有意識地調整、儀式化並制度化。
反觀十七至二十世紀的臺灣,曾治理臺灣的三個不同政府,亦建構不同的文化大一統圖景,在臺灣族群意識的表達上也有所展現。陳春聲對於臺灣三山國王信仰傳說及分香系統的研究,便具體展示了臺灣社會該流域的移民如何透過這一信仰,表達正統意識和國家觀念,以及以祖籍為基礎的分類意識。而六堆嘉年華背後隱含的、不同歷史時期疊加的禮儀,亦是最佳例證:六堆忠義祠的建立和忠勇公拜祭,可以上溯到曾治理臺灣兩百餘年的清帝國時期(1684-1895);六堆運動會和聖火傳遞活動,源頭則可以追溯到在臺灣持續半個世紀的日治時期(1895-1945);而運動會的聖火由忠義祠點燃,則是中華民國政府時期(1945年至今)的事。在這個客家族群節日的背後,其實亦是一場複數的國家意識展演。它往往被視為是「地方性的」、「族群性的」,但是回溯其歷史,每一個禮儀和人群分類概念的形成背後,均浸染著當時國家意識形態和分類觀念的影子。
進一步而言,正是透過具有強烈國家意識的廟宇忠義祠,六堆地方人士才能表達自己是客家人。從忠義祠牌位的不斷變化,不難窺見國家意識對於地方社會的影響。今天的六堆忠義祠,正殿中央最核心的牌位為「敕封六堆歷代忠勇公王之神位」,媽祖與土地公的牌位亦進入廟中。不過2005年我初次去調查的時候,廟中正中擺放的乃是「中華民族列祖列宗神位」。再回溯上去,清代立廟之初供奉的牌位實際上是「大清皇帝萬萬歲」,至日治時期則演變為「天皇陛下萬萬歲」,戰後初期則曾變為「中華民國萬歲」!人們往往將拜祭義民視為客家族群與其他群體存在差異的文化特徵,事實上,這一特徵恰恰是在將地方社會歸納進曾經治理臺灣的不同政權過程中形成的。這樣一個歷史過程背後的社會結構和演變與國家的關係,是理解其認同變化的關鍵。
再次,族群自覺意識的衍生和傳播,與從傳統帝國向近代國家的演變過程,以及民族主義及相關社會理論在其中的傳播和擴散,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學者們對於族群與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以來,民族主義從美洲發源、在歐洲壯大和擴散,並影響至亞、非等地的過程,以及與近代民族國家的關係,已經做了深入的研究。在研究者看來,近代以前雖然存在族群及族群特性,但它們和民族國家的建立並沒有直接關聯。民族的近代含義,是十九世紀以來形成的。而十九世紀末的民族主義與之前存在極大差異,族裔和語言成為界定民族的重要標準,因為當時才發展出具有影響力的生物學理論或偽理論,可以說明彼此之間的關係。與之相伴隨的,則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民族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廣泛傳播。學者們雖然並沒有否定特定族群或民族與之前的歷史關聯,但更強調對其共同的來源、語言文化,甚至血統的「想像」,與其對於近代新興國家的因應之道有關。在同一時期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客家族群意識的興起,也正是與西方種族觀念的傳入、民族主義的興起和近代國家的建構同步。程美寶對於廣東地方文化的研究,便揭示了在近代民族主義興起的背景下,廣東地區學術與族群意識建構之間的關聯:西方種族主義思想的傳入,使得在城市地區活躍的客家知識分子,將客家族群塑造聯繫到其作為漢人的血統及文化優越性上。地方族群和文化的塑造,與知識分子對於新的民族國家想像息息相關。
就臺灣而言,清帝國之下特殊的開發歷程,已經使得客語群體的地方文化和認同,與其祖籍地華南社會存在差異。而在中國東南沿海客家族群建構風起雲湧的時候,臺灣已經處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而走上不同的近代化道路。借用按照安德森的話來說,殖民地下的社會建構,不但催生了臺灣人意識的衍生,亦使得一個臺灣「客家」(儘管當時用的詞彙是廣東種族)的想像形成,只是它更大程度上和語言文化聯繫起來,血統色彩則頗為淡漠。而血統色彩強烈的所謂「中原客家」族群觀念,則是在進入二戰末期以及戰後,才逐漸深入臺灣社會。帕特森亦已經指出,一個群體中部分成員具有了族群意識,並不等於整體具有了這一意識。在臺灣客家族群運動興起之前,這一自覺意識亦帶有菁英群體的色彩,這一群體是在日治及戰後時期逐漸擴大的。這一群體與不同國家理念之下的民族主義及族群建構的關係,同樣值得進一步探討。
在本書中,我要強調的是客家人在臺灣的經驗,除了可以用語言、祖籍、地域社群等變量進行衡量外,亦包括不同時期治理臺灣的國家對於地方社會的影響。在我看來,國家既是行政治理的機構,同時也是文化理念的集合體。族群意識並不是一種地方性的、和國家相對的分析概念,恰恰相反地,它的衍生和表達,深深地植根於不斷變化的國家意識當中。它並不僅僅透過制度性因素表現出來,亦透過禮儀和象徵表現出來。不同國家之下的禮儀和文化元素,如何被臺灣六堆地方人士巧妙地、選擇性地納入歷史記憶的框架,成為晚近表達客家認同的方式,便是我感興趣的問題。
本書從一個具體的地域社會出發,關懷的是地方人士如何以納入不同國家為機制,創造其獨特的身分認同。這也體現了歷史人類學的研究旨趣,因為對於歷史學者而言,將田野調查和文獻分析相結合,將國家制度研究和地方基層社會研究相融匯,其目的乃是為了從國家制度和國家觀念出發,「理解具體地域中『地方性知識』與『區域文化』被創造與傳播的機制。」 臺灣六堆便是一個在長期的時空脈絡中,族群認同在不同國家下形成和轉變的實證個案。透過這一研究,我希望不僅是勾勒出一個臺灣客家族群認同形成過程的故事,亦能夠為重新思考帝制時期到當代的族群塑造,提供一個具體的參照。
第一章 導論:六堆地區的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節錄)
本書要講述的,是族群認同如何從傳統時代至當代形成和演變的歷史。我關注的群體是臺灣的客家人,他們在近年來臺灣社會政治和學術轉向的潮流中,已經日益成為一個「顯形化」的群體。而反觀歷史,臺灣社會從清代以來經歷了三個不同國家政權的治理(清帝國、日本、中華民國),這一特殊歷史經驗對於客家族群認同形成的影響,便是本書的主題。
為了將這一關心落實到具體的地域社會脈絡中,我選擇臺灣南部的六堆地區作為研究地點。這是因為該地號稱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客家聚落,目前亦是...
作者序
代序 客家認同的民族誌研究:讀《族群與國家》(節錄)
王甫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臺灣客家研究在過去十年中有相當大的進展。
過去清代的各類地方志記載許多「客人」、「客庄」、「粵人」、「粵庄」情事,日治時期日人對於「廣東種族」的風俗民情也有頗多記載及詳盡的人口統計,甚至包括漢人祖籍的鄉貫調查。然而,戰後初期卻因為多數臺人經過日本統治後,對於中文與中文古典文獻已經不熟悉,以及國民政府在「去日本化」政策下,對日語與日文文獻的排拒與禁限,以及「再中國化」政策對本地社會的刻意忽視,而使得多數具有客家背景者對自己祖先來臺拓墾與發展的歷史,僅有口語傳說的模糊印象。雖然在1960年代就已經有大陸來臺的客家人透過《中原》雜誌,引介1930年代在中國大陸出現的客家研究(以羅香林的《客家研究導論》為代表),但是這些研究主要介紹的是臺灣客家人的大陸原鄉人物與情事,對於臺灣本地客家的認識與理解幫助相當有限。
1970年代初期,六堆客家人士鍾壬壽曾透過整理有限的歷史文獻(中、日文都有)、親身的田野調查、及對各鄉鎮現況的問卷調查,出版《六堆客家鄉土誌》,是目前比較為人熟知的戰後最早臺灣本地客家研究。透過對於具有長遠歷史發展的地域社會「六堆」地區的研究,以及對於客家人幾次大遷移的歷史溯源(主要是羅香林的論述之影響),本書代表有客家身分意識的文化菁英,建構區域性客家社區歷史的重要文本。其內容也在後來出版的《六堆》集刊中一再被引述。1978年,苗栗頭份客家人士陳運棟也曾在類似影響下出版《客家人》一書,並在1980年代主編《三臺雜誌》。在早期學院內學術研究幾乎都不處理臺灣本地歷史與文化課題的情境下,這一類鄉土誌文獻,成為表達本土性認同的重要、但隱幽的管道之一。
1980年代在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浪潮下,臺灣研究開始引起較多關注。本土意識的上升,使得探究過去一直被忽略的臺灣歷史、語言、與文化,成為新的文化現象。而臺灣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也在此時開始引介西方學界族群關係研究的分析概念、詞彙與理論,探討臺灣各類族群關係問題。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對於族群關係的研究,主要是關注於當代族群團體之間在各種權力與資源分配的不均衡現象,以及試圖改變這些不平等結構關係的集體行動如何能出現及其影響。換言之,雖然社會科學研究者大多同意「族群團體」(或族群類屬)的界定,必然有其文化與歷史的淵源,但是這些研究的分析焦點,通常是聚集在「現在」(的不平等現象)與「未來」(如何創造一個比較平等的制度性安排),也因此對於族群團體(或類屬)「過去」(包括群體或認同的起源與變遷)的探究,相對缺乏與不足。更重要的是,由於過去沒有相關研究,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中期所出現的臺灣族群關係研究,大多是直接引用西方的分析概念與理論性解釋或問題意識,並套用到臺灣的情境與個案上,而尚無能力去反省這些分析概念與理論,背後對於社會既有結構的預設,是否適宜於臺灣狀況的問題。而臺灣多重而複雜的各類「族群關係」,更增添這些研究在臺灣進一步深化的困難。
在這種狀況下出現的客家族群關係研究,尤其具有挑戰性。相對於「原住民/漢人」、或是「本省人/外省人」的族群關係研究,有相當明顯的當代權力及社會與經濟資源不平等面向,「客家族群」所面臨族群不平等面向,除了作為「本省人」(相對於「外省人」在民主化之前的不對等權力位置)的一部分之外,尚有「本省人」內部相對於福佬(閩南)人的不對等部分。然而,臺灣客家人作為人口或政治權力分配上的少數人,並非社會經濟地位上的少數或弱勢者(其整體教育成就與經濟地位甚至在福佬人之上),其所面臨的族群不平等問題也和其他本省人不盡相同。文化或語言特殊性的保存、歷史記憶的尊重、族群身分與族群尊嚴的認可,對於臺灣客家人來說可能是更為重要的族群問題。尤其是1970年代以後,在現代化及工業化的趨勢下,愈來愈多客家人離開原本居住的、客家人占有絕對多數人口的客家村落或客家鄉鎮,而進入到與其他族群混居的都市社區後,使用客語的機會大為下降,許多客家人隱藏自己的身分,客語能力在世代之間的逐步流失問題愈發明顯而急迫。臺灣客家人最擔心的問題是,作為其族群身分獨特標記的客家語言與文化面臨消失的危機,而不僅是變成「隱形族群」而已,甚至有族群消失的危險。而在臺灣民主化與本土化轉型的過程中,客家語言、文化、與歷史記憶的特殊性,並未得到對等的重視,更讓許多客家菁英憂心忡忡而發起客家文化運動。1990初期以來的客家族群關係研究,似乎已經相當清楚地點出這項特殊性。這項客家族群關係或族群問題的特性或許能夠部分說明,為何當代客家研究中一個重要主題是客家語言、文化、歷史及客家認同形成的研究。
1980年代末期客家文化運動的出現,使客家族群的訴求逐漸受到主要政黨的重視,而以提出客家文化政策或組織性建置回應。在2000年首度政黨輪替之後,中央政府在制度上的一個重要的回應是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另外,在多所大學內也紛紛成立客家研究中心,以及在桃竹苗地區的大學分別成立三個客家學院。這些高等研究機構中的客家教學與研究機構的設置,帶動了新一波客家學術研究的風潮,也吸引了不少優秀的新生代學者投入客家研究。
相對於早期的客家文化運動者或文史工作者不全然以學術研究格式書寫客家研究,或是客家文化運動出現後原先並不研究客家的學者開始進入客家學術研究的領域,這些新生代的客家研究者,從學生時期就開始閱讀客家相關文獻與研究,絕大多數也以客家研究的題目完成碩士或博士學位論文。這些新一代的研究者有幾項值得注意的特色,第一,由於在研究及撰寫學位論文時期,就已經投入客家研究,他們往往能在反省既有研究發現(特別是臺灣本地的研究)或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更深刻、以及更能契合本地社會需要的研究問題。第二,他們往往挖掘或運用更多新出土的史料,來進行研究。過去比較難以獲得的各種史料,特別是日治時期大量文獻與檔案,也在首次政黨輪替後,本土化意識逐漸成為政策及資訊更為公開流動的時期,大量出土或翻譯出版,而能為臺灣研究者所用。第三,這些新一代的研究者往往能夠運用不同傳統學科領域中已經發展成熟的方法、理論、研究工具、與基本訓練,包括人類學、歷史學、語言學與社會學,來進行客家研究。雖然傳統上不同學科領域之間因為預設與問題意識的不同,很少能夠進行有效對話,但是「客家研究」的共同專注,卻讓不同學門領域有了對話的平臺與可能性。總體來說,新一代研究者的出現,意味客家學術研究成果已經通過既有學術體制的檢驗,也讓客家研究的體制化與深化,邁進一大步。過去十年來這些新的客家學術研究成果已經逐漸出版,呈現在讀者面前。
陳麗華博士這本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的《族群與國家: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1683-1973)》,正是這一波學術研究潮流下,最新的客家研究成果之一。本書採取歷史人類學的觀點與方法,試圖描繪及說明臺灣六堆地區的客家族群認同,如何由清代、日治、到戰後民國統治的三個政權時期,將近三百年的時間中逐漸演變與形成的過程。本書特別強調「族群」與「國家」之間的互動,包括國家行政與法律體系中隱含的人群分類概念與登記制度、國家作為大一統的文化理念集合體,以及國家的現代化等因素,對於地域社會中人群分類概念的衝擊。而本書以高屏地區的六堆客家地域社會作為研究對象,亦展現歷史人類學非常獨特的研究觀點。透過歷史材料的重新耙梳與整理,陳麗華所完成的民族誌清楚地呈現六堆的起源,以及六堆客家文化菁英在不同歷史時期,面對不同政權與國家法制,如何在傳統的文化、生計與社會組織的基礎上,找到足以維繫六堆地域認同的制度或文化創新。
這本書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以民族誌的方法描繪六堆地區在不同歷史時期下的變化。透過各類歷史材料的蒐集與整理,將具體的人物行動與反應鮮活地刻畫出來,但是又往往經過不同材料的交叉比對分析,而不致流於只是當事者的片面說詞。這些嚴謹的鋪陳與論證,往往是以流暢而引人入勝的敘說方式進行,而不會流於一般學術論文的艱澀。這充分展現歷史人類學取向的優點。而更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本書的分析主體是六堆社會,但是作者經常會引用臺灣北部桃竹苗客家社會、或是中國廣東客家原鄉的狀況來做比較,以突顯六堆的特色,例如比較六堆忠義祠與新竹義民廟在日治時期興衰的不同境遇。這是一本論證嚴謹、又有相當可讀性的著作,值得向客家研究、臺灣研究的學者,以及一般讀者推薦。
代序 客家認同的民族誌研究:讀《族群與國家》(節錄)
王甫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臺灣客家研究在過去十年中有相當大的進展。
過去清代的各類地方志記載許多「客人」、「客庄」、「粵人」、「粵庄」情事,日治時期日人對於「廣東種族」的風俗民情也有頗多記載及詳盡的人口統計,甚至包括漢人祖籍的鄉貫調查。然而,戰後初期卻因為多數臺人經過日本統治後,對於中文與中文古典文獻已經不熟悉,以及國民政府在「去日本化」政策下,對日語與日文文獻的排拒與禁限,以及「再中國化」政策對本地社會的刻意忽視,而使得多數具...
目錄
代序 客家認同的民族誌研究:讀《族群與國家》/王甫昌
第一章 導論:六堆地區的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六堆的客家節慶
臺灣客家研究的脈絡
國家與族群
六堆地區的環境與開發
第二章 六堆地域社會的形成
庄與嘗會
六堆地域聯盟的形成
忠義亭的拜祭結構
省籍與學額
「土」、「客」之別
結語
第三章 殖民地下的種族塑造
六堆的收編
土地與水利政治
改奉天皇
從籍貫到種族
結語
第四章 從傳統走向近代
小學生的背後意義
紳章背後的資本流動
一體化之下的禮儀
再祀明治
語言學的關懷
結語
第五章 新興階層的自覺意識
新領袖,新舞臺
香蕉通海外
新興的傳統
忠義亭之外的運動會
都市裡的自覺意識
結語
第六章 戰爭時期的民族建構
戰爭陰影下的鄉村
統制下的空間
廢廟危機
聖火與庄葬
民族主義還是殖民主義?
結語
第七章 融入民族國家
戰後初期
資本變動與土地改革
六堆運動大會
從忠義亭到忠義祠
「客家」觀念的興起
結語
第八章 結論:從清帝國、殖民地到民族國家的族群認同
清帝國下的人群分類與族群認同
晚清至日本殖民帝國下的客家族群塑造
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交織
後民族國家時代的禮儀、族群與認同
後記
參考文獻
索引
代序 客家認同的民族誌研究:讀《族群與國家》/王甫昌
第一章 導論:六堆地區的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六堆的客家節慶
臺灣客家研究的脈絡
國家與族群
六堆地區的環境與開發
第二章 六堆地域社會的形成
庄與嘗會
六堆地域聯盟的形成
忠義亭的拜祭結構
省籍與學額
「土」、「客」之別
結語
第三章 殖民地下的種族塑造
六堆的收編
土地與水利政治
改奉天皇
從籍貫到種族
結語
第四章 從傳統走向近代
小學生的背後意義
紳章背後的資本流動
一體化之下的禮儀
再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