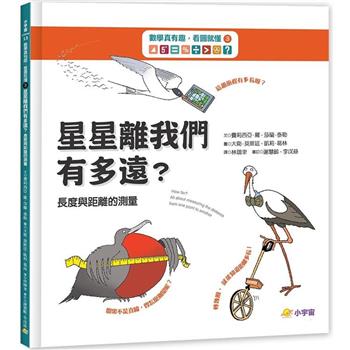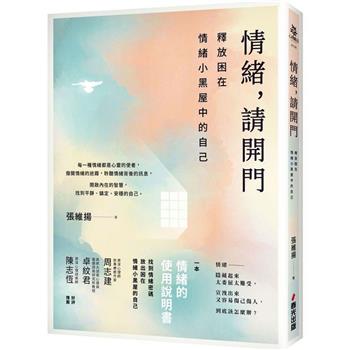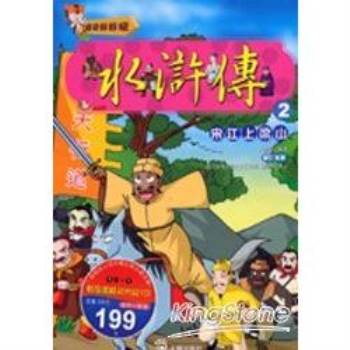本書係作者二十餘年間專注於最新出土戰國竹簡研究之集大成。內容涵蓋面極廣,舉凡竹簡復原、簡制分析、字形書法、語文考釋、義理詮釋、書寫馴化、學術傳播、司法文書等皆有精當之論述。
全書內容概分為「綜論」、「考釋研究」、「其他」三大部分。作者的具體研究成果除深化戰國竹簡研究之外,對於「郭店儒家佚書」、「上博藏『諸子』類佚書」、「上博藏『國語』類竹書」、「北京清華大學藏『書』類竹書」、「包山與九店楚簡」的研究,更可發先秦學術之微眇,故廣為兩岸及國際漢學界所推重。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朋齋學術文集 戰國竹書卷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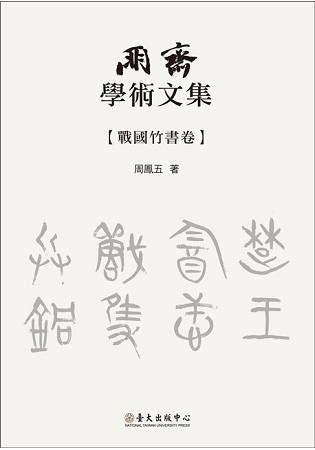 |
朋齋學術文集 戰國竹書卷 作者:周鳳五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7-04-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474 |
教育學習 |
$ 528 |
中文書 |
$ 528 |
中國古典文學 |
$ 540 |
教育學習 |
$ 540 |
社會人文 |
$ 540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540 |
科學科普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朋齋學術文集 戰國竹書卷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周鳳五(1947-2015)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中華民國國家文學博士。曾任國立臺灣大學特聘教授、講座教授、胡適紀念講座教授、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教授、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客座教授、國立中正大學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所創所所長、臺灣楚文化研究會會長、臺灣書法藝術協會會長。曾獲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國立臺灣大學傑出研究獎、教育部學術獎等。從事學術研究四十餘年,學問兼及經學、古文獻學、語言文字學、敦煌學、簡帛學及古典文學等領域。著有《偽古文尚書問題重探》、《六韜研究》、《敦煌寫本太公家教研究》、《華夏之美―─書法》等書。近廿年來更專注於出土古文字與古文獻,涵蓋古代漢語、古典文獻學、學術思想史等等,著有〈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等論文數十篇。論述周浹,學養博雅,備受學界敬重。
周鳳五(1947-2015)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中華民國國家文學博士。曾任國立臺灣大學特聘教授、講座教授、胡適紀念講座教授、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教授、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客座教授、國立中正大學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所創所所長、臺灣楚文化研究會會長、臺灣書法藝術協會會長。曾獲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國立臺灣大學傑出研究獎、教育部學術獎等。從事學術研究四十餘年,學問兼及經學、古文獻學、語言文字學、敦煌學、簡帛學及古典文學等領域。著有《偽古文尚書問題重探》、《六韜研究》、《敦煌寫本太公家教研究》、《華夏之美―─書法》等書。近廿年來更專注於出土古文字與古文獻,涵蓋古代漢語、古典文獻學、學術思想史等等,著有〈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等論文數十篇。論述周浹,學養博雅,備受學界敬重。
目錄
編輯凡例
金字塔底的劬勤身影—記從朋齋先生學習的二三事(代序)/林志鵬
第壹編 綜論:文本復原及方法論
第一篇 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
第二篇 郭店竹簡編序復原研究
第三篇 楚簡文字的書法史意義
第四篇 傳統漢學經典的再生—以清華簡〈保訓〉「中」字為例
第五篇 文字考釋與文本解讀—以出土楚簡為例
第六篇 論上博〈孔子詩論〉竹簡留白問題
第貳編 郭店儒家佚書
第七篇 郭店楚簡〈忠信之道〉考釋
第八篇 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新釋
第九篇 讀郭店竹簡〈成之聞之〉札記
第十篇 郭店〈性自命出〉「怒欲盈而毋暴」說
第十一篇 郭店楚簡識字札記
第十二篇 郭店竹簡文字補釋
第十三篇 簡帛〈五行〉引《詩》小議
第參編 上博藏「諸子」類佚書
第十四篇 上博〈性情論〉小箋
第十五篇 上博〈性情論〉「金石之有聲也,弗叩不鳴」解
第十六篇 讀上博楚竹書〈從政(甲篇)〉劄記
第十七篇 上博三〈仲弓〉篇重探
第十八篇 上博楚竹書〈彭祖〉重探
第十九篇 試說〈季康子問於孔子〉的榮鴐鵝
第二十篇 〈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
第肆編 上博藏「國語」類竹書
第二十一篇 上博四〈柬大王泊旱〉重探
第二十二篇 上博四〈昭王與龔之脽〉重探
第二十三篇 上博五〈姑成家父〉重編新釋
第二十四篇 上博五〈競建內之〉、〈鮑叔牙與隰朋之諫〉補釋
第二十五篇 上博六〈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新探
第二十六篇 上博六〈競公瘧〉「公乃出視朝」解
第二十七篇 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新探
第二十八篇 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重編新釋
第伍編 北京清華大學藏「書」類竹書
第二十九篇 北京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保訓〉新探
第三十篇 說「尹既及湯咸有一德」
第三十一篇 清華三〈說命上〉「王命厥百工向,以貨徇求說于邑人」解
第三十二篇 清華三〈赤鵠之集湯之屋〉新註解
第陸編 包山與九店楚簡
第三十三篇 包山楚簡文字初考
第三十四篇 〈睪命案文書〉箋釋—包山楚簡司法文書研究之一
第三十五篇 包山楚簡〈集箸〉〈集箸言〉析論
第三十六篇 九店楚簡〈告武夷〉重探
第柒編 其他
第三十七篇 楚簡文字瑣記(三則)
第三十八篇 楚簡文字考釋
第三十九篇 楚簡文字零釋
參考書目
金字塔底的劬勤身影—記從朋齋先生學習的二三事(代序)/林志鵬
第壹編 綜論:文本復原及方法論
第一篇 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
第二篇 郭店竹簡編序復原研究
第三篇 楚簡文字的書法史意義
第四篇 傳統漢學經典的再生—以清華簡〈保訓〉「中」字為例
第五篇 文字考釋與文本解讀—以出土楚簡為例
第六篇 論上博〈孔子詩論〉竹簡留白問題
第貳編 郭店儒家佚書
第七篇 郭店楚簡〈忠信之道〉考釋
第八篇 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新釋
第九篇 讀郭店竹簡〈成之聞之〉札記
第十篇 郭店〈性自命出〉「怒欲盈而毋暴」說
第十一篇 郭店楚簡識字札記
第十二篇 郭店竹簡文字補釋
第十三篇 簡帛〈五行〉引《詩》小議
第參編 上博藏「諸子」類佚書
第十四篇 上博〈性情論〉小箋
第十五篇 上博〈性情論〉「金石之有聲也,弗叩不鳴」解
第十六篇 讀上博楚竹書〈從政(甲篇)〉劄記
第十七篇 上博三〈仲弓〉篇重探
第十八篇 上博楚竹書〈彭祖〉重探
第十九篇 試說〈季康子問於孔子〉的榮鴐鵝
第二十篇 〈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
第肆編 上博藏「國語」類竹書
第二十一篇 上博四〈柬大王泊旱〉重探
第二十二篇 上博四〈昭王與龔之脽〉重探
第二十三篇 上博五〈姑成家父〉重編新釋
第二十四篇 上博五〈競建內之〉、〈鮑叔牙與隰朋之諫〉補釋
第二十五篇 上博六〈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新探
第二十六篇 上博六〈競公瘧〉「公乃出視朝」解
第二十七篇 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新探
第二十八篇 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重編新釋
第伍編 北京清華大學藏「書」類竹書
第二十九篇 北京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保訓〉新探
第三十篇 說「尹既及湯咸有一德」
第三十一篇 清華三〈說命上〉「王命厥百工向,以貨徇求說于邑人」解
第三十二篇 清華三〈赤鵠之集湯之屋〉新註解
第陸編 包山與九店楚簡
第三十三篇 包山楚簡文字初考
第三十四篇 〈睪命案文書〉箋釋—包山楚簡司法文書研究之一
第三十五篇 包山楚簡〈集箸〉〈集箸言〉析論
第三十六篇 九店楚簡〈告武夷〉重探
第柒編 其他
第三十七篇 楚簡文字瑣記(三則)
第三十八篇 楚簡文字考釋
第三十九篇 楚簡文字零釋
參考書目
序
代序
金字塔底的劬勤身影——記從朋齋先生學習的二三事
猶記三年前周師榮膺胡適紀念講座,他以「為學當如金字塔」為題作專題演講,自比為「金字塔底的一塊磚」。先生以磚瓦礫石自居,固是謙辭,然亦有其深意:他希望大學的教師要厚植學養,樂於作時賢晚輩攀登高峰的踏腳石,為廣大崇高的金字塔添磚加瓦,劬瘁其力。
一般熟悉周師的同道會認為他是一位古文字學家及書法家,但他在一次公開場合明白地說:「我是語言學家,學術專業是古代漢語。」在先生的心目中,文字學應當納入語言學的範疇,因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文字形體脫離了語言脈絡,便只是點畫線條。周師從上世紀九零年代投入戰國竹簡的研究領域,從最早發表的〈包山楚簡文字初考〉開始,到後來一系列考釋郭店、上博、清華竹書的專文,莫不細心還原文本所涉語境,充分考慮文獻的性質、對話人物的身分及古代的詞彙、語法特點,從而最大程度地復原文本,讓一幅幅古代思想文化的圖卷生動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正因為周師將文字納入廣大的語言系統及文化背景,所以在其研究中,考釋文字並非目的,而是考證史實、闡明義理的手段。收於本書中討論上博所藏國語類竹書的幾篇專文,集中反映了先生考史的成就,如其論〈昭王與龔之脽〉、〈君人者何必安哉〉聯繫楚昭王經吳兵入郢後勵精圖治的經歷,考釋〈姑成家父〉則窮究晉「三郤之亂」的原委,均能呈現一個時代或一歷史事件的鮮明面貌。
在思想的闡發方面,如〈郭店竹簡文字補釋〉一文論〈五行〉首章仁義禮智聖「型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型於內謂之行」之「型」,周師未從俗說釋為「形」,而如字讀為「型範」之「型」。他解釋道:「仁、義、禮、智、聖五種道德意識在人心中產生如模型、器範的規範作用,使人的行為合乎道德標準,這就是『德之行』;若任性縱情而為,心中缺乏道德意識的規範,這只是『行』。」更引郭店竹書〈成之聞之〉「型於中,發於色」及〈大學〉「誠於中,形於外」證之。通過此一「型」字的精確破譯,使我們深切地體悟到先秦儒家成德成聖之修養,始於內在道德對於心的規範,歸結於表裏如一的彬彬君子。對於子思學派此一論述的學術史意義,先生也隻眼獨具地指出:「〈五行〉為儒家後學留下了一個問題:即道德意識究竟從何而來?這正是孟、荀思想同源異派的起點。」
先生的為學宗旨大體如上所陳,而在微觀的古文字考釋上,他十分強調方法的重要性。1930年代,唐蘭於《古文字學導論》慨嘆當時古文字學界「根本沒有是非的標準,所以人人得自立其說」,到了八十年後的今日,這種情況似乎沒有多大的改善。正因如此,周師近年針對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的研究方法,籌辦多次讀書班及研討會,屢次撰文希望學術界的同道正視此一問題。他曾總結清乾嘉以來學者考釋文字的經驗,提出十二字要領:「析形定音」、「循音別詞」、「因文求義」,將古文字研究應該遵循的法則,和盤托出,可謂金針度人。在考證戰國竹書諸多疑難字詞時,周師極力貫串上述三項原則,如其解郭店〈老子〉「大曰衍,衍曰轉,轉曰反」、釋上博〈彭祖〉之「沖子」、說郭店〈窮達以時〉及上博〈姑成家父〉之「顑頷」,莫不如此,洵為後學之範式。
對於讀書,周師強調要在無字處讀書,貴能發現問題、獨立思考,每以「讀書得閒」勉勵後學。竊以為最能體現先生此一特長者,非〈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莫屬。在該文中,他提出郭店竹書各篇的簡長、簡端形狀等形式特徵,可以做為判斷文獻性質的標準,即「簡策長者為經,短者為傳」,「簡端修為梯形者為經,平齊者為傳」,據此可將這批竹書分為經典及傳注兩類。字體方面,先生指出郭店竹書的部分篇章如〈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具有齊國文字的特徵,從而提出戰國寫本在傳播的過程中有所謂「馴化」之現象,如傳入楚地較久者,經學者反覆抄寫,逐漸褪去文本起源地的字體特色;而新近傳入者,因馴化尚暫,所以仍保有原來的書體風格。由文字的馴化現象,先生進一步強調「研讀出土楚簡不能局限於楚國一隅,必須從字形的特徵與戰國諸子學術的大格局來追溯楚簡的文本來源,進而釐清先秦諸子的傳播與學派形成。」(別見〈讀書與釋字方法的省思〉)這些創見,無非是先生平日精思深慮的成果。
提及此文,也不禁令人慨嘆,當今學術界對於竹書形式特徵的系統研究並無長足之進展,原因不在後繼無人(馮勝君先生於十年前即在周師的字體研究基礎上有所推進),主要的障礙在於郭店楚簡發現之後,中國大陸掀起一波盜掘竹簡的高潮。近年公布的戰國秦漢出土古書,如上博簡、嶽麓簡、清華簡及北大簡等,均為盜墓所得。這些材料雖經各單位「搶救性蒐購」,但盜掘流出的同一批竹書,出土地可能不同,且材料本身無法參照考古地層及共出器物的脈絡,這對於實際研究產生很大的干擾,尤其是對竹書時代的判定及形制的歸納而言,更是如此。中國的文物主管單位應當正視此一問題,切莫讓簡帛文獻的發現熱潮演變成一場文化浩劫。
筆者於九零年代進入臺大中文系就讀,當時周師講授大學部文字學課程,於漢字起源借鑒汪寧生、李孝定之說,於文字構形則評介唐蘭、龍宇純先生之理論,並兼及唐代以來的正字之學及俗字、簡化字的概況。對於許慎「六書」說,周師主張還原其時代背景,將之視為受漢代經學影響的文字理論,明其局限,不必糾纏於「轉注」異說之是非。在先生課上,文字初誼的探討並非枯燥地舉例解說,而有生動的呈現。一次上課,我因故遲到,趕到教室時,見三兩同學跪坐於講臺前,心裡納悶「究竟作了如何大逆不道之事,竟需跪地悔過?」原來,先生正講解「鄉」、「即」、「既」三字之創意,為了直觀地呈現古人席地就食的情況,所以讓諸生上臺示範。此一事例足見周師教學之用心,也可看出他強調「文字並不僅是語言的符號,亦是歷史與文化載體」的立場。
1999年,《郭店楚墓竹簡》出版不久,是年我在碩士班選修先生郭店竹書討論課。課上由同學輪流進行導讀,主講者除介紹各篇竹書的概況外,並需即席回答老師及其他同學提出的問題。每回上課宛如一次嚴格的答辯,主講者莫不全力以赴,而先生也以極大的耐性聽著我們淺薄的發言,通過質疑、辯難、討論,進行腦力的激盪。有時,遇疑難問題無法解決,如郭店三組〈老子〉是處在發展中的本子抑或摘抄本,〈五行〉之心性說究竟近荀還是近孟等,先生並不馬上點破,而是讓我們當下自己去思考,任由課堂時間隨沉默流逝。先生指導研究生,雖屬「大音希聲」之類型,然則「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一旦學生接觸到問題的核心,必扣其兩端而竭之,毫無保留地分享自己的心得。
在私下從先生問學的過程中,有兩次珍貴的經驗,令我難以忘懷。2004年我在武漢大學攻讀博士,當時周師撰寫〈上博三〈彭祖〉新探〉,我因幫忙核查文中所涉文獻,得以最早拜讀此文初稿。先生在文中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即竹書「心白身懌」四字,明顯與《管子》「白心」說有關,不妨假設其為稷下學派之產物。同時,他發現郭店儒家佚書〈五行〉、〈性自命出〉等也出現見於《管子》的稷下學派術語「心術」與「內業」,周師認為此一現象值得深入探究。受其啟發,我集中精力將此篇竹書與《管子.心術》、〈白心〉及〈內業〉等反覆對讀,發現上博〈彭祖〉的思想與《莊子.天下》所述宋銒一派尤近,而《管子.心術》諸篇存在較多的文本校勘、詮解之問題,彼此之間的關係及學派歸屬,近世學者頗有爭論,如果能解決這些疑難,不但可以增進稷下道家之瞭解,對於戰國時期儒、道二家彼此競爭、互相影響的過程,也能得到更深一層的認識。我將上述構想告訴周先生,並大膽地擬了一份論文寫作計畫,想徵求他的同意,以此做為博士論文的選題,先生欣然允諾,並惠賜〈上博三〈彭祖〉新探〉之定稿,鼓勵我繼續探索。
2009年筆者在北京大學作博士後研究,返臺期間周師邀我回母校作報告,我集中討論了戰國楚簡中的「曷」字(原作),將其形構說為以人停步張口表達問疑之意,惟此字往往於左側增一直筆,原本我以飾筆目之,沒有追究此一筆劃之深意。在報告後,先生告訴我,應該將此字與「疑」字合觀,甲骨文「疑」作「」,象人駐杖顧盼而有惑之形,「曷」字所增之筆即人所持之杖。得其開導,形構上的疑點渙然冰釋,且因「疑」、「曷」之形義俱有一定的關聯,也增強了拙文的論證強度。筆者雖非周師門下的指導學生,卻屢屢得到先生無私的幫助及提攜,盛情美意,讓在異鄉飄泊求學的我備感溫暖。
去年仲夏,周師囑門生為其編訂文集,原本想將先生以往的學術文章匯為全集,然卷帙過大,加以先生學問所涉除古文字學、簡帛學及經學外,更旁及金石學、楚辭學、敦煌學、書法史、語文教育等領域,一時無法找到理想的編排方案。後來,我建議不妨先匯集先生近二十年來最為著力的戰國楚簡研究專文,其餘則日後陸續編訂為別卷,如此一來不但主從有序,更能呈現出先生學術堂廡之宏壯。此一提案得到周師的贊同,遂指示由我初步整理篇目,范麗梅博士負責文集的統籌及校訂工作。我參考了周師的論著目錄,從其中擇取戰國竹書專文三十餘篇,略依主題別「文本復原及方法論」、「郭店儒家佚書」、「上博藏『諸子』類佚書」、「上博藏『國語』類竹書」、「北京清華大學藏『書』類竹書」及「其他」等六編。其後,范博士在上述編次的基礎上又增補若干篇,並新加「包山與九店楚簡」一編。今周師的文集付梓在即,謹記下從其受業近二十年來的體會,愚雖不敏,且深知執筆為序難免僭越之譏,然師之所望厚矣,亦不敢推辭,遂化用其「我在金字塔底」之語,以誌先生治學之旨趣。
金字塔底的劬勤身影——記從朋齋先生學習的二三事
猶記三年前周師榮膺胡適紀念講座,他以「為學當如金字塔」為題作專題演講,自比為「金字塔底的一塊磚」。先生以磚瓦礫石自居,固是謙辭,然亦有其深意:他希望大學的教師要厚植學養,樂於作時賢晚輩攀登高峰的踏腳石,為廣大崇高的金字塔添磚加瓦,劬瘁其力。
一般熟悉周師的同道會認為他是一位古文字學家及書法家,但他在一次公開場合明白地說:「我是語言學家,學術專業是古代漢語。」在先生的心目中,文字學應當納入語言學的範疇,因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文字形體脫離了語言脈絡,便只是點畫線條。周師從上世紀九零年代投入戰國竹簡的研究領域,從最早發表的〈包山楚簡文字初考〉開始,到後來一系列考釋郭店、上博、清華竹書的專文,莫不細心還原文本所涉語境,充分考慮文獻的性質、對話人物的身分及古代的詞彙、語法特點,從而最大程度地復原文本,讓一幅幅古代思想文化的圖卷生動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正因為周師將文字納入廣大的語言系統及文化背景,所以在其研究中,考釋文字並非目的,而是考證史實、闡明義理的手段。收於本書中討論上博所藏國語類竹書的幾篇專文,集中反映了先生考史的成就,如其論〈昭王與龔之脽〉、〈君人者何必安哉〉聯繫楚昭王經吳兵入郢後勵精圖治的經歷,考釋〈姑成家父〉則窮究晉「三郤之亂」的原委,均能呈現一個時代或一歷史事件的鮮明面貌。
在思想的闡發方面,如〈郭店竹簡文字補釋〉一文論〈五行〉首章仁義禮智聖「型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型於內謂之行」之「型」,周師未從俗說釋為「形」,而如字讀為「型範」之「型」。他解釋道:「仁、義、禮、智、聖五種道德意識在人心中產生如模型、器範的規範作用,使人的行為合乎道德標準,這就是『德之行』;若任性縱情而為,心中缺乏道德意識的規範,這只是『行』。」更引郭店竹書〈成之聞之〉「型於中,發於色」及〈大學〉「誠於中,形於外」證之。通過此一「型」字的精確破譯,使我們深切地體悟到先秦儒家成德成聖之修養,始於內在道德對於心的規範,歸結於表裏如一的彬彬君子。對於子思學派此一論述的學術史意義,先生也隻眼獨具地指出:「〈五行〉為儒家後學留下了一個問題:即道德意識究竟從何而來?這正是孟、荀思想同源異派的起點。」
先生的為學宗旨大體如上所陳,而在微觀的古文字考釋上,他十分強調方法的重要性。1930年代,唐蘭於《古文字學導論》慨嘆當時古文字學界「根本沒有是非的標準,所以人人得自立其說」,到了八十年後的今日,這種情況似乎沒有多大的改善。正因如此,周師近年針對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的研究方法,籌辦多次讀書班及研討會,屢次撰文希望學術界的同道正視此一問題。他曾總結清乾嘉以來學者考釋文字的經驗,提出十二字要領:「析形定音」、「循音別詞」、「因文求義」,將古文字研究應該遵循的法則,和盤托出,可謂金針度人。在考證戰國竹書諸多疑難字詞時,周師極力貫串上述三項原則,如其解郭店〈老子〉「大曰衍,衍曰轉,轉曰反」、釋上博〈彭祖〉之「沖子」、說郭店〈窮達以時〉及上博〈姑成家父〉之「顑頷」,莫不如此,洵為後學之範式。
對於讀書,周師強調要在無字處讀書,貴能發現問題、獨立思考,每以「讀書得閒」勉勵後學。竊以為最能體現先生此一特長者,非〈郭店竹簡的形式特徵及其分類意義〉莫屬。在該文中,他提出郭店竹書各篇的簡長、簡端形狀等形式特徵,可以做為判斷文獻性質的標準,即「簡策長者為經,短者為傳」,「簡端修為梯形者為經,平齊者為傳」,據此可將這批竹書分為經典及傳注兩類。字體方面,先生指出郭店竹書的部分篇章如〈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具有齊國文字的特徵,從而提出戰國寫本在傳播的過程中有所謂「馴化」之現象,如傳入楚地較久者,經學者反覆抄寫,逐漸褪去文本起源地的字體特色;而新近傳入者,因馴化尚暫,所以仍保有原來的書體風格。由文字的馴化現象,先生進一步強調「研讀出土楚簡不能局限於楚國一隅,必須從字形的特徵與戰國諸子學術的大格局來追溯楚簡的文本來源,進而釐清先秦諸子的傳播與學派形成。」(別見〈讀書與釋字方法的省思〉)這些創見,無非是先生平日精思深慮的成果。
提及此文,也不禁令人慨嘆,當今學術界對於竹書形式特徵的系統研究並無長足之進展,原因不在後繼無人(馮勝君先生於十年前即在周師的字體研究基礎上有所推進),主要的障礙在於郭店楚簡發現之後,中國大陸掀起一波盜掘竹簡的高潮。近年公布的戰國秦漢出土古書,如上博簡、嶽麓簡、清華簡及北大簡等,均為盜墓所得。這些材料雖經各單位「搶救性蒐購」,但盜掘流出的同一批竹書,出土地可能不同,且材料本身無法參照考古地層及共出器物的脈絡,這對於實際研究產生很大的干擾,尤其是對竹書時代的判定及形制的歸納而言,更是如此。中國的文物主管單位應當正視此一問題,切莫讓簡帛文獻的發現熱潮演變成一場文化浩劫。
筆者於九零年代進入臺大中文系就讀,當時周師講授大學部文字學課程,於漢字起源借鑒汪寧生、李孝定之說,於文字構形則評介唐蘭、龍宇純先生之理論,並兼及唐代以來的正字之學及俗字、簡化字的概況。對於許慎「六書」說,周師主張還原其時代背景,將之視為受漢代經學影響的文字理論,明其局限,不必糾纏於「轉注」異說之是非。在先生課上,文字初誼的探討並非枯燥地舉例解說,而有生動的呈現。一次上課,我因故遲到,趕到教室時,見三兩同學跪坐於講臺前,心裡納悶「究竟作了如何大逆不道之事,竟需跪地悔過?」原來,先生正講解「鄉」、「即」、「既」三字之創意,為了直觀地呈現古人席地就食的情況,所以讓諸生上臺示範。此一事例足見周師教學之用心,也可看出他強調「文字並不僅是語言的符號,亦是歷史與文化載體」的立場。
1999年,《郭店楚墓竹簡》出版不久,是年我在碩士班選修先生郭店竹書討論課。課上由同學輪流進行導讀,主講者除介紹各篇竹書的概況外,並需即席回答老師及其他同學提出的問題。每回上課宛如一次嚴格的答辯,主講者莫不全力以赴,而先生也以極大的耐性聽著我們淺薄的發言,通過質疑、辯難、討論,進行腦力的激盪。有時,遇疑難問題無法解決,如郭店三組〈老子〉是處在發展中的本子抑或摘抄本,〈五行〉之心性說究竟近荀還是近孟等,先生並不馬上點破,而是讓我們當下自己去思考,任由課堂時間隨沉默流逝。先生指導研究生,雖屬「大音希聲」之類型,然則「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一旦學生接觸到問題的核心,必扣其兩端而竭之,毫無保留地分享自己的心得。
在私下從先生問學的過程中,有兩次珍貴的經驗,令我難以忘懷。2004年我在武漢大學攻讀博士,當時周師撰寫〈上博三〈彭祖〉新探〉,我因幫忙核查文中所涉文獻,得以最早拜讀此文初稿。先生在文中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即竹書「心白身懌」四字,明顯與《管子》「白心」說有關,不妨假設其為稷下學派之產物。同時,他發現郭店儒家佚書〈五行〉、〈性自命出〉等也出現見於《管子》的稷下學派術語「心術」與「內業」,周師認為此一現象值得深入探究。受其啟發,我集中精力將此篇竹書與《管子.心術》、〈白心〉及〈內業〉等反覆對讀,發現上博〈彭祖〉的思想與《莊子.天下》所述宋銒一派尤近,而《管子.心術》諸篇存在較多的文本校勘、詮解之問題,彼此之間的關係及學派歸屬,近世學者頗有爭論,如果能解決這些疑難,不但可以增進稷下道家之瞭解,對於戰國時期儒、道二家彼此競爭、互相影響的過程,也能得到更深一層的認識。我將上述構想告訴周先生,並大膽地擬了一份論文寫作計畫,想徵求他的同意,以此做為博士論文的選題,先生欣然允諾,並惠賜〈上博三〈彭祖〉新探〉之定稿,鼓勵我繼續探索。
2009年筆者在北京大學作博士後研究,返臺期間周師邀我回母校作報告,我集中討論了戰國楚簡中的「曷」字(原作),將其形構說為以人停步張口表達問疑之意,惟此字往往於左側增一直筆,原本我以飾筆目之,沒有追究此一筆劃之深意。在報告後,先生告訴我,應該將此字與「疑」字合觀,甲骨文「疑」作「」,象人駐杖顧盼而有惑之形,「曷」字所增之筆即人所持之杖。得其開導,形構上的疑點渙然冰釋,且因「疑」、「曷」之形義俱有一定的關聯,也增強了拙文的論證強度。筆者雖非周師門下的指導學生,卻屢屢得到先生無私的幫助及提攜,盛情美意,讓在異鄉飄泊求學的我備感溫暖。
去年仲夏,周師囑門生為其編訂文集,原本想將先生以往的學術文章匯為全集,然卷帙過大,加以先生學問所涉除古文字學、簡帛學及經學外,更旁及金石學、楚辭學、敦煌學、書法史、語文教育等領域,一時無法找到理想的編排方案。後來,我建議不妨先匯集先生近二十年來最為著力的戰國楚簡研究專文,其餘則日後陸續編訂為別卷,如此一來不但主從有序,更能呈現出先生學術堂廡之宏壯。此一提案得到周師的贊同,遂指示由我初步整理篇目,范麗梅博士負責文集的統籌及校訂工作。我參考了周師的論著目錄,從其中擇取戰國竹書專文三十餘篇,略依主題別「文本復原及方法論」、「郭店儒家佚書」、「上博藏『諸子』類佚書」、「上博藏『國語』類竹書」、「北京清華大學藏『書』類竹書」及「其他」等六編。其後,范博士在上述編次的基礎上又增補若干篇,並新加「包山與九店楚簡」一編。今周師的文集付梓在即,謹記下從其受業近二十年來的體會,愚雖不敏,且深知執筆為序難免僭越之譏,然師之所望厚矣,亦不敢推辭,遂化用其「我在金字塔底」之語,以誌先生治學之旨趣。
林志鵬(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