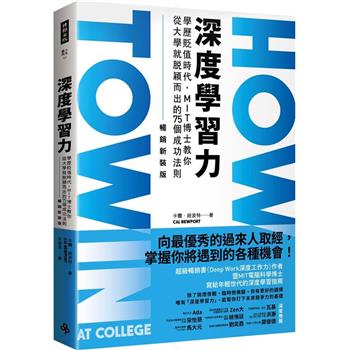導論(摘錄)
一、漢語基督教小說的翻譯與創作
十九世紀,隨著歐美各國的擴張,基督教傳教運動蔓延全球,這差傳運動與宣布、傳揚「天國」(Kingdom of God)的降臨密切相關,而天國的概念既涉及世界末日的來臨,又與改變人世現狀的訴求逐漸結合。在十九世紀的自由神學思潮中,「天國」常被詮釋為理想基督教社會的建立,即使其基督教色彩依然濃厚,但該理想已經變得世俗化。他們認為天國的實現,可藉由社會進步、發展及富庶達成。至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北美工業城市興起的「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更以天國為焦點,社會福音不僅關注個人的得救,同時著重社會的轉化及救贖。即使神學和宗派背景各異的傳教士對「福音」內涵的理解不盡相同,傳播天國的福音始終是他們遠赴中國的核心目標,例如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傳教士紀好弼(Rosewell H. Graves, 1833-1912)明言:「今且全球五大洲幾無一國不獲聞耶穌福音,而以方言翻譯聖經,亦已逾四百種。……而如此傳佈者,實因其是萬國應共率循,萬民悉莫能外之世界唯一真道。」
1807年,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來華,揭開了基督新教在中國傳教運動的序幕。從基督新教來華開始,一直到清朝覆亡(1807-1911)之間,不少西方來華的傳教士致力參與文字出版的工作,其中翻譯西方的基督教著作成為關鍵的傳教策略。晚清時期,傳教士譯著的作品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分別為敘事文學類,以及神學思想與崇拜禮儀類,前者主要包括《聖經》故事、宗教寓言、基督教兒童文學及基督徒傳記等,後者主要包括護教書籍、講道集、靈修作品、教義問答、信仰聲明,以及規範崇拜禮儀的《公禱書》(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等。翻譯本身更是極為複雜的多元系統,作者、譯者、讀者、文本、社會、歷史等因素互相制約。譯文往往受以上種種錯綜因素影響,我們也可把翻譯視為對原著的一次重寫或改寫(rewriting),即是對源文本(source text)的重新解釋、改變或操縱(manipulation)。因此,翻譯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大量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之間的溝通和交流,這一點在來華傳教士的文學翻譯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傳教士欲把西方基督教作品移植到中國的文化土壤之中,無可避免地要跟中國的歷史、文化、文學傳統接軌和對話。為求遷就不同讀者的文化知識水準和接受能力,譯者須考慮譯入語的文化與宗教處境,也必然會受到翻譯目的和出版經費等限制,因此他們往往會大刀闊斧地改寫、改編、節錄和重述原來的故事。倫敦會傳教士楊格非(Griffith John, 1831-1912)在《紅侏儒傳》(1882)的跋中談及翻譯的經驗和策略:「譯以中國文字,其間或芟其冗煩,或潤以華藻,推陳出新,翻波助瀾,是脫胎於原本,非按字謹譯也。閱是編者,謂之譯可,謂之著可,謂之半譯半著亦無不可。」
《紅侏儒傳》的原著The Terrible Red Dwarf引用了不少《聖經》、西方神話及童話的典故。由於中西文化的差異,譯者楊格非採用了「半譯半著」的翻譯策略,要麼把這些典故刪去,要麼對其加以「歸化」或「中國化」。舉例而言,《聖經》中最長壽的人物「馬土撒拉」(Methuselah)搖身一變,成了相傳享壽八百歲的「彭祖」。另外,《紅侏儒傳》的原著具備許多西方童話故事的元素,包括侏儒、巨人、隱形衣、七里靴、魔法書等,這些元素在翻譯的過程中往往會被淡化或改寫。例如,原著把孀婦之子Jack戲稱為Giant-killer(巨人殺手),此喻的典故出自西方童話《傑克與魔豆》(Jack and the Beanstalk)。故事的主角Jack把巨人殺死,譯著只輕描淡寫地提到「孀婦之子膽力過人」。此外,譯者也把不少西方生活環境、職業的描述改寫,例如原著中的酒吧名稱“Blue Boar”被略去,而酒徒(drunkard)則變成「吸鴉片者」,反映了晚清中國鴉片氾濫的社會現象。這種「半譯半著」的現象反映了跨文化翻譯的挑戰。若把漢譯小說跟英文原著參相對照,我們會在本書討論的數部翻譯作品中發現,這種「半譯半著」的現象或「譯述」的策略屢見不鮮,以致翻譯與創作的關係和界線顯得模糊不清,充分體現了譯者的文化觸覺與創造性。每部文學作品都是藝術創作,而文學翻譯透過再創作賦予了譯作獨立的新生命。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在〈譯者的任務〉(“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提出,譯作既與原作保持聯繫,但又獨立於原作而存在,譯作讓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續」(continued life),或說譯作是原作的「來生」(afterlife)。原作在「來生」中產生了變化,這種再創作確保了原作的「生存」(survival)。
借用班雅明的翻譯理論,上述不少西方基督教小說翻譯為漢語,把原著的生命繼續延伸下去。進一步而言,譯著不僅賦予原著生命,甚至把原著「殺掉」(kill the original),取而代之成為原著。
除了翻譯西方作品之外,西方傳教士還從事基督教小說的創作。較重要的作品,除了倫敦會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的《張遠兩友相論》(1819)、楊格非的《引家當道》(1882)外,不得不提的是荷蘭佈道會(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為數可觀的原創小說。這些小說大部分具有濃厚的本土化特徵,如採用章回體,故事多以明清兩代為時代背景,以中國官員、儒生和商人等為角色,又涉及不少中國社會、文化、風俗的描繪,並時常援引中國傳統的文史哲經典來論述基督教思想。除了西方傳教士外,中國基督徒於十九世紀末亦參與小說創作。1895年,曾任英行教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的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發起的「時新小說」徵文比賽,徵求小說抨擊社會弊病,並提供政治良方,有一批華人基督徒參賽,嘗試於小說中運用基督教的思想及文化資源,探求令中國達致富強興盛之道。無論是翻譯或原創的基督教小說皆有明顯的中國文學特徵,尤具中國傳統小說的神韻風貌,同時承載著鮮明的基督教宗教內涵,可算是一類特殊的宗教文學作品。
對於這批基督教小說的命名,學界並沒有統一規範的稱法。如韓南(Patrick Hanan, 1926-2014)所謂「傳教士小說」(missionary novel),意指基督教傳教士及其助手以小說形式著譯的中文敘事文本。又如吳淳邦稱「中國基督教小說」,陳慶浩稱「基督教古本漢文小說」,宋莉華稱「傳教士漢文小說」等。韓南及宋莉華的稱法,沒有涵蓋中國基督徒單獨創作的小說;吳氏沒有規定語言載體,不利於集中研究;陳氏的「古本漢文」並非現代華人圈廣泛通用的辭彙。綜合以上幾種命名,筆者認為謂之「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Late-Qing Chinese Christian novel)較為合理,這基本從時段、語言載體、宗教內涵及文學形式上恰當地規限了本書的研究對象,也更符合已掌握文獻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基督教小說當中,只要是用漢語翻譯或撰寫的,無論作者或譯者是中國人或其他國籍的人,都應歸為「漢語基督教小說」。
二、漢語基督教小說的研究進路
漢語基督教小說處於宗教與文學之間,長期以來並未受到宗教學者或文學研究者應有的重視,究其原因,也許有宗教學者視其宗教內涵不夠深刻,文學研究者則指其文字造詣難登大雅之堂。另一方面,宗教學與文學研究各自有其學術傳統與規範,無論從宗教的視角研究文學,抑或從文學的角度研究宗教,皆非兩個學術傳統的重點所在。近年來,隨著學界發現更多原始資料,不少學者已開始關注並研究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這批文本。韓南在2000年發表的〈中國十九世紀傳教士小說〉可謂開山之作,這篇論文提出了「傳教士小說」(missionary novel)的概念,梳理了部分重要傳教士小說的作者和源流,為研究十九世紀基督教小說奠定了基礎。受韓南啟發,陳慶浩、吳淳邦、李奭學、宋莉華等學者開始關注這批彌足珍貴的文本,近年來也有可喜的研究進展。吳淳邦深度探討傳教士小說在韓國的傳播與翻譯概況。他新近的貢獻是就著近年發現的晚清「時新小說」開展了文本研究。此外,宋莉華綜述傳教士小說的研究現狀時,把這批小說視為「西方傳教士漢學的分支」,並在單篇論文的基礎上完成了專著《傳教士漢文小說研究》及《近代來華傳教士與兒童文學的譯介》,主要以傳教士的文化適應策略為切入點,以米憐、郭實獵及楊格非等人的作品為個案分析,審視這些小說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中的價值,特別在譯介兒童文學方面的貢獻。
另外,歷史學和文獻學的研究進路(approach),可讓我們了解個別作品在中國的著譯、出版、傳播的情況﹕莊欽永在〈「鍍金鳥籠」裡的吶喊:郭實獵政治小說《是非略論》析論〉中,著力展示及分析作品成書背後的歷史背景及政治角力;姚達兌則考證了傳教士作品的版本及時新小說的作者。林惠彬〈晚清基督教小說《紅侏儒傳》考論〉藉版本考察的手法探討作品的宗教背景及功能。李奭學致力於明末清初天主教著作的研究,強調從比較文學及翻譯史的角度研究基督宗教作品的重要性,亦關注明末天主教文學及清末基督新教文學的關聯,為相關的研究開闢了新路徑。總的來說,無論是整體文獻、研究框架、理論方法,還是從文本分析的角度看,上述學者為研究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奠下了穩當的基礎。惟相關論著主要仍集中於考證之上,對於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的書寫策略似尚有頗大研究空間。
正如上文所述,傳播「福音」是西方傳教士來華,以及書寫漢語基督教小說的核心目標,故本書特以「福音演義」為題,重點探討基督教的福音如何透過中國小說的形式敷演成文,推陳義理;分析這批漢語基督教小說如何利用中國文學的敘述資源(如章回體、夾敘夾議、小說評點等),藉以改寫《聖經》,譯述西方基督教文學,與中國本土宗教對話、與中國的社會文化處境互動等,從而歸納出作品所採用的跨文化的敘事策略,以及文學與宗教傳播的緊密關係。漢語基督教小說既有豐富的宗教內涵,又有明顯的文學特徵;既可視為宗教文獻,又可視為中國文學中的特殊部分。因此,無論從宗教學或文學的角度進行單方面的研究,都不足以展現其特色,我們必須同時借助宗教學和文學兩方面的學術資源開展綜合性考察。
就研究方法而言,本書不會定於一尊,而是針對個別文本來設計研究方法,務求能有多元的思考進路。具體來說,在研究一部基督教作品在中國的譯著、出版、傳播的情況時,本書主要採用歷史學和文獻學的方法;在分析這批小說的敘事藝術和技巧,例如敘事結構、情節、人物、意象和語言等,就會借用敘事學(narratology)的方法;在討論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對話與融合,不同的讀者層對基督教作品詮釋的多樣性,以及將這些小說放置在《聖經》文化語境中進行文本分析,以期探討其中的母題、典故和象徵等《聖經》原型時,我們將會借鑑詮釋學(hermeneutics)和文學原型理論(theory of archetypes)等方法。總而言之,本書希望透過綜合性和多元化的研究視角,揭示這批宗教文學作品的豐富內涵及書寫策略。
如前所述,晚清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所漢譯的小說,近十多年來備受學界關注,不少學者先後就多部作品進行個案研究,逐步描繪出晚清基督教小說的歷史輪廓,揭示出作品的跨文化現象。然而,除了傳教士的著譯小說作品外,晚清的漢語基督教小說有部分亦由華人基督徒創作,而上文提及傅蘭雅舉辦的「時新小說」比賽就是典型的例子。再者,西方傳教士所著譯的小說與華人基督徒創作的小說之間,存在一脈相承的關係。若要窺探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的整體面貌及發展脈絡,研究者必須同時涵蓋翻譯與創作的小說,以及西教士與華人基督徒的作品。故此,本書按照作品的性質分為上下兩編,分別為「翻譯編」及「創作編」,精選了晚清時期七部具代表性的小說作為研究個案,包括首部漢譯德文基督教小說《金屋型儀》(1852)、以儒家經典評點基督教寓言的《勝旅景程》(1870)、想像天國樂園的兒童小說《安樂家》(1882)、把英國建構成「無上之國」的《是非論》(1835)、演義《聖經》的史傳體小說《約瑟紀》(1852),以及兩部藉基督教思想為中國社會革故鼎新的「時新小說」,分別為《無名小說》(1895)及《驅魔傳》(1895)。每一章從小說作品的內部結構及敘事特徵出發,於宗教思想及文學形式之間穿梭往來,多角度探析傳教士與華人基督徒作者的書寫策略。
總而言之,漢語基督教小說作為承載思想及文化的文本,讓我們窺見來華傳教士在文字工作上的種種嘗試:傳教士在漢語程度有限的前提下如何創作易於被讀者接受的文體?他們如何調和文化上的差異?他們如何在一個陌生的地域中引入全新的宗教概念?至於華人基督徒在吸收傳教士作品的思想資源基礎上,發揮自身的文筆、想像力及對《聖經》的詮釋,又在創作手法上嘗試將基督教元素及西方的宗教小說融入中國文學體系,為清末小說創作提供了新的思想概念及元素。清末華人基督徒創作的時新小說,能讓我們理解清末一代基督徒的宗教想像與表述:他們如何挪用中國傳統文學資源來論述外來的宗教思想?他們的作品為研究傳教士文學的傳播與接受情況提供了重要的線索。職是之故,漢語基督教小說的宗教與文學價值不容小覷,對跨文化視域的宗教研究尤有參考價值。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福音演義: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的書寫【限量精裝版】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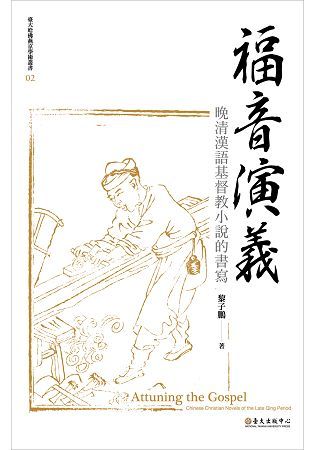 |
福音演義: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的書寫(限量精裝版) 作者:黎子鵬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7-07-2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3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356 |
文學研究 |
$ 356 |
小說/文學 |
$ 396 |
中文書 |
$ 396 |
中國古典文學 |
$ 405 |
教育學習 |
$ 405 |
文學作品 |
$ 405 |
宗教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福音演義: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的書寫【限量精裝版】
西方傳教士與華人基督徒小說家,
如何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中進行「福音演義」......
本書研究晚清時期具代表性的漢語基督教小說,上編「翻譯編」分析首部漢譯德文基督教小說《金屋型儀》、以儒家經典評點基督教寓言的《勝旅景程》、想像天國樂園的兒童小說《安樂家》;下編「創作編」考察把英國建構成「無上之國」的《是非畧論》、演義聖經的史傳體小說《約瑟紀畧》,以及兩部藉基督教思想為中國社會革故鼎新的「時新小說」──《無名小說》及《驅魔傳》。每一章從作品的敘事結構及特徵出發,於宗教思想及文學形式之間穿梭往來,多角度探析西方傳教士與華人基督徒小說家的書寫策略,如何在中國的文化語境中進行「福音演義」。
作者簡介:
黎子鵬
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漢語基督教文學、中國小說與宗教文化、宗教文學翻譯等。專著有Negotiating Religious Gaps: The Enterprise of Translating Christian Tract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2012)、《經典的轉生──晚清〈天路歷程〉漢譯研究》(2012);編著有《晚清基督教敘事文學選粹》(2012)、《贖罪之道傳──郭實獵基督教小說集》(2013)、《道德除害傳──清末基督徒時新小說選》(2015)、《中國基督教文字事業編年史(1860-1911)》(2015)、《中外宗教與文學裡的他界書寫》(2015;與李奭學合編)。曾獲香港中文大學「卓越研究獎」(2011)及「文學院傑出教學獎」(2010、2011、2013、2014及2015)。
TOP
章節試閱
導論(摘錄)
一、漢語基督教小說的翻譯與創作
十九世紀,隨著歐美各國的擴張,基督教傳教運動蔓延全球,這差傳運動與宣布、傳揚「天國」(Kingdom of God)的降臨密切相關,而天國的概念既涉及世界末日的來臨,又與改變人世現狀的訴求逐漸結合。在十九世紀的自由神學思潮中,「天國」常被詮釋為理想基督教社會的建立,即使其基督教色彩依然濃厚,但該理想已經變得世俗化。他們認為天國的實現,可藉由社會進步、發展及富庶達成。至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北美工業城市興起的「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更以天國為焦點,社會福音...
一、漢語基督教小說的翻譯與創作
十九世紀,隨著歐美各國的擴張,基督教傳教運動蔓延全球,這差傳運動與宣布、傳揚「天國」(Kingdom of God)的降臨密切相關,而天國的概念既涉及世界末日的來臨,又與改變人世現狀的訴求逐漸結合。在十九世紀的自由神學思潮中,「天國」常被詮釋為理想基督教社會的建立,即使其基督教色彩依然濃厚,但該理想已經變得世俗化。他們認為天國的實現,可藉由社會進步、發展及富庶達成。至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北美工業城市興起的「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更以天國為焦點,社會福音...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李奭學(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福音演義: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的書寫》分為「翻譯編」及「創作編」,綰結七部出現於晚清的基督教小說為一帙。此中的著譯者有英國漢學大家理雅各,也有德國傳教士中的「梟雄」郭實獵等,俱是時傳教士中頭角崢嶸的人物,不論所論小說或所涉譯著者都代表性十足。《無名小說》與《驅魔傳》則是中國人最早創作的基督教小說。上下兩編合而為一,恰是清末基督教小說最佳的代表,可代表其全景,《福音演義》以小窺大,呈現出來的正是這幅全景。這也是目前為止,所有涉及晚清基督教小說涵蓋面最大的一部著作...
《福音演義: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的書寫》分為「翻譯編」及「創作編」,綰結七部出現於晚清的基督教小說為一帙。此中的著譯者有英國漢學大家理雅各,也有德國傳教士中的「梟雄」郭實獵等,俱是時傳教士中頭角崢嶸的人物,不論所論小說或所涉譯著者都代表性十足。《無名小說》與《驅魔傳》則是中國人最早創作的基督教小說。上下兩編合而為一,恰是清末基督教小說最佳的代表,可代表其全景,《福音演義》以小窺大,呈現出來的正是這幅全景。這也是目前為止,所有涉及晚清基督教小說涵蓋面最大的一部著作...
»看全部
TOP
目錄
序文/李奭學
自序
導論
上編 翻譯編
第一章 模範聖徒:葉納清《金屋型儀》(1852)
一、女徒四德
二、靈性維度
三、宗教矛盾
四、族群張力
第二章 評點天路:胡德邁《勝旅景程》(1870)
一、天路歸化
二、小說評點
三、儒家評批
四、多元評述
第三章 想像樂園:博美瑞《安樂家》(1882)
一、樂園鄉愁
二、聖女形象
三、天堂曲調
四、夢中幻境
下編 創作編
第四章 建構大英:郭實獵《是非畧論》(1835)
一、英國想像
二、誠非外夷
三、興旺超卓
四、持守正教
五、崇英緣起
第五章 稗說聖...
自序
導論
上編 翻譯編
第一章 模範聖徒:葉納清《金屋型儀》(1852)
一、女徒四德
二、靈性維度
三、宗教矛盾
四、族群張力
第二章 評點天路:胡德邁《勝旅景程》(1870)
一、天路歸化
二、小說評點
三、儒家評批
四、多元評述
第三章 想像樂園:博美瑞《安樂家》(1882)
一、樂園鄉愁
二、聖女形象
三、天堂曲調
四、夢中幻境
下編 創作編
第四章 建構大英:郭實獵《是非畧論》(1835)
一、英國想像
二、誠非外夷
三、興旺超卓
四、持守正教
五、崇英緣起
第五章 稗說聖...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黎子鵬
- 出版社: 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7-07-20 ISBN/ISSN:978986350244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線裝 頁數:316頁 開數:15×23×2.4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中國古典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