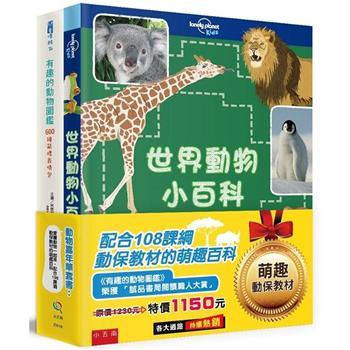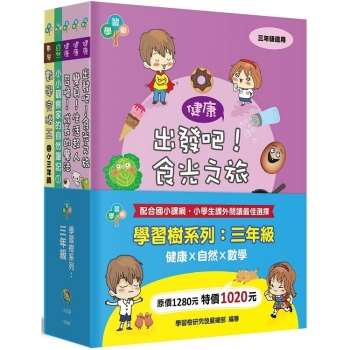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帝國」在臺灣II的圖書 |
 |
「帝國」在臺灣(II):「日本時代」的歷史記憶 作者:陳偉智、汪俊彥、曾文亮、林文凱、李衣雲、呂紹理、蔡慶同、李育霖、李承機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0-04-0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帝國」在臺灣II
從「個人記憶」到「集體記憶」
追尋戰後作為歷史記憶的「日本時代」
從1895至1945年的日本殖民地統治時期,臺灣一般習慣上也稱為「日本時代」。「日本時代」是一個歷史記憶的方法或過程,而非只是一個過去的「歷史階段」。日本時代的歷史記憶不僅存在於高階知識系譜的建構,同時也存在於一般大眾生活的日常活動場所及各種文化領域中。
本書共分三部,著重被殖民經驗過後,也就是二戰後臺灣社會在不同時期面對政治、經濟、社會等狀況變化時,對於過往日本帝國殖民時期知識與社會文化的重新理解。整體討論範圍涵蓋不同面向,包括從學術論述到民間議論的形構、從傳統的戲劇類型到大眾庶民的文化傳播、從個人的回憶到具有集體意義的歷史記憶,以及從律法的建構到檔案的製作管理等,恰恰體現歷史記憶運作的豐富面向與無所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