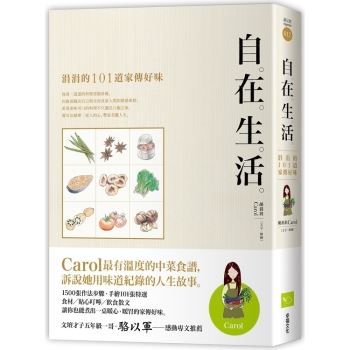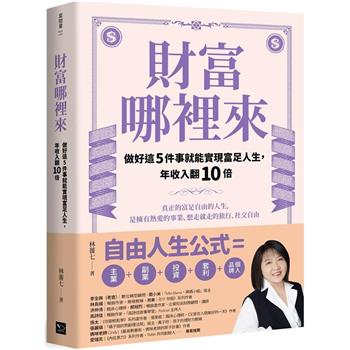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文學美綜論的圖書 |
 |
文學美綜論 作者:柯慶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0-08-04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文學美綜論
文學,該從整個文學活動,亦即作者的創作、作品的結構、以及讀者的欣賞,所同時反映的心靈活動,來加以體認與瞭解。它是一個以心鑄心,以心傳心,以心感心,以心應心的複雜歷程。它既是獨立的,那是指它於種種文化的活動中,自有其獨特而不能為其他活動所化約或取代的意義而言;它也是不自足的,它永遠是人類心靈狀態的一種呈現。
本書探討文學的基本性質,與文學美的諸般形態:抒情、敘事;悲劇、喜劇;言志、神韻;並涵蓋苦難的諦視與和諧的感悟等等層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