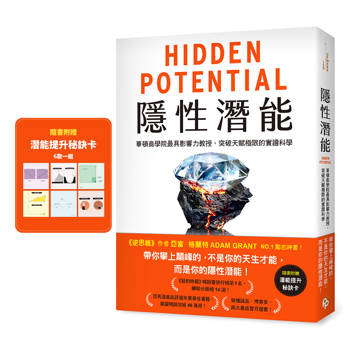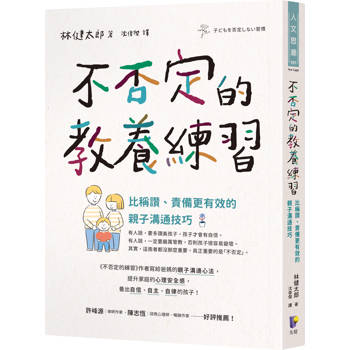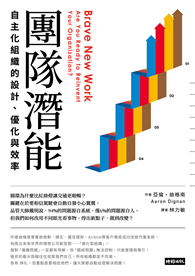【第九屆臺大學生哲學桂冠獎 人文組首獎】
在民主社會,執政者的私德是否重要?
汪旻寬(哲學系碩士班)
一、私德與公德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這是《論語‧為政篇》的第一句話,帶出了華人傳統對於執政者「以德治國」的期待。這種期待不只是對於公領域的道德,更延伸到私領域,構成了人們對於執政者「私德」的要求。然而,這種觀念形成的背景並不是民主社會,在我們今日的民主社會中能否依然適用,就是個值得反思的問題。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回答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是否真的有「私德」和「公德」的區分?就字面意義而言,這兩者的差別應該在於「作用對象」的不同:「私德」所作用的對象是私人關係,「公德」所作用的對象是非私人關係。不過,這樣的區分似乎還是不夠清楚,因為我們可以想像有些德行在這兩種關係都有可能出現;比如誠實,人可以對家人誠實,也可以對陌生人誠實。對這個疑問,可能的處理方式是:對家人的誠實是私德,對陌生人的誠實是公德。如此一來,就不需要堅持特定名稱的德目必定要是私德或公德,而是可以視情境脈絡來予以界定。
在這個界定下,某種德行之所以為私德,是因為其作用在私人關係中;而在非私人關係中,類似的性格傾向可能就會是公德。比如「孝順」是感念父母養育之恩,可以對應到「感恩」;而「專情」是信守對情人的承諾,可以對應到「守信」。這種理解引發了一個新的問題:「私德」和「公德」在本體上是否可以區分?而這個問題是討論「執政者的私德是否重要」的重要基礎:如果這兩者在本體上無法區分,則私德的狀況就會直接影響到公德;又,因為我們看重執政者的公德,所以也應該看重執政者的私德。
對此,前述華人傳統的觀點正是認為兩者在本體上無法區分。不只是古代的儒家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近代的儒者梁啟超也在〈論私德〉中引用孟子的話:「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進而認為「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這種觀點把公德視為私德的延伸,而使私德成為公德的前提。更甚者,這種觀點也能在西方找到強力的哲學傳統來支持。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人的靈魂被分為「智慧、勇氣、節制」三個部分,這些部分都不只是個人的德行,也關乎個人在城邦中的作用;比如衛士階級必須要有勇氣來保衛城邦,而執政者必須要有智慧來統治。這些觀點從道德心理學的角度出發,認為私德和公德往往是相似性格傾向的不同表現,即使在語言上可以區分,但在本體上卻是密不可分。
然而,當代的自由主義對此可能有不同看法。羅爾斯(John Rawls)在《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中指出: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中,存在著既定的「合理多元事實」,即基於不同道德理論或宗教學說而產生的深刻分化;對此,需要找到公共可接受的政治正義觀來提供容忍的基礎,進而使得多元價值的共生共存成為可能。對於公民和公職人員而言,這種政治正義觀表現為「公共理性」,用以處理公共領域的事務。此外,「公共理性」不能訴諸特定的道德理論或宗教學說,而是必須基於公共可接受的政治正義觀來進行判斷。舉例而言,在「墮胎問題」的爭議中,不同的道德理論或是宗教學說可能會作出不同的判斷,可能也會展現出不同的「私德」;但「公共理性」要求我們從公共的政治價值來進行判斷,像是「對人類生命的尊重」和「對女性平等性的尊重」。由此觀之,「公共理性」提供了我們私德以外的公德來源,讓我們可以不需要依賴私德,而是從政治生活的角度來建立公德。如此一來,確實可能存在著不來自於私德的公德,而使得這兩者在本體上可以區分。
進一步言,上述兩種觀點反映出了對德行養成的不同理解:前者是自然主義的觀點,指出德行的養成和人原先的性格傾向有關,後者是人文反思的觀點,指出德行的養成和人在社會生活中的思考有關。對此,本文認為兩者都捕捉到了德行養成的重要面向;而我們可以同時接受兩者,進而肯定德行的多元來源:公德有可能是從私德發展而來,也有可能是從反思而來。因此,討論「私德是否重要」的問題可能涉及公德,但不能把兩者劃上等號:有私德的人可能從中發展出公德,但沒有私德的人也可能反思出公德。基於這樣的理解,本文認為:在民主社會,執政者的私德並非必要,但是具有工具價值。
二、私德的價值
如果公德的來源未必是私德,則我們就不應該認為私德必然是公德的前提,而主張執政者應該以「修身為本」的資格論也會隨之瓦解。儘管如此,資格論者可能還是會退一步主張:因為私德好的人可以透過延伸私德或是反思來養成公德,而私德差的人少了其中一種養成方式,所以有更高的可能公德不佳。
然而,這種訴諸可能性的理由不應該成為用來排除執政者人選的指標。舉例而言,即使心理學的研究指出,童年被家暴的經歷可能引發暴力傾向,所以有這類經歷的人比其他人多了一種誘發暴力傾向的因素,進而有更高的可能有暴力傾向,我們也不會認為應該排除這類人當醫護人員。因為就算他們失去了從家庭習得愛與關懷的能力之機會,也可能從其他地方習得這種能力;而我們只需要確認他們有沒有這種能力即可。同樣的道理,即使私德差有可能引發公德差,我們也不應該排除私德差的人當執政者。因為就算他們失去了從私德發展出公德的機會,也可能透過對社會生活的反思來養成公德;而我們只需要確認他們有沒有公德即可。進一步言,我們之所以應該冒著多一種可能性的風險,接受私德差的人成為執政者人選,正是基於民主社會尊重合理多元的價值:如果我們否定私德差者成為執政者人選的資格,就是在政治的場域主張一種「德行應該以私德為根源」的道德學說,而排斥了其他類型的人格養成方式,違背了政治正義觀的理想。
資格論者的最後抵抗,是從道德動力的角度出發:私德好的人有內在的道德動力去遵守道德,所以比較能「不欺暗室」;而私德差的人缺乏內在的道德動力,會讓社會付出比較大的監督成本。此外,外在的監督難免有疏漏,私德差的人會讓社會承受更大的道德風險。因此,為了避免這些成本與風險擴大,我們不應該讓私德差的人擁有權力。
然而,這個觀點並不契合民主社會的制度設計。英國歷史學家艾克頓(Lord John Acton)曾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民主社會理解到了這個道理,所以設計了各種權力分立的制衡機制。這種制度的設計理念是:不論私德好壞,擁有權力之後都有腐化的可能;所以應該把權力分散到各個機關,進而產生制衡與監督的效果。在這種制度設計下,任何執政者都需要接受同樣的監督,並不會有監督成本上的差異。至於道德風險的問題,一方面,上述「權力使人腐化」的看法指出了:任何執政者都有很高的道德風險,所以私德好者的道德風險並不會比私德差者低太多。另一方面,誠如前文所述,「多一種可能性的風險」並不是排除執政者人選的好指標;在這種風險沒有真正損及公德的情況下,我們不應該排除私德差者擁有權力。
綜上所述,不論是從可能性的推論,還是道德動力的角度,都無法論證出私德是成為執政者的必要條件。然而,這並不代表執政者的私德對社會毫無意義,本文認為執政者的私德對社會仍然有工具價值。首先,誠如前文所述,私德是養成公德的來源之一,而且能提供遵守道德的內在動力,所以具有促進養成與遵守公德的工具價值。
再者,執政者的私德也可能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中被賦予特殊的價值。舉例而言,如果人民把執政者視為道德典範,而且會效法執政者的德行,則私德就會成為另類的施政項目,具有影響社會風氣的工具價值。而如果人民就是會參考私德的狀況來投票,則私德就會成為選戰重點,具有影響誰會當選的工具價值。這些工具價值雖然不在理論上伴隨著私德,卻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特別是在民主社會:因為民主社會的狀況特別容易受到人民偏好的影響,所以即使私德不是成為執政者的必要條件,但只要人民認為是,執政者就必須配合演出;否則不但可能造成不良的示範效果,還可能因此而敗選,無法實現任何政治理想。由此觀之,執政者的私德可能基於社會脈絡而變得非常重要。如此一來,「執政者的私德是否重要」這個問題就無法簡單以「重要」或「不重要」來回答,而會牽涉到社會中人民的價值觀。
三、私德的迷思
以本文前面的討論而言,回答「執政者的私德是否重要」這個問題的基本意義,就是回應社會上對於這個議題的爭論,即指出爭論雙方各自的問題:主張私德重要的人不應該忽視公德可能有私德以外的來源,而主張私德不重要的人不應該忽視私德有工具價值。不過,我們可以在這個基礎上繼續追問:在怎樣的民主社會中,執政者的私德有重大的工具價值?而這樣的現象合理嗎?換而言之,本文不只想探問執政者的私德在客觀的社會環境中是否重要,也想探問執政者的私德是否「應該」是重要的,進而對客觀的社會環境進行反思。誠如前文所言,民主社會所追求的價值是尊重多元,而制度設計上也不重視私德;然而,為什麼有些民主社會的人民非常看重執政者的私德呢?首先,文化傳統對此可能有很大的影響。比如前文提到華人傳統所看重的「以德治國」,這種觀點不只期待執政者處理
公共事務,更期待執政者展現人格特質,進而以「風行草偃」的方式來感化社會。再者,媒體的報導方式也可能助長這種思維。因為報導私生活比報導政策更沒有知識門檻的問題,所以對媒體而言,以私生活為報導題材是比較輕鬆的選擇。如此一來,如果社會中的人民關心執政者的私生活,媒體就會更樂意報導這類消息。而如果這種狀況嚴重,就會排擠到關於政策的報導,造成報導資訊聚焦在私生活,進而助長人民對執政者私生活的關注與討論。
然而,本文認為這些社會狀況阻礙了人民和執政者雙方的自由,是應該被反思與批判的。先以人民方面而言,把執政者視為道德典範的觀念所隱含的思維是:人民不應該擁有自己對道德的價值觀,而是應該跟隨著執政者;如此不但可以避免錯誤,而且可以讓社會更為穩定。但以民主社會的理念而言,社會中的合理多元價值觀不但是可以被接受的,而且未必比執政者的價值觀差;更重要的是,民主社會不把社會的穩定建立在道德價值觀的統一上,而是建立在公共可接受的憲政原則之上。因此,民主社會把執政者視為「公僕」:要求執政者按照憲政原則來施政,但不要求執政者提供道德典範。就此而論,儘管有些社會在制度上成功轉型為民主,但人民的觀念中還是留存著威權時代的思維,所以才會繼續把執政者視為道德典範。不過,民主理念已經在各方面肯定了人民形成道德價值觀的能力,只是在文化傳統與媒體引導的作用下,人民還是被籠罩在威權典範的陰影下,所以才會更加猛力地去批評執政者的私德,卻沒有意識到自己其實已經自由了。由此觀之,人民對執政者私德的看重是民主轉型不完全所留下的問題;儘管並沒有以強制力來直接阻止人民擁有自己的道德價值觀,卻造成社會價值的迷思,間接阻礙了人民形成自己的道德價值觀。再以執政者方面而言,儘管人民仍然傾向於把執政者視為道德典範,但民主社會的人民也同時有著各種價值觀,可能在媒體的協助之下從各種角度批評執政者的私德。然而,人民和媒體對私德的看法未必真的有助於促進道德。因為在私德的領域中,存在著許多複雜的情境因素,而這是以「文化傳統」或「社會通念」為基礎的社會討論所可能忽略的。舉例而言,「孝順」在華人社會中是重要的美德,但除了養育之恩,人和父母之間可能還有其他的情感,比如受到暴力管教的童年陰影,就是個在社會討論中可能被忽略的情境因素。退而言之,即使社會討論涵蓋了所有的情境因素,所得出的主流聲音也可能只是社會中特定群體的價值觀。舉例而言,「專情」也被華人社會視為美德,但在感情關係中,發展其他感情的可能性是否違反對情人的承諾,其實也可能因為不同的當事人而有不同的答案。正是因為道德問題的討論涉及許多因素,而且很難找到被所有人所認可的答案,所以尊重合理多元的民主社會並不會預設特定的道德理論,而是以公共可接受的憲政原則來建立社會環境,讓人民在這個場域中追尋與構築自己的道德價值觀。而民主社會的這種理念不只適用於人民,也應該適用於執政者:我們不應該以人民看重的特定「私德」來約束執政者的道德價值觀,而是應該把自由追尋價值觀的空間還給執政者。
綜上所言,本文認為看重私德是民主轉型不完全所造成的現象,這種現象詭異地綑綁著人民與執政者,讓雙方都難以擺脫對方的束縛:人民難以擺脫威權典範的陰影,而執政者難以擺脫人民對私德的批評。這種束縛阻礙了人們追尋與構築道德價值觀的自由,是尊重合理多元的民主社會所不贊同的。因此,本文認為即使執政者的私德在客觀的社會環境中可能是重要的,但以民主社會的理念而言,執政者的私德不應該是重要的。
評論意見
在此篇論文中,作者先說明並澄清為什麼這個題目值得反思,因為執政者最重要的德行應該是「公德」,但如果私德與公德之間的關係是密不可分或者互為因果,那麼執政者私德的重要性當然不言可喻。然作者從來源論與資格論兩方面進行精闢的分析,得到「在民主社會,執政者的私德並非必要,但是具有工具價值」的結論。此篇論文最精彩之處在於第三部分澄清執政者私德的迷思,從多元價值的觀點來說明,任何證明私德攸關執政品質的理論其實都是值得再進一步地深思,且不以特定的私德觀點限制執政者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由於此篇論文論證架構非常清楚,且能夠以適當的實例輔以說明其主張,得到許多評審委員一致推薦,得獎乃實至名歸。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臺大學生哲學桂冠獎得獎作品集(第五輯)的圖書 |
| |
臺大學生哲學桂冠獎得獎作品集第五輯 出版日期:2020-11-06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79 |
Social Sciences |
$ 422 |
中文書 |
$ 432 |
亞、非與其他哲學 |
$ 432 |
社會人文 |
$ 432 |
哲學 |
$ 432 |
Social Sciences |
$ 432 |
教育學習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臺大學生哲學桂冠獎得獎作品集(第五輯)
本書收錄「臺大學生哲學桂冠獎」第九屆(2019)、第十屆(2020)共三十四篇精華作品,各依人文、社會、自然與生命教育四組,分訂不同重要議題。學生依題深入思考、論述,理性、自省與關懷兼具;學者專家之評論,鞭辟入裡。
各議題如:在民主社會,執政者的私德是否重要?應該立法禁止假新聞嗎?道德問題可以靠科學解答嗎?有道德的人比較快樂嗎?在多元社會中,念大學到底有什麼意義?為了爭取民主,值得犧牲繁榮穩定到什麼地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有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吃豬肉和吃狗肉有什麼分別?
2020年,因應全球冠狀病毒肆虐,另增議題:人文學科對於思考疫情能有所貢獻嗎?面對新興傳染病,疫情是否應該完全公開透明?科學在對抗疫情上所扮演的角色與其限制為何?當人道考量與防疫嚴重衝突時,如何抉擇?本書既富微觀之哲思,亦有宏觀之剖析,篇篇精彩,值得細讀深思。
作者簡介:
林明照 主編(臺大哲學系教授兼主任)
作者(得獎學生,依姓氏筆畫)
方律元
王彥鈞
王偉丞
李巧于
李典澄
杜威儒
汪旻寬
林世峰
邱懷萱
金德翰
侯乃中
洪千雯
張閔喬
梁豐綺
莊文琪
陳羽辰
陳嘉凱
黃俊嘉
黃禹翔
黃詠晴
黃楚岳
楊劭楷
廖耕賢
熊偉均
賴永承
韓翔中
章節試閱
【第九屆臺大學生哲學桂冠獎 人文組首獎】
在民主社會,執政者的私德是否重要?
汪旻寬(哲學系碩士班)
一、私德與公德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這是《論語‧為政篇》的第一句話,帶出了華人傳統對於執政者「以德治國」的期待。這種期待不只是對於公領域的道德,更延伸到私領域,構成了人們對於執政者「私德」的要求。然而,這種觀念形成的背景並不是民主社會,在我們今日的民主社會中能否依然適用,就是個值得反思的問題。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回答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是否真的有「私德」和「公...
在民主社會,執政者的私德是否重要?
汪旻寬(哲學系碩士班)
一、私德與公德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這是《論語‧為政篇》的第一句話,帶出了華人傳統對於執政者「以德治國」的期待。這種期待不只是對於公領域的道德,更延伸到私領域,構成了人們對於執政者「私德」的要求。然而,這種觀念形成的背景並不是民主社會,在我們今日的民主社會中能否依然適用,就是個值得反思的問題。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回答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是否真的有「私德」和「公...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出版緣起
林明照(臺大哲學系教授兼主任)
大學作為人才培養最重要的機構,不僅是給予學生專業領域的養成及訓練,更重要的是讓學生有能力反思自身生命的意義及價值,同時能夠關懷社會甚至全人類的發展。臺大哲學桂冠獎所著眼的,正是提供一個寫作平臺,讓同學們透過分析、思辯與推論,對自我、社會與人類整體進行意義與價值的反思。目前臺大哲學桂冠獎已舉辦了十屆,歷屆皆包含人文組、社會組、生命教育組以及自然組,囊括了值得大學生加以反思的諸般領域。
目前呈現在各位讀者眼前的這本專輯,收錄了第九屆及第十屆的得獎論文,...
林明照(臺大哲學系教授兼主任)
大學作為人才培養最重要的機構,不僅是給予學生專業領域的養成及訓練,更重要的是讓學生有能力反思自身生命的意義及價值,同時能夠關懷社會甚至全人類的發展。臺大哲學桂冠獎所著眼的,正是提供一個寫作平臺,讓同學們透過分析、思辯與推論,對自我、社會與人類整體進行意義與價值的反思。目前臺大哲學桂冠獎已舉辦了十屆,歷屆皆包含人文組、社會組、生命教育組以及自然組,囊括了值得大學生加以反思的諸般領域。
目前呈現在各位讀者眼前的這本專輯,收錄了第九屆及第十屆的得獎論文,...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一/管中閔校長
序二/校長黃慕萱院長
出版緣起/林明照主任
第九屆得獎作品
人文組——在民主社會,執政者的私德是否重要?
首獎/汪旻寬
叁獎/金德翰
佳作/黃俊嘉
佳作/邱懷萱
佳作/陳嘉凱
社會組——應該立法禁止假新聞嗎?
首獎/金德翰
貳獎/楊劭楷
叁獎/李巧于
佳作/張閔喬
佳作/賴永承
自然組——道德問題可以靠科學解答嗎?
貳獎/廖耕賢
叁獎/王彥鈞
叁獎/汪旻寬
佳作/金德翰
生命教育組——有道德的人比較快樂嗎?
首獎/方律元
貳獎/洪千雯
佳作/林世峰
佳作/王偉丞
第十...
序二/校長黃慕萱院長
出版緣起/林明照主任
第九屆得獎作品
人文組——在民主社會,執政者的私德是否重要?
首獎/汪旻寬
叁獎/金德翰
佳作/黃俊嘉
佳作/邱懷萱
佳作/陳嘉凱
社會組——應該立法禁止假新聞嗎?
首獎/金德翰
貳獎/楊劭楷
叁獎/李巧于
佳作/張閔喬
佳作/賴永承
自然組——道德問題可以靠科學解答嗎?
貳獎/廖耕賢
叁獎/王彥鈞
叁獎/汪旻寬
佳作/金德翰
生命教育組——有道德的人比較快樂嗎?
首獎/方律元
貳獎/洪千雯
佳作/林世峰
佳作/王偉丞
第十...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