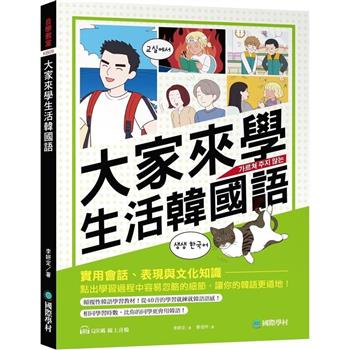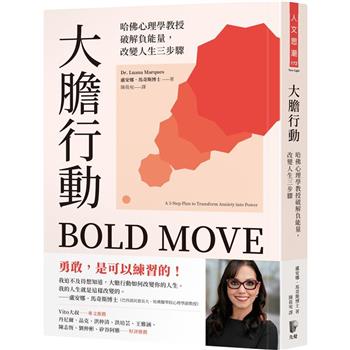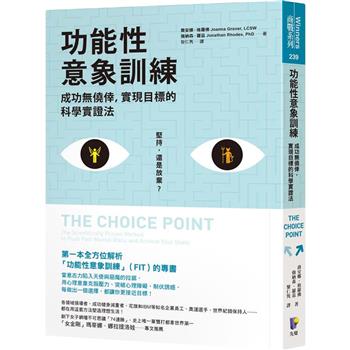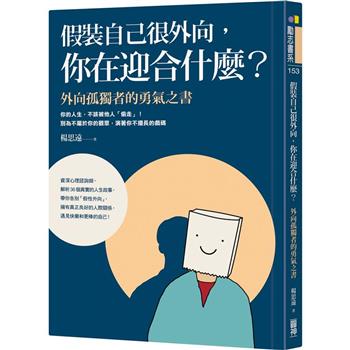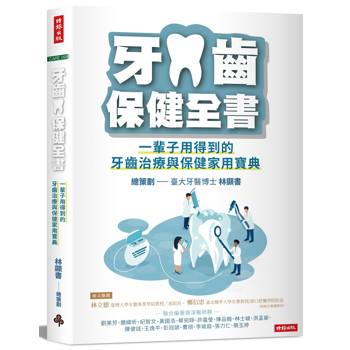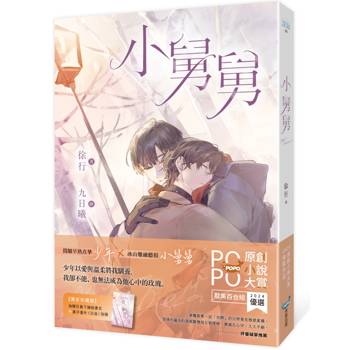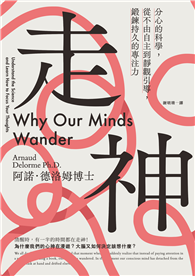第一章 引言
文學批評的發展與所謂「文藝思潮」,表面看來似乎相關,其實它們的意涵並不一致。「文藝思潮」就像時裝一樣,通常泛指某一個時期內所流行於社會上的文學主張,它的基本特質就在於它的「時髦性」。一方面反映當時的社會感性,一方面總不脫離一切流行的「喜新厭舊」特質。偏見或偏至是一切時髦性玩意兒的必要條件,否則,就無以映現它的陷溺於歷史時空的年代性。所以它總是「飄」的,一旦隨風而逝,留給我們的就只是一份思古幽情的憑藉而已,並不再具有任何功用。無論是「國防文學」也罷,或者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也罷,正如抗戰時期的草鞋粗布衣,我想今天是再沒有人會真正想要去穿它過日子的,不論是創作也罷、批評也罷。所以所謂「文藝思潮」,不論在當道之時是如何顯赫炫目,終究是要淪為「明日黃花」的。落花只合埋葬,並不宜拿來供作「腐朽」大展。
文學批評作為一種歷久常新的「文化」活動,它的意義並不在於所謂的「時代性」,而是在於「時代性」的超越。它所尋求的是永恒的文學真理。繫連起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甚至不同文化的「文學批評」者的,是一種共通的對於文學本質、文學發展、文學作品的試圖瞭解的努力。不論努力的收穫如何,文學批評工作的核心,就是一種認知的活動與歷程。它的進展與成就,也取決於它在文學認知上的進展與成就。因此十字街頭的喧囂或象牙塔裏的孤寂,都不能改變它在人類認知文學、瞭解文學之進展上的貢獻。因此,宣傳家或許一時在社會上有更大的影響力,但是文化史上所要記載的永遠是把人類帶入一種新境界、新視覺的創見者。
文學批評,在民國以來的發展,基本上可以說是一段近代意義下的文學批評在中國文學的探討上逐步成立的歷程。原因是中國雖然在六朝即有像《文心雕龍》、《詩品》之類的具有高度認知性質的批評著作產生,但是自宋代的詩話開始,一直到明清之際的文論與詩論,卻泰半都只是黨同伐異的文學主張,缺乏真正尋求瞭解文學的認知意識,更談不上一種較有系統的文學知識的建立了。因此,這種以認知為核心,以創構一種系統化的文學知識為目標的近代意義下的文學批評要在中國重新建立,事實上就不能不有賴於外來的刺激與西方的影響了。因此中國的新文學批評,正如中國的新文學一樣,多多少少都具有某種「橫的移植」的現象。但是一方面正值近代意義的文學批評建立之初,尚未能夠充量的發展;一方面是中國的所有重要的文學批評者,事實上更關切中國文學傳統的此一「縱的繼承」的問題,因此幾十年來中國的文學批評方面的成就,總是偏重在於中國文學的瞭解上,而仍未能擴展到對於外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較為深入的探討上。憑藉西方的文學觀念重新認識中國文學作品的各種現象和意義,因而確立起一個內容更為豐富、生命更為蓬勃的中國文學的傳統,幾乎是這段時期文學批評工作的主要方向與重點。
在借用西方的文學觀念重新認識中國文學作品方面,王國維在光緒三十年所發表的〈紅樓夢評論〉,不但首開其端,而且幾乎可以說是現代中國文學批評的第一篇經典之作。他首次借「悲劇」這個觀念來深入探討了《紅樓夢》的內在精神與其美學、倫理學上之價值。雖然王國維在民國元年即已完成了他開創性的《宋元戲曲史》,但對中國文學的整體傳統的根本改弦易轍的新認識,則要等到民國六年「文學革命」發生之後才逐漸醞釀成熟。「文學革命」的影響,不但從此決定了中國文學創作的發展方向,事實上更改變了此後的對於整個中國文學此一大傳統的範疇意識與價值觀點。因此,憑藉著「橫的移植」來為「縱的繼承」注入新血以更新擴大中國文學的生命,不但在文學創作上是現代中國文化上的一大契機,在文學批評的建設上,亦是一大轉捩的里程碑。就是在這種「縱」、「橫」的經緯交雜中,現代的中國文學批評織出了它在民國以來的第一章。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的圖書 |
 |
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 作者:柯慶明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0-12-0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05 |
中文書 |
$ 405 |
華文文學研究 |
$ 414 |
文學作品 |
$ 414 |
小說/文學 |
電子書 |
$ 460 |
文學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
文學批評作為一種歷久常新的文化活動,
它的意義並不在於所謂的「時代性」,
而是在於「時代性」的超越。
中國文學批評自有源遠流長的傳統,作者相信它是一個生生不息,日益壯大的活的傳統,藉由對它的重新檢視,或許最能啟示我們抉擇,甚至開創自己的方向。
本書包含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紹此一方興未艾的文學批評的活傳統;第二部分則集中在凸顯梁啟超和王國維在近代中國文學批評形成之際,對於傳統批評的承先啟後之努力所達致的成就,以及因而形成的典型的對立;第三部分為附錄。在這些短論與演講中,作者始終關切文學與時代,與現實的若即若離的關係,這個問題顯然正觸及「言志」傳統與「神韻」傳統的對立。
作者簡介:
柯慶明(1946-2019)
前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和臺灣文學。曾任《現代文學》雜誌主編,《文學評論》雜誌編輯委員兼執行編輯,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協同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訪問研究員,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招聘教授,捷克查理士大學客座教授。著有《一些文學觀點及其考察》、《萌芽的觸鬚》、《分析與同情》、《境界的再生》、《境界的探求》、《文學美綜論》、《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中國文學的美感》、《臺灣現代文學的視野》、《柯慶明論文學》、《古典中國實用文類美學》等文學論著,以及詩集《清唱》、散文集《出發》、《靜思手札》、《省思札記》、《昔往的輝光》。日記《2009/柯慶明:生活與書寫》等。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引言
文學批評的發展與所謂「文藝思潮」,表面看來似乎相關,其實它們的意涵並不一致。「文藝思潮」就像時裝一樣,通常泛指某一個時期內所流行於社會上的文學主張,它的基本特質就在於它的「時髦性」。一方面反映當時的社會感性,一方面總不脫離一切流行的「喜新厭舊」特質。偏見或偏至是一切時髦性玩意兒的必要條件,否則,就無以映現它的陷溺於歷史時空的年代性。所以它總是「飄」的,一旦隨風而逝,留給我們的就只是一份思古幽情的憑藉而已,並不再具有任何功用。無論是「國防文學」也罷,或者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文學批評的發展與所謂「文藝思潮」,表面看來似乎相關,其實它們的意涵並不一致。「文藝思潮」就像時裝一樣,通常泛指某一個時期內所流行於社會上的文學主張,它的基本特質就在於它的「時髦性」。一方面反映當時的社會感性,一方面總不脫離一切流行的「喜新厭舊」特質。偏見或偏至是一切時髦性玩意兒的必要條件,否則,就無以映現它的陷溺於歷史時空的年代性。所以它總是「飄」的,一旦隨風而逝,留給我們的就只是一份思古幽情的憑藉而已,並不再具有任何功用。無論是「國防文學」也罷,或者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1987年版序
中國文學批評自有源遠流長的傳統,在這方面著述已有不少。但是在近代意義的文學批評產生之後迄今,是否可以說也自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傳統呢?是否今天的學者除了向古代的大傳統,或者西方的新潮流學習之外,也可以自近代以迄當代的這些學者的努力有所取法?這本書或許就是一個回答。作者相信它正是一個生生不息,日益壯大的活的傳統,因此對它的重新檢視,或許最能啟示我們抉擇甚至開創自己的方向。
本書包含三個部分,第一輯正是對於此一方興未艾的文學批評的活傳統的一個扼要的敘述。這個敘述始於晚清的梁啟超與王國維而...
中國文學批評自有源遠流長的傳統,在這方面著述已有不少。但是在近代意義的文學批評產生之後迄今,是否可以說也自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傳統呢?是否今天的學者除了向古代的大傳統,或者西方的新潮流學習之外,也可以自近代以迄當代的這些學者的努力有所取法?這本書或許就是一個回答。作者相信它正是一個生生不息,日益壯大的活的傳統,因此對它的重新檢視,或許最能啟示我們抉擇甚至開創自己的方向。
本書包含三個部分,第一輯正是對於此一方興未艾的文學批評的活傳統的一個扼要的敘述。這個敘述始於晚清的梁啟超與王國維而...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學術研究叢刊」出版緣起
2005年版序
1987年版序
第一輯 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草萊初闢
一、舊學嬗變
二、文學革命
第三章 規模始具
一、文學史的建立
二、批評史的整理
三、史傳批評的豐收
四、美學知覺的興起
五、新文學的檢討
第四章 復興基地的發展
一、史傳批評與境界說的承揚
二、新批評與比較文學的盛行
三、其他方面
第二輯 中國文學批評的兩種趨向
第五章 梁啟超、王國維與中國文學批評的兩種趨向
一、前言
二、文學論
三、一個暫時的結論
第六章 從梁啟超與王國維...
2005年版序
1987年版序
第一輯 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草萊初闢
一、舊學嬗變
二、文學革命
第三章 規模始具
一、文學史的建立
二、批評史的整理
三、史傳批評的豐收
四、美學知覺的興起
五、新文學的檢討
第四章 復興基地的發展
一、史傳批評與境界說的承揚
二、新批評與比較文學的盛行
三、其他方面
第二輯 中國文學批評的兩種趨向
第五章 梁啟超、王國維與中國文學批評的兩種趨向
一、前言
二、文學論
三、一個暫時的結論
第六章 從梁啟超與王國維...
顯示全部內容
|